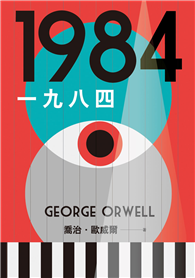在情人的臂膀中起舞
獨立大道走到盡頭,就是公園廣場。
午後的公園廣場像個遊樂場,賣氣球的小販渾身掛滿了氣球,五顏六色,滿天飄飛。街頭藝人來來去去,有的穿著傳統服飾,戴著墨西哥帽,以小提琴演奏著墨西哥民謠,也有流行樂團,吟唱歌手,雜耍小丑,各憑本事讓觀光客從口袋裡掏出錢來。
人潮比上午更多,綠蔭下的座椅擠滿了人,其中不乏卿卿我我的戀人。墨西哥的戀人很張狂,一對對的公然在烈日下、在人潮中親吻擁抱。戀人的行為雖大膽,卻少了浪漫的氣氛,不像巴黎的空氣中嗅得到戀愛的因子。
你說,那是極度限制下的反撲。
墨西哥是個天主教國家,嚴禁婚前性行為和墮胎,情侶們在避免犯規和惹麻煩的情況下,只好相約在公共場合。旁人不知是出於同情還是尊重,或是見怪不怪,對於這種親密行為並沒有多大反應。
一個頭頂著花籃的女人穿梭在咖啡座中,賣著象徵愛情的紅玫瑰。我不知道墨西哥的氣候是否養得出如此嬌貴的花朵,墨西哥女人似乎很愛它,只要有男伴在旁,那位小姐就能賣出一把。當她來到我們眼前,你微微一笑,咕嚕了幾句,她以悲憫的目光望了我一眼,轉身而去。
我問你跟她說了什麼,你說,「我告訴她,我的花園裡多得是玫瑰。」難怪她以悲憫的目光看我,她一定覺得你不是個好情人。你反駁說,街頭的玫瑰讓愛情變得廉價,只有對自己沒信心的男人,才會以玫瑰來換取愛情。
我不贊同你的話,卻心疼那些玫瑰,在這麼熱的天氣裡,那一朵朵象徵著愛情的玫瑰,究竟撐得了多久?也許浪漫的夜還未過,它便已經凋萎了。想到這兒,我竟因你未買玫瑰而感到高興。
我們一邊喝著啤酒,一邊看著來來去去的人潮。
咖啡座上的人兒,就像海潮一樣,去了一批,另一批立刻湧上。他們不全是遊客,也有不少在地人,有的和朋友喝一杯,有的談著公事,也有才剛下了課的中學生,和進城辦事的農民。不管什樣的人,臉上都掛著笑容,說話的姿態既熱烈又輕鬆,笑聲隨著溫熱的空氣飄浮在空氣中。
風從樹梢滑落下來,輕輕從臉龐拂過,溫溫熱熱的,就像情人的手,我愉悅的靠在座椅上,悠然的喝著冰涼的啤酒。
你又和鄰坐的一家人聊了起來。他們是德國人,講的是英文,我不再有被冷落的感覺,不過我並沒有開口。
你詳盡的告訴他們瓦哈卡的特色,什麼地方一定要去,哪家餐廳好吃,隔天有什麼市集,鉅細靡遺,如數家珍,讓對方以為你是久居此地的外僑。你毫不掩飾的說出你對瓦哈卡的愛戀,還說可能的話,以後會年年回來。
德國人也顯得很熱情,說什麼才來幾天,便已感覺到瓦哈卡迷人之處。他們喜歡這裡多采的文化,穩定的氣候,和親切的民眾。最令他們開心的是,物價便宜。
聽著你們閒聊,我不禁想著,是因為歐洲的天氣太冷了,而讓你們對熱帶地區充滿遐思?還是在你們的文化中少了慵懶的因子,讓你們對印第安文化感到好奇?我想起以前的一個英文老師,他來自陰冷的英國北部,到了亞洲後彷彿走入了人間勝境,寧可在香港、台灣、泰國過著教英文,四處遷徙的生活,也不願意回英國定居。我認識他時,他已在亞洲住了十七年,這當中只回過英國三次。
德國人離開後,我向你提出了心裡的疑問。
你正思索著如何答覆我時,一首滄桑的旋律讓你轉過頭。
那是個盲人歌者,大約五十來歲,穿著一身破舊的衣服,頭髮雜亂,打著赤腳,一手握著盲人手杖,一手拿著小碗,沿著咖啡座黯然低唱。他的嗓音低沉而哀傷,眉頭深鎖,我雖聽不懂歌詞,卻被歌聲中的滄桑感動了。當他來到我們面前,你毫不吝嗇的給予掌聲和賞金。
很快的,盲人歌者的歌聲又從鄰桌傳來,你聽了兩句後,回到我的問題。你說你對瓦哈卡的愛戀,也許是年少時的一種憧景。
一九七○年代時,你正好在美國,那是嬉皮當道的一段歲月,你不喜歡嬉皮,也不喜歡歐洲的冷漠,渴望到一個有熱度的國度。
來到瓦哈卡或許是偶然,也可能是宿命,總之當你到達這裡時便無法自已的愛上了她。之後,在無數次的造訪中,你學會她的語言,熟悉她的文化,你對她的愛愈加濃厚的。這麼多年來,她成了你遠離日常生活的場地,也是你疲憊煩悶時的喘息地。你迷戀她,不只是她的風景,還有在此地交往的朋友。最後,你不忘幽默的加了一句,你愛瓦哈卡是因為空氣中瀰漫著巧克力的芳香。
時間在午後的公園廣場悄悄移動著,陽光卸下刺人的外衣,搖身變成淘氣的精靈,在人們的髮稍染上一層銀光。馬林巴琴隨風而起,一對對人兒開始翩然起舞。馬林巴琴聲也是吸引你來瓦哈卡的原因之一,那是一種源起於瓜地馬拉,卻在瓦哈卡茁壯的樂器。
美妙的音樂,空氣中的餘溫,和輕輕吹送的風兒,讓舞者的腳步愈來愈輕快,臉上的神韻也愈來愈柔美。而你也渾然忘我的陶醉在音樂中。
突然間,我似乎懂了,瓦哈卡真正讓你迷戀的應該就是這種難以言喻的氣氛。這種氣氛不但在英國沒有,在美國,在歐陸也很罕見,甚至在墨西哥其他的城市也找不到,那是一種經由環境、氣候、文化和民族特性交揉後,經過時間的醞釀而產生的,那是一種獨特的,無法複製的氛圍。它讓人感到放鬆,感到自在,還有種歸屬感。
發現了你的祕密,我心裡充滿了喜悅,不過我故作沉默,不想讓你太得意。不然你又會說:「哈,你總算見識到我的情人是多麼棒了吧!」
你的身體跟著音樂的節奏擺動著,眼中盪漾著笑意。我很少看到你這麼放鬆,這麼歡愉,在情人的懷中果然是甜蜜的。
另一首曲子響起時,你拉起我的手,「我們跳舞吧!」
不擅跳舞的我,腳步有些凌亂,幾次踩到你,你卻好像沒有感覺似的,滿心沉醉在優美的旋律中。你說,等我們老得無法四處旅行時,依然可以在瓦哈卡相擁而舞。我說,在情人的臂膀中,就算面對著牆壁,依然看得到滿城風光,何必跑那麼遠呢!
情人的雷波娑
你說,那叫雷波娑(Rebozo)。
就像回教婦女一樣,此地的婦女也都隨身帶著一條長巾。入夜天涼時,長巾一披,比一件毛衣還保暖。
雷波娑最普遍的用處是揹孩子,小嬰兒被包在雷波娑裡,斜掛在母親胸前,就像還停留在子宮裡似的,既舒服又安全。孩子想吃奶時,隨時扯開母親的衣衫,既不妨礙母親工作,又可盡情暢飲。或許是因為這樣,在瓦哈卡很少聽到印第安孩子哭鬧。
我看到有些婦女將雷波娑折疊成方塊,放在頭上,當成頂重物的墊子,垂下來的流蘇成為裝飾,實用又好看。有的則掛在頸間,有的當成斜揹的袋子,也有人將長巾掛在額頭上,揹著比身體大兩倍的貨物。
你說了許多雷波娑的好處,其中最令我驚奇的是,有些婦人用它把喝得爛醉的男人拖回家。
一條簡單的長巾,讓我看到了當地婦女的韌性,想必那也是吸引你的原因吧!
你向來很敬佩那些具有堅毅性格,不屈不饒的人,而這正是你的情人的特徵。在來瓦哈卡之前,我是下過功夫的,早已摸透了她的前世今生。
她的生命始於西元前七世紀,據說是原自於奧爾梅卡族。當時的瓦哈卡水土豐碩、氣候宜和,她悄悄的成長,到了西元後,她已出落的亭亭玉立。她的美壯大了她的生命,卻也為她帶來了災難。十世紀時,北方的阿茲特克人聽聞她的美豔,很快的展開征服行動。那是一場可怕的磨難,她卻以最大的容忍力,包容著欺凌她的人,再經由歲月之手,巧妙的將兩種不同的文化揉合起來,焠鍊出成熟的少婦之美。
從公園廣場南邊的壁畫館和聖多明哥教堂博物館裡的文物裡,我看到了她在災難後浴火重生,她的美就像館外的火鳳凰,燃燒著瓦哈卡的天空,她萬萬沒想到的是,不久後一陣從東邊吹來的狂風,幾乎吹熄了炙熱的火苗。在她還搞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時,一群高大的白種人已經將槍桿子瞄準她。
她從沒看過這樣的人種,失去了應對的從容,從十五世紀起,她在西班牙人強勢的歐洲文化欺凌下,幾乎徹底毀滅了。她安靜得如土壤中的木石,對統治者的要求逆來順受,但她沒有忘記自身的特質,_再次運用她的韌度與智慧,默默的吸取了歐洲人帶來的新視野,經歷兩百多年的沉潛後,終於孕育出一股強大的力量,經由她鍾愛的子民貝尼托.胡亞雷斯(Benito Juarez)帶著她走向歷史的高峰。
胡亞雷斯這個名字,我是在墨西哥市國際機場聽見的,它就掛在機場最醒目的地方。他不僅是引領外國人進入墨西哥的入口,也是帶領印第安人走入現代文明的橋樑。他是墨西哥人的偉大總統,更是瓦哈卡人世代懷念的英雄。沒有他,你的情人恐怕還還湮沒在厚厚的塵泥中。
不過,為你的情人趕走西班牙的人,並不是他。西元一八一○年,獨立戰爭的號角在墨西哥響起時,在瓦哈卡山區牧羊的胡亞雷斯並沒有聽見,那時他只是個牧羊童。
他之所以能在歷史上找到位置,說來得感謝他所遺失的那頭羊。
十一歲那年,他遺失了一隻羊,因為賠償不起,只好連夜走了幾十公里的山路,逃到瓦哈卡城裡投靠表姊。他被送到裝訂廠當學徒。在這之前,他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書,也不認得記載在書本裡的那些符號,但這都不影響他追求知識的決心。
一八二四年,獨立戰爭終於有了結果,墨西哥人開始當家做主。
許久未當過主人的墨西哥一下子亂了手腳,四處亂糟糟的,已經當上律師的胡雷亞斯看到了自己的機會,他棄法從政,進入州政府工作,並於西元一八四七年當上州長。他修改制度,廣建學校,廢除殖民時代延續下來的種種特權。他的大刀闊斧,受到百姓鼓舞,卻得罪了既得利益者,六年後,在保守派的排擠下,他失去了州長的位置。
他並不沮喪,因為他的志向在更高的位置上。他於是前往墨西哥市,在混亂的政壇中,另起爐灶,幾年後,成為墨西哥史上第一位原住民總統。
以憲法確立政教分治,是胡亞雷斯最為人樂道的貢獻。他同時改革民法,提倡信仰的自由,並解除奴隸制度,從此印第安人才能和帶有西班牙血統的墨西哥人同起並坐。他因而擁有墨西哥「林肯」的美名。
博物館的牆上,提寫著胡亞雷斯生前留下的名言:「尊重別人的權益,就是和平。」這句話就像耳畔的微風,輕輕淡淡,在酷暑中帶來一股涼意。我站在牆前,一直看著那句話,眼前卻浮起台灣那些政治人物的嘴臉,如果他們也有這般修養,台灣社會必然也會吹起一陣涼風。
走到出口,原以為你會在那兒等我,卻看不到你的人影,於是又繞回展覽廳。你正聚精會神的看著革命時代遺留下的文件。我覺得奇怪,這些東西你以前不都已經看過了嗎?你說,不管來過多少次,每一次都像第一次,永遠都有值得學習的東西。
舊地重遊,除了緬懷舊情外,很多人都會因為缺乏新鮮感而減低熱度,而你依舊興致高昂,真的就像第一次前來一樣。我真的很好奇,你對瓦哈卡究竟懷著什麼樣的情感?
走出博物館,陽光刺得睜不開眼。館前的鳳凰木燒得更旺,更烈,火紅的花朵壓得枝椏無力下垂,緊挨著避暑的人兒。我真怕火鳳凰一翻身,那些人會被燒成黑炭。心裡雖然擔憂,我們還是朝它走去。
才剛坐下,四、五個小販不知從哪兒冒出來,不懼烈日的焚燒向我聚集過來。他們看似世故,其實都還是孩子,十三、四歲,正是青春年少的美好時光,卻為了賺幾個零頭在烈日追逐著遊客。你以溫和的態度告訴他們我們不想買任何東西,他們卻不肯罷休,逼得我們只好再走入烈日中。
午後的獨立大道被陽光切成兩半,明亮的那一端死氣沉沉,陰暗的這一端充滿生機。沿街叫賣的小販、形形色色的旅客、揹著手風琴,彈出不成曲調的乞討者,在陰暗處攢動著。我隨著你的節奏,試圖抓出你心裡的感受,可惜我所能感受的,只是這個城市迷人的一面,卻找不到鍾愛她的理由。像這樣的古城世界上並不少,義大利的佛羅倫斯,中國的麗江,日本的京都,隨便數就能數出好幾個,雖然不盡相同,卻不比她遜色。
我不想再探究了,決定當個普通的觀光客,於是開始逛起商店來。你倒是很有耐心,陪著我隨處逛著,可惜都找不到當地婦女所用的那種黑白相間的雷波娑。我感到有些氣餒,你故作幽默的說,你不會留連在酒館裡,我根本不需要那條長巾。
我看了你一眼,就算我有十條雷波娑也無法將你從酒館拖回,不過倒想用來孕育下一代。
你急了起來,連著說,有了孩子,我們還怎麼旅行?
我不吭聲,腳步移向街心,我在其中一個小販的手上看到幾條類似的花色。才剛靠過去,附近的小販都圍了過來,爭相把雷波娑往我身上塞。連孩子也來了,舉著掛滿項鍊的手,在我眼前搖來晃去,我發現大勢不妙,轉身向你求助,你卻不在我的視線中。我急忙扯下身上的商品,像急於突圍的士兵,推開熱切的小販。
我四處張望著,在如織的人潮中,終於發現了你的身影。
一個老婆婆打著赤腳,頂著烈日在街上乞討。你握著她的手,親切的跟她說起話來。陽光將她的身體曬成了茶色,歲月在她的臉上刻下一道道的印記。她以低沉的嗓音對你訴說著生命的苦悶,人生的不幸。你不停點著頭,時而附和她,時而安慰她。你和老婆婆說完話,臨去前將一張鈔票塞進她的手心裡。
你認識她?我問你。
你說遊走在瓦哈卡這麼多年,見過許許多多的臉,不是匆匆一瞥,就是擦身而過,你記不得所有的面容,卻總有那麼一、兩張深印在心底。
幸好那不是一張年輕美麗的臉。
我又問,她認出你了嗎?
你頗有詩意的說,旅客就像海潮,一波退去,另一波緊跟著來,很難在陌生的土地上留下任何印記。你來瓦哈卡,只是因為喜歡這個地方,不在意有沒有人記得你。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墨西哥情人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墨西哥情人 作者:林滿秋 出版社: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9-04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272 |
小說/文學 |
$ 281 |
中文書 |
$ 282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墨西哥情人
墨西哥,值得守護一輩子的國度,每個旅人都甘願成為她的情人墨西哥,這個既神祕又熱情的國度,散發著紅辣椒、巧克力、龍舌蘭酒混合的特殊風情,一直是許多旅人心目中的祕密情人。《墨西哥情人》不是愛情小說,而是一本記載著無數旅人從驚鴻一瞥、愛上墨西哥、成為墨西哥情人的故事手札,滿盛著旅人的真摯情感與深深依戀。他們有的終老於墨西哥,有的和作者滿秋一樣,每隔一、兩年就會回去一次。書中滿秋循著先生三十多年來對墨西哥的熱愛與城市記憶,他們不僅在空間中移動,也在時間中旅行:女畫家芙烈達濃烈卻悲傷的愛情故事、謎樣神祕
章節試閱
在情人的臂膀中起舞獨立大道走到盡頭,就是公園廣場。午後的公園廣場像個遊樂場,賣氣球的小販渾身掛滿了氣球,五顏六色,滿天飄飛。街頭藝人來來去去,有的穿著傳統服飾,戴著墨西哥帽,以小提琴演奏著墨西哥民謠,也有流行樂團,吟唱歌手,雜耍小丑,各憑本事讓觀光客從口袋裡掏出錢來。人潮比上午更多,綠蔭下的座椅擠滿了人,其中不乏卿卿我我的戀人。墨西哥的戀人很張狂,一對對的公然在烈日下、在人潮中親吻擁抱。戀人的行為雖大膽,卻少了浪漫的氣氛,不像巴黎的空氣中嗅得到戀愛的因子。你說,那是極度限制下的反撲。墨西哥是個天...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林滿秋
- 出版社: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9-04 ISBN/ISSN:9789866807282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2008/09/24
2008/09/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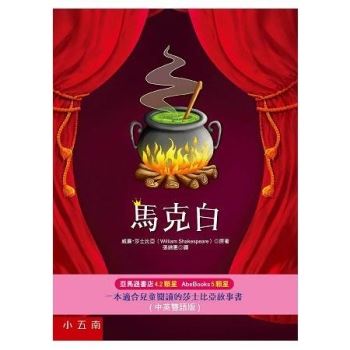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