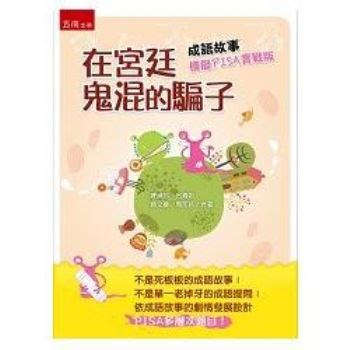她不是毒梟,然而全世界的毒梟都需要她——
她對權力沒有慾望,她所計算安排的一切,只是生存下來的必要手段。
一個單純的墨西哥女孩,無意間踏入充滿殺戮與背叛的毒品世界。
機會讓她扭轉了自己的命運,運氣讓她躲過無數次死亡的威脅,而她的膽識,讓她周旋其中,成為傳奇。
然而,真相往往隱藏在傳說的背後……
一段黑暗的過去與撲朔迷離的現在,交織成一個眾說紛紜的故事。
德蕾莎原本是個單純的墨西哥女孩,她的駕駛員男友魁羅在運送毒品時背叛黑道老大,招來殺身之禍,她的性命也危在旦夕。德蕾莎只得逃離墨西哥、遠渡重洋到西班牙。她在那裡認識了走私販山迪亞哥,於是和他一起以快艇往返摩洛哥與西班牙運載毒品。
她因運毒被捕入獄,認識了出身世家的牢友、綽號「中尉」的芭特麗西亞,兩人結為莫逆。出獄後的她,在因緣際會下踏入毒品運輸一行,展開一場震撼全球毒品市場的革命。德蕾莎從此登上國際舞台,與加利西亞、法國、俄羅斯和義大利黑手黨周旋,雇用高級律師、賄賂法官和警察,成為徹底掌控地中海毒品運輸的「南方女王」。
就在事業如日中天之際,德蕾莎卻赫然發現,十二年前在墨西哥被派去殺她的殺手,居然出現在西班牙……
作者簡介
阿圖洛.貝雷茲-雷維特(Arturo Perez-Reverte, 1951-)
是當前西班牙文壇集讀者和評論家一致喜愛的作家。他的作品不僅完美結合文學內涵、閱讀娛樂和藝術高度,且每每穩居排行榜之列。
這位現年五十五歲、正值創作顛峰的小說家原為新聞工作者,在二十多年的記者生涯中,他有九年擔任戰地記者,冒著生命危險在戰火前線從事報導,成了西班牙家喻戶曉的新聞英雄。貝雷茲-雷維德豐富的報導經驗培養了他敏銳的洞察力和飛快的寫作速度。
從事新聞工作的同時,貝雷茲-雷維德開始提筆創作,自1986年推出處女作《輕騎兵》以來,他維持著幾乎一年一部長篇力作的旺盛創作力。截至目前,貝雷茲-雷維德出版過十六部長篇小說,以及一系列以艾拉崔隊長為主角的歷史冒險小說,不僅廣受讀者歡迎、獲得西班牙國內外重要文學獎,也成功售出多國語言版權(附註)。2003年他當選西班牙皇家學院院士,這位當代西班牙作家最暢銷、被譯成最多國語言的人物,稱他是西班牙「國民作家」,絕不為過。


 2008/06/28
2008/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