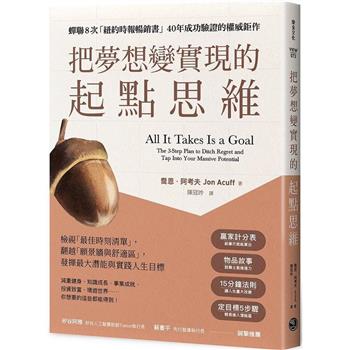推薦序
幽默筆下最道地的北京 徐淑卿
認識季紋是在一次訪談中。雖然之前我早已聽說過她,也在報紙上看過她的文字,知道她剛出版《北京男孩女孩》這本書,對於她隻身到中央戲劇學院唸書、教書的經歷很好奇,但那次見面時間倉促,似乎並沒有觸及太多她對北京的觀感。爾後幾次見面,印象中我也沒有好好問過她在北京生活的感受,現在想來有些不可思議,但這可能反映著我向來的心情,在北京生活幾年之後,最怕人家問起這類很難三言兩語道盡的話題,因此季紋的北京,對我來說始終是一種陌生,一直看到這份書稿,才補充了這個好奇與陌生所調和在一起的奇特的空白。
我曾經不太精確的說,北京對我而言就像一個「安樂椅」。這是我在這個城市生活幾年後協調出來的一種關係。我曾經歷初來乍到時和各種新舊朋友流連夜店暢談狂歡的階段,因此還被戲封為「什剎海傑出青年」,也曾在假日踩著腳踏車穿越胡同,想要探索這個城市發生過的故事,然後為被拆除的四合院遺跡痛苦難當。那個時候我感覺這個寬闊的城市充滿隙縫,可以讓所有的異鄉人找到一個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但是當時我還無法想像自己的隙縫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形狀,一直到現在這個輪廓越來越清楚了,我覺得北京對我來說就像冬日燃燒著燭火的書房一角,我可以在這裡靜謐的讀書,認識各式各樣有意思的人,工作與生活摶合在一起,過濾掉這個城市因為快速崛起而放大的浮躁,同時也摒除掉台北因為過於熟悉而浮動於心的各種雜念。
「安樂椅」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是看待這個城市的一種視角,這個視角因為太容易自給自足,因此難免有它的封閉性。也因此在看季紋的書稿時,我時常津津有味的發現,她提供了許多新奇有趣的語言與觀察角度。比如說,戲謔一些自以為高人一等的台灣女生的「薩達姆的女兒」,我把這個比喻告訴一些北京朋友,他們都笑岔了氣。還有,我從來不知道我住家門口的「7-ELEVEN」,落戶北京後有了在地化的暱稱「七槓么么」。另外,像〈寶馬牌機車〉、〈北京怪譚〉、〈「A包的女人」與「真包的男人」〉、〈監工的女人〉等,這些生活裡有時驚詫有時可氣有時好笑的怪現狀,在季紋幽默的筆調裡,都成了有趣的北京風情畫。
其實,我一直很難言說的是,對於北京我始終有種傷逝之情。我對北京的想像是建立在文字上的,隨著城市的拆建,我心裡的老北京已成斷垣殘壁,隨時在消失中,這與許多人寄望於二○○八年奧運,可以讓北京城帶來煥然一新的面貌,無疑是大異其趣。也因此,季紋在寫到〈在北京拜訪永遠美麗的陳永玲〉這樣的文字時,給我的觸動格外深刻。說來這是我的幸運,我有許多機會認識一些生活在這個城市裡的老人,他們有的有赫赫之名,有的大隱隱於市,可是每個人幾乎都有不平凡的故事,每次看到這些從歷史中走來的老人,我都想從他們已然衰老的軀殼中辨認出輝煌的過去,然後又感到自己何其榮幸,可以親睹他們的風采,但是同時又知道這樣的機緣極其脆弱,猶如風中燭火,隨時有熄滅的一天。所以,如果要我說出自己在北京生存的理由,那麼留住這個城市與這些人逐漸被湮滅的故事,絕對是最重要的初衷。
那麼,什麼又是我們留在北京的故事呢?我想這是季紋不用擔心的,她至少有兩本書作為回憶的註腳。不過,看到她在自序中寫道:「那麼,如果有一天我要離開北京,托運行李限重二十公斤,我會帶走什麼呢?」還是讓我一陣悵然。因為我也曾看著住處越來越多的物品,想著如果有一天我要離開這個城市,我會帶走什麼呢?我的答案與季紋大同小異,畢竟這個在北京「涮」過的自己才是最真實的,而這也是我們唯一可以帶走的吧。
作者簡介
徐淑卿
曾任中國時報開卷版記者,現任職大塊文化出版公司,常駐北京。
自序-後現代甜心
「在北京特別想要有屬於自己的東西」,球球說。「我也好想要有完全屬於我自己的東西喔」,我也跟著哀嚎起來。球球結婚後隨夫在北京定居,她心中「屬於自己的東西」,就是房子,逐著房價飆升的泡沫,她趕緊著手買房子的事情。那麼我呢?屬於我的東西,在北京嗎?「屬於自己的東西」到底是什麼?我回到我在北京東城的租屋,環顧四面沒有任何裝飾的白色牆面,滿櫃子與戲劇專業相關的書、雜誌、碟,還有堆在玄關好幾盒只穿過一兩次的高跟鞋(這是我在全世界最大的製鞋工廠發展出來的小嗜好),我開始思考,在北京有什麼是只屬於我的?於是我開始想:有一天我要離開這裡,若只能帶走二十公斤的東西,我會帶走什麼?送給朋友什麼?賣掉什麼?燒掉什麼?
會這麼想,表示我在北京可能永遠都是一個異鄉人。不只一個到我家拜訪的朋友說:「到了你家就很想睡覺。」(或許是我在無意識的狀況下,把房子佈置成只適合睡覺跟讀書的地方。)每次來打掃的家政小時工都不一樣,每個女孩都問:「小姐你剛搬來呀?」還有一位長輩到我家參觀後,很委婉的說:「你自己一個人過日子,想怎麼過就怎麼過唄。」如果要捨棄二十公斤以外的東西,應該很簡單:絕版書怕以後買不到,可以用寄的,印刷品的郵費很便宜。其他的東西,若還能買到,也可以送人或賣掉。那麼想燒掉的是什麼?大概就是我在北京第一、二年的日記吧?現在重新再看覺得幼稚無比,年輕時的慾望與夢境,現在看起來是虛妄的,那時候的痛苦和煩惱,現在看起來不算什麼,因為我已經有了新的煩惱與慾望。
有次我訪問在北京工作的台灣出版人徐淑卿,希望她能用一個詞總結一下她三四年在北京的感覺,她說:「安樂椅。」她覺得她在北京可以摒除一切雜念與雜事,靜靜的做自己的事情。我又訪問了我的北京朋友超級玩家兼餐飲業之星陳建。見證了這幾年北京夜店與D廳的發展,他覺得北京是什麼?他說:「北京火鍋。」他覺得北京並不是一個明確的什麼,而是一個「平台」,清湯本身沒有味道,大家丟食材下清湯裡涮,金針菇或涷豆腐丟下去以後都變成北京的味道,你說不出來那是什麼味道,但那的確是北京的味道。而且進去涮的時間點前後不一樣,涮出來的味道也不一樣。我想他對北京的定義是很中肯的:必須自己下去涮才能嘗到北京的味道,別人說的都不算。
還有一件事情很有趣,陳健雖然對台灣人編的書《在北京生存的100個理由》感覺不是很服氣(我想沒有任何一個北京人會服氣,因為他們每個人都能說出1000個以上在北京生存的理由),可是他很喜歡同系列在十年前出的另一本書《在台北生存的100個理由》,他對於「能夠由五個小孩拍板說了算」這件事感到振奮、有趣,而同樣的提案在北京,根本不可能以這樣的思維進行。我想這有可能是北京與台北這兩個城市,在性格上最大的不同。
就在我還在思考北京對我來說是什麼的時候,球球已迅速的把房子定下來了。我問:「買在什麼地方?」球球說:「後現代城。」我知道在國貿附近有現代城,但後現代城在哪裡呢?球球說:「就在現代城的後面啊,那就是後現代城。」
蓋在現代城後面的樓房,就叫做後現代城,以這種直白的方式理解現代與後現代,好像也不能說不對。全世界華人地區的房地產產品的命名方式與邏輯,有其地域特色,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為房產命名,意味著對某種即將到來的生活方式的嚮往。台灣有「村上春墅」,為什麼北京不能有「後現代城」?中國還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但已經有人在追求心目中現代甚至是後現代的生活了。對境外人士來說,北京可以提供他們在本國可以享受到的一切,甚至可以玩得更瘋,艾蜜莉.諾童(Emilie Nothomb)在《愛傷害》(Le Sabotage Amoureux)一書中描述的,境外人士在孤島中做國王的情境,至今仍存在;在三里屯、朝陽公園附近的夜店狂練電音爬梯(Party),乃至到金山嶺長城的烽火台上蹦D,或只讀英文報紙、只看衛星電視,連在中國境內的書信往返,信封上都一律寫英文,也無任何生活上的妨礙。至於境內人士呢,總是左一句右一句自豪的說:「這兒是首都呀」,但沒有北京戶口的大學畢業生,甚至很難在北京的公司找到工作;而隨著拆遷與房市狂漲,原本住在城內的居民,紛紛搬到了郊區;通勤時間大塞車,空氣品質低劣。北京現在是東亞最可愛的一顆後現代甜心,一切都在劇烈的地殼變動中,一切皆有可能,所以這麼多人奮不顧身的往裡面扎,即便頭破血流也情有可原,所以是「愛的傷害」呀。
那麼,如果有一天我要離開北京,托運行李限重二十公斤,我會帶走什麼呢?有形的東西似乎在哪裡都買得到,但離開了北京火鍋的金針菇和凍豆腐,就不是北京火鍋,僅僅是金針菇跟凍豆腐而已。這就是北京奇怪的地方,什麼東西拿下去涮,都會變成北京的,離開了這鍋湯,就不是北京的了。大家愛看的,是在北京火鍋裡所有東西都在翻騰的狀態跟煙霧,其實食材極其普通,哪裡都吃得到的。我能帶走的,就是我在中戲學的專業,還有在北京東城涮過四年的我了
誌謝:《北京男孩女孩》能出續集,要感謝「木馬文化」與《幼獅文藝》一直以來對我的愛護、小心肝聶永真設計的美麗封面,還有在北京陪我一起長大的男孩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