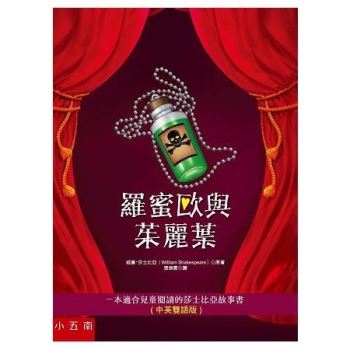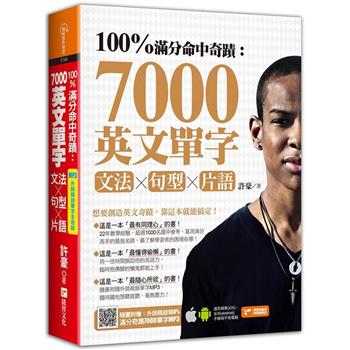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背過身的瞬間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56 |
二手中文書 |
$ 237 |
中文書 |
$ 238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滾滾二十世紀的煙塵,奔成一條最浮沉的歷史軌跡。面對歷史的景致,小說家無法逃躲的大問題長期壓著胸臆,而今決志透過複雜的小說追索百年台灣的荒蕪,還原生命驚心動魄的場景,展演小說家面對歷史之不可思議的豐饒視覺。
楊照此番以【百年荒蕪系列】為總目沛然寫作,計畫完成一百篇的小說巨構。寫的是台灣自一九○一年至二○○○年的故事,以年分為題,歷史時空為景,一個年分一篇小說,一百年一百個故事;單篇自成一格,總體則相互鎖鏈,集成小說家的文學世紀。
《背過身的瞬間》乃中短篇小說集,是系列一的出版。全書收錄小說家已動筆完成的七篇小說。書中透過不同個年輕的心靈,涉世未久或正逢啟蒙憂愁的年紀,與另一個背負故事的老人或是某段歷史的靈魂,相遇並憶話出每篇故事。他們有冒牌的台灣蕃人、戰爭時代的失格少年、戰後專門找人的人尋、理想年代哼著披頭四歌曲的人、政治恐怖目睹血凍漂流的人,以及追尋落日的人,和開發本能的色情片演員等。他們或掀起記憶的蓋骨,重勘自己與歷史的身世,或僅以淒傷的笑容默然回應結局;總總無非是為那些在歷史轉瞬間消滅的蹤影,那些藏起來或失蹤的某些心靈,抵抗時間的輕忽與忘卻。
作者簡介:
楊照
本名李明駿,1963年生,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候選人。曾任《明日報》總主筆、遠流出版公司編輯部製作總監、台北之音《台北話題》主持人、政治大學中文系、靜宜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等職,現為《新新聞》周刊總編輯、東森 ETFM聯播網《1200領先開講》主持人。楊照藉書寫釋放對社會的關懷,以不滅的熱情思索人生與文學,犀利的風格在文壇中生代裡獨樹一幟。曾獲得聯合報小說獎、賴和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吳三連文學獎等,並榮選為1996年年度出版風雲人物。
著有長篇小說《吹薩克斯風的革命者》、《大愛》、《暗巷迷夜》(1994年「開卷」十大好書),中短篇小說集《星星的末裔》、《黯魂》、《獨白》、《紅顏》、《往事追憶錄》,散文《知識份子的炫麗黃昏》、《悲歡球場》、《場邊楊照》、《Cafe Monday》、《迷路的詩》、《軍旅札記》,文學文化評論集《為了詩》、《流離觀點》、《夢與灰燼》、《文學的原像》、《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詩》等。
W. H. Auden寫過一首詩,獻給愛爾蘭前輩詩人W. B. Yeats,詩句中有:Mad Ireland hurt you into poetry.「瘋狂的愛爾蘭傷你為詩人」,勉強這樣翻譯,卻翻譯不出詩裡那種無奈的感情。Auden試圖要說的,應該是愛爾蘭不尋常的歷史經驗,使得Yeats不得不用詩來表達,來發洩。詩與瘋狂之間,有一種既抗拒又親和的關係,應該也有一種神妙又痛苦的彼此印證吧。
有一段時間,我常常想起Auden的這句詩,還有,Yeats與愛爾蘭與瘋狂。從詩句我回頭去想,小說之於我的意義究竟為何。我知道就像詩和Yeats之間,夾著愛爾蘭一樣,小說...
自序「百年荒蕪」緣起
一九二三‧獵熊者
一九四六‧戰爭失格
一九四八‧人尋
一九七一‧背過身的瞬間
一九八九‧圳上的血凍
一九九二‧午後九點零五分的落日
一九九四‧愛情動物
附錄:〈沒有浪漫不能活──兩個查經班同學的書信往來〉成英姝VS.楊照
- 作者: 楊照
- 出版社: INK印刻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6-07-31 ISBN/ISSN:986710868X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56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