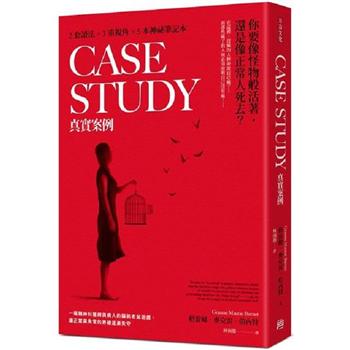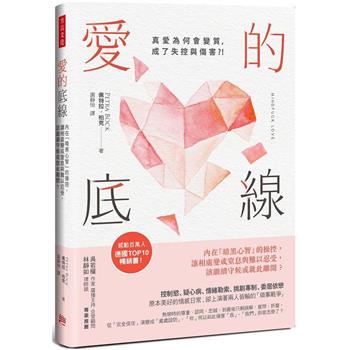她在小時候有個夢想:以為自己長大後會是兒女成群的媽媽。但在30歲以後,她才發現自己既不想要小孩,也不想要丈夫。
這是女性對自己的覺醒,當然也是對自己困惑的開始。為什麼我想要的,和原來的世俗標準都不一樣?既然如此,不如享受自己的最佳身心暢快計畫!
在義大利極盡吃喝的享受後,作者忽然有了罪惡的感覺,這個感覺的出現,讓她害怕:既然我擔心罪惡,為何我還要放假?原來,以往我們是在耗費心神後,才去尋找「休閒娛樂」,然而,有人正是以「無所事事的生活」為最高目標!
這是個漂亮的措辭。Bel far niente是「無所事事之美」的意思。聽我道來──傳統來說,義大利人自古以來一直存在著勤奮工作的人,尤其是那些長期受苦的勞動者,即所謂braccianti。但即使在艱苦勞動的背景下,「無所事事」始終是大家抱持的一個義大利夢想。無所事事的美好是你全部工作的目標,使你倍受祝賀的最後成果。你越是閒暇舒適地無所事事,你的生活成就越高。你也不見得要有錢才能體驗。
◎體驗!印度 以前是「觀光」->現在要懂得「體驗」
作者到了印度,學習瑜珈與禪坐,這是人人對於印度習以為常的印象,也似乎是到了印度該去學習的事,但是她其實不喜歡每日早晨之後古魯梵歌的詠唱。外在的標準是教導我們必須忍受,或努力學習外界「認為對的事」,但是只有「勉強忍耐」一個方法嗎?既然得面對「不愉快」,不如學習體驗人生吧!
「這東西或許不好受,卻很有益。」
「該如何保持堅持下去的動機?」
「有別種選擇嗎?每回遇上挑戰就放棄?瞎混一生,過著悲慘、不完整的生活?」
「你剛說『瞎混』?」
「沒錯,我是這麼說。」
「我該怎麼做?」
「你得自己決定。但是我勸你-既然你問我-趁待在這裡的時候繼續吟唱古魯梵歌,特別是因為你對它有如此極端的反映。假如哪個東西這麼用力摩擦你,八成對你奏效。古魯梵歌正是如此。它燒燬你的自我,把你變成純粹的灰燼。小莉,它是一條艱苦的道路,其動力超越理性所能理解。你待在道場的時間不是只剩下一個星期?之後你可以隨意去旅行,找樂子。所以,就請你再吟唱七天吧,之後永遠不用再去碰它。記得你的導師說過──研究你自己的心靈經驗。你不是來這裡觀光或報導,你是來這裡追尋。所以就去體驗吧。」
◎去愛!峇里島 自以為是的「自由」,其實是混亂->尋求定位自己,才能身心平衡
作者以為走出平常的生活是追求自由,沒想到和峇里島人相比,只是更顯得自己的步調混亂!在峇里島,人們最常問外來客的問題是:「你要去哪裡?」、「你從哪裡來?」、「你已婚嗎?」,三個問題表現了峇里島人相當注重自己的人生定位:了解自己與家人朋友的關係,與上天的關係,才能找到自己的平衡。
◎好吃!義大利 以前我們尋求娛樂->這裡的人尋求快樂
在令人疲憊的婚姻結束之後,作者在義大利、印尼、印度等三個不同國度之間尋找自己。108個短篇象徵了靈魂探索、自我發現之旅:到義大利品嘗感官的滿足,在世上最好的披薩與酒的陪伴下,靈魂就此再生。她再到了印度,與瑜珈士的接觸,洗滌了她混亂的身心。峇里島上,她尋得了身心的平衡。
章節試閱
尋求娛樂,還是快樂?
我承認,有時我不懂自己在這裡做什麼。
我來義大利是為了體驗快樂,但我到這裡的頭幾個星期卻提心吊膽,不知該如何做。老實說,純粹的快樂並非我的文化概念。我來自一個世世代代超級勤勉的家系。我母親的家族是務農的瑞典移民,相片裡的他們看起來像是,他們若看見任何令人快樂的東西,就用腳上的釘靴一腳踩上去(我舅舅把他們統稱為「耕牛」)。我的父方家族是英國清教徒,拙於吃喝玩樂的人。假使把我的父方族譜一路回溯到十七世紀,我確實能找到名叫「勤勉」和「謙恭」的清教徒親戚。
我自己的父母有個小農場,我姊姊和我在工作中長大。
我們學會可靠、負責,在班上名列前茅,是鎮上最一絲不茍、最有效率的保母,我們那位刻苦耐勞的農人/護士母親的縮影,一對年幼的瑞士小刀,天生擅於多種任務。我們在家中擁有許多快樂與歡笑,但牆上貼滿工作清單,因此我未曾體驗或目睹遊手好閒,這輩子從未有過。
儘管一般說來,美國人無法放鬆享受全然的快樂。我們是尋求娛樂的國家,卻不見得是尋求快樂的國家。美國人花費數億元逗樂自己,從色情、主題樂園、到戰爭,卻和平靜的享受是兩回事。美國人比世上任何人工作得更賣力、更久、更緊張。但正如盧卡.斯帕蓋蒂所說,我們似乎樂此不疲。令人擔憂的統計數字支持此一觀察,顯示許多美國人在公司比在自己家的時候感覺更快樂、更滿足。沒錯,我們無疑都工作得太賣力,而後筋疲力竭,必須整個週末身穿睡衣、直接從盒子裡拿粟米片出來吃、頭腦呆滯地盯著電視看(沒錯,跟工作正好對立,但跟快樂可不算同一回事)。美國人不懂得如何無所事事。這是可悲的美國典型─壓力過度的總管去度假,卻無法放鬆─的起因。
我曾經問過盧卡,度假的義大利人是否有相同的問題。他捧腹大笑,幾乎把摩托車撞上噴泉。
「喔,沒有!」他說。「我們是bel far niente的能手。」
這是個漂亮的措辭。 “Bel far niente”是「無所事事之美」的意思。聽我道來─傳統來說,義大利人自古以來一直存在著勤奮工作的人,尤其是那些長期受苦的勞動者,即所謂braccianti(因為他們除了手臂─braccie─的蠻力幫助他們在這世上活下去之外別無所有,故名)。但即使在艱苦勞動的背景下,「無所事事」始終是大家抱持的一個義大利夢想。無所事事的美好是你全部工作的目標,使你倍受祝賀的最後成果。你越是閒暇舒適地無所事事,你的生活成就越高。你也不見得要有錢才能體驗。另有一個美妙的義大利措辭:l’arte d’arrangiarsi─無中生有的藝術。將幾種簡單配料變成一場盛宴、或是幾個聚在一起的朋友變成一場喜慶的藝術。
然而對我來說,追求快樂的主要障礙是我根深蒂固的清教徒罪惡感。我是否該擁有這種快樂?這也是很典型的美國態度─對於自己是否掙得快樂,感到惶惑不安。美國的廣告系統完全環繞在說服拿不定主意的消費者:是的,你確實有權享受特殊待遇。這啤酒是給你的!你今天應該休息一下!因為你值得!苦盡甘來了,寶貝!缺乏安全感的消費者心想,是啊!謝啦!我就去買個半打吧,可惡!甚至一打!而後開始反動式地狂飲。接著才懊悔不已。這類廣告戰在義大利文化中很可能起不了效用,因為人們早已知道他們有權享受人生。在義大利,「你今天應該休息一下!」的回答可能是:對啊,不,廢話。所以我打算中午休息一下,去你家和你老婆睡覺。
或許因為如此,當我告訴義大利朋友們,我到他們的國家來體驗四個月純粹的快樂,他們對此並無任何心理障礙。Complimenti!Vai avanti!恭喜,他們會說。就這麼辦吧。盡情玩吧。來我們家做客吧。從來沒有人說:「你完全缺乏責任感,」或者「多麼自我耽溺的享受」。然而儘管義大利人完全允許我好好享受,我卻仍無法完全放鬆。在義大利的頭幾個禮拜,我的每根清教徒神經都在竄動,找尋任務。我想把快樂當作家庭作業或龐大的科學研究來處理。我思索這類問題:「如何以最效的方式強化快樂?」我心想或許我在義大利的全部時間應當待在圖書館研究快樂的歷史。或者應去採訪在生活中體驗許多快樂的義大利人,問他們快樂是什麼感覺,然後以此為題寫篇報告。(或許雙倍行距、留一吋邊?週一大早就交出去?)
當我明白手邊的唯一問題是:「如何定義快樂?」,而我真正待在這個人們准許我放手探索這個問題的國家時,一切都改觀了。一切都開始變得…美味。有生以來第一次,我每天只需問自己:
「你今天樂於做什麼事,小莉?現在什麼東西能帶給你快樂?」無須考慮任何人的議程,也無需憂心任何責任,這個問題終於變得純粹而確定。
了解自己在義大利不想做什麼,對我而言是有趣的事,一旦准許自己在這兒享受經驗。義大利有多種快樂的表現形式,而我沒有時間嘗試全部。你得在這兒宣告你的主修,否則會應接不暇。既然如此,我感興趣的並非時尚、歌劇、電影、高級車、或去阿爾卑斯山滑雪。我甚至不那麼想觀看藝術。在義大利的整整四個月當中我沒去過任何博物館,我承認這一點讓我有些羞愧。(天啊─更糟糕的是,我得承認我的確去過一家博物館:位於羅馬的國立麵食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Pasta。﹞我發現我真正想做的是吃美好的食物,盡可能多說美好的義大利語。就這樣。因此事實上,我宣告了雙主修-說話與飲食(專修冰品)。
這樣的飲食與說話帶給我至高無上卻又簡單樸素的快樂。我在十月中旬度過的幾個小時,對旁觀者來說或許沒啥大不了,但我始終認為是自己生命中最愉快的時期。我在公寓附近發現一個市場,僅幾條街之遠,我先前不曾注意到這市場。我走近有個義大利婦女的小蔬菜攤,義大利婦女和她兒子販賣各式各樣的產品—像是葉片豐潤、綠藻色的菠菜,血紅有如動物器官的蕃茄,外皮緊繃的香檳色葡萄。
我挑了一綑細長鮮豔的蘆筍。我輕鬆地用義語問這位婦女,能不能帶半綑蘆筍回家?我向她說明,我只有一個人—份量無需太多。她立即從我手中拿過蘆筍,分成兩半。我問她每天能否在老地方找到市場,她說,是的,她每天都在這裡,從早上七點開始。而後她俊俏的兒子表情詭祕地說:「這個嘛,她盡量想在七點來這裡…」我們全笑了。整段談話以義語進行—才幾個月前,這語言我還無法講半個字呢。
我走回公寓,把兩個蛋煮嫩吃午餐。我剝了蛋殼,排放在盤子上,擺在七條蘆筍旁(它們又細又美,根本無須烹煮)。我還在盤子上擺了幾顆橄欖,以及昨天在路上的formaggeria買來的四小團羊乳酪,還有兩片粉紅油嫩的鮭魚。飯後點心是一棵漂亮的桃子,是市場的婦女免費給我的,桃子曬了羅馬的陽光,餘溫猶存。好長一段時間,我甚至無法碰這餐飯,因為這是如此的午餐傑作,真正表現了無中生有的藝術。最後,充分享受菜餚之美後,我在乾淨的木地板上一塊陽光中坐下,用手指頭吃掉每一口菜,一面閱讀每日的義語報紙。幸福進駐我的每個毛細孔。
直到—如同頭幾個月的旅行期間每當我感覺到此種幸福時經常發生的那樣—我的罪惡警報響起。我聽見前夫的聲音在我耳邊不屑地說:所以,你放棄一切就為了這個?這就是你把我們的共同生活一手摧毀的理由?為了幾條蘆筍和一份義語報紙?
我高聲回覆他:「首先,」我說:「我很抱歉,這已不干你的事。其次,讓我回答你的問題…沒錯。」
關於我在義大利追求快樂一事,顯然有件事仍得提出:性的問題怎麼說?
回答這問題,我只能說:我人在此地的時候不想有任何性關係。
更徹底、更誠實的回答是—當然,有時我確實很渴望,但我已決定暫不參加這項特定活動。我不想跟任何人扯上關係。我自然懷念親吻,因為我喜歡親吻。(有一天我向蘇菲抱怨起這件事,最後她憤怒地說:「看在老天爺份上,小莉—假如情況夠糟,就讓我親你吧。」)但目前我不去做任何事。
近來我若覺得寂寞,我就想:那就寂寞吧,小莉。學學處理寂寞。為寂寞做計畫。一輩子就這一次,與它並肩而坐。接受這種人生體驗。別再利用他人的身體或感情,抒發你未滿足的渴望。
這是一種緊急時期的求生方針,尤甚於其他任何事情。早在人生初期,我即已開始追求性與浪漫之樂。我在交往第一個男友前幾乎沒有青春期,而打從十五歲起,我一貫有男孩或男人(有時兩者)作伴。那大約是—喔,十九年前的事了。足足有二十個年頭,我一直與某男子糾結於某場戲劇當中。彼此重疊,之間從沒有一個星期的喘息時間。我不禁要想,這在我的成熟道路上多少造成阻礙。
再者,我跟男人之間有分界的問題。或許這麼說不公平。照說有分界問題,理當一開始就有界線,對吧?但我卻是消失成為我愛的那個人。我是可滲透的薄膜。我若愛你,你即可擁有一切。你能擁有我的時間,我的忠誠,我的屁股,我的金錢,我的家人,我的狗,我的狗的金錢,我的狗的時間—一切的一切。我若愛你,我會扛起你所有的痛苦,為你承擔所有的債務(就每一種定義而言),我將保護你免於不安,把你從未在自己身上養成的各種優秀品質投射給你,買聖誕禮物給你的全家人。我會給你雨和太陽,假使沒辦法給你的話,我會改天給你。除了這些,我還會給你更多,直到我筋疲力竭,耗盡心力,只能靠迷戀另一個人才能再使我恢復精力。
我並非引以自豪地傳遞這些關於我本身的事實,但事情一貫如此。
離開我先生一段時間之後,在一次派對上有個我不太熟悉的男子對我說:「你知道嗎?現在你跟這新男友在一起,似乎完全變了個人。從前你跟你先生看起來很像,但現在的你看上去活像大衛。你甚至連穿著講話都像他。你知道有些人跟他們養的狗看起來很像吧?我想或許你一向跟你的男人很像。」
天啊,我真該暫時擺脫這種循環,稍事休息,給自己一些空間去發現在我不試著與他人融為一體時,我自己看起來、說起話來的樣子。
還有,讓我們都誠實點吧—暫把親密關係放在一旁,或許在我來說是一種慷慨的公共服務。當我回顧我的浪漫史,發現看起來並不怎麼好。可說是一個接著一個災難。還能再有幾種不同類型的男人讓我繼續嘗試去愛,繼續失敗?這樣想吧—你若連續出十場重大車禍,難道最後不會被吊銷駕照?難道你不會多少希望駕照被吊銷?
我之所以對捲入另一段感情有所遲疑,還有最後一個原因。我碰巧還愛著大衛,我想這對下一個男人來說並不公平。我甚至不曉得大衛與我是否已完全分手。在我動身前往義大利之前,我們仍常和彼此消磨時間,儘管我們已有很長一段時間未同床共枕。但我們依然承認,我們倆都仍抱著希望,或許有一天…
我不曉得。
我只曉得—一生倉促的抉擇和混亂的激情累積而成的後果使我心力交瘁。在我前往義大利時,已是身心俱疲。我就像某個絕望的佃農耕種的土壤,負擔過重,亟需休耕。這正是我放棄的原因。
相信我,我知道在自願獨身期間來義大利追求快樂,所蘊含的諷刺意味。但我認為禁慾是目前該做的事。那晚當我聽見我的樓上鄰居(一個很漂亮的義大利姑娘,收藏了一批令人吃驚的高跟靴)在她最近期的幸運訪客陪同下,經歷著我所聽過時間最長、聲音最大、最肉體撞擊、最床搖舖動、最粉身碎骨的做愛時刻。這場打擊之舞的持續時間遠超過一個小時,伴隨著超通風聲效以及野獸的呼喊。我在他們底下僅一層樓,孤單疲倦地躺在床上,只能想著:聽起來真費勁…
當然,有時我確實充滿慾望。我一天內大約從平均一打能輕而易舉想像跟我上床的義大利男人身邊走過。對我的口味而言,羅馬的男人美得可笑、有害、愚蠢。說實話,甚至比羅馬女人還美。羅馬男人的美就像法國女人的美,也就是說—鉅細靡遺地尋求完美。他們像參賽的貴賓犬。有時他們看起來完美得令我想鼓掌叫好。這裡的美男子迫使我不得不延用浪漫小說的讚賞語詞來描述他們。他們「極端迷人」、「英俊得無情」、或「強壯得教人訝異」。
然而,容我承認對自己來説不怎麼愉快的事吧,街上這些羅馬人並未朝我多看一眼。甚至第一眼也沒。一開始我發現這有點令人擔憂。從前在我十九歲的時候,我來過義大利,記得被街上的男人不斷騷擾。在比薩店。在電影院。在梵蒂岡。無止無境,恐怖至極。從前在義大利旅行是一大負擔,幾乎能破壞你的食慾。如今,三十四歲的我顯然成了隱形人。當然,有時男人態度友善地告訴我:「你今天看起來很美,女士。」但這不常發生,而且從未超過分寸。不被公車上討厭的陌生人伸手亂摸儘管是件不錯的事,一個女人卻有她的自尊,不禁要猜:是什麼改變了?是我嗎?還是他們?
於是我到處問人,每個人都同意,是的,義大利在過去十到十五年間的確發生變化。或許是女性主義的勝利,或文化的進化,或加入歐盟而導致無可避免的現代化結果。或只是年輕人這方面對父親和祖父們惡名昭彰的猥褻之舉感到困窘。無論原因為何,義大利整個社會似乎一致決定,這種跟蹤、騷擾婦女的行為不再能讓人接受。甚至我漂亮的年輕朋友蘇菲,還有那些白白淨淨、從前被騷擾得最嚴重的瑞典女孩也沒在街頭碰上這種事。
總而言之—義大利男人似乎已為自己贏得「最佳進步獎」。
這教人鬆一口氣,因為有一陣子我擔心是我自己的緣故。我是說,我擔心之所以不被人注意,是因為我不再是十九歲的美少女。我擔心或許我的朋友史考特去年夏天說得對:「啊,甭擔心,小莉—那些義大利男人不會再騷擾你。這跟法國不同,法國人專找徐娘。」
我的串連交流雙胞胎喬凡尼和達里歐出身於拿波里。這令我無法想像。我無法想像害羞、勤奮、和善的喬凡尼在少年時代屬於這個-我用這詞兒可一點也不誇張-匪幫。但他確實是拿波里人,因為在我離開羅馬前,他給了我拿波里一家比薩餅店的名字,要我非去嚐嚐不可,喬凡尼告知我,因為這家店賣的比薩餅在拿波里無出其右。這使我十二萬分期待,鑒於義大利最好的比薩餅來自拿波里,而全世界最好的比薩餅來自義大利,這意味這家比薩餅店肯定提供…我幾乎迷信得說不出來…全世界最好的比薩餅?喬凡尼遞店名給我時,態度嚴肅熱烈,我幾乎覺得自己正闖進一個秘密會社。他把住址塞入我手中,悄悄地說:「請去這家比薩餅店。點瑪格麗特比薩(margherita pizz)加雙份起司。如果你去拿波里沒吃這種比薩,請騙我說你去吃了。」
於是蘇菲和我來到米凱爾比薩店(Pizzeria da Michele),我們剛剛點的一人一份的餅使我們為之瘋狂。事實上,我對這份比薩餅的愛使我熱昏了頭,我相信我的比薩餅也回敬了我的愛。我和這份比薩建立了關係,幾乎是一場戀情。同時,蘇菲簡直吃得感動涕零,發生某種形而上的危機,她向我懇求:「斯德哥爾摩幹嘛還費心做比薩?我們在斯德哥爾摩幹嘛費心吃東西?」
米凱爾比薩店地方不大,僅兩個房間,和一個烘烤不停的烤爐。在雨中從火車站走去約十五分鐘路程,根本連擔心也不用擔心,走就是了。你得及早到那兒,因為有時他們用完麵皮,會使你傷心欲絕。午後一點,比薩店外頭的街道已擠滿想進店裡的拿波里人,推推搡搡,彷彿嘗試擠上救生船。店裡沒有菜單。這裡的比薩餅只有兩種-普通口味和雙份起司。沒有所謂新時代南加州的橄欖加蕃茄干式的夢幻比薩。進餐中途,我才琢磨出麵皮嚐起來不像我吃過的任何比薩麵皮,倒像是印度麵包(nan)。柔軟耐嚼,卻特別薄。我一向認為談到比薩餅皮,我們一生只有兩種選擇—薄而脆,或者厚而軟。
怎知這世上有一種薄而軟的餅皮?神聖的上帝!薄、軟、韌、黏、好吃、耐嚼、鹹味的比薩天堂。最上面放的甜味蕃茄醬汁讓新鮮起司溶解時 溢出泡沫乳脂,中央的一枝羅勒葉讓藥草芬芳充滿整個比薩,就像閃閃發光的電影明星在派對中給周圍每個人帶來迷人陶醉的感覺。就技術而言,吃這東西當然不可能。你試著咬一口軟黏的脆褶皮,熱起司排山倒海般地散開,把你和週圍的一切弄得一團糟,不過,就隨遇而安吧。
創造這項奇蹟的人把比薩餅從燃燒木頭的烤爐鏟進鏟出,酷似在船腹工作的鍋爐工把煤炭鏟入熊熊燃燒的火爐裡。他們的袖子捲在流汗的前臂,臉部因費勁而發紅,嘴裡叼著香菸、瞇著一隻眼睛抵擋爐子的高溫。蘇菲和我每人又點了一份餅-每個人又吃了一整個比薩-蘇菲嘗試控制自己,但比薩實在太棒,幾乎使我們無法應付。
順帶說說我的身體。我當然每天都在增加體重。在義大利,我粗魯對待自己的身體,消耗數量驚人的起司、麵食、麵包、美酒和比薩餅。(有人告訴我,在拿波里別處竟吃得到所謂巧克力比薩餅。無聊透頂!我是說,之後確實被我找到,很好吃,只不過說實話-巧克力比薩?我沒運動,
我沒吃足夠的纖維,我沒吃維他命。現實生活中,我早餐吃的是撒了小麥胚芽的有機羊乳優格。我的現實生活早已遠去。我在美國的朋友蘇珊告訴大家,我正在從事「絕對攝取碳水化合物」之旅。但我的身體卻對這一切極富雅量。我的身體對於我的罪惡與放縱視而不見,彷彿在說:「沒事,孩子,盡情享受生活吧,我看得出這只是暫時的。讓我知道你對純粹快樂的小小試驗何時結束,再看看如何採取防治損害措施。」
儘管如此,當我在拿波里最佳比薩店的鏡子裡看見自己時,我看見一個眼神喜悅、氣色明亮、快樂健康的臉蛋。我有好一段時間沒看見這樣的臉蛋。
「謝謝你。」我低聲說。而後蘇菲和我冒著雨跑出去找糕餅吃。
尋求娛樂,還是快樂?我承認,有時我不懂自己在這裡做什麼。我來義大利是為了體驗快樂,但我到這裡的頭幾個星期卻提心吊膽,不知該如何做。老實說,純粹的快樂並非我的文化概念。我來自一個世世代代超級勤勉的家系。我母親的家族是務農的瑞典移民,相片裡的他們看起來像是,他們若看見任何令人快樂的東西,就用腳上的釘靴一腳踩上去(我舅舅把他們統稱為「耕牛」)。我的父方家族是英國清教徒,拙於吃喝玩樂的人。假使把我的父方族譜一路回溯到十七世紀,我確實能找到名叫「勤勉」和「謙恭」的清教徒親戚。我自己的父母有個小農場,我姊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