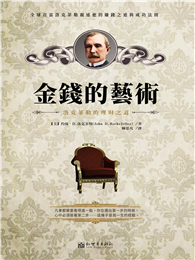這隻學說話的狗,將如何說出他們愛情的謎底?
一個謎樣的女人、一個思念亡妻的男人、 一段永無法喚回的燦爛時光……
全美650,000人為它落淚!感動全球21國的讀者!
一個晚秋的黃昏裡,有個女人從蘋果樹上墜落而亡。這死亡到底是意外或自殺?無人知曉。而女人最後以仰躺的姿勢與世界告別之時,心裡到底是懷著絕望,或只是單純想以死來報復別人?也沒有人知道。唯一的目擊者,卻是這個女人心愛的狗「蘿麗」。
女人的丈夫是個語言學家,因為思念妻子卻無從得知她真正的死因,竟然異想天開打算教蘿麗說話,讓牠說出當天出事的原因。也就在教狗說話的期間,這個男人逐漸開啟了和妻子之間的記憶之盒:從他們第一次為期一週的約會、信守彼此的時刻,而至妻子製做亡者面具、她對於亡靈世界的著迷、接連不斷詭異而殘破的夢境……至此,男人才漸漸拼貼出妻子的樣貌。
男人最後是否能教會蘿麗說話?這個男人和這隻狗,各自擁有全然不同的世界,將會用何種方式找到他們共通的語言?他們之間那座語言的「巴別塔」是否真能建立起來?這將是作者企圖藉由這部小說給予讀者思考的地方:人都以為和自己最親近的人共有一座巴別塔,以為自己瞭解那個最親近的人,以為彼此說著同樣的語言、心靈一致──然而,這座巴別塔是否真的存在,似乎只有在真相浮現之時才能知道答案。
本書特色
※全美銷售 650,000 冊。
※全球已售出 21 國語言版權。
※即將改拍成電影。
※具有強烈的阿言德風格。
※美國新生代最耀眼的作家。
※李奭學 專文推薦。
作者簡介:
卡洛琳.帕克斯特
畢業於美利堅大學創作研究所。大學畢業後,曾經在書店工作三年,而後才全心投入創作。她的作品散見於「北美評論」、「明尼蘇達評論」、「夏威夷評論」、「新月評論」。《巴別塔之犬》是她正式出版的第一部小說,甫一出版即引起熱烈迴響,有書評家說她具有強烈的阿言德風格:霧氣濃重的鬼魅深夜、古老的民間傳說、給予人如夢般的閱讀歷程;更有書評家讚許她是美國新生代作家之中最耀眼的一位。卡洛琳.帕克斯特現今與丈夫及兒子住在華盛頓特區,第二本小說Lost&Found即將出版。
譯者簡介:
何致和
1967年生於台北。文化大學英文系,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畢業。短篇小說曾獲聯合報文學獎、寶島小說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著有小說集《失去夜的那一夜》、長篇小說《白色城市的憂鬱》。另有《酸臭之屋》、《惡夢工廠》、《時間線》、《人骨拼圖》、《戰爭魔術師》等十餘部譯作。目前正於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
各界推薦
媒體推薦:
「這部小說有著不可臆測的魔力,它能將讀者帶往未知而驚奇的境地!你必定會為它動容,然後甘心接受它給予你的一切邏輯,並且無從抵抗地被這個故事擺弄,隨它歡喜、傷悲、起伏……」──【紐約時報書評】
「一個女人從樹上墜落致死,死因不明,唯一的目擊者竟是她的狗……如此吸引人的開場,帶出了這個動人故事……學講話的狗、如謎一般的人物、精采的轉折,在在都讓讀者無法移開目光。」──【出版家週刊】
「讓狗開口說出真相?選擇這個主題確實是一次高難度的挑戰!尤其是如何說服讀者、化解他們心中的疑慮,並且讓他們為這故事著迷……然而,卡洛琳.帕克斯特在這部處女作的表現相當令我們讚賞!」──【今日美國】
「一個關於回憶、語言、悲傷和贖罪的故事,一次令人心碎的探尋!」 ──【老爺雜誌】
「相當耀眼的小說!它精采的地方在於男主角探尋妻子謎樣個性的真相,討論人與人之間是否永遠存在著無法跨越的距離……在真相逐漸顯露之時,伴隨而來的是一股強大的情感力量,衝擊著我們,讓人在搖晃不定的心緒中對它難以忘懷……」──【好書情報】
媒體推薦:「這部小說有著不可臆測的魔力,它能將讀者帶往未知而驚奇的境地!你必定會為它動容,然後甘心接受它給予你的一切邏輯,並且無從抵抗地被這個故事擺弄,隨它歡喜、傷悲、起伏……」──【紐約時報書評】
「一個女人從樹上墜落致死,死因不明,唯一的目擊者竟是她的狗……如此吸引人的開場,帶出了這個動人故事……學講話的狗、如謎一般的人物、精采的轉折,在在都讓讀者無法移開目光。」──【出版家週刊】
「讓狗開口說出真相?選擇這個主題確實是一次高難度的挑戰!尤其是如何說服讀者、化解他們心中的疑慮,並且讓他們為這...
章節試閱
1
目前為止,我所知道的事就只有這樣——十月二十四日的那個下午,我的妻子蕾西.藍森從後院的蘋果樹上墜落而死,當時現場除了我們養的狗蘿麗之外,沒有任何目擊者。那天不是周末,鄰居們都不在家,沒人把窗戶打開坐在廚房裡,因此當我的妻子從高處墜下時,沒人知道她是否驚聲尖叫、是否哀鳴,或根本沒發出半點聲音。那天不是假日,鄰居們沒人利用晚秋的好天氣在院子裡整理花園,因此當她落下時,沒人看見半空中的她是縮成一團、是展開身體,或只是張開雙臂迎向遼闊的天空。
意外發生時,我正在大學的圖書館裡準備研討會的論文,那天傍晚還有一堂研究生的課要上。要不是因為我看到一筆資料和蕾西一直想看的電影有關,而迫不及待打電話回家想告訴她相關的趣事,那麼我可能和過去一樣,在教完這堂課後和研究生們一起去喝啤酒,開開心心和他們共度幾小時時間,而完全不知道我家院子的泥地上已蹲滿了警察。
不過,我畢竟打了這通電話,撥了自家的電話號碼。但接起電話的卻是一個男人。「這裡是藍公館。」陌生男人說。
我愣了一下,一時有些迷惑。接著,我腦海中的記憶資料庫便開始快速翻動,檢索任何可能會為了某種理由而突然造訪我家的朋友或親戚,但就是比對不出電話那端的男子聲音。此外,那句「藍公館」也讓我困惑不已。我的姓氏是艾佛森,聽見一個陌生人把我的房子說成似乎只有蕾西一個人住在那裡,讓我起了一種奇怪的感覺,彷彿在這一天中,我突然被人排擠出自己的生命劇本之外。
「我想找蕾西。」我終於說。
「請問您是哪位?」陌生男人問。
「我是她丈夫,保羅.艾佛森。」
「艾佛森先生,我是安東尼.史塔克警探。你家出事了,請你趕快回來。」
很顯然,警方之所以會出現在我家全是因為蘿麗的關係。當我的鄰居們一個個上完工回家時,他們都聽見了蘿麗悲嚎慟哭的嗥叫聲,一聲聲似永無止息地從我家院子傳出。他們都知道蘿麗,大部份人都認識牠,都聽過牠的吠聲和在院裡追逐松鼠或小鳥時發出的喘息,但沒人聽過蘿麗發出這樣的聲音。最先好奇過來打探的是我家左邊的鄰居吉姆.柏拉索,他走到籬笆邊往我家後院看,登時明白發生了什麼事。隨著秋季漸去,夜幕來得一天比一天早,那時天色已暗了,但當蘿麗發了瘋似地在蘋果樹和房舍後門之間來回奔跑時,觸動了院子裡的自動感應燈光。電燈一亮,牠便跑回蕾西那裡,用鼻子輕推她的身體;燈光熄滅後,牠又起身在院裡四處狂奔,再次觸動讓電燈打亮。如此動作不斷重覆循環,就在燈光一明一暗閃爍下,吉姆才得以瞧見躺在樹下的蕾西,於是撥了九一一報警。
當我趕回家時,警方已在我家後院拉起了封鎖帶,而我才一踏上草皮,先前接電話的那位警官便把我攔下。他再次自我介紹,然後把我帶到客廳。我默默跟著他走,滿肚子疑問全卡在喉嚨裡,哽得我差點無法呼吸。我知道接下來等著迎接我的會是什麼。沒錯,儘管擺設依舊,但我的家此時的感覺卻是寂靜而荒涼,彷彿有人趁我不在的這段時間把屋裡的種種傢俱全搬空了。就連蘿麗也不見了。動物收容所的人已讓牠平靜下來,把牠帶走到另一個地方過夜。
我茫茫然在沙發上坐下,讓史塔克警探親口告知我這個噩耗。
「你知道你太太爬到樹上去做什麼嗎?」他問。
「不知道。」我說。我們在一起這麼久了,就我對她的瞭解,她從未顯露出對爬樹的愛好,而這次絕不可能是她突發奇想之下的行為。我們院裡那棵蘋果樹長得高大非凡,跟觀光果園那種任遊客自行摘取的矮小蘋果樹比起來,它簡直就是個怪物。我們根本不理它,從搬來到現在一次也沒修剪過,任其胡亂生長,迄今已有八、九公尺高。我現在實在沒心思猜想她爬到樹上究竟想做什麼,但史塔克警探的雙眼卻牢牢盯著我。「也許她想摘點蘋果吧。」我小聲地說。
「嗯,這似乎是很符合邏輯的推斷。」他看看我,又看看地板。「以我們的看法,你太太很顯然是死於意外,但案發當時現場沒有目擊者,所以我們還是得調查一下以排除自殺的可能。恕我冒昧……你太太最近是否出現沮喪的情緒?她有沒有說過想要自殺?有沒有在不經意中提到這點?」
我搖搖頭。
「我想也不可能,」他說:「只是問問而已。」
在後院拍照蒐證的警察結束工作後,史塔克警探過去和他們說了些話,然後又回來向我報告。大家的看法完全一致,毫無疑問這是一場意外。墜落的方式有兩種,背後各有不同的含義。若一個人是自己跳下,即使從七、八層樓的高處,也是有辦法控制自己墜落的姿式的。他往往會以腳先觸地,雙腿和脊椎可能會受到重傷,但仍有存活的機會。假如他沒活下來,那麼由骨頭折斷的情況、由足踝和膝蓋因重力而碎裂的方式,也可以讓我們判斷這個跳樓的行為是故意的。然而,若一個人從離地面約八公尺高的蘋果樹上不小心失足滑下,就很難控制墜落的方式了。著地的部位也許是頭、也許是肚子,也許是背部,摔下後整個人外觀似乎毫髮未傷,但體內的骨頭與器官卻都已碎裂。這兩者不同差異,正是我們據以判斷是否為意外的證據。當他們發現蕾西時,她面朝上仰躺在地,頸椎已經摔斷了。由此,我們可以得知蕾西不是自己跳下來的。
當警方離開,蕾西的屍體也運走後,我一個人走進了後院。蘋果樹下,散落著一些從樹上掉下來的水果。蕾西之所以爬到樹上,是想趁這些殘餘的蘋果在過熟掉落前把它們摘下嗎?也許她想烤個蘋果派;也許她打算把蘋果放在漂亮的碗裡,找個陽光充足的地方和我一起享用。我把地上的蘋果一個個撿起來,帶回屋內。它們就這麼被我擺在廚房的桌上,直到腐爛的甜味引來蒼蠅為止。
直到葬禮過後幾天,我才發現了確定的線索。唔,用「線索」這兩個字可能不太恰當,此詞一出,就排除了純粹巧合和我個人過度分析的可能性。說我找到了線索,就好像有人故意精心設計留下跦絲馬跡,目的是想引導我找出一個祕而不宣卻又極其顯著、且正確性不容爭議的答案。我並不奢望自己能有這種運氣。因此我應該說,我開始發現一些不尋常的事實,一些和過去不同的跡象,足以讓我懷疑蕾西死亡的那天並不是一個平常的日子。
第一件不尋常的事是我們的書架。我和蕾西閱讀的興趣都很廣泛,但和大部份人一樣,我們收藏這些書籍並沒有一套有系統的方式,而是隨興依照好幾種不同的分類方法擺放。有些書架上的書是依尺寸歸類的,一些開本較大的書全被擺在書架的最下層,而那些平裝本的小書則塞在空間較小的地方。另一種歸類法則是依照主題(例如,我們所有的食譜都擺在同一層書架上),不過這種歸類法頗傷腦筋,後來也就不了了之了。還有一種區分法是分成「她的書」和「我的書」,從書籍的主題可反映出我們兩人不同的興趣,而這些婚前就已各自擁有的書,就這麼各成一區地待在自己的位置。除了這幾種分類法外,剩下的書就可說像大雜燴般混在一起了。儘管如此,我還是有辦法知道哪本書放在哪個地方。憑著記憶,我可以馬上指出那本我在二十歲時頗為喜愛的小說,是夾在我們結婚時朋友送的詩集和那本我在某個夏天沙灘上消遣的科幻小說之間。若你再問,那本我和別人合著的教科書放在何處,我也能馬上指出正確位置,告訴你它就插在披頭四傳記和一本教你如何自己釀啤酒的書之間。正因如此,我才知道蕾西在死前曾經更動過一些書籍的位置。
第二件異常之事和蘿麗有關。就目前所拼湊的,我發現蕾西那天似乎從冰箱拿了一塊牛排給蘿麗。這塊牛排本來是我們準備當天晚上烤來吃的,一開始,我以為是蕾西自己吃了這塊牛排,只把骨頭丟給蘿麗啃咬——意外發生後幾天,我在臥房角落發現了這塊牛骨。問題是,我只看到廚房的爐上子留著一個平底鍋,卻沒發現用過的盤子和刀叉。洗碗機的門是關著的。那天早餐後我曾讓它運轉一次,當我打開它時,發現沒人更動過我的親手傑作,裡面的杯盤仍依照當天早上排列的方式擺放。洗碗機沒人碰過,水槽邊的杯盤瀝水架上也是空的,擦盤子用的抹布也沒有沾濕。這種種現象讓我導出兩個結論:蕾西若不是給蘿麗一次驚喜,讓牠得到一整塊肉排,否則就是自己站在爐子前,在她生命的最後一天用手代替叉子吃掉了重達二十盎司的牛排。現在再仔細想想,當然可能還有第三種劇本,而這可能才是最理想的情況——說不定她和蘿麗一人一半共享了這塊牛排。
也許這些事件根本不具任何意義。但是,悲痛中的我,正盡一切努力想合理解釋我妻子死亡的原因。不過,我發現的證據實在夠古怪的了,足以讓我懷疑那天的事,懷疑是否真的是因為蘋果的誘惑,才讓我的愛妻爬上那棵巨樹。我只有蘿麗這一位目擊者,牠不單目擊了蕾西的死,也目擊了所有導致這個意外的過程。牠從早到晚都盯著蕾西的一舉一動。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我和蕾西的婚姻關係都一覽無遺呈現在牠眼前。簡單地說,牠一定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事。我感覺自己必須盡一切努力,從牠那裡把這些祕密給挖出來。
2
關於狗的語言能力,也許你已耳熟能詳一些著名的案例了,但為了喚起記憶,請容我先針對這段歷史做一點簡短的說明。一開始,我們當然要講講十六世紀里昂的那隻靈犬。牠是一隻毛獅犬,母親被荷蘭商人帶到里昂,出生不久便被一名婦人收養。這個女人自己的孩子剛生下來沒多久就夭折了,哀傷不已的她把狗當成自己的小孩,讓牠穿上小睡衣和小童帽,甚至用自己的奶水哺育牠。當狗兒漸漸長大,牠的「母親」便開始教牠說話,經過一番不屈不撓艱辛努力,她終於成功讓這隻狗說起人話。雖然旁人還是得透過婦人翻譯才能知道這隻狗說什麼,但牠很快就成為社會上的知名人物,而且從來不像其他狗兒那樣只會打鬧嬉戲。這一人一狗就這樣在一起快樂地度過了十三年,直到婦人生了重病臨終之時,那隻狗也從未離開過她的床邊。婦人過世的那天晚上,在她最後一次閤上眼睛的時候,那隻狗對她說了最後一句話:「沒妳的耳,就沒我的舌。」(英文的tongue和法文的langue都有雙重意義,同時具有「舌頭」和「說話能力」的意思。)這隻靈犬在「母親」死後又活了一年,卻從此沒發出任何一個聲音,無論對其他狗或人都一樣。在牠死後,里昂的人們替牠造了個雕像紀念牠,刻在基座上的正是牠最後所說的那句話。
這個由前人記錄的故事極具童話奇幻色彩,又充滿哀傷的氛圍,非常適合做為我這本書的開場白。我勤奮不休,孜孜矻矻研究,一心只想用這本著作向那些困惑不解的同僚們解釋,為何我在花了二十年精力投入語言學研究後,會突然決定著手教一隻狗說話。
以歷史案件開場是有必要的,這足以證明我的行為並非異想天開,而是有史可考的。回顧過往,我們當然不能不提到瓦西爾(Vasil)這位十八世紀的匈牙利人。他深受知名哲學家傑佛瑞.隆威(Geoffrey Longwell)的影響,認為狗是失落的以色列部族,因而對一窩新生的維茲拉獵犬進行一連串的實驗。瓦西爾從聖經的伊甸園故事得到靈感,雖然聖經中並未明確提到伊甸園裡是否有狗存在,但瓦西爾認為上帝當然不會漏掉這麼美好的動物。他把開口對夏娃說話的那條蛇視為證據,推斷那時生活在伊甸園中的動物也都具有說話的能力,但隨著亞當和夏娃被逐出樂園,動物們的語言能力也跟著一起喪失了。對動物來說,這並不是件公平的事。瓦西爾相信,只要他能讓動物還原這種能力,就能明瞭世界在創始之初所用的原始語言。
為了重新挖掘出這種語言,瓦西爾把這些幼犬安置在一座以高牆圍繞起來的花園裡,每隻幼犬都被單獨隔離,不讓牠們與自己的兄弟姐妹接觸,企圖以這種方式重建出當時伊甸園的情景。他替這些幼犬準備充裕的食物和清水,並且每天都幫牠們按摩頸部,以刺激聲帶的發育。他的實驗大有斬獲:一隻小狗從未發出聲音,另一隻發出的聲音則頗像一個人咕噥說出的法文(不過根據後來的研究者發現,這些聲音比較像亞爾沙斯的克里奧爾語),還有一隻狗甚至學會說出匈牙利語的「烤牛肉」這個字。至於其他五隻小狗雖然只會吠叫,但牠們似乎都很清楚彼此的吠叫聲所代表的意義。
瓦西爾的學說引來了教會的責難,特別是上帝很不公平地剝奪了狗的說話能力的假設,因此他生命中的最後二十年全在牢裡度過。讓他東窗事發而被捕的正是這些維茲拉獵犬——有天這幾隻狗兒偷偷溜到了街上,那隻會說法文的狗狂吠著低級下流的打油詩,而那隻會說匈牙利文的狗則到處向人討烤牛肉,於是,驚訝的群眾才一路跟著牠們找到了瓦西爾的住處。
不過,最關鍵的例子,我認為還是溫德爾.賀里斯(Wendell Hollis)的悲劇。研究語言學的人幾乎都知道這個故事,關於狗語言能力的研究,此事堪稱現代版的經典。賀里斯曾花費數年時間,替上百隻狗動過上顎手術,改變牠們的嘴部構造以適合用來說話。他在紐約自家進行這個實驗,儘管有些狗兒在手術後死亡,但有更多狗兒在大劫過後逃回街上。賀里斯後來也難逃被捕命運——這些動過手術的狗兒怪里怪氣的吠叫聲讓左右鄰居忍受了好幾年,最後終於有隻狗學會了開口求救,才讓附近一位居民報案請警方前來處理。這隻嘴巴嚴重變形、喉嚨上還留有開刀疤痕的野狗被帶上法庭作證。雖然牠還無法說出完整的句子,但憑牠說出的「可恨」、「很痛」和「兄弟們死了」等幾個字眼,讓陪審團只花一個小時便裁定賀里斯有罪,法官於是判處他五年徒刑。
當然,上述這些例子沒有一個可說是完全成功的,但從這些失敗的不同面相、從這些功敗而「垂成」的特質,讓我產生了這個領域尚有探索可能的想法。
事實上,我發現自己除了這件事之外,也沒別的事情可想了。
雖然我不再確定自己是否在意,但如果我想在學界保持好名聲的話,就不允許拋出這麼主觀的議題。我必須這麼告訴我的同僚,說我研究的是一個整體性的工作,不但早已有人進行,而且差不多和語言學研究本身那般古老。我必須告訴他們,我所從事的並不是什麼全新的研究。
要是我能的話,我還想學學詩人的方法,仿效他們敘述有關愛情、戰禍和煩擾故事的方式。我想在論文開始之前寫下這麼一段話:
我歌頌一位雙手沾染墨汁、秀髮下藏有圖畫的女人。我歌頌一隻毛皮像倒豎天鵝絨的狗。我歌頌那落下的人體在樹底泥地留下的痕跡,也歌頌一位平凡人——他想知道沒有人可以告訴他的事。這是真正的開始。
讓我們回到原本的話題,討論一下我所要從事的計畫。前面說到我這隻名叫蘿麗的母狗,牠是羅德西亞脊背犬,是我妻子在結婚前養的,後來自然也就變成了我的狗。我的計畫是運用一系列練習和實驗,以任何可能的方法讓牠增加生理和心理上的能力,以瞭解人類的語言。簡單地說,我想讓蘿麗開口說話。
我知道你們現在的想法。若在一年前,我也會和你們一樣對此感到懷疑。但我不得不提,過去這幾個月來發生的事,確實改變了我的想法。容我提醒各位,科學家們在上世紀已目睹一項奇蹟,見證黑猩猩能以手語表達完整的句子。我們看過飼主為了尋朋友開心,教會鸚鵡說上幾句髒話。我們也知道,受過訓練的導盲犬能開啟電燈開關,替失聰的父母注意嬰孩的啼哭。我個人還在電視上見過一位業餘人士的表演,他教會自己的狗發出類似「我愛你」的聲音。
我舉出上述例子,並不是用來推論我最後一定能成功。一開始我便相當清楚,比起黑猩猩或其他高等靈長類,狗的頭蓋骨容量可說小得太多。我也不會欺騙自己,深知無論說出「我愛你」的狗或像水手一樣粗魯罵人的鸚鵡,表現出來的只是一種小把戲,牠們知道只要這麼做就會得到一點點食物的賞賜。
然而,在無數個晚上,當蘿麗坐在我身旁以又大又不可理解的眼睛看著我時,我不禁這麼想:如果牠能說話,將會告訴我什麼事?有時我乾脆在地毯上躺下,用手撫摸牠那顆布滿皺紋的大腦袋,一邊輕聲對牠說出我心中的疑問。好幾次我就這麼睡著了,醒來時才發現自己的頭正枕在牠那毛茸茸的寬闊腰背上。
目前為此,我只得到一點最重要的結論:狗是最完全的目擊者。牠們被允許跟在我們身邊,參與我們最祕密的舉動,當我們自以為孤獨時,牠們卻一直伴隨在那兒。想看看狗能告訴我們什麼事?牠們坐在歷任總統的膝蓋上,牠們目睹愛情和狂熱、爭執和仇恨以及孩童們的祕密遊戲。如果牠們可以把見到的一切告訴我們,便足以縫補弭平人與人之間的諸多鴻溝。我覺得自己別無選擇,非得這麼一試不可。
3
一個關於狗說話的笑話。有個男人牽狗走進酒吧,酒保說:「抱歉,老兄,狗不能進來。」男人說:「喔,可是你並不知道,這是一隻很特別的狗喔——牠能開口說話。」酒保露出狐疑表情說:「那好,你讓牠講幾句話來聽吧。」男人把狗抱上高腳凳,專注凝視著狗的雙眼。「你說蓋在房子上面的東西是什麼?」男人問。「Roof、roof!(屋頂)」狗開口說。「那麼,砂紙給你的感覺又是什麼呢?」男人再問。「Ruff、ruff!(粗糙)」狗回答。「很好,再說說誰是史上最偉大的棒球選手?」男人問。「Rooth、rooth!(貝比魯斯)」狗兒立刻說。「夠了,老兄,」酒保說:「你們兩個給我一起滾出去。」男人把狗抱下高腳凳,一起離開酒吧。他們走出大門,那隻狗抬起頭納悶地看著男人說:「是我說錯了嗎?難道是狄馬喬?」
這是當我和蘿麗一起坐在地上,看著牠深棕色的眼珠時,心中所想到的故事。目前為止,我已努力了兩個小時,試了一些很初步的智能測驗。我必須按捺住放棄擔任教師的衝動,才能裝傻以對待幼犬的方式對牠說話。「你去哪了呢,狄馬喬?」我想以對嬰兒說話般這麼對牠說,並握住牠的前爪,舉高,直到牠翻過身落回地上,進行這個我們常做的小小室內遊戲。「嗯,妹妹?」我想撫摸牠的肚子,以輕聲細語說:「狄馬喬去哪了呢?」但是,我們還有一點別的事要做,於是我只拍拍牠的頭,然後以充滿威嚴的語氣說:「乖妺妹。」
羅德西亞脊背犬的體型很大,當蘿麗站起來時,牠的頭部高過我的膝蓋。這種狗最早是拿來獵獅子用的。在野外,牠們能發揮極大力量和敏捷性追捕兔子或其他小獵物(畢竟在我們這個小鎮上想見到獅子並不容易),但在家裡時,卻又相當溫馴穩重。牠們名稱的由來,是因為脊背中央有一長條逆生的毛流,像亂髮般突起在光滑柔順的棕色體毛上。當你把手放在這道毛流上時,感覺會有些扎手,有如我們小時候剛理完的平頭。此外,這還讓我想到我祖母家的那張天鵝絨椅子。若沒穿長袖衣褲,是不可能坐在這張椅子上的,因為這椅子布料非常硬,不管你從哪個方向摸,都覺得刺刺地扎痛皮膚。然而,只要你用手指細心撫平絨毛,就可以感覺到那股藏在一根根纖維之間的柔軟。
在開始進行的第一天早上,我先整理出蘿麗所有聽得懂的字。當然,她最熟悉的就是自己的名字,於是我馬上做了一個小實驗,以呼喚牠名字時所用的音調喊出「巴克雷」、「水床」、「聖誕老人」等幾個字眼。牠一聽見我的聲音便坐了起來,凝視著我,露出一副專注聆聽的樣子,但仍留在原位不動。直到我正確喊出「蘿麗」時,牠才一躍而起跑來我這裡。妹妹乖,我稱讚牠。真是乖妹妹。
接著,我對牠進行一些指令測試。「過來」、「坐下」、「不動」、「趴下」、「握手」和「換手」、「上來」(下這命令的同時要拍拍沙發,示意牠可以這麼做)以及「要不要出去?」
在我們新婚的那段日子,蕾西還教會牠這個指令:「保羅呢?去找保羅。」星期六我往往會睡得很晚,有時蕾西懶得叫我,而我一睜開眼睛看見的就是蘿麗的臉,發現牠的前爪已搭上床沿,正用那雙大眼睛凝視著我。奇怪的是,我永遠也沒辦法報復,無法教會蘿麗聽懂「去找蕾西」這個指令。當我說「去找球」或「去找小鹿」(小鹿是指牠最喜歡的長頸鹿玩具,因為細長的頸子很適合玩拔河遊戲)之時,牠總是活蹦亂跳地馬上回應,但牠永遠也聽不懂「去找蕾西」這個命令。牠是不知道蕾西的名字嗎?或是根本清楚得很,只是拒絕服從,不想破壞屬於牠和蕾西(牠的第一位飼主和最愛的人)所共有的這個把戲?
我統計了一下,蘿麗大約知道十五個不同字眼的意義。吃飯、散步、很好和不乖……數量相當於人類嬰兒在十三個月大時所能認識的字眼。不過這種比較並沒什麼幫助,因為嬰兒只要到了十六個月大,他們知道的字眼就會膨脹兩、三倍,而且還能開始說出「媽媽果汁」或「車車嘟嘟」之類不完全的句子。對狗來說,牠們一旦學會辨別這一長串指令後,這一生中就僅能或多或少維持在這個數量了。而且,就表面上來看,狗並沒辦法像人類一樣,具有把單字連接起來組成句子的能力。
然而,讓我感興趣的是嬰兒時期的語言發展,他們對語言的理解早在能使用語言之前就已開始了——在一歲到三歲之間,嬰孩認識的字眼大約超出他們可說出的五倍。是什麼機制讓十三個月大的嬰孩發生如此大的變化,從理解躍進到使用?我相信,這個疑惑將是我整個研究計畫的最核心問題。
蘿麗強過人類嬰孩的地方,在於牠具有敏銳的感知力,能掌握一些我們人類所無法查覺的非語言上的線索。即使隔著兩個房間,牠仍能聽見繫鞋帶的聲音而立刻起身,知道這聲音代表有人可能正準備出門,而且說不定牠可以跟著一起出去。牠能辨別銀製餐具在抽屜裡發出的噹啷聲,以及有人坐在沙發上看報紙時的聲響。當蕾西站在浴室鏡子前化妝,而牠嗅到這個動作所產生的特殊複雜氣味(也許是化妝粉刷的刷毛味,結合粉底香味及睫毛膏濃濃的顏料味),牠便明白這味道的含意。此時牠會從不知哪個地方鑽出來,站在浴室門口,在發現浴室的房門微微敞開後,便把鼻子伸進門縫,耐心等待自己是否會被邀請參加蕾西即將從事的任何冒險。
我繼續對蘿麗進行初步的智能測驗。我拿了一塊狗餅乾給牠看,再用杯子把餅乾蓋住。她嗅了一下杯子,旋即把杯子撥倒取得狗餅乾,整個過程只讓我的馬錶跑了六秒。這個成績相當優秀,證明牠具有極佳的解決問題的能力。接下來,我再測驗牠的記憶力,先拿了一塊狗乾餅在牠注視下藏在客廳角落,然後把牠帶到另一個房間待上五分鐘。當我們再度回到客廳時,牠便直接撲向藏有餅乾的那個角落。這讓我開心極了。
我在進行第三種測試時,又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這項測驗是以毛巾蓋住牠的頭,然後計算牠需要多久時間才能把毛巾甩開。此為另一種類型的解決問題測試,而我滿心以為蘿麗會以優異的成績過關。然而,當我把毛巾蓋上去後,牠竟然不想反抗,除了腦袋因承受了毛巾的重量而微微低下外,身體一動也不動。我等了足足一分鐘,又再等了一分十五秒,牠卻沒有擺脫毛巾的打算。看著牠弓著身體頂著厚厚的綠色毛巾站在那兒,使我聯想到一名頭戴面紗的寡婦,不禁讓人突然覺得有點難過。於是,我決定替牠把頭上的毛巾拿下,可正要這麼做時電話鈴聲卻響了。我先去接了電話,而當我掛斷電話轉頭過來時(這是一通打錯的電話,我和對方通話的時間不超過五秒),蘿麗不知何時已把毛巾甩開,早已好端端坐在那裡看著我了。我這才想到,牠在我注視牠的時候之所以一動也不動,是因為不知道我的意圖,說不定牠還以為我希望牠頂著毛巾安安靜靜地站著。這項測驗是今天所做的遊戲中最奇怪的,而光憑這第一次接觸,牠當然搞不清楚遊戲的規則。
突然間,我覺得好累,覺得我們兩個都受夠了。我蹲下來,張臂抱住這隻大狗。「好了,妹妹,」我溫柔地說:「我們去散個步吧。」
1目前為止,我所知道的事就只有這樣——十月二十四日的那個下午,我的妻子蕾西.藍森從後院的蘋果樹上墜落而死,當時現場除了我們養的狗蘿麗之外,沒有任何目擊者。那天不是周末,鄰居們都不在家,沒人把窗戶打開坐在廚房裡,因此當我的妻子從高處墜下時,沒人知道她是否驚聲尖叫、是否哀鳴,或根本沒發出半點聲音。那天不是假日,鄰居們沒人利用晚秋的好天氣在院子裡整理花園,因此當她落下時,沒人看見半空中的她是縮成一團、是展開身體,或只是張開雙臂迎向遼闊的天空。意外發生時,我正在大學的圖書館裡準備研討會的論文,那天傍晚還有...


 2015/04/30
2015/04/30 2015/01/29
2015/01/29 2009/02/08
2009/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