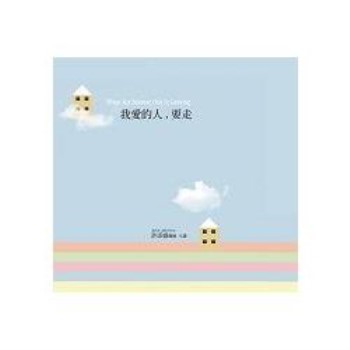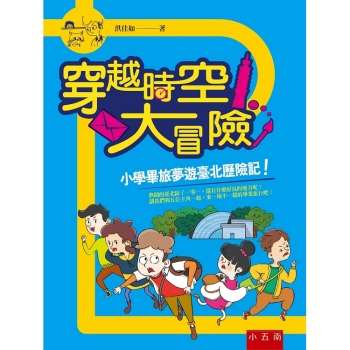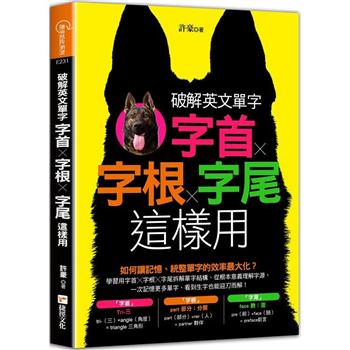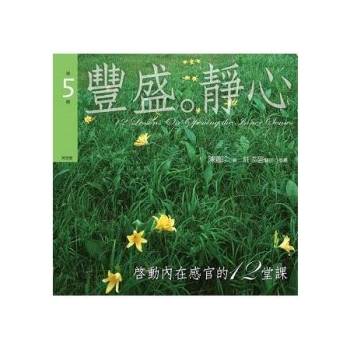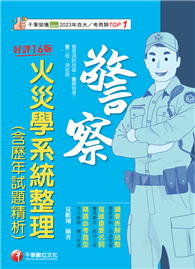導 言
在這部著作,如果我的目的是提出一套指導人生的完整文獻,我就得重複無數的雋語箴言(其中有一些絕妙),那些由各時代的思想家,從西奧格尼斯和所羅門到拉勞士福古,所留下的心血;我要是那麼做,不可避免地會讓讀者面對大量的陳腔濫調。事實是,在徹底探討主題上,我甚至不敢說這部著作能與其他拙著相比。
著者既然未敢說對題目有詳細交代,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也得放棄有系統地安排題材。對於這樣的雙重損失,讀者可以告慰的是,在指導人生這一題目上,如果要求予以詳盡而有系統的處理,整個作品幾乎一定會淪為無趣乏味。我只是寫出我的思想中值得寫出的 一些據我所知還沒有別人說過,無論如何,別人還沒有用完全同樣形式表達的思想;我的討論可以認為對這一廣大的領域所已獲得的成就,有所補充。
在本書中,我所談論的「人世智慧」,只是這個詞語的一般意義,那就是講求如何整理我們的生活,讓我們獲得最大可能的快樂和成功;探求這一方面之藝術的理論可以稱為「幸福學」,因為它教導我們如何度過一個快樂的人生。這樣的人生,如果完全從客觀的觀點來看,或者說,經過我們冷靜和成熟的思考之後(本問題不可能不涉及主觀的考慮),可以認定為絕對是勝於「無此一生」。這就是說,我們應該為了存活而存活,並不只是因為怕死;還有就是,我們應該樂於見到此生永遠繼續。
就我記憶所及,有一本著作跟本書的目的相同,而且對本書所論各篇富有啟發的,是卡丹的《談苦難的用途》,非常值得一讀,可以補助本著有所不足之處。不錯,亞里士多德在《修辭學》卷1第5章有幾句談到「幸福論」的話;但是他的討論並不深入。編書不是我的特長,前人的著作對我的用處不大;更重要的是,編輯的過程會把觀點的獨特性喪失,而觀點的獨特性是這類著作的靈魂。一般說來,各時代的賢者所說的話大體相同,愚者則亙古以來總是佔大多數,他們我行我素,所作所為相似,無不反其道而行;那些蠢事會繼續下去。正如伏爾泰說的,「我們來到地球時所見到的愚蠢和邪惡,在我們離開之際仍然是老模樣。」
第一章 基本的劃分
亞里士多德(見所著《尼可馬氏倫理》I.8)將人生的福分劃分成三類,那就是得自外界的福分,得自心靈的福分,以及得自肉體的福分。我不計較前面這種劃分的內容,只想保留它的數字;據我觀察,人的命運的根本不同點,可以歸結為三類﹕
一. 人的自身:換言之,就是從人格 (personality) 一詞的最廣泛意義而言;其中包括健康,精力,美,脾氣,品性,才智和教養。
二. 人的所有:就是指財產和其他各種可能佔有的一切。
三. 人的地位: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人把你看成什麼,或更嚴格地說,他人是根據什麼看待你。這可以從別人對你的看法表露出來,而別人對你的看法,又從你所獲得的榮譽、階級和名聲中明白地顯示。
上面第一類的差異是「大自然」賜給各人的;就從這一事實,我們立刻可以推斷出,這些區別對各人的幸福與否所造成的影響,比之後兩類要重大和深刻,後兩類只是人間安排的結果。得自地位或出身、甚至包括王室所帶來的種種特權,跟「真正優異品質」,例如偉大心靈或偉大心胸相比,只不過是舞台上的國王,見到真實人生中的國王。很久以前,希臘哲學家伊匹鳩魯(Epicurus)最早的弟子麥闕多魯斯(Metrodorus),作為他的著作的一個篇章的題目,說過同樣的話:「從我們內心得來的快樂,遠超過自外界得來的快樂」(比較克雷孟著《基質》,Ⅱ,21)。個人幸福的主要因素,還有我們生存的整個模式,都取決於我們內在的品質,也就是在乎我們是如何構成的;這是明顯的事實,無可置疑。人的心靈對於一己的感性、欲望和思想所獲致的總效果,是否覺得滿足,跟他的本質具有直接關係;在另一方面,外界只不過是對我們產生一種間接的影響罷了。這就是為什麼同樣的外在事件或環境,對任何兩個人的影響都不同;甚至在完全相似的環境,每個人都生活在各自不同的天地。一個人能直接領悟的,只是他自己的觀念、感情和願望。外在世界對他的影響,只是它促使他產生那些觀念、感情和願望。我們所處的世界是怎樣,主要在於我們以什麼方式來看它,所以不同的人得出不同的世界;有人認為它荒蕪、枯燥和膚淺,有人覺得它豐富、有趣而充滿意義。聽到別人在人生中所經歷頗富興味的事,各人也都想經歷相似的事件,完全忘記那些事件之所以具有意義,是在人家訴說時,他具有那種令人羨慕的性向所致。對於天才來說,某些事情是有趣的冒險;但對於普通人的平凡想像,不過是一般的日常事件。在最為極端的程度上,可以拿歌德 (Goethe) 和拜倫 (Byron) 的詩為例子,他們的詩很多是明顯的來自實事;愚癡的讀者可能會妒忌詩人,因為那麼多有趣的事發生在他們身上,而並未羨慕詩人莫大的想像力可以把極平凡的經驗變得那麼偉大和美麗。
同樣的,某一情景對樂觀的人看來只不過是一次可笑的衝突,憂鬱的人卻把它當做一幕悲劇,而恬淡的人會認為毫無意義。所有這些都依賴一個事實,那就是每一實際經驗的事件,都必須具有兩個因素,即主體和客體兩者的協同,猶如水中的氧和氫那麼緊密和必要地結合,才可望體認出來。所以,當某一經驗的客體或外在因素相同,但主體或個人對它的認知並不相同,該事件就好像是外在因素不同似的;對於遲鈍的人,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實際上微不足道——好像美好的景色在壞天氣中、或是照相機的暗箱不佳時,所顯露的情況。明白的說,每個人都受到自己意識的限定,我們無法直接地超越這些限定,正如人體受到皮囊的限定一樣;因此,外界的幫助對我們沒有多大用處。在舞台上,有人扮王侯,另一人做大臣,還有人是僕人,或是兵士,或是將軍,等等——都只是外表的不同;其內在的實質是一樣的 都是可憐的演員,都各有自己可焦慮的命運。在現實生活中也一樣。地位和財富不同,給予每個人不同的角色,但這並不意味我們內在的幸福和快樂會相對地有所不同;在這裏,我們的本質也都相同——可憐的凡人,生命充滿憂患困厄。雖然每一情況的原因不同,生命中各種憂患困厄在形式上都基本相同,只是程度不同,但無論如何跟每人所扮演的角色,或者地位和財富之有無,絕對不相對應。因為每一件事的存在或發生,只存在於有關人的意識之中,而且只是為意識而發生,因此,對於人最為關鍵性的事,是這一意識的素質,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意識素質的重要性,遠超過構成意識內涵的外在情況。世界上所有的驕傲和快樂,由笨人遲鈍的意識所見到的,跟塞凡提斯(Cervantes)在悲慘的監獄中撰寫《唐‧吉訶德》時的想像力相比,自然有天淵之別。生命和實在是客觀的一半,執於命運的手中,因之在不同的情形中所展現的形式就不同;主觀的一半是我們自身,它基本上是始終不變的。
因此,無論外在環境如何變化,每個人的生命自始至終都具有同一性格;每人的一生就像用同一主題所寫出的不同文章而已。沒有人能超出他自己的個性。一種動物不管被放在任何環境中,總是限定在上蒼所賦予它的狹窄的天性之中;所以,我們如果要使寵愛的動物快樂,必須依據那一寵物的天性,以及它所能感覺到的範圍之內,著手努力。人也一樣;我們所能獲得的快樂,事先就由我們的個性決定了。人的心智能力的情況更是這樣,它決定了我們是否有能力覓取精神價值更為高級的享受。心智能力如果不高,任何外在的努力,不管別人或是幸運多麼肯幫助,都不足以讓我們超越普通人所可得的幸福和快樂。心智不高的人,其快樂的唯一來源是他的感官欲望,他要低級伴侶,粗俗的消遣——充其量想過一種舒適而愉快的家居生活;就整體來說,教育對這類的凡夫俗子可幫的忙不多,大不了擴大他們的一些眼界罷了。不管「青春」會如何欺騙我們,最高尚、最有變化、最能持久的快樂得自心靈;心靈的快樂又依賴我們的心智能力。很明顯的,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的幸福視乎我們的本質和個性,而所謂命運一般是指我們的財富和名聲之類。就這一點來說,我們的命運是可能改善的;但如果我們內心富足,就不必多所外求了:另一方面,笨人終其一生仍然是笨人,他還是笨頭笨腦,儘管他被天堂的美女包圍著。因此,歌德在《西東詩集》(Westostlicher Diwan) 這麼說:
貴賤高下各式人等
無不說明,
世人的至高幸運
只在於性格。
一般的經驗指出,生命中的主體因素,對於我們的幸福和快樂而言,其重要性遠遠超過客體因素,這從「飢不擇食」、老年對青春女神無動於衷,以及天才和聖賢的生活可以看出來。在各種福分之中,健康又比所有其他的福分來得重要,我們真的敢說,體健力壯的乞丐比之惡疾纏身的君王要快樂得多。一種沈靜而愉快的性情,對享有充分健全的體格感到欣喜,智力清明活潑,洞徹事理,意欲溫文,從而心地善良 —— 這些都不是地位和財富所能作成或取代的。因為我們的內在本質,獨處時陪伴自己的「又我」,以及他人無法給予或是取走的自身,拿來跟我們所能擁有的一般財物、甚或世人如何看待我們相比較,很明顯的更為基本和重要。一個具有高度智慧的人在完全孤獨的時候沈浸於一己的思想和遐念之中,其樂也融融,但社交、戲院、外遊、各種娛樂,無論是多少,怎麼有變化,總不能讓愚人免於煩悶。個性溫文和善的人在困苦環境中能得快樂,而貪婪、妒忌、心地惡毒的人,縱然是富甲天下,仍然是生活愁苦的。世人所追逐的那些歡樂,對於一個具有高度智慧、享盡自己獨特個性的人,完全是多餘的;我們甚至可說是麻煩和負擔。賀瑞斯(《書函集》,II.2.180)談到他自己:
象牙,雲石,飾物,雕像,圖畫,
銀盤,染有葛杜紫的衣袍,
許多人無緣,有些人不理。1
蘇格拉底看到各種奢侈貨品攤開出售,大聲說道:世界上有多少東西是我不需要的啊。
因此,人生幸福的最首要的因素是我們自身——我們的品質和性格,「自身」是在所有情況中都在那裏發生作用的一個因素。此外,它跟其他兩類所指的福祉不同,它不由命運任意操縱,不會從我們手中奪走,這類福祉有絕對價值,其他兩類的價值是相對的。這一認識的結果是,我們從外在掌握一個人,比大家所設想的要困難。但是,全能的「時間」在這裏將會提出它的權利,在它的影響下,人們在體力和智力上的優勢,會慢慢地衰退,只有品性不受時間的影響。由於遭受時間的破壞所致,第一類的福祉倒不如另兩類,後兩類是時間無法直接從我們手中奪去的。另兩類的其他好處是,因為它們是客觀的和外來的,所以是可以獲取的,也就是每個人都有可能獲得;主觀的福祉不然,它是「天命」,跟我們一生不可分割,是命中注定的。歌德就這樣無情地指出:
你來到世上的那天
太陽接受行星敬禮,
你立刻而且永遠地須按照
你來到世間的規律才得成長。
無可選擇,你逃不開自己,
男女預言家們都這麼說過;
時間和權力都無從變動
在此蓋過印的生命體的發展。
我們力量所及唯一能做到的事,就是盡力發揮我們個人的品質,讓我們從事的事業,能夠用上我們的才智,在能力範圍內,做到極致,避免其他的紛擾;因此,我們就得選擇最適合我們發展的職位、行業和生活方式。
試想,一個孔武有力的人為環境所迫,例如去從事伏案的工作,或是做需要精細手藝的行業,或是做研究、需要用腦力的事,被迫不用他具有的過人的長處;處於這種情況的人,終生都不會快樂的。更為悲慘的命運是,有人具有極高的智力,被迫未得發展或不讓使用,而去做他體力可能不濟的勞動。儘管如此,遇到這種情形,我們得要小心,特別是在年輕時,避免胡亂臆斷,認為自己具有某種並不存在的特異能力。
因為前面所述的第一類的福分,大大的超過其他兩類,很明顯的,比較明智的途徑是致力於維護健康,培養能力,而不是全力賺錢;但是,這一定不可誤解為我們可以疏忽賺取足夠維持生活的錢財。嚴格的說,過多的財富對我們的幸福幫助不大;許多富人之所以不快樂,就是因為他們沒有任何真正的教化和知識,因此就不具有客觀興趣,讓他們夠資格參與智能活動。具有財富能滿足某些真正的和自然的需要,除此之外,它其實對我們的幸福所起的作用有限;的確,還可能有礙幸福,因為維持財富,必然會導致不可避免的憂慮。儘管我們敢說,人的品質比人的財富,更有助於他的幸福,然而,人對發財的打算,比之吸取教化,其專心程度何止千倍。你會看到許多人,從早到晚像螞蟻一樣忙碌不堪,為的是增加財富。除了賺錢的方法之外,他什麼都不懂;他的心靈是一片空白,因而不能接受其他的影響。理性的最高級的享受,跟他無緣,他無奈就只好沈迷於聲色犬馬中,任意揮霍,求得片刻的感官享受。如果他幸運,他奮鬥的結果會真的發一筆大財,可錢財始終得留給後人,後人或是把它滾成更大一筆,或是揮霍精光。這樣的一生,縱然看來度過得有聲有色,煞有介事,實際上和其他蠢人一樣,愚昧地浪費了。
這就可以說,「人的自身」對於各人的幸福是最主要的因素。所以一般而言,享有幸福的人並不多,因為大部分不必為生活發愁的人,跟那些終日為衣食奔走的人一樣,畢竟同樣感到不快樂。他們的心靈空虛,想像力遲鈍,精神委靡,最後是物以類聚2,他們就跟同類的人為伍,於是大家一起消遣,追求歡樂,主要就是恣情縱欲,放浪形骸。富家子弟擁有一大筆錢,常常是短期內極度浪費地揮霍一空,為什麼?其原因還是相同,根本是心靈空虛,對生存感到厭倦。他來到這世界,外表富有,內心貧乏,他盡力要用外在的財富,企圖從外界所得到的一切,去彌補內心的貧窮,就像一些老人想藉少女的汗水增強自己一樣。到頭來,內心貧窮的人,外在也同樣貧窮。
其他兩類福分對於人生的重要性,無須我在此多說;如今,利和名的價值,人盡皆知,無須宣揚。的確,跟第二類相比,第三類似乎是縹緲的,因為名聲只是由他人的看法而構成。可是,大家都追求名聲,要有好名譽。在另一方面,勛位應該限於獻身公務的人才可獲得,大名望只有極少數人可以得到。無論如何,名聲是無價之寶,大名望是所有福分之中人們可能到手的最高級珍品;另一方面,只有笨人才寧要勛位不要財產。此外,第二類和第三類是因果交替的,有財產就有名聲,反之,任何好名譽都會不時幫助我們取得所需,正好應驗了古羅馬人彼特羅紐斯(Petronius)氏的一句格言,「人的價值在於他所擁有」(habes,habeberis3)。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叔本華《雋語與箴言》(中英對照)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6 |
二手中文書 |
$ 228 |
中文書 |
$ 229 |
西方哲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叔本華《雋語與箴言》(中英對照)
【本書特點】
★梁實秋說:「《雋語與箴言》是影響我生平最深遠的一本書。」
文學大師梁實秋、心理及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依德、文豪托爾斯泰、音樂家華格納等曠世巨匠,曾表示其生平深受叔本華的啟迪。尼采說:「叔本華讓我有勇氣並自由的面對人生。」
本書擷取叔本華譽滿天下的著作《處世智慧錄》中影響世人最深遠、最精采的<思辨與箴言>部分,採中英對照方式,是能幫助我們進入叔本華思想的哲學著作,更是兼習英文的最佳工具書。
叔本華融合東西哲學主流、從勸勉世人和實用觀點著手,科學地披露人性和世故,復以睿智和生動的筆觸,娓娓道來如何求取幸福和成功,以其充分發揮此生。
作者簡介:
叔本華 Arthur Schopenhauer 1788年02月22日~1860年09月21日/歐洲
叔本華,19世紀德國哲學家,思想影響深遠,其中尤以尼采所受影響最為突出。尼采說:「叔本華讓我有勇氣並自由的面對人生。」文學大師梁實秋、心理及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依德、文豪托爾斯泰、音樂家華格納等曠世巨匠,都曾表示其生平深受叔本華的啟迪。
譯者簡介:
胡百華 台灣
胡百華,六十年代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主修英語教學)和英語研究所(主研英國文學),留原校執教,曾參與名著翻譯(如杜蘭著《哲學的趣味》),稍後轉往美國夏威夷大學和澳洲Monash大學攻讀語言學,並在該校開辦中文課程,致力發展亞洲語言與研究學系。九十年代初至香港嶺南大學任教,繼在城市大學專事語言資訊研究,現為香港一個語文專業雜誌的編輯。
章節試閱
導 言
在這部著作,如果我的目的是提出一套指導人生的完整文獻,我就得重複無數的雋語箴言(其中有一些絕妙),那些由各時代的思想家,從西奧格尼斯和所羅門到拉勞士福古,所留下的心血;我要是那麼做,不可避免地會讓讀者面對大量的陳腔濫調。事實是,在徹底探討主題上,我甚至不敢說這部著作能與其他拙著相比。
著者既然未敢說對題目有詳細交代,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也得放棄有系統地安排題材。對於這樣的雙重損失,讀者可以告慰的是,在指導人生這一題目上,如果要求予以詳盡而有系統的處理,整個作品幾乎一定會淪為無趣乏味。我只是...
在這部著作,如果我的目的是提出一套指導人生的完整文獻,我就得重複無數的雋語箴言(其中有一些絕妙),那些由各時代的思想家,從西奧格尼斯和所羅門到拉勞士福古,所留下的心血;我要是那麼做,不可避免地會讓讀者面對大量的陳腔濫調。事實是,在徹底探討主題上,我甚至不敢說這部著作能與其他拙著相比。
著者既然未敢說對題目有詳細交代,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也得放棄有系統地安排題材。對於這樣的雙重損失,讀者可以告慰的是,在指導人生這一題目上,如果要求予以詳盡而有系統的處理,整個作品幾乎一定會淪為無趣乏味。我只是...
»看全部
目錄
CONTENTS 目 錄
Foreword 英華本前言胡百華
Introduction (Einleitung) 導言
Ⅰ. Fundamental Division(Grundeintheilung)
基本的劃分
Ⅱ. General Views(Allgemeine)
總的看法
Ⅲ.Our Attitude to Ourselves
(Unser Verhalten gegenuns selbst betreffend)
處己之道
Ⅳ.Our Attitude to Others
(Unser Verhalten gegen Andere betreffend)
處人之道
Ⅴ.Our Attitude to the Ways of the World and to Fate
(Unser Verhalten gegen den Weltlauf und das Echicksal betreffend)
如何對待世道和...
Foreword 英華本前言胡百華
Introduction (Einleitung) 導言
Ⅰ. Fundamental Division(Grundeintheilung)
基本的劃分
Ⅱ. General Views(Allgemeine)
總的看法
Ⅲ.Our Attitude to Ourselves
(Unser Verhalten gegenuns selbst betreffend)
處己之道
Ⅳ.Our Attitude to Others
(Unser Verhalten gegen Andere betreffend)
處人之道
Ⅴ.Our Attitude to the Ways of the World and to Fate
(Unser Verhalten gegen den Weltlauf und das Echicksal betreffend)
如何對待世道和...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叔本華 譯者: 胡百華
- 出版社: 健行 出版日期:2004-04-10 ISBN/ISSN:9867753321
- 類別: 中文書> 哲學宗教> 西方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