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大學英語系講師、作家、文評家伍軒宏專文導讀。
加拿大國寶級女作家瑪格麗特‧愛特伍在台最新作品。
作家蔡素芬、女書店創辦人鄭至慧、交通大學外文系教授馮品佳、淡江大學英文系系主任黃逸民、新竹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系主任孫德宜、輔大英文系副教授劉紀雯好評推薦。
胖的、瘦的是我;美的、醜的也是我;
善良的、邪惡的是我;愛你的、恨你的也是我;
天使、惡魔也通通都是我……
為了這些藏在我心中,無法對任何人說出口的祕密,
成就了我那永無止盡的背叛與逃亡……
這是我雙重生活的開端。但我不是始終過著雙重生活嗎?我那朦朧的雙胞胎在我肥胖時瘦削,在我瘦削時肥胖,就像是銀色底片上的我,黑色的牙齒,白色的瞳仁在另一個世界的黑色陽光下閃閃發亮,而我則袖手旁觀,禁錮在肉體中面對日常生活中無趣的灰塵和永遠沒有清空的菸灰缸。那是我那個莽撞雙胞胎想要的夢幻國度。其實也不能叫雙胞胎,因為我不止兩個,我是三胞胎,多胞胎,而現在我看見不止一個新生活的到來,而是許多個新生。
從胖到瘦,從紅髮到泥褐色髮,從倫敦到多倫多……羅曼史小說家瓊,終其一生都在逃避。
小時候因為體重過重,不斷被母親批評,從此她便以暴食抗議,「胖」這個字如影隨形。
為了得到姑姑的遺產,遺囑中規定瓊必須減肥一百磅。變瘦後,拿到遺產,也決定離家重新做人,並虛構她的過往。
瓊到了倫敦不久後,邂逅波蘭伯爵,成為他的情婦,並發現自己的文采,開始以姑姑的名字為筆名,寫作羅曼史。
後來她與政治狂熱份子亞瑟結婚,但是卻瞞著羅曼史小說作家的身分,後又與藝術家「皇家刺蝟」發展地下情。她寫作遇到瓶頸,使用通靈者的自動書寫方式結集的新詩集《女祭司》意外成為暢銷書,因此一舉成名。
瓊一生都在為生活中的多重身份所苦,她接獲黑函,要揭穿她肥胖的過往。瓊決定在義大利山城開始新的人生。但首先,她必須安排自己的死亡……
作者簡介:
瑪格麗特‧愛特伍 Margaret Atwood
1939年11月18日/ 美洲
1939年出生於加拿大渥太華。高中時即展現文采,在校刊發表散文及詩作,後就讀多倫多大學維多利亞學院,並繼續於拉德克利夫學院攻讀維多利亞時期英國文學,獲碩士學位。
1966年自從她的第二本詩集《圈戲》(The Circle Game)出版後,愛特伍在加拿大文學界嶄露頭角。而她的小說創作更是引人入勝,寫作風格獨特,大量採用意識流和寓言式寫作技巧,女性主義色彩濃郁。
獲獎紀錄無數,1996年以《雙面葛蕾斯》獲加拿大文學吉勒大獎;2000年8月《盲眼刺客》甫出版,便得到英國布克圖書獎;2008年更榮獲西班牙阿斯圖里亞斯王子獎。
作品有《盲眼刺客》、《使女的故事》、《末世男女》、《雙面葛蕾斯》、《當半個神不容易——愛特伍隨想手札》、《女祭司》等,共出版作品四十餘種,在世界三十五國出版,是最被看好的諾貝爾獎候選人。目前擔任國際筆會副會長,並與夫婿作家格姆‧吉伯森(Graeme Gibson)同為世界鳥盟「稀有鳥類俱樂部」榮譽主席。
譯者簡介:
謝佳真,學的是理智精明的財金、國貿。從事貿易工作一年有餘,後因閱讀的世界太美好,索性棄商從文,決定當個信達雅兼具的翻譯小工。
章節試閱
第24章
這是我雙重生活的開端。但我不是始終過著雙重生活嗎?我那如影隨形的雙胞胎在我肥胖時瘦削,在我瘦削時肥胖,就像是銀色底片上的我,黑色的牙齒,白色的瞳仁在另一個世界的黑色陽光下閃閃發亮,而我則袖手旁觀,禁錮在肉體中面對日常生活中無趣的灰塵和永遠沒有清空的菸灰缸。那是我那個莽撞雙胞胎想要的夢幻國度。其實不止雙重人生,我有三重,多重,而現在我看見不止一個新的人生到來,而是許多個。皇家刺蝟打開了第五象限的時空之門,那扇門高明地偽裝成一個貨運電梯,其中一個我便魯莽地衝出來。
但其他的我沒有出來。「我什麼時候可以再見到妳?」他問。
「不久之後。」我說:「但別打電話找我,我會打給你,好嗎?」
「我又不是應徵工作。」他說。
「我知道。請諒解。」我給他一個晚安之吻,覺得不能再和他見面。那太危險了。
回到公寓時,亞瑟不在,但已經將近十二點。我倒在床上,頭埋到枕頭下開始哭泣,覺得自己再次摧毀了人生。我會悔改,我會展開新頁,我會按捺著不打電話給皇家刺蝟。我要如何彌補亞瑟?或許我能為他一個人寫一本哥德式羅曼史,將他的想法改寫成一般人能理解的說法。我知道沒人閱讀《復甦》,會讀的人只有編輯、一些大學教授,以及所有自己辦雜誌的激進團體,這些競爭對手每一期刊物都耗費三分之一的篇幅彼此攻詰。但會看我作品的讀者至少十萬人,其中不乏國內的母親們。我要將書名取為《卡薩羅馬城堡玝驚魂》,我會提到家族盟約瓝的邪惡、路易斯‧雷爾瓨的殉難、英美兩國殖民主義的恐怖、勞工的掙扎、溫尼伯大罷工甿……
但這絕對行不通。若要讓亞瑟明白我的用心,便必須透露露薏莎‧K的身分,而我清楚不能這麼做。無論我怎麼做,亞瑟必然會鄙視我。我永遠不會是他希望的模樣。我永遠不會是瑪蓮。
凌晨兩點時,亞瑟才回來。
「你去哪裡了?」我帶著鼻音問。
「我在瑪蓮家。」亞瑟說。我的心往下沉。他去尋求慰藉,而……
「唐恩也在嗎?」我低聲問。
原來瑪蓮向唐恩說出山姆的事,唐恩便揍了瑪蓮眼睛一拳。瑪蓮召來了《復甦》的全部編輯,包括山姆。他們齊聚在瑪蓮家,熱烈討論唐恩動粗是否師出有名。認為無妨的人主張勞工常常毆打太太的眼睛,揮拳頭只是坦率無隱地表達自己的感覺。反對者則說那貶低了女性。瑪蓮宣告她要搬走,山姆說她不能住進他家,於是引發另一場論戰。有些人說他拒不讓瑪蓮搬入很可惡,其他人認為如果他不是真心想和瑪蓮在一起,他就有權拒絕。討論到一半時,稍早去葛羅斯曼酒館買醉的唐恩回來,要他們統統滾出他家。
我暗自高興有這番騷亂。亞瑟再也不能將瑪蓮視為楷模,連帶減輕我的壓力。
「那瑪蓮呢?」我佯裝關心。「她還好嗎?」
「她在我們門口外面的樓梯上。」亞瑟沉重地說:「我覺得應該先問妳一聲。我不能把她留在那裡,至少在唐恩那個樣子的時候不行。」
他完全沒有提起電視採訪,對此我心存感激。或許他沒有看到節目,否則必然會大感羞辱。希望不會有人告訴他內容。
瑪蓮在大沙發過了一夜,又一夜,再一夜,顯然已經搬進我們家。我無能為力,因為她不正是落難女子嗎?她不正是政治難民嗎?那是她對自己處境的看法,也是亞瑟的看法。
在那段期間,她用電話與唐恩協商,奇怪的是她也用電話和山姆協商。不打電話的時候,她會坐在我的廚房桌前不斷抽菸,喝我的咖啡,問我她該如何是好。她不再乾淨俐落;她有黑眼圈,她的髮絲一綹一綹,她將指甲啃得參差不齊。她應該繼續和山姆交往嗎?她應該回到唐恩身邊嗎?目前小孩在唐恩手上。一待她找到住處,她便會帶走孩子,即使打官司也在所不惜。
我按捺著不問她打算何時去找住處。「我不知道耶。」我說:「妳愛的是哪一個?」我心想,我的口吻正如同我哥德式羅曼史中的友善管家,但我還能說什麼?
「愛情。」瑪蓮嗤之以鼻。「愛情無關緊要,要緊的是他們誰配得上真正平等的男女關係。要緊的是誰最不會剝削對方。」
「這樣啊,」我說:「我的直覺反應是山姆。」他是我的朋友,唐恩不是,因此我是在為山姆出力。話說回來,我對瑪蓮仍然沒有多少好感,為何要希望她和我的朋友在一起?「但我相信唐恩也是很好的人。」我補上一句。
「山姆是豬玀。」瑪蓮說。女性主義剛出現時,被瑪蓮唾棄為中產階級;現在她改弦易轍了。「只有親身的體驗,才能真正打開眼界。」她如此告訴我。她不斷暗示我承受的苦難不夠多,而那也是我的缺陷。我明白我不該有自我辯護的念頭,卻撇不下那種感覺。
當瑪蓮去拜訪山姆,唐恩會過來問我意見。「也許你應該搬到其他城市。」我說。那會是我的作法。
「那是逃離問題。」唐恩說:「她是我太太。我要她回到我身邊。」
當瑪蓮在傍晚去看小孩,山姆會過來,我會為他備酒。「天啊,我要瘋了。」他會如此說。「我愛她,我只是不想和她一直在同一個屋簷下。我告訴她,我們可以共度重要的時間、要緊的時間,兩人各有各的住處會好得多。再說,我看不出我們為何不能和其他人談感情,只要我們都以這一段感情為主就是了,但她不能明白這一點。我是說,我不是會吃醋的人。」
他們就這樣來來去去,我開始覺得我住在火車站內。亞瑟難得在家,因為瑪蓮和唐恩雙雙辭去《復甦》的職務,而亞瑟試圖維持雜誌社的運作。心煩意亂的瑪蓮幫不了我烹飪和清掃,她對我生活中的其他層面更是毫無助益。我愈來愈常讓皇家刺蝟進入我的白日夢。我仍未聯絡過他,但我知道自己隨時會打電話給他。我在報紙翻找SQUAWSHT的藝評,在星期六的娛樂副刊找到一則:「對這個時代的坦率、尖刻評論。」
「妳想不想去看藝術展覽?」我問瑪蓮。展覽仍未結束,去那裡一趟無傷大雅。
「去看虛偽的資產階級狗屁?」她說:「免了吧。」
「哦,妳看過展覽了?」我問。
「沒有,但我看過藝評,一看就知道是那種東西。」
此時,我也要為文學事業煩心。電視採訪後的第二天,便開始有人打電話給我。他們多數是相信我說法的人,想了解如何聯絡另一個世界。不過也有一些人認為我取笑主持人,或是身為唯靈教派信徒,或兩者兼而有之,因此打電話指摘我。有些人認為我能預言未來,要我為他們算命。目前沒有人向我要愛情靈藥或治疣祕方,但那應該只是遲早的事。
除了電話,我也收到出版社轉來的信件。寫信的人多半是請求協助出書。起初我盡力回信,但我旋即發現他們並不希望幻想破滅。當我解釋我在出版界沒有人脈,他們很憤慨我使不上力,令我滿心罪惡感,覺得自己辜負了他們的期望。因此,一段時間後,我開始只看信,不予回覆;又一段時間後,便不再拆信閱讀。之後,開始有人登門質問我為何沒有回信給他們。
報上每星期都有新文章,標題諸如:「《女祭司》的暢銷」和「《女祭司》:騙局或幻覺?」而由於第一場一塌塗地的電視採訪上了報(作者宣稱作品出於靈界的指引),史特吉斯安排的其他採訪者便緊咬這個主題。即使我說不願多談也無濟於事,那只令他們更加好奇。
「聽說《女祭司》是天使寫的,有點類似《摩門經》。」他們會如此說。
「也不盡然。」我會如此回答,然後試圖轉移話題,暗禱亞瑟不會收看節目。有時,他們當真興趣濃厚,而那更加糟糕,因為他們問:「所以,妳認為死亡後仍然有另一種生命形式?」
「我不知道,應該也沒人說得準,對吧?」
錄完節目後,我會打電話給史特吉斯,淚眼汪汪地求他取消下一場採訪。有時他會為我提振低落的自信:我很棒,我表現很好,銷售成績優異。有時他會一副傷心的模樣,說在我們簽約時,我們便了解我會上一定數量的節目,我難道都忘了嗎?
我覺得自己非常引人注目,但感覺像某人以我的名義在真實世界中扮演我,說著那些我不曾說過卻上了報紙的話語,而她的一舉一動要由我承擔後果:我的黑暗雙胞胎,我的哈哈鏡影像。她比我高,比我美,比我更能威嚇別人。她要殺掉我,取代我,等她取代我之後,不會有人察覺異狀,因為媒體也是共謀,他們在協助她。
事情不僅如此。如今我是公眾人物,我很害怕遲早會有人察覺我的真面目,循線追查到過去的我,揭發我。往昔關於胖女郎的白日夢回來了,只是這回她穿著粉紅色芭蕾舞裙走鋼索,失足摔落,慢動作地翻轉再翻轉,掉向地面……或者她會穿著薄紗服裝和紅鞋。但那不會是舞蹈表演,而是脫衣舞,她會在我的注視下褪去衣物,而我無力阻止她。她會擺動臀部,移除一層層的薄紗,但沒有人會吹口哨,沒有人會叫嚷把衣服脫掉,小妞。我試圖關掉這些失控的幻想,卻徒勞無功,只能一路看到結尾。
一天下午,山姆離開後,我坐在廚房桌前喝蘇格蘭威士忌。瑪蓮出去見一位律師;她將早餐用過的盤子留在桌上、一堆柳橙果皮和半碗泡了水的早餐米片。她的健康飲食習慣蕩然無存,我也是。我察覺自己神經兮兮,而且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我的家是一個遍佈別人垃圾的營地:實際的垃圾與情緒的垃圾。亞瑟從不在家,我也不怪他;我對他不忠,卻沒有勇氣告訴他,也不敢依照自己的心意再次出軌。阻擋我去找皇家刺蝟的並不是意志力,而是懦弱。我無能,我邋遢而空洞,我是一場騙局,一個幻覺。淚水滾下我的臉,滴到佈滿碎屑的桌面。
第24章
這是我雙重生活的開端。但我不是始終過著雙重生活嗎?我那如影隨形的雙胞胎在我肥胖時瘦削,在我瘦削時肥胖,就像是銀色底片上的我,黑色的牙齒,白色的瞳仁在另一個世界的黑色陽光下閃閃發亮,而我則袖手旁觀,禁錮在肉體中面對日常生活中無趣的灰塵和永遠沒有清空的菸灰缸。那是我那個莽撞雙胞胎想要的夢幻國度。其實不止雙重人生,我有三重,多重,而現在我看見不止一個新的人生到來,而是許多個。皇家刺蝟打開了第五象限的時空之門,那扇門高明地偽裝成一個貨運電梯,其中一個我便魯莽地衝出來。
但其他的我沒有出來。「我什...
推薦序
導讀:紅頭髮與綠蜥蜴/文學評論家 伍軒宏
這是小胖妹變身的故事。
母親管控、同學欺負、過重、孤獨,加拿大女孩瓊在挫折與不快樂中,度過童年與青少年。「瓊」之名,來自影星瓊.克勞馥,出於母親的期望,成了沉重負擔。她並非特別苦命,但體重問題使她得不到肯定,沒有自信,越來越退縮,幾乎完全失去自我。小胖妹如何甩掉肥肉?在二十世紀後半葉,體重問題是已開發國家女性的典型焦慮,肥胖、瘦身、厭食症、貪食症等一連串「身體政治」議題成為女性主義的論述焦點。本書在一九七六年出版,透過少女瓊「身材肥胖,卻幾乎隱形」的弔詭,早期愛特伍述說了一則北美地區女性成長的原型敘事。
這也是脫逃的故事。
身體是身分,女性對此感覺特別強烈。六○年代之後的母女關係張力,除了傳統的權力鬥爭外,也牽涉性別角色自我認定的世代差異。《女祭司》裡的瓊,反抗母親,抗拒母親要她減肥的要求,家裡就像戰場。此外,無論在舞蹈班、學校、社團,她都找不到自我,沒有自己的空間,沒有朋友。唯有姑姑對她好,愛她,跟她一起去看展覽,帶她去看電影《紅菱豔》。姑姑猝死後,遺囑留下轉折的契機,打開一扇門,帶來變化。一次激烈的母女衝突後,瓊終於體認到,不離開沒有未來。她逃家,逃離多倫多,逃離北美,逃到倫敦,甚至逃到陽台欄杆有綠色蜥蜴在曬太陽的義大利。
這是女性創造身分的故事。
她逃走,不止一次。逃到不同國家、城市,變換身材容貌,交往不同的情人,採用不同的名字,從事各種職業,創造多重身分,成為不同的人。隨著瓊的身體、身材、身分變化,讀者一定會注意到小說裡不斷浮現「鏡子」意象,映照出主角的多重自我。身分的創造是脫逃招數、生存策略,紅頭髮的瓊在不同形象間穿梭,尋找出路:「我希望能有不止一種人生」,「不止雙重人生,我有三重,多重,而現在我看見不止一個新的人生到來,而是許多個。」有趣的是,多重的自我片段不見得要統合起來:「假如我讓生活中各自獨立的部分合而為一(像鈾,像鈽,乍看毫不起眼,卻擁有致命的能量),必然會引發爆炸。」
這是很像羅曼史的故事,也是有關書寫的故事。
身分是分身。沒幾個人知道瓊是哥德式古裝羅曼史(Costume Gothics)寫手,連她丈夫都沒察覺。逃家後,流浪到倫敦,搭上號稱「波蘭伯爵」的男人之後,瓊寫起羅曼史來。一方面為了賺錢,另一方面,哥德小說的「志怪」屬性可以抒發隱藏內心的深層情慾。但是寫著寫著,哥德式羅曼史的奇情也慢慢滲入瓊的人生!從一開始,愛特伍就在《女祭司》裡以楷體字,穿插瓊所撰寫的羅曼史片段,跟主要情節交錯、平行。終於有一天,留著山羊鬍子,「穿著黑色長斗篷和鞋罩,手杖頭鑲嵌著金色金屬,帶著白手套」的奇男子「皇家刺蝟」,靜靜出現在身邊,進入主角的生命。
羅曼史一向被視為女性文類,哥德式羅曼史是其中怪力亂神的一支。傳統文學研究輕視羅曼史,只是消遣娛樂;左派理論認為羅曼史提供逃避、化解不滿、為體制服務、移轉社會動員的力量。一直到八○年代,茉樂斯基(Tania Modleski)與芮德薇(Janice Radway)出版女性主義觀點研究,認為女性讀者以兩手策略,「使用」羅曼史文類,主動為自己開拓出路,才有改觀。在一九七六年的《女祭司》裡,愛特伍安排瓊出入羅曼史寫作,與她丈夫亞瑟所代表的哲學、理論、大學、毛澤東、卡斯楚、政治改革、民族主義、社會運動等等「大」問題,形成「學術界 vs. 小女子」、「男性知識 vs. 女性小說」的強烈對比,並提出質疑。
透過祕密書寫羅曼史,瓊為自己建構另類空間。此祕密書寫主體,漸漸跟官方版本的「我」分庭抗禮。不同於安徒生童話〈美人魚〉和〈紅舞鞋〉(改編電影《紅菱豔》)的主角,瓊靈活運用她的分身:「我同時是兩個人,有兩套身分證明文件、兩個銀行帳戶、兩群不同的人各自相信我存在於世界上。我是瓊.福斯特,這點無庸置疑;別人叫我那個名字,我也有真實的文件可茲證明。但我也是露薏莎.K.德拉寇。」因此,從雙重到多重,「也是」的修辭貫穿整本小說。本書不乏羅曼史的語言、人物、風格、情節安排,讀起來頗有通俗劇的味道:《女祭司》是文學小說,「也是」羅曼史文類小說。
還有,這也是後現代小說。
為了拓展寫作題材,瓊偷偷進行無意識「自動書寫」,意外累積了一些文字,經編輯後以真名出版,大受好評。那是一本紀伯倫(《先知》作者)風格的詩文書,也叫《女祭司》,這是書中書、盒中盒的後設策略,點出文本與世界之間的交互指涉、循環遊戲、無限反射等關係,讓我們看到本體的不確定性。琳達.賀琪恩(Linda Hutcheon)論「加拿大後現代」時指出,本書中愛特伍刻意自我倣諷(parody),連結自己其他著作,加上眾多書中書互相穿梭,意在探索女性主體性。派翠西亞.沃(Patricia Waugh)討論愛特伍時說,在沒有內在、本質自我的情況下,掙脫權力束縛的方法,是運用偽裝、倣諷,凸顯身處的後現代情境。《女祭司》小說出版之際,「後現代」爭論方酣,也許這是閱讀此書的起點之一。
小說最後(我沒有把情節講出來),瓊說不想再寫哥德式羅曼史,要嘗試科幻小說。以後見之明,我們知道那會是愛特伍一九八五年名作《使女的故事》。故事裡的又跑到故事外了?但,那是另一則故事了。
*伍軒宏先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英美文學博士候選人,任教政大英文系。專長:文學理論、文化研究、德希達與解構、後殖民論述、英美小說、科幻小說與電影、性別敘事、黑道電影等。曾以〈阿貝,我要回去了〉獲第一屆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以〈殘念筆記〉獲第二屆林榮三文學獎散文獎。
導讀:紅頭髮與綠蜥蜴/文學評論家 伍軒宏
這是小胖妹變身的故事。
母親管控、同學欺負、過重、孤獨,加拿大女孩瓊在挫折與不快樂中,度過童年與青少年。「瓊」之名,來自影星瓊.克勞馥,出於母親的期望,成了沉重負擔。她並非特別苦命,但體重問題使她得不到肯定,沒有自信,越來越退縮,幾乎完全失去自我。小胖妹如何甩掉肥肉?在二十世紀後半葉,體重問題是已開發國家女性的典型焦慮,肥胖、瘦身、厭食症、貪食症等一連串「身體政治」議題成為女性主義的論述焦點。本書在一九七六年出版,透過少女瓊「身材肥胖,卻幾乎隱形」的弔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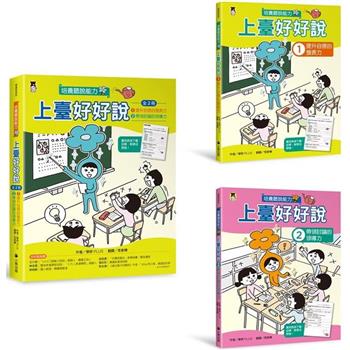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