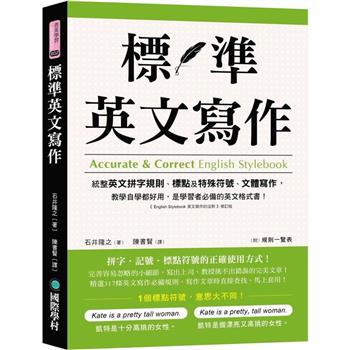在我們懂得之前,張小嫻早已說出了愛情的殘酷與可愛。
那個時候,我沒有想過,我是一個既想要麵包,也想要愛情的女人。
我常常覺得兩個人沒有可能永遠在一起,結合是例外,分開才是必然的。
我們都是為終會分開而熱烈相愛。
因為下雨天電台播出的一首歌,程韻愛上了林方文,從此為他流了一輩子的眼淚。
愛你?還是愛自己?我們都是程韻與林方文。
三個女孩,三種愛情觀,一同經歷成長的歡笑、初戀的迷惘、愛與恨、哀與痛。
麵包樹三部曲,是我們愛情的最初與最終。
愛情小說到了張小嫻,已登峰造極。
【本書特色】
◆ 華文愛情天后 張小嫻長篇小說出道作「麵包樹」系列,感動百萬讀者!
◆ 永恆的都會愛情經典,經典就像初戀,承載第一次的心跳,也沉澱往後的悲傷。
◆ 雋永經典,新裝上市,以精緻書衣包覆,呵護永難忘懷的初戀。
◆ 特別收錄張小嫻新版序:「麵包樹三部小說也是我用文字譜成的一首長歌,歌唱著燦爛的青春,為世間的相聚而唱,也為那樣纏繞執拗的愛情而歌。」
麵包樹的確存在,是產於亞、美兩洲的喬木,其果肉厚實,像生麵糰,烤過之後的味道像烤麵包。
故事中的三個好朋友程韻、朱迪之、沈光蕙各自尋找屬於自己的麵包樹。
麵包可能是物質,可能是虛榮,也可能並不真實。
他們在十三歲認識,友誼從排球隊開始,一同經歷成長的歡笑、初戀的迷惘、愛與恨、哀與痛。
女人做得最好也最失敗的事便是愛男人。
朱迪之說,如果她死了,她的輓歌便是一個女人不斷遇上壞男人的故事。
沈光蕙說,嫁去屯門太不光彩了,至少也要嫁去跑馬地。
程韻說,能令對方傷心的,才是兩個人之間的強者。
女人擅於愛,也因此受傷至深,我們都曾經為愛情墮落──
作者簡介:
張小嫻
沒有人比她懂得愛情的好、愛情的壞。
沒有人像她,在你為愛苦惱時,給你一記左鉤拳,再給你一個大大的擁抱。
從今以後,在愛情中,你擁有一個永不離棄的守護者。
你一定聽過:「世上最遙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的距離,不是天各一方,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卻不知道我愛你。」這是張小嫻的暢銷作品《荷包裡的單人床》裡的金句。
你也一定讀過:「當你愛著一個人時,連折磨也是一種幸福」。這是引自用張小嫻〈Channel A〉系列中《那年的夢想》的名句。
爾後《那年的夢想》被改編成22集的都會時尚劇《如有月亮有眼睛》,成為她第一部搬上電視螢幕的作品。
大學畢業後,為《明報》撰寫專欄「嫻言嫻語」,94年因《明報》連載的《麵包樹上的女人》聲名大噪,成為繼瓊瑤、亦舒後,兩岸三地最受歡迎的愛情小說家。
近年除了持續創作外,98年創辦了香港第一本本土女性雜誌《AMY》,擔任總編輯,更設立了「Amy Blog」線上部落格,與讀者長期保持互動。
據統計,在香港700萬人口中,每60人手裡就有一本張小嫻的小說。在中國、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等華人世界更擁有無數讀者。
愛情,是她永遠的主題。在她筆下,愛,是人生永不落幕的演出。
各界推薦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編者的話
左鉤拳與擁抱—華文世界暢銷都會愛情經典【麵包樹三部曲】全新上市
每一個故事總會有一首主旋律,在故事的底層隱隱流動著。青峰唱著:「我們只能在愛時候悲傷,在愛時候如絲般迷惘」。
程韻愛上林方文時,並非林方文愛上了她。程韻是怎麼愛上林方文呢?可能是那頂鴨舌帽,可能是裹在涼鞋裡乾淨好看的腳趾,可能是他寫的一首首動人的情歌。誰知道呢?
愛上了誰,都是一個謎。
程韻第一次深深被一個人吸引,程韻第一次面對自己被別人深深吸引的手足無措和軟弱,如同卸了甲的士兵,但又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該受降。因為還沒有完全確定自己的心和對方的心。
到底是確定自己的心困難呢?還是確定別人的心。
如此被強烈曳引著航向的小舟,竟也懷著深切的想望奮不顧身地,投入愛情的湖面,徜徉在綺麗的風光中;儘管一波波隱然的不安激起了漣漪,終究在層層的試探、壓抑和對方的背叛後掀起巨浪。
於是,那小舟便四處打轉、遍體鱗傷了。
要愛,還是不愛呢?哪個選擇會比較容易些?
程韻懷疑起林方文、懷疑起自己、懷疑起愛情。
「快別讓我,快別讓我,快別讓我顫抖,快對我說,快對我說,快對我說愛」,然而,林方文說得如此微弱。
程韻掉頭走了,林方文卻不放,程韻祈求這一次的回頭會換來林方文永遠的忠誠。她細心地維護著回歸到日常生活的感情,在平淡中她是滿足的,但林方文不。他再次叛離了。
程韻的心支離破碎。她只能黯然走開,快速投入另一個愛她的人的懷抱。她以為從此將擺脫對舊愛的執迷,她以為心頭的那個人影淡了,不料一樁意外清晰地告訴她:她從來沒有忘了他。
走了這麼長一段愛情路,青春都老了。要怎樣安放自己的心呢?要怎樣再相信愛情?
程韻變成了一個人。
愛情似乎遠了,對林方文的回憶在月的陰晴圓缺中噬咬著她的靈魂。
如何放掉過去的一切?如何釋放禁錮在過去之中的自己?
命運總是會給人一個重擊,而那重擊,通常也是出口。
青峰唱著:「直到自由像海岸線一樣,隨潮汐衝散,什麼都自然。」
呵,當我們問,到底是愛自己?還是愛你?
我們都是愛情當中的程韻與林方文。
當我們為愛情中的嫉妒、猜疑、渴盼而宛如被燙灼一樣地團團轉時,張小嫻總會在那兒。她對你的愚痴充滿理解,但她不同於別人的是,她先給你一記左鉤拳,打中你的死穴,在你大聲呼痛,或大叫自己有多傻多蠢時;她又給你一個大大的擁抱,讓你知道你不是孤獨的,你的愛如此珍貴。
張小嫻的「麵包樹三部曲」,華文世界重量級暢銷都會愛情經典,那樣真實直樸地寫出了一個女人最早的愛情,她在愛當中的快樂、痛苦與孤單。作者細膩如珍珠般的文字,碰觸了我們心裡最最柔軟的部分、讓我們明白我們熾烈的愛可以這般光燦奪目,而那份愛的心情,如此值得我們珍視疼惜。
因著這份守護,我們或許能面對命運予以愛情的種種重擊,繼續憧憬愛情,甚至在愛之中得到自由。
註:文中歌詞,引用自蘇打綠《愛人動物》。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編者的話
左鉤拳與擁抱—華文世界暢銷都會愛情經典【麵包樹三部曲】全新上市
每一個故事總會有一首主旋律,在故事的底層隱隱流動著。青峰唱著:「我們只能在愛時候悲傷,在愛時候如絲般迷惘」。
程韻愛上林方文時,並非林方文愛上了她。程韻是怎麼愛上林方文呢?可能是那頂鴨舌帽,可能是裹在涼鞋裡乾淨好看的腳趾,可能是他寫的一首首動人的情歌。誰知道呢?
愛上了誰,都是一個謎。
程韻第一次深深被一個人吸引,程韻第一次面對自己被別人深深吸引的手足無措和軟弱,如同卸了甲的士兵,但又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
章節試閱
闖進教室的男生,戴著一頂鴨舌帽,架著一副粗黑框眼鏡,我沒法看清楚他的眼睛,只看到他有一張過分蒼白的臉,比一張白紙稍微有點顏色。他叫林方文,開課後一個月才到,肯定是候補生。
林方文選了前排的位置,就在我前面。他把喝了一半的可樂放在桌上,然後掏出一本書看得津津有味,那本不是什麼書,而是漫畫,是《龍虎門》。大學中文系一年級生,日常讀物竟是《龍虎門》!
「如果要看《龍虎門》,為什麼不坐到後面呢?」我跟他說。
他回頭,打量我一下。
「前面比較涼快。」他說。
「啊!原來是這樣。」
我最討厭故弄玄虛的人。
像他這種人,一定會在三個月內勾搭一個女生,那個傻兮兮的女生便會替他收拾房間,他坐享其成,然後在離開大學之前拋棄她。他的房間除了有大量《龍虎門》外,應該還有大批色情雜誌和一副麻將牌。
一天,上新詩課的時候,他竟然穿了一雙涼鞋,露出十根腳趾,翹起雙腳看《姊妹》。《姊妹》是我上髮廊才看的。他為什麼看一本女性雜誌呢?難道他也有婦科問題?
那天,我無心細想他為什麼看《姊妹》,我只留意他的腳趾。我覺得腳趾是一個人身體最神祕的部分。除了在家裡或去游泳,我外出一定不會讓人看到我的腳趾。腳趾好比私處,讓人看見,總是很不自然。
林方文的十根腳趾很乾淨,不太長也不太短。最難得的,是他的第二根腳趾比大拇趾短,應該不會是一個窮人。看著他的十根腳趾,我有偷窺的感覺。
下課後,林方文走到我面前,問我:「你為什麼一直看我的腳趾?」
嚇了我一跳,沒想到他知道我一直在偷看他的腳趾。
「誰看你的腳趾!」我若無其事在他身邊走過。
我感覺到他在我身後盯著我。那是頭一次,我對一個男人,有一點怦然心跳的感覺。但,我找不到任何一個理由,我會喜歡他。如果有一點揪心,那是因為被他揭穿了我在偷窺他,因此感到尷尬。
同一天下午上另一堂課,林方文換了一雙帆船鞋。他坐在我前面,回頭對我說:「我特意換上一雙包頭鞋,不讓你看到我的腳趾。」
說罷,他得意洋洋翻看新出版的《龍虎門》。而那一刻,我竟然沒有還擊之力,被他打得一敗塗地。晚上,我跟迪之吃飯,她拿了林正平最新的唱片給我,裡面有那首《人間》。迪之說,林正平已經一個星期沒找她了。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看著她哀傷地離去。男人如果要走,又怎能留得住呢?
我在被窩裡聽《人間》:
有幾多首歌,
我一生能為你唱,
從相遇的那一天,
那些少年的歲月,
該有雨,洗去錯誤的足印,
該有雪,擦去臉上的模糊……
我在歌聲中睡去。
幾個星期後的一個早上,下著滂沱大雨,我在街上站了四十五分鐘,還沒法招到一輛計程車。終於有一輛計程車停在我面前,裡面的人叫我上車,是林方文。我已經全身濕透,不想再跟自己過不去。
「謝謝你。」我對他說。
他沒有理會我,那頂鴨舌帽壓得很低,臉孔很模糊。電台剛好播放《人間》:
從相遇的那一天,
那些少年的歲月,
該有雨,洗去錯誤的足印,
該有雪,擦去臉上的模糊……
我的身體輕微隨著歌聲擺動。
「你很喜歡這首歌嗎?」林方文問我。
我點頭,他沉默不語。我們聽著同一首歌。
那首歌,總是教每一個人無端地傷感,連看《龍虎門》和《花花公子》的林方文,也不例外。
計程車到了香港大學,我找錢包付錢,林方文對我說:「不用你付。」
他就這樣付了車費,完全不認為需要徵求我的同意。
「喂!」他叫我。
「什麼事?」
他把外套脫下來扔給我。
「你把衣服拿去。」
「不用。」我說。
「你的衣服濕透了。」他說。
「我不怕冷。」我說。
「我不知道你冷不冷,但你現在好像穿了透視裝。」
我看看自己,才發現身上的白襯衫濕透了,整個胸罩浮現得一清二楚,我把林方文的外套抱在胸前,尷尬得不敢望他。
接下來的那堂課,林方文沒有出現。我的襯衫已經乾了,我把外套拿去宿舍還他。他不在宿舍裡,房門沒有關上,我走進去,以為自己走進了一間舊書局。整個房間都是書,半張床被書本霸占了。房間裡並沒有大量的《龍虎門》、《花花公子》或《姊妹》。有《戰爭與和平》,也有《百年孤寂》,他原來也看那些書。桌面很凌亂,我翻看一下桌上的紙張,其中一張紙上有《人間》的歌詞。
有幾多首歌,我一生能為你唱?
從相遇的那一天,那些少年的歲月……
他竟然那麼無聊把歌詞抄一遍。
即使抄歌詞,也沒有可能連簡譜一起抄下吧?《人間》的填詞人是林放,林方文,方字跟文字合併,不就是「放」字嗎?難道林方文就是林放?
這個猛啃《龍虎門》的人,能寫出那樣動人的歌詞?《人間》不是我聽過最好的歌,卻是最能感動我的歌。
我看見床上有一支頗為破舊的樂風牌口琴,是填詞的工具嗎?
「你在這裡幹什麼?」他突然闖進來,把我嚇了一跳。
「我把外套還給你。」
「哦。」
他沒有理會我,把剛洗好的幾件衣服掛在房間裡。
「《人間》的歌詞,是你寫的嗎?」
「沒想到吧?」
「是你?真的是你?」
「你的樣子很吃驚,是不是像我這種人,不像會寫出這樣的歌詞?」
我從來沒想過,那段日子裡,每晚陪著我入夢的歌,竟是他寫的。一個我最心儀的填詞人,竟然站在我面前,他是我認識的人。
我有點不知所措,應該離去,卻不由自主地留下,期望他會跟我說些什麼。
林方文沒有跟我說話,溫柔地擁抱著我,我竟然沒有反抗,好像已經跟他認識了很久。
才氣令女人目眩,不是他的臂彎融化了我,是他的歌詞,是他的才情,令我失去矜持。
那是我有生以來,頭一次跟一個和我沒血緣的男人擁抱,他的體溫溫熱著
闖進教室的男生,戴著一頂鴨舌帽,架著一副粗黑框眼鏡,我沒法看清楚他的眼睛,只看到他有一張過分蒼白的臉,比一張白紙稍微有點顏色。他叫林方文,開課後一個月才到,肯定是候補生。林方文選了前排的位置,就在我前面。他把喝了一半的可樂放在桌上,然後掏出一本書看得津津有味,那本不是什麼書,而是漫畫,是《龍虎門》。大學中文系一年級生,日常讀物竟是《龍虎門》!「如果要看《龍虎門》,為什麼不坐到後面呢?」我跟他說。他回頭,打量我一下。「前面比較涼快。」他說。「啊!原來是這樣。」我最討厭故弄玄虛的人。像他這種人,一定...
作者序
《麵包樹上的女人》是我第一部小說,十六年了,往事如昨,卻也是遙遙遠遠的昨日,許多感想,真的不知道從何說起。這個小說一九九四年在香港《明報》每天連載,一九九五年出版成書。六年後,我先後寫了《麵包樹出走了》和《流浪的麵包樹》兩個續篇。這些年來,常常有讀者問我,麵包樹的故事會不會繼續寫下去?我心中沒有答案。
所有的故事,是不是也會有一個終結?一本書最好的結局,往往是在讀者心中,而不是在創造它的人那裡。寫書的時候,我是這部小說的上帝,我創造它,盡我所能賦予它美麗的生命;故事寫完了,我便再也不是上帝,我只是個母親,時候到了就該放手,讓這孩子自由飛翔。
麵包樹是我寫於青春的故事,當時的技巧或許比不上現在,心思卻是單純的,就像每個人最早的愛情,雖然青澀,甚至稚拙,卻也是最真切的。它是我第一部小說,或多或少有許多我自己的故事,我無可避免把我認識的人寫進書裡,不懂得怎樣去掩飾和保護他們,也不懂得隱藏些什麼。結果,明明是虛構的故事,一旦下筆,卻寫了很多的自白,既是程韻和林方文的愛恨成長,也是我的成長愛恨。「本事文化」把麵包樹系列三部小說重新修訂,陸續出版,讓它再一次面對喜愛它的讀者,我也再一次重溫林方文和程韻之間那段從青澀走到心痛的愛情,再一次經歷程韻對林方文的執迷。她為什麼如此愛他?為什麼情願流著淚愛這個人也不能夠微笑去接受一個永遠守候著她的人?這樣的愛情難道不苦嗎?可是,愛情豈是可以理喻的?
我總是在想,小說跟人生有什麼不同?有些小說比作者短命;另一些小說,卻活得比作者長久,甚至活到千百年後,也將會活到永遠。人生從來就沒有小說那麼傳奇,那麼繾綣悠長。《麵包樹出走了》是二○○○年出版的,故事裡,紅歌手葛米兒患上了無藥可治的腦癌,她坦然接受事實,堅持要辦一場告別演唱會,用歌聲告別塵世。那天晚上,唱完最後一首歌,這個虛弱的女孩獨個兒回到後台,幽幽地死在化妝室裡。這本書出版三年後,香港歌后梅豔芳證實患上了子宮頸癌,她同樣舉辦了一場告別演唱會。演唱會結束沒多久,她走了,留下了最後也最使人傷感的歌聲。後來才讀到這部小說的許多讀者紛紛問我,葛米兒的故事是不是就是梅豔芳的故事?怎麼可能呢?我不是先知,不會知道幾年後發生的事。
若說人生跟小說不一樣,小說與人生的巧合有時卻會讓人吃驚。麵包樹終歸是個虛構的故事,讀者卻早就把它看成了真實的人生,多少年來,無數讀者都問我同一個問題,他們想知道,林方文是不是就是林夕?這幾年,又有許多新一輩的讀者問我,林方文是不是就是方文山?也許,再過十年或是五十年,當我已經很老了,讀者們也許會猜測林方文就是某個他們喜歡的寫詞人。終於我明白,小說與人生的不同,是人會逐漸老去,小說裡的人物卻永遠還是那個年紀,永遠不會老去。這多好啊!都說小說是為人生而寫的,它填補了我們每個人的遺憾,圓滿了我們的想像。
在麵包樹的故事裡,林方文為程韻寫了許多美麗的歌,麵包樹三部小說也是我用文字譜成的一首長歌,歌唱著燦爛的青春,為世間的相聚而唱,也為那樣纏繞執拗的愛情而歌。就請你把這一篇序當成一首短歌,我不是葛米兒,我沒有一個動人的嗓子,這首歌,是為了新知舊雨而唱,惟願這一曲永不落幕,就像我們擁有過的所有刻骨銘心的愛情,時日漸遠,始終與記憶相伴,不曾老去;每一次回首,還是會心痛。
《麵包樹上的女人》是我第一部小說,十六年了,往事如昨,卻也是遙遙遠遠的昨日,許多感想,真的不知道從何說起。這個小說一九九四年在香港《明報》每天連載,一九九五年出版成書。六年後,我先後寫了《麵包樹出走了》和《流浪的麵包樹》兩個續篇。這些年來,常常有讀者問我,麵包樹的故事會不會繼續寫下去?我心中沒有答案。
所有的故事,是不是也會有一個終結?一本書最好的結局,往往是在讀者心中,而不是在創造它的人那裡。寫書的時候,我是這部小說的上帝,我創造它,盡我所能賦予它美麗的生命;故事寫完了,我便再也不是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