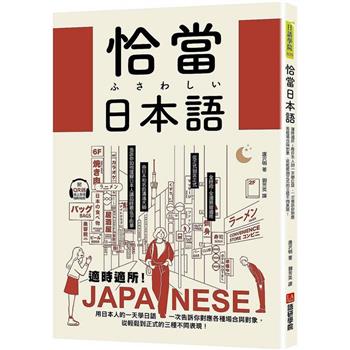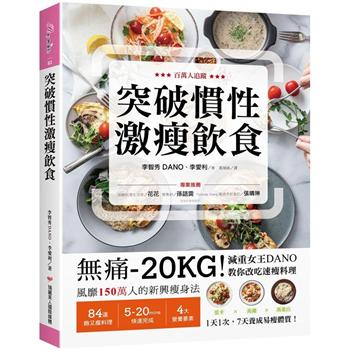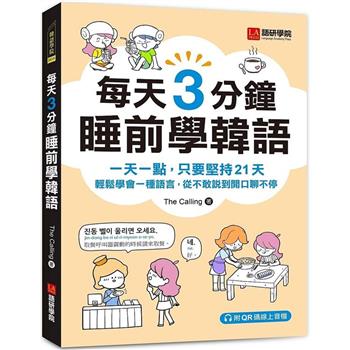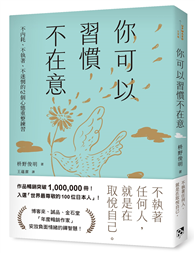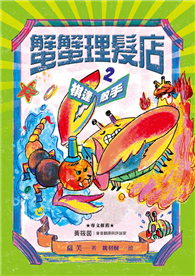東部綿長的海岸線,中央山是中央山,海岸山是海岸山,太平洋是太平洋,它們恆常在那裡,矗立或者拍岸,在我們年幼的時候,時間移動得十分緩慢。—陳雨航
陳雨航輕描淡寫他在台灣東部海邊長大的村莊,小村的各種角色以悠哉自在、風和日麗的步調生活著。各擁心思的各路人馬齊聚村子口,以雜貨店為中心緩慢度日,有時又像唯一一家深夜戲院播映的話題電影:沉默勤勞的店老闆,某天出乎意外地帶回一個年輕的女人,老闆娘過去開朗的笑容枯萎,以淚洗面好幾天後失去蹤影……。
作者文字描繪內斂深刻,剪輯場景別出心裁,長鏡頭般的視野和緩移動,營造出一幕幕動人的畫面:住在深山電廠的宿舍,母親為了買不到零食的孩子親手做燕菜、長得像飛碟的紅豆餅;童年繪製的亭亭玉立的木瓜樹,枝葉婆娑,略顯孤寂,卻又帶著成長的力量;一顆紅藍色小皮球,一截竹筒當球棒,石塊是壘包,一群人克難地玩史前棒球,球擊向外野,一位站在腳踏車上大鵬展翅般接住球的少年,在時光濾鏡下,鏡頭跳接成為蘇花公路上奔波的卡車司機。
陳雨航說:「一燈如豆,人間的喜怒哀樂,世俗的男歡女愛,江湖的恩怨情仇,盡在我手中的紙上乾坤。」他寫活了舊日時光和現代風景,感情躍然紙上,書寫平淡有味,在書中可以見到熟識的家人朋友,也看到記憶裡熟悉的事物,這種樸實的寫作方式,卻蜿蜒出娓娓動聽的故事。世事多變,政治峰迴,家鄉路轉,面對人生與工作上的起伏波濤,我們需要時光流轉中不變的人情與景色,讓人回憶青春的美麗與哀愁,叩問生命長河流動的深遠意義。
本書特色
★首刷限量陳雨航親筆簽名,值得珍藏。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三少四壯集專欄作者的文章集結,書寫溫暖的鄉土人情的最新散文集。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小村日和(首刷限量簽名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29 |
現代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小村日和(首刷限量簽名版)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陳雨航
一九四九年生於花蓮。師大歷史系、文化學院藝術研究所畢業。曾任職報紙副刊、雜誌、出版編輯多年。七〇年代從事小說寫作,著作有短篇小說集《策馬入林》和《天下第一捕快》。二〇一二年發表首部長篇小說《小鎮生活指南》,榮獲:二〇一二年《亞洲週刊》十大小說獎、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二〇一三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等。二〇一五年出版散文集《日子的風景》。
陳雨航
一九四九年生於花蓮。師大歷史系、文化學院藝術研究所畢業。曾任職報紙副刊、雜誌、出版編輯多年。七〇年代從事小說寫作,著作有短篇小說集《策馬入林》和《天下第一捕快》。二〇一二年發表首部長篇小說《小鎮生活指南》,榮獲:二〇一二年《亞洲週刊》十大小說獎、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二〇一三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等。二〇一五年出版散文集《日子的風景》。
目錄
輯一記憶的村子
記憶的村子
小村雜貨店遺事
葡萄的故事
鄰村寺院
有竹叢麵店和茅草營房的村莊
門前小店本末
鄉村的夜晚
村街夜景
深夜戲院
輯二吃食種種
便當
四月的早晨遇見100%的麵疙瘩
芒果的滋味
木瓜
年糕
昔日甜食
輯三家庭節日
初返鄉
充滿電影的夏天
我的舅舅
秋子
交集與重逢
生日
失業
人間問
輯四物語
安全刀片
眼鏡
電話
排球
足球
史前棒球
郵票
計算尺與算盤
鋼筆
輯五終將遠去的
台北初印象
鐵絲網裡的風景
作家老師與非典型學生
當我們篳路藍縷的時候
遇見
裝備顧問
洗澡
私 披頭流水帳
路很夭壽,但貓喜歡我
貓的身世
輯六私影記
從慌亂到墮落
1967年的電視影集
電影夢
銀翼殺手
蝴蝶春夢製罐巷
蓬門碧玉紅顏淚
奇異恩典
咖啡館的庫布力克迷
記憶的村子
小村雜貨店遺事
葡萄的故事
鄰村寺院
有竹叢麵店和茅草營房的村莊
門前小店本末
鄉村的夜晚
村街夜景
深夜戲院
輯二吃食種種
便當
四月的早晨遇見100%的麵疙瘩
芒果的滋味
木瓜
年糕
昔日甜食
輯三家庭節日
初返鄉
充滿電影的夏天
我的舅舅
秋子
交集與重逢
生日
失業
人間問
輯四物語
安全刀片
眼鏡
電話
排球
足球
史前棒球
郵票
計算尺與算盤
鋼筆
輯五終將遠去的
台北初印象
鐵絲網裡的風景
作家老師與非典型學生
當我們篳路藍縷的時候
遇見
裝備顧問
洗澡
私 披頭流水帳
路很夭壽,但貓喜歡我
貓的身世
輯六私影記
從慌亂到墮落
1967年的電視影集
電影夢
銀翼殺手
蝴蝶春夢製罐巷
蓬門碧玉紅顏淚
奇異恩典
咖啡館的庫布力克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