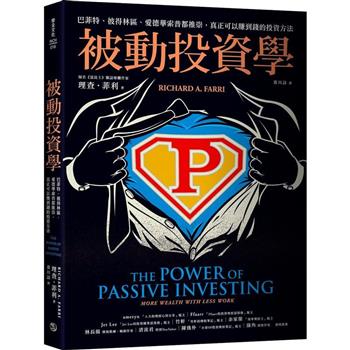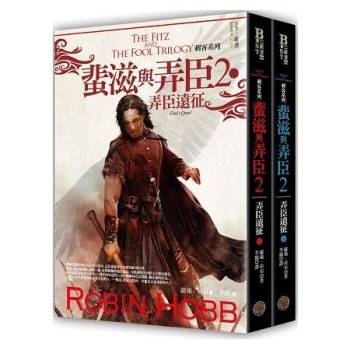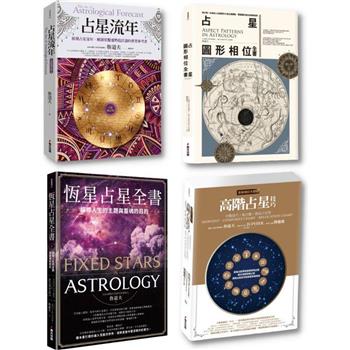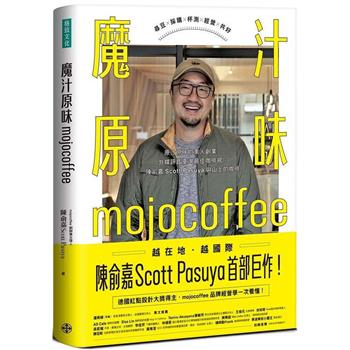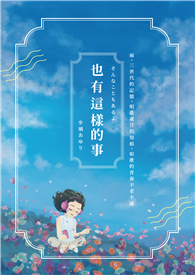游擊文化與內容力合作企劃,於2016年一系列出版了陳舜臣的《青雲之軸》(青雲の軸,1974)、《憤怒的菩薩》(怒りの菩薩,1962)及《半路上》(道半ば,2003),並將三本書所組成的「大時代三部曲」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以文豪筆下虛實交錯的「陳舜臣生命經驗」為核心內容,提供讀者相互參照的閱讀視角,獲得進入陳舜臣作品中時代故事的全新體驗。
《青雲之軸》
撥開名為戰爭的烏雲,年輕悸動的心能否得見朗朗青空?
「神戶,一個東西向帶狀的細長城市,山和海非常靠近。
如果有什麼地方稍微讓人認為是有深度的,或許就是因為這個城市充滿了離別吧。
在幕府末期,由於對外開港,神戶終於開始有了都市的雛形。不過這裡又和京都、大阪那種傳統城市不同,無論如何都讓人覺得淺薄。然而以港口為舞臺所上演的無數離別劇碼,卻為這份膚淺帶來了救贖。如果沒有這一點的話,神戶一定只能淪落為一個粗淺港町了吧。」
這是陳舜臣筆下的神戶,也是自傳小說《青雲之軸》發生的舞臺。
主角陳俊仁,1924年出生於日本神戶元町的台灣籍貿易商之子,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他的身邊送往迎來。在成長過程中,「家裡的話」與「外面的語言」的不同啟蒙了他,讓他發覺自己與身邊同伴在身分上的歧異。伴著阿公在花市看蘭花,卻被日本人店老闆怒喊「清國奴,滾開」。阿公當時灼熱如火的掌心,成了殖民地人民悲傷的烙痕,震撼著俊仁幼小的心靈。
在名為戰爭的烏雲壟罩的神戶,台灣人、朝鮮人、日本人、中國人、印度人與韃靼人等來自不同國境的人,在這個海港城市彼此相遇、分離。有狡詐卑劣、有徬徨無措,但其中也有同樣身為殖民地人民的溫暖情意。這是陳舜臣筆下那個烽煙漫天,但又離我們不遠的大時代。
戰爭終將結束,撥開烏雲之後,陳俊仁與共同經歷這一切的朋友的年輕之心能否得見朗朗青空?
《憤怒的菩薩》
台日中三地的複雜糾葛,在黑紅交替的歷史舞台上,釀成了殺人慘劇。
而台灣島上的菩薩,究竟又為何而怒?
1946年3月,貨船「朝風丸」載著三百多名在日台灣人,從日本回到基隆港。楊輝銘和新婚妻子林彩琴,也搭著這艘船回到久違的家鄉。沒想到,在彩琴娘家菩薩庄附近,一位駐守兵舍等待遣返的日本軍官,竟在兩人回台當天遭到殺害。兩位警備司令部的中國軍人奉命進行調查。不久後,在猶如密室的菩薩山上又發生了另一樁案件,被捲入事件中的楊輝銘,開始了追兇的旅程……。
本書是陳舜臣唯一一本以台灣為場景的長篇推理小說。書中如實呈現了戰後初期台灣社會的樣貌,以及在歷史夾縫中求生存、努力適應政權交替的台灣人民的心聲。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無可奈何地深陷在時代洪流之中,五十年前先是被迫成為「日本人」,戰後又在一夕之間變成「中國人」,連「國語」都必須從頭學習。然而,到底何謂中國人呢?陳舜臣為所有對這份哀傷產生共鳴的人們,寫出了屬於他們的故事。
《半路上》
「我到底是誰?」的身分疑惑,
是小說家在人生旅途上不住回望的緣由,
也是他寫作生涯裡探尋不懈的永恆提問。
「自己到底是誰?或許長久以來,心中都沒有拋開這個疑惑。年幼時期的自言自語,其實就是我成為作家的出發點,每次只要回頭展望,就能看到當初自己的起點,也能重新找到自己現在身處的定位。」
以推理小說享譽日本文壇、與司馬遼太郎並列「歷史小說雙璧」的陳舜臣,著作等身且獲獎無數。然而,中文世界的讀者多半只知其書而不識其人。陳舜臣在兩度中風之間完成了唯一的自傳《半路上》,此時年近八十的他已行至人生旅程的最後階段,佇足回首寫下前半生的昭和時光。
在這部半生記裡,陳舜臣回憶自己於殖民母國的成長點滴,以及身為在日台灣人的真切感受;戰後回到故鄉新莊待了三年半,參與台灣社會紛擾動盪的新局,也經歷令他沈痛哀傷的二二八事件;重返日本後蟄伏於家族事業,十年的沈潛期為日後波瀾壯闊的文豪生涯奠定重要基礎。
這些在歲月沖刷後沈澱下來的文字,揭露了陳舜臣埋藏心中最深的情感與記憶,也呈顯出他如何在時勢左右下,從命運中汲取孕育文學人生的珍貴養分。
跨時代推薦
「以閱讀者熟悉的日常經歷或聽聞過的往昔歷史作為敘事經緯,結合推理類型特有的線索埋設與串接,陳舜臣內斂的文字深處有困惑、有憤怒,亦有彷若預言的洞察針砭,即便在成書半世紀後來看,依然令人深思低迴不已,強烈感受到一位優異小說家的纖細心思與成熟智慧。」──冬陽(推理評論人)
「見過空襲、看過二二八的陳舜臣,對歷史境遇有深刻感想,對時代的人性理解且同情。這種柔軟、悲憫且反戰的態度,存在『推理』這種類型創作中,形成獨特的魅力。《憤怒的菩薩》是陳舜臣唯一以台灣為背景的長篇推理小說,他揭開戰後台灣那段權力真空時期,這塊土地的經歷。也寫滿了他留台三年在鄉土上所體會的情感。」──阿潑(文字工作者)
「誰用小說鉅細靡遺描繪了戰後的台灣?誰以那個兵荒馬亂、時代轉瞬為背景寫了推理小說?除了緊湊暢快的節奏和扣人心弦的情節,本書更顛覆了固有的『台灣視角』,以『在日台灣人』的獨特眼光,為台灣的特殊時刻留下彌足珍貴的社會素描,以及大量的信息。松本清張的推理小說為日本社會留下大量的戰後浮世繪;而台灣的戰後,幸虧有陳舜臣,幸好有《憤怒的菩薩》。台裔日本文豪陳舜臣的《憤怒的菩薩》,可說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推理小說,是被遺忘半個世紀的滄海遺珠。」──譚端(偵探書屋店長)
「在拍《阿罩霧風雲》時,一直隨著故事主人翁之一的林獻堂,在清國、日本、國民政府三個時代之間無奈地擺盪著。心想,那真是個苦悶又無奈的年代啊!如今讀了《半路上》,陳舜臣藉由自己的親身經歷,更為深且真地道出了那一輩出生於日本,在戰後選擇回到台灣的青年們所面對的國籍轉換的強大衝擊,敘事風格異常冷靜,帶給我的後座力卻是意料之外的強大。在我的想像中,歷史一直是一個沒有終點的平行時空,而如今我們是不是也在那條不斷輪迴的『半路上』呢?」——許明淳(歷史紀錄片 《阿罩霧風雲》導演)
「持續以豐饒 『日本』語創作『中國』歷史小說的『台灣』人——陳舜臣這位作家的偉大之處,在於他鮮明地跨越了國境。 在《半路上》中,即便不斷遭受歷史翻弄,仍在感性的次元穿梭於『日本』與『台灣』之間,保有作家豐富精神的原點。身為現代東亞世界的一員,在自己人生路途上邂逅此書的踏實感,至今仍讓我玩味不已。」——溫又柔(《來福之家》作者、2016日本隨筆作家俱樂部獎得主)
「終於來到陳舜臣大時代下的三部曲最直接、最赤裸的最後一本,『在日台灣人』的故事怎能如此舉重若輕?一個人擁有悲歡震盪的人生,或許是浮沈世間的無奈,陳舜臣卻喃喃說明他如何慎重面對無奈的人生,所以起初因為他的天真在笑,不久濕濕的眼角感覺淚珠有點老,然後吸一口氣其實會痛的。」——蘇碩斌(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大時代下的陳舜臣三部曲:青雲之軸、憤怒的菩薩、半路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950 |
日本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大時代下的陳舜臣三部曲:青雲之軸、憤怒的菩薩、半路上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陳舜臣
1924年2月18日出生於日本神戶元町的台灣人家庭。1941年進入大阪外國語學校印度語科就讀(隔年司馬遼太郎入讀蒙古語科,此後兩人結為終生摯友),1943年因戰事提早畢業,留在母校西南亞細亞語研究所擔任助手,參與編纂印度語辭典的工作。1946年回到宛如異鄉的故鄉──台灣,受聘擔任新莊中學英語教師,並親眼見證戰後台灣的社會巨變。二二八事件的爆發,造成他極大的衝擊與創傷,在第一屆學生畢業後便於1949年返回日本。
在家族事業從事貿易工作的十年間,陳舜臣見識了各式各樣的人物,也興起寫作的念頭。1961年,他以《枯草之根》獲江戶川亂步賞,初入文壇。之後陸續發表推理小說、中國歷史小說、隨筆、評論等作品,並得到直木賞、推理作家協會賞、每日出版文化賞等文壇大獎的推崇。1993年,NHK將歷史小說《琉球之風》改編為同名大河劇。
陳舜臣於1962年發表了以戰後台灣為場景的長篇推理小說《憤怒的菩薩》。1974年,發表自傳體小說《青雲之軸》,揭述其生為在日台灣人所遭逢的身分認同問題與成長故事。2003年發表自傳《半路上》,讓人一窺這位小說家動人的半生歲月與他走過的大時代。
日中建交後,陳舜臣為了方便到中國取材考證而申請中國護照。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他放棄中國籍,正式歸化日本籍。2015年1月21日,陳舜臣於最鍾愛的城市神戶辭世,留下一百六十多部作品以及波瀾壯闊的一生。
書系企劃團隊簡介
內容力(Power of Content; POC)
由 一群擁有豐富東亞跨國生活經驗的人文社會學者所組成的新興「內容策畫」團隊,相信「內容」能生產出各種形式的溝通力量,並且促進東亞區域內的相互理解與發 展。因此,不拘泥於既有產業類別的限制,而致力挖掘能跨越語言、文化、國境限制,並引發人們共鳴的「好內容」,再經由專業團隊在製作、編輯、轉譯、代理授 權等方面的努力,跨越「內容流通」的障礙,最終開發出具有文化內涵與市場價值的多元化「智慧財產」(Intellectual Property),並為台灣與東亞區域內的文化交流與內容產業發展貢獻心力。
譯者簡介
郭凡嘉
台灣大學日文系畢,現為東京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內容力公司特約譯者。譯有森見登美彥《空轉小說家》、角田光代《肉記》、中村地平《霧之番社》、溫又柔《來福之家》等,並撰有日本小說家評論數篇。
游若琪
也敲鍵盤也拿畫筆,遊走於日文與圖畫之間的專職譯者。一邊翻譯著故事中爬山的片段,一邊想像八仙樓的雞捲到底是什麼味道。不時出現在故事中的台灣人事物,有一種既親切又遙遠的感覺。內容力有限公司特約譯者。
林琪禎
一橋大學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博士(學術),曾任出版社外稿譯者多年,目前為和春技術學院應用外語系專任助理教授,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兼任助理教授,內容力有限公司內容流通總監。著有《帝国日本の教育総力戦:植民地の「国民学校」制度と初等義務教育政策の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日本學研究叢書18)。
黃耀進
曾任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研究員,目前為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博士候選人,內容力有限公司內容製作總監。譯有《東京日和》(流行風)、《寫真的思考:攝影的存在意義》(流行風)、《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聯經)、《亂世的犧牲者:重探川島芳子的悲劇一生》(八旗文化)等書。
陳舜臣
1924年2月18日出生於日本神戶元町的台灣人家庭。1941年進入大阪外國語學校印度語科就讀(隔年司馬遼太郎入讀蒙古語科,此後兩人結為終生摯友),1943年因戰事提早畢業,留在母校西南亞細亞語研究所擔任助手,參與編纂印度語辭典的工作。1946年回到宛如異鄉的故鄉──台灣,受聘擔任新莊中學英語教師,並親眼見證戰後台灣的社會巨變。二二八事件的爆發,造成他極大的衝擊與創傷,在第一屆學生畢業後便於1949年返回日本。
在家族事業從事貿易工作的十年間,陳舜臣見識了各式各樣的人物,也興起寫作的念頭。1961年,他以《枯草之根》獲江戶川亂步賞,初入文壇。之後陸續發表推理小說、中國歷史小說、隨筆、評論等作品,並得到直木賞、推理作家協會賞、每日出版文化賞等文壇大獎的推崇。1993年,NHK將歷史小說《琉球之風》改編為同名大河劇。
陳舜臣於1962年發表了以戰後台灣為場景的長篇推理小說《憤怒的菩薩》。1974年,發表自傳體小說《青雲之軸》,揭述其生為在日台灣人所遭逢的身分認同問題與成長故事。2003年發表自傳《半路上》,讓人一窺這位小說家動人的半生歲月與他走過的大時代。
日中建交後,陳舜臣為了方便到中國取材考證而申請中國護照。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他放棄中國籍,正式歸化日本籍。2015年1月21日,陳舜臣於最鍾愛的城市神戶辭世,留下一百六十多部作品以及波瀾壯闊的一生。
書系企劃團隊簡介
內容力(Power of Content; POC)
由 一群擁有豐富東亞跨國生活經驗的人文社會學者所組成的新興「內容策畫」團隊,相信「內容」能生產出各種形式的溝通力量,並且促進東亞區域內的相互理解與發 展。因此,不拘泥於既有產業類別的限制,而致力挖掘能跨越語言、文化、國境限制,並引發人們共鳴的「好內容」,再經由專業團隊在製作、編輯、轉譯、代理授 權等方面的努力,跨越「內容流通」的障礙,最終開發出具有文化內涵與市場價值的多元化「智慧財產」(Intellectual Property),並為台灣與東亞區域內的文化交流與內容產業發展貢獻心力。
譯者簡介
郭凡嘉
台灣大學日文系畢,現為東京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內容力公司特約譯者。譯有森見登美彥《空轉小說家》、角田光代《肉記》、中村地平《霧之番社》、溫又柔《來福之家》等,並撰有日本小說家評論數篇。
游若琪
也敲鍵盤也拿畫筆,遊走於日文與圖畫之間的專職譯者。一邊翻譯著故事中爬山的片段,一邊想像八仙樓的雞捲到底是什麼味道。不時出現在故事中的台灣人事物,有一種既親切又遙遠的感覺。內容力有限公司特約譯者。
林琪禎
一橋大學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博士(學術),曾任出版社外稿譯者多年,目前為和春技術學院應用外語系專任助理教授,文藻外語大學日本語文系兼任助理教授,內容力有限公司內容流通總監。著有《帝国日本の教育総力戦:植民地の「国民学校」制度と初等義務教育政策の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日本學研究叢書18)。
黃耀進
曾任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研究員,目前為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博士候選人,內容力有限公司內容製作總監。譯有《東京日和》(流行風)、《寫真的思考:攝影的存在意義》(流行風)、《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聯經)、《亂世的犧牲者:重探川島芳子的悲劇一生》(八旗文化)等書。
目錄
《青雲之軸》
序章
兩個世界
祖父
英雄形象
熱衷的季節
消失的海上閱兵
在逆流中
我的英雄
崩壞
支撐的力量
小麻雀
山洪
動搖
滑翔機
成長的代價
來自故鄉的考生
殖民地印度
即將逼近的烏雲
祝你好運
覺醒之路
世界大戰
孤獨的夜間步行
提前到來的畢業
騷動的血液
燃燒的世界
在烈焰與煙霧之下
揭開序幕
《憤怒的菩薩》
序章
朝風丸
歸鄉
回門
逛寺廟
軍人們
復活的男子
衝破黑暗的影子
槍聲
搜山
兩輛腳踏車
回家
再次陷入混亂
另一人復活了
迎雲寺會議
善後
落幕
三把鏟子
尾聲
《半路上》
童年歲月
位於海岸通的家
中山手和北長狹
升學
水災前
飄落的旗幟
太平洋戰爭前夕
戰爭的序幕
越洋的人們
上八時代
大火前後
戰爭結束
歸鄉
登陸
歸隱田園
開始授課
消逝的牧歌時代
二二八事件
紛亂不息
台灣春秋
別了台灣
獲頒亂步賞為止
後日譚
序章
兩個世界
祖父
英雄形象
熱衷的季節
消失的海上閱兵
在逆流中
我的英雄
崩壞
支撐的力量
小麻雀
山洪
動搖
滑翔機
成長的代價
來自故鄉的考生
殖民地印度
即將逼近的烏雲
祝你好運
覺醒之路
世界大戰
孤獨的夜間步行
提前到來的畢業
騷動的血液
燃燒的世界
在烈焰與煙霧之下
揭開序幕
《憤怒的菩薩》
序章
朝風丸
歸鄉
回門
逛寺廟
軍人們
復活的男子
衝破黑暗的影子
槍聲
搜山
兩輛腳踏車
回家
再次陷入混亂
另一人復活了
迎雲寺會議
善後
落幕
三把鏟子
尾聲
《半路上》
童年歲月
位於海岸通的家
中山手和北長狹
升學
水災前
飄落的旗幟
太平洋戰爭前夕
戰爭的序幕
越洋的人們
上八時代
大火前後
戰爭結束
歸鄉
登陸
歸隱田園
開始授課
消逝的牧歌時代
二二八事件
紛亂不息
台灣春秋
別了台灣
獲頒亂步賞為止
後日譚
序
出版緣起
大時代下的身世飄零與歸屬——重訪陳舜臣
陳思宇(台灣大學歷史學博士、內容力營運企劃長)
那是2014年的一個炎熱夏日,當我拉著行李走出神戶三宮車站時,隨即湧現一種異樣的情緒,事實上這才是我第二次到神戶,非但無法說出眼前的街景與建築物名稱,如果不依賴手中的地圖與當地指標,也難以前往元町、南京町、海岸通、神戶港等地,但經過大半年閱讀陳舜臣的作品,卻似乎是來到一座熟悉的城市。
午後,往海邊走去,先參觀了位於南京町中華街附近的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陳舜臣筆下的華僑偵探陶展文,正是活躍於這個充滿各色人等的海岸地帶,而他家族的舊居「三色之家」也在附近。根據博物館人員的介紹,陳舜臣與司馬遼太郎常在博物館碰面閒談,館內還掛著一幅兩位文豪會面時的珍貴寫真。館方人員也告訴我,正在試營運階段的「陳舜臣亞細亞文藝館」離此地不遠,因此問明地址及方向後,便獨自前往位於神戶港埠頭附近的文藝館一探究竟!
當我在參觀陳舜臣寫作使用的工具與手寫原稿之際,不經意發現一份印刷資料,原來陳舜臣曾在神戶新聞及一份名為《陳舜臣中國圖書館》的刊物上,連載他的半生傳記。因此,我開始一篇篇細讀這份資料,而在那個下午,曾在閱讀過程中出現的疑惑,居然都有了初步的答案!陳舜臣在系列連載中,不但記錄家族從台灣移居神戶的發展,敘述自己在神戶的成長過程,也提及他跟台灣的文化與血脈因緣。令我感到驚訝的是,陳舜臣以相當多的篇幅,敘述戰後三年他的「台灣經驗」,包括他在台北及新莊當地的所見所聞、學校中的人事關係,在家鄉遭遇的另一種語言衝突等等。
由於時間已近閉館,而我尚未能消化手邊的閱讀資料,雖然無理但也只能碰碰運氣向志工們詢問是否能影印這份連載?有位志工伯伯突然拿出一本書,告訴我這系列連載日後已集結修改出版,成為他手上那本名為《半路上》的傳記著作!當我翻開書,內心實在百味交陳,因為這本書出版於2003年,算起來已有十年之久,但包括我在內的中文世界讀者、出版界、研究學者卻不曾聽聞或討論這本傳記,似乎代表陳舜臣確實已被眾人遺忘了!我試著想像,當時年近八十且因腦溢血而行動不便的作家,是以什麼心情寫下這份生涯紀錄?他將這本書定名為《半路上》,是因為胸懷未竟之志,而有繼續寫作的計畫?或是對自己走過的人生道路仍有未解的困惑?
記下手邊《半路上》一書的出版資料,匆匆謝過志工的幫忙後,我便離開文藝館,但望著神戶海邊的朗朗青空,思緒及心情卻有些混亂,因此隨手在路邊的自動販賣機按了罐冰可樂喝,順便整理一下腦中混亂的想法。思慮略為沉澱後,我在腦海中逐漸形成兩個構想:一方面,陳舜臣先生的生涯與他寫下的紀錄,確實有助中文世界讀者了解「在日台灣人」的歷史經驗,或許有機會能在台灣翻譯出版《半路上》;另方面,《半路上》實際上是一部「半生記」,陳舜臣雖在書中細數了他自出生到出道成為作家的點滴,但對後半生的記敘相對較少,讀者無法了解他為何在寫作黃金期,突然選擇加入中國籍,放棄了回台灣的機會?我想或許能透過拍攝紀錄片或傳記書寫的方式,補上一些空白,更清楚呈現陳舜臣先生走過的生命軌跡。
我當時已得知有日本及台灣的紀錄片團隊,正在拍攝以殖民時期台灣「日本語世代」及「在台出生日本人(灣生)」為主題的歷史紀錄片,但似乎都忽略了「在日台灣人」的歷史處境。但我認為,由於日本帝國力量在短期間由擴張到崩潰,導致大量人口必須在快速變化的界線中移動,各種身分及文化認同都處於極不穩定的狀態,但冷戰各方卻迅速建立意識型態的僵硬壁壘,瞬間阻擋了人群的移動,並且劃分出政治、語言、文化等各種界線,因此同時形成了如「日本語世代」、「灣生」或「在日台灣人」等身分群體。記得曾聽一位學者這麼形容:「日本語世代、灣生、在日台灣人,都算是習慣以日語溝通的『台灣人』!承載了複雜多變的東亞近代史。」無論此種說法是否適切,但我想,拍攝一部以陳舜臣生涯為主題的影像紀錄,應該能使台灣人或台灣史的圖像更為完整。
結束在關西的畢業旅行後,我回到東京,繼續完成手上的工作,再不久,便離開日本返回台灣,結束了在日本的「外國人生活」。在這段期間,我持續與幾個朋友討論如何完成整個計畫,最終,大家決定創立一間公司、一個團隊,跨出學界,到未曾涉足的市場上尋找完成計畫的各種資源。經由許多人的合作與努力,我們的計畫逐漸得到關鍵性的發展資源,並且逐漸發展出不同於其他內容製作計畫的特色。
整個計畫的核心精神與執行方向同時包含兩個內容:「大時代下的陳舜臣」與「陳舜臣筆下的時代故事」,即陳舜臣本人的故事與他筆下的創作作品。具體的內容呈現方式最初包含兩部分:影像紀錄與作品出版。然而,我們希望這是個具有生命力的企劃,而且深信故事內容所具有的潛力,必能不斷創造出足以展現內容的最佳形式。最初,我們也曾苦惱於如何定義、定位整個計畫,就如同我們難以辨識陳舜臣是台灣人?中國人?日本人?他的文學是台灣文學?日本文學或中國文學?如今則期待這個立體、具備延伸性、穿透性的內容創作及出版計畫,能夠不斷跨出既有的界線,開拓出更寬廣的想像空間。
2015年初,由於傳來陳舜臣先生去世的消息,促使我們加速推動計畫的腳步,由游擊文化主導的「大時代下的陳舜臣三部曲」出版專案成為第一個企劃完成並上市的項目。此一項目是以《半路上》一書的出版構想為原型,結合紀錄片田調活動,進一步發展出的「陳舜臣作品出版計畫」。在企劃紀錄片內容的研究階段,內容力企劃團隊與游擊文化的編輯團隊,便定期在獨立書店偵探書屋研讀陳舜臣的其他作品,希望進一步發掘企劃與編輯靈感,因此在《半路上》之外,又陸續挖掘了《青雲之軸》與《憤怒的菩薩》這兩部類型迥異的陳舜臣小說作品,並且與《半路上》一書組成三部曲。
《青雲之軸》是部自傳性小說,主角陳俊仁是以陳舜臣本人塑造的人物。故事始於主角幼時經歷的內外不同語言文化世界,觸及戰前台灣人在殖民母國遭受的歧視與戰爭經驗,最終結束於1945年8月15日,也正是陳舜臣失去「日本人」身分而成為「在日台灣人」的那天,以往並未見過其他作家曾嘗試類似的創作形式與主題。《憤怒的菩薩》是陳舜臣唯一以戰後台灣為背景創作的長篇推理小說,小說背景設定在1946年的台北新莊,也正是陳舜臣自日本回台的同一年。小說以「漢奸」問題引發的殺人事件為主題,勾勒出戰後初期台灣的社會樣態,以及台灣人面臨舊殖民者離去、新政權到來時的複雜情緒。
當初,企劃與編輯團隊是以「憂喜參半」的心情,看待手上挖掘出的這三本著作:一方面,眾人對於挖掘出以往少見的陳舜臣作品感到興奮;另方面,由於這三本作品的寫作體例、類型與故事主題差異甚大,編輯們擔心無法整合出一個引起讀者閱讀興趣的鮮明主題。但隨著編輯團隊也參與了紀錄片製作過程,逐漸能把握陳舜臣的生命經驗與創作特性,便一掃原有的憂心,我們將由《青雲之軸》、《憤怒的菩薩》、《半路上》組成的「大時代下的陳舜臣三部曲」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以陳舜臣筆下虛實交錯的「陳舜臣生命經驗」為核心內容,提供讀者一種可隨機運用閱讀方法與視角進入陳舜臣筆下時代故事的全新體驗。
當我撰寫這篇出版緣起時,記憶回到在神戶港邊的那個下午,而我的眼前也浮現起陳舜臣當年望著的那片海。在被國籍、身分及意識型態禁錮的時代,陳舜臣似乎知道那片海會帶著他到達想像力所能延伸最遠的地方,並且能連結他與各色各樣的人與故事。或許,我也是在海邊的那天成了陳舜臣手中拾起的那片「濕雪」,重新滾動起屬於他與我們及所有愛讀「故事」的人們的那顆「雪球」。如今這個「雪球」從我當初在神戶港邊的空想,已經越滾越大,不但一步步滾出一個包括「大時代下的陳舜臣三部曲」出版項目在內,結合出版、影像紀錄、文學活動、策展等等的跨界合作計畫,也滾出了一個難以定位的合作團隊,連結的網路由神戶、東京,擴及到台北、北京,而「大時代下的陳舜臣三部曲」的正式出版,將能讓這個繼續滾動的「雪球」留下一道最深刻的軌跡。
大時代下的身世飄零與歸屬——重訪陳舜臣
陳思宇(台灣大學歷史學博士、內容力營運企劃長)
那是2014年的一個炎熱夏日,當我拉著行李走出神戶三宮車站時,隨即湧現一種異樣的情緒,事實上這才是我第二次到神戶,非但無法說出眼前的街景與建築物名稱,如果不依賴手中的地圖與當地指標,也難以前往元町、南京町、海岸通、神戶港等地,但經過大半年閱讀陳舜臣的作品,卻似乎是來到一座熟悉的城市。
午後,往海邊走去,先參觀了位於南京町中華街附近的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陳舜臣筆下的華僑偵探陶展文,正是活躍於這個充滿各色人等的海岸地帶,而他家族的舊居「三色之家」也在附近。根據博物館人員的介紹,陳舜臣與司馬遼太郎常在博物館碰面閒談,館內還掛著一幅兩位文豪會面時的珍貴寫真。館方人員也告訴我,正在試營運階段的「陳舜臣亞細亞文藝館」離此地不遠,因此問明地址及方向後,便獨自前往位於神戶港埠頭附近的文藝館一探究竟!
當我在參觀陳舜臣寫作使用的工具與手寫原稿之際,不經意發現一份印刷資料,原來陳舜臣曾在神戶新聞及一份名為《陳舜臣中國圖書館》的刊物上,連載他的半生傳記。因此,我開始一篇篇細讀這份資料,而在那個下午,曾在閱讀過程中出現的疑惑,居然都有了初步的答案!陳舜臣在系列連載中,不但記錄家族從台灣移居神戶的發展,敘述自己在神戶的成長過程,也提及他跟台灣的文化與血脈因緣。令我感到驚訝的是,陳舜臣以相當多的篇幅,敘述戰後三年他的「台灣經驗」,包括他在台北及新莊當地的所見所聞、學校中的人事關係,在家鄉遭遇的另一種語言衝突等等。
由於時間已近閉館,而我尚未能消化手邊的閱讀資料,雖然無理但也只能碰碰運氣向志工們詢問是否能影印這份連載?有位志工伯伯突然拿出一本書,告訴我這系列連載日後已集結修改出版,成為他手上那本名為《半路上》的傳記著作!當我翻開書,內心實在百味交陳,因為這本書出版於2003年,算起來已有十年之久,但包括我在內的中文世界讀者、出版界、研究學者卻不曾聽聞或討論這本傳記,似乎代表陳舜臣確實已被眾人遺忘了!我試著想像,當時年近八十且因腦溢血而行動不便的作家,是以什麼心情寫下這份生涯紀錄?他將這本書定名為《半路上》,是因為胸懷未竟之志,而有繼續寫作的計畫?或是對自己走過的人生道路仍有未解的困惑?
記下手邊《半路上》一書的出版資料,匆匆謝過志工的幫忙後,我便離開文藝館,但望著神戶海邊的朗朗青空,思緒及心情卻有些混亂,因此隨手在路邊的自動販賣機按了罐冰可樂喝,順便整理一下腦中混亂的想法。思慮略為沉澱後,我在腦海中逐漸形成兩個構想:一方面,陳舜臣先生的生涯與他寫下的紀錄,確實有助中文世界讀者了解「在日台灣人」的歷史經驗,或許有機會能在台灣翻譯出版《半路上》;另方面,《半路上》實際上是一部「半生記」,陳舜臣雖在書中細數了他自出生到出道成為作家的點滴,但對後半生的記敘相對較少,讀者無法了解他為何在寫作黃金期,突然選擇加入中國籍,放棄了回台灣的機會?我想或許能透過拍攝紀錄片或傳記書寫的方式,補上一些空白,更清楚呈現陳舜臣先生走過的生命軌跡。
我當時已得知有日本及台灣的紀錄片團隊,正在拍攝以殖民時期台灣「日本語世代」及「在台出生日本人(灣生)」為主題的歷史紀錄片,但似乎都忽略了「在日台灣人」的歷史處境。但我認為,由於日本帝國力量在短期間由擴張到崩潰,導致大量人口必須在快速變化的界線中移動,各種身分及文化認同都處於極不穩定的狀態,但冷戰各方卻迅速建立意識型態的僵硬壁壘,瞬間阻擋了人群的移動,並且劃分出政治、語言、文化等各種界線,因此同時形成了如「日本語世代」、「灣生」或「在日台灣人」等身分群體。記得曾聽一位學者這麼形容:「日本語世代、灣生、在日台灣人,都算是習慣以日語溝通的『台灣人』!承載了複雜多變的東亞近代史。」無論此種說法是否適切,但我想,拍攝一部以陳舜臣生涯為主題的影像紀錄,應該能使台灣人或台灣史的圖像更為完整。
結束在關西的畢業旅行後,我回到東京,繼續完成手上的工作,再不久,便離開日本返回台灣,結束了在日本的「外國人生活」。在這段期間,我持續與幾個朋友討論如何完成整個計畫,最終,大家決定創立一間公司、一個團隊,跨出學界,到未曾涉足的市場上尋找完成計畫的各種資源。經由許多人的合作與努力,我們的計畫逐漸得到關鍵性的發展資源,並且逐漸發展出不同於其他內容製作計畫的特色。
整個計畫的核心精神與執行方向同時包含兩個內容:「大時代下的陳舜臣」與「陳舜臣筆下的時代故事」,即陳舜臣本人的故事與他筆下的創作作品。具體的內容呈現方式最初包含兩部分:影像紀錄與作品出版。然而,我們希望這是個具有生命力的企劃,而且深信故事內容所具有的潛力,必能不斷創造出足以展現內容的最佳形式。最初,我們也曾苦惱於如何定義、定位整個計畫,就如同我們難以辨識陳舜臣是台灣人?中國人?日本人?他的文學是台灣文學?日本文學或中國文學?如今則期待這個立體、具備延伸性、穿透性的內容創作及出版計畫,能夠不斷跨出既有的界線,開拓出更寬廣的想像空間。
2015年初,由於傳來陳舜臣先生去世的消息,促使我們加速推動計畫的腳步,由游擊文化主導的「大時代下的陳舜臣三部曲」出版專案成為第一個企劃完成並上市的項目。此一項目是以《半路上》一書的出版構想為原型,結合紀錄片田調活動,進一步發展出的「陳舜臣作品出版計畫」。在企劃紀錄片內容的研究階段,內容力企劃團隊與游擊文化的編輯團隊,便定期在獨立書店偵探書屋研讀陳舜臣的其他作品,希望進一步發掘企劃與編輯靈感,因此在《半路上》之外,又陸續挖掘了《青雲之軸》與《憤怒的菩薩》這兩部類型迥異的陳舜臣小說作品,並且與《半路上》一書組成三部曲。
《青雲之軸》是部自傳性小說,主角陳俊仁是以陳舜臣本人塑造的人物。故事始於主角幼時經歷的內外不同語言文化世界,觸及戰前台灣人在殖民母國遭受的歧視與戰爭經驗,最終結束於1945年8月15日,也正是陳舜臣失去「日本人」身分而成為「在日台灣人」的那天,以往並未見過其他作家曾嘗試類似的創作形式與主題。《憤怒的菩薩》是陳舜臣唯一以戰後台灣為背景創作的長篇推理小說,小說背景設定在1946年的台北新莊,也正是陳舜臣自日本回台的同一年。小說以「漢奸」問題引發的殺人事件為主題,勾勒出戰後初期台灣的社會樣態,以及台灣人面臨舊殖民者離去、新政權到來時的複雜情緒。
當初,企劃與編輯團隊是以「憂喜參半」的心情,看待手上挖掘出的這三本著作:一方面,眾人對於挖掘出以往少見的陳舜臣作品感到興奮;另方面,由於這三本作品的寫作體例、類型與故事主題差異甚大,編輯們擔心無法整合出一個引起讀者閱讀興趣的鮮明主題。但隨著編輯團隊也參與了紀錄片製作過程,逐漸能把握陳舜臣的生命經驗與創作特性,便一掃原有的憂心,我們將由《青雲之軸》、《憤怒的菩薩》、《半路上》組成的「大時代下的陳舜臣三部曲」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以陳舜臣筆下虛實交錯的「陳舜臣生命經驗」為核心內容,提供讀者一種可隨機運用閱讀方法與視角進入陳舜臣筆下時代故事的全新體驗。
當我撰寫這篇出版緣起時,記憶回到在神戶港邊的那個下午,而我的眼前也浮現起陳舜臣當年望著的那片海。在被國籍、身分及意識型態禁錮的時代,陳舜臣似乎知道那片海會帶著他到達想像力所能延伸最遠的地方,並且能連結他與各色各樣的人與故事。或許,我也是在海邊的那天成了陳舜臣手中拾起的那片「濕雪」,重新滾動起屬於他與我們及所有愛讀「故事」的人們的那顆「雪球」。如今這個「雪球」從我當初在神戶港邊的空想,已經越滾越大,不但一步步滾出一個包括「大時代下的陳舜臣三部曲」出版項目在內,結合出版、影像紀錄、文學活動、策展等等的跨界合作計畫,也滾出了一個難以定位的合作團隊,連結的網路由神戶、東京,擴及到台北、北京,而「大時代下的陳舜臣三部曲」的正式出版,將能讓這個繼續滾動的「雪球」留下一道最深刻的軌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