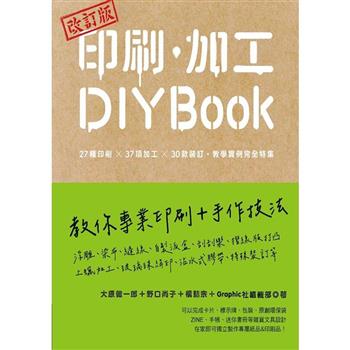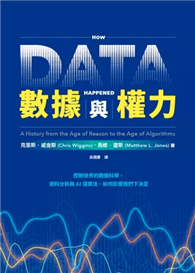從醬園弄到鹿港:詹周氏殺夫的跨國演繹 美國著名黑人女作家愛麗絲‧華克(Alice Walker)曾經這樣評價李昂發表於一九八三年的經典之作:「《殺夫》直面性別壓迫這一確鑿而普遍的社會現實,毫不諱言。李昂的寫作凝聚了女兒的情感投入和女性作家的社會責任感。」華克此言是就小說的英文版而論。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英文翻譯初版於一九八六年,對它的閱讀很快超越了學界和課堂,一時間使《殺夫》成為第三世界女性書寫的代表作 。譯本問世之初,評論家們聲稱,這個故事不管在任何時代、任何地點都有發生的可能,因為它描述的就是女性生活的一種普遍狀態。在《洛杉磯時報》的書評中,《殺夫》被稱作是「關於女性受到男性壓迫的最恐怖的小說」,而《亞洲週刊》的評論員則認為:「李昂所要表達的主題是在男權社會中,一位女性對實現自我價值的訴求」 。對於熟悉李昂的讀者來說,這些評論多少有點隔靴搔癢,但《殺夫》從八○年代初的台灣文壇一躍而起,借助葛浩文的英譯昇華為第三世界女性書寫的一個成功的範本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本文以李昂小說在海外的接受為始,關注的不是作品的普遍性,而是李昂寫作的歷史性和地域性,著眼點在文本背後跨越國族界限和文化溝壑的各種穿越和旅行。透過對「婦人殺夫」這個敘述原型在近半個世紀裡飄洋過海的轉寫歷程的描述,筆者力圖重新檢索文本的可攜帶性、可譯性和伸張性。《殺夫》作為一個女性書寫的範本,更可以用來重新檢視二十世紀華語文學寫作中處處埋伏的國族和文化的界限。在人和物都頻繁流通的年代,敘述和它的衍生體也可以裝在箱籠裡遊蕩,異地生根,外域的故事可以本土化,老舊的佚聞可借嶄新的面貌重現。可以說,跨時代、越國界的敘述演繹也是一個國家文學寫作史的重要脈絡,而殺夫本事近半世紀的演繹闡明的則是當代台灣文壇與民國上海文化史之間若即若離的關聯。要將這一關聯細緻地梳理出來,我們必須從六十多年前淪陷時期的上海說起。一、上海‧一九四五:殺夫案本事一九四五年春天的上海是殺夫案本事的發源地。三月二十日凌晨在一個普通的平民住宅區發生了一起兇殺案。第二天,對案件的最初報導出現在上海各個大報小報的版面上。這裡作為樣板的報紙是當時家喻戶曉的《申報》。《申報》創刊於一八七二年,到一九四五年已歷經七十餘年的風風雨雨,是民國上海的文字見證。自一九四一年底起,如同淪陷上海的其他出版物一般,《申報》也被日本占領勢力所掌控,它的頭版刊登的一律是大東亞戰事新聞,但翻到第二版的讀者仍能窺到老上海報紙的一貫面貌。對案件的報導即刊登在三月二十一日報紙的第二版,擠在五花八門的本埠新聞中,占著一個不起眼的位置。這則新聞的標題是〈新城警察分局破獲一起謀殺親夫案〉。剛發生的案件,標題裡已大言「破獲」,顯得有些急不可待。細看這草率的報導,短短幾句中已有諸多渲染的成份:本市新昌路四三二弄八五號,於昨晨發生一毒婦謀殺親夫血案,緣有該號後樓居戶詹雲影(三十歲,安徽人,業舊貨)被其妻詹周氏(廿九歲,浙江人)於昨晨未知何故,用切菜刀先砍頭部,繼砍額角及頸部,并連砍小腿大腿上股下肢腰部等十餘刀,將屍分成八段,裝入白色空皮箱中,企圖移屍滅跡。經二房東王燮陽發覺,將兇手詹周氏當場捕獲,扯交該管新成分局,該分局正縝密偵查中。 豆腐乾大小的報導夾雜在類似「每戶實行定量供煤」,「各區防空洞陸續修迄」,「對日包裹運價徵收附加費」,「空襲遇難者財產被用于學費補貼」等帶有非常時期特色的本埠新聞中。說「未知何故」,是因為事件剛發生,警察分局仍在「縝密偵查中」,可見詹周氏殺人動機未明。但為何砍殺的程序已如此清楚,先是頭部,然後是額、頸、腿?是詹周氏的供詞,還是二房東的推斷,抑或是寫作者的臆想?這裡的用辭亦十分蹊蹺。丈夫既是「親夫」,殺了「親夫」的妻子則必然是「毒婦」,加上「謀殺」、「血案」幾個詞,已是聳人聽聞,況且還有幾個視覺性極強的細節,比如屍體不多不少,分成八塊,裝入一個皮箱,皮箱又恰恰是白色的。短短的幾句,惜墨如金,卻又極盡描述。對細節的追蹤和渲染使這一則消息在整版的本埠新聞中一躍而出。接下來的幾天裡,詹周氏殺夫案迅速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各種上海小報更是找到了一個黃金契機,爭相以大版面對案情大肆渲染。更多真真假假的細節被曝光,比如,最初報導的分屍八塊被認為是不準確的,媒體眼中的詹周氏的狠毒在於將屍體分成了很多塊,乃所謂的「碎屍」,一說是十幾塊,一說是十六塊。為了強調事件的視覺性,各路報導還披露了犯罪事實被發現的詳細過程:砍殺導致血流如注,以致滲透了地板,樓下的二房東發現天花板上有血跡滴漏,於是起疑,繼而報警,終使詹周氏滅跡的企圖未能得逞。眾多報導的說辭又常常是互相矛盾的,比如屍體到底分成多少塊,詹周氏究竟砍了多少刀,皮箱究竟是甚麼顏色,是否乾脆就只是個藤箱而已,撲朔迷離,眾說紛紜,吊足了讀者的胃口 。小報上鬧得沸沸揚揚,《申報》在最初報導後卻選擇了沉默,五天後,終於也忍不住了,在第二版上發了一個追加報導,題為〈謀殺親夫案縝密偵察中〉:詹周氏謀殺親夫詹雲影慘案,兇犯經當場捕獲,屍首經法醫驗明,生前確係被人用切菜刀謀殺致死,並分屍十餘段放入灰色皮箱,企圖滅跡。死者已送普善山莊收殮,兇犯及嫌疑犯均由檢察署提審一過,准警局之申請,關押二星期繼續偵查在案。茲悉經辦該案之新成分局,於前日又拘獲兇犯姦夫賀賢惠(賀大麻子)。各犯尚無確切之供詞,正由探長王政惟縝密研審及搜集證據中。日來有一般好閒之徒,竟放謠言,有兇犯詹周氏遊街示眾之說,全屬無稽,當局甚望民眾勿輕信謠言,作無謂之虛擾,一俟當局偵查完竣,當可公開發表。 言簡意賅的段落,語氣謹慎有加,儼然是要堅守上海第一大報的姿態,表示與花花綠綠的小報不可同日而語。作者諄諄告誡民眾不能輕信謠言,警示媒體不得散佈無稽之談。但嚴詞之外,也不忘了對細節的追蹤。分屍八段修正成十餘段,白色皮箱換成灰色的除外,「姦夫」的出現也抓足了眼球。可見《申報》亦不能免俗,在對細節的熱衷上它與《海報》等各小報是一致的。在對案件的追蹤報導中上海媒體遇到的難題也是一致的。這難題的關鍵是,罪犯詹周氏相貌平平,毫無個人魅力可言,是一個再平常不過的市井婦人。此外,「姦夫」賀大麻子雖然被發掘出來了,他比詹周氏本人更不起眼,而且殺人動機與姦情絲毫無關,再追蹤下去必是死胡同一條。詹周氏本人和與她相關的人物是如此的缺少看點,媒體的注意力便集中在發掘案情的「奇」和「巧」上。一九四五年的這起兇殺案,之所以被認為「奇」,是因為案件竟然不涉姦情。如此慘烈的暴行背後竟沒有情色成份,可謂罕見,因而是「奇案」。而案件的「巧」乃在於那滲透樓板的血跡。沒有這一關節,沒有樓下愛管閒事的二房東,詹周氏或許早已清洗所有犯罪證據,對外宣稱丈夫失蹤,繼續過她的平常人的日子。媒體不斷渲染案情的「奇」和「巧」,持續營造事件的戲劇性,使得詹周氏手持菜刀砍下丈夫的頭、脖子和四肢的景象,在案件發生後的一個月中,躍然紙面,在讀者面前反覆上演。一個多月來《申報》基本上是沉默的,選擇不參與小報的喧嚷。它第三次開腔是在四月二十八日的第三版上刊發了一篇署名為姚炯的文章,題為〈取締黃色新聞〉:不久前發生的詹周氏斬殺親夫案,經各報揭載後,立刻傳遍了全上海,成為各種人茶餘酒後的閒談資料了。甚至竟有不肖之徒從中造謠,引得滿街滿弄人山人海似的立在街頭,希望一看兇手遊街的情形。於此可推測報紙揭新聞對於社會上大多數人民影響的巨大了,如果在這時候,被有組織的不肖份子利用為擾亂地方治安的工具,誠為不堪設想。照筆者的意見,報紙殊不宜發表此類案件,希望新聞檢查當局加以取締。 這裡已經沒有了細節,因為細節已被諸小報發掘殆盡了。詹周氏在上海灘已是家喻戶曉的人物,印有她和詹雲影、賀大麻子照片的宣傳資料幾乎人手一冊。《申報》要採取的便是另一種姿態。作者以衛道士咄咄逼人的口吻要求當局出面釐清混亂的場面,遏制「不肖之徒」。這裡不清楚的是,作者到底是要求當局取締諸小報呢,還是封鎖對詹周氏案件的報導?將上海各小報稱為「有組織的不肖份子」,將對案件的諸多報導上綱上線為「黃色新聞」未免出言毒辣,這本身是否亦有聳人聽聞的嫌疑?這裡的「黃色」究竟指的是甚麼?既然沒有情殺、姦殺的可能,何來的「黃色」?是否「黃色」已經成為所有「擾亂地方治安」的因素的標籤?既有「黃色」之嫌,則封殺勢在必行。危言聳聽的作者姚炯的背景已很難查詢,但從文中當可窺見詹周氏一案的轟動效應。顯然,《申報》所呼籲的新聞的取締並沒有發生。幾天後,詹周氏被判死刑。五月三日,上海地方法院刑事庭的一審裁決書在上海各大媒體上公佈,法律公文成了大上海無人不曉的公共閱覽資料。判決主文是短短的一句:「詹周氏殺人處死刑剝奪公權終身菜刀一把沒收」。這裡的亮點似乎是對菜刀作為殺人工具的強調。手持菜刀的「毒婦」詹周氏無疑已經成為那一年上海深入人心的公眾形象。這份法律文件值得細細研讀,其語言風格混雜,讀起來半文半白,然而故事性極強,敘述延伸的可能性甚大,比如這一節:周氏以遇人不淑,夜不成寐,感慨身世,頓起殺機,於是乘雲影酣睡之際,離床啟屜,覓取菜刀,猛砍雲影頸部,雲影痛極狂呼,聲震屋宇,同居王燮陽驚問事由,周氏諉稱其夫夢囈,以想掩飾,其後復連砍六七刀斃命,又恐事發,因支解屍體成十六塊,密藏皮箱中,冀圖湮滅罪證,血流下注,為同居王陳氏發覺。 如此形象的文字出現在法院的告示中似乎有點出人意料之外,可見一個多月來爆發性的公眾輿論已經深入到司法制度的運作中。法律文書的書寫者難抑其憤慨,更有類似「房幃喋血,情無可原,而分屍成塊,殘忍尤烈」的句子,最後說「應以殺人罪之重罪處斷」,是刑事訴訟,更像是道德審判,針對的是一個多月來左右人們飯後談資的公眾輿論 。此份讀起來頗是縮印版公案故事的法政文件何其珍貴,正是在這裡我們找到了詹周氏殺夫案幾十年演繹的雛形。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台灣文學學報第18期(POD)的圖書 |
 |
台灣文學學報第18期(POD) 出版社: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出版日期:2011-06-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37 |
中文書 |
$ 238 |
華文文學研究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台灣文學學報第18期(POD)
台灣文學學報第18期
文化發展的趨勢,往往能夠反映國家的實力與智慧。構成台灣文化最基本的思考之一,當推台灣文學這門學術領域。《台灣文學學報》每期皆收入了台灣文學研究的精彩文章。
章節試閱
從醬園弄到鹿港:詹周氏殺夫的跨國演繹 美國著名黑人女作家愛麗絲‧華克(Alice Walker)曾經這樣評價李昂發表於一九八三年的經典之作:「《殺夫》直面性別壓迫這一確鑿而普遍的社會現實,毫不諱言。李昂的寫作凝聚了女兒的情感投入和女性作家的社會責任感。」華克此言是就小說的英文版而論。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英文翻譯初版於一九八六年,對它的閱讀很快超越了學界和課堂,一時間使《殺夫》成為第三世界女性書寫的代表作 。譯本問世之初,評論家們聲稱,這個故事不管在任何時代、任何地點都有發生的可能,因為它描述的就是女性生...
»看全部
目錄
◆一般論文從醬園弄到鹿港:詹周氏殺夫的跨國演繹 黃心村日據末期小說的「發展型」敘事與人物「新生」的意義 崔末順台灣社會「立字」形成的鏡與燈 ──「省政文藝叢書」中的現代化變遷 郭澤寬失落的「新村」?楊逵、田中保男和入田春彥的文學交誼與思想實踐 陳淑容試探曾貴海詩中的原住民書寫 簡銘宏《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九期稿約《台灣文學學報》撰稿體例《台灣文學學報》目錄索引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出版社: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出版日期:2011-06-01 ISBN/ISSN:716081692018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華文文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