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華語電影研究學者白睿文從2000年代初即開始訪談各個領域的創作人,對象從導演到作家,又從音樂家到藝術家,二十餘年間,漸漸累積成為一個宏大的文化口述史。「白睿文訪談錄」就是從這些訪談中萃取出來的精華。
繼前幾冊對賈樟柯、崔子恩乃至各個華語電影人的對談後,《字裡行間:華人作家對談錄》收錄的是白睿文與華人作家的對話,因訪談內容豐富,又分為《字裡行間:華人作家對談錄‧中國及海外卷》與《字裡行間:華人作家對談錄‧台灣卷》兩部,收錄〈中國文學的寫實與魔幻〉、〈華文創作的國際視野〉、〈島嶼談藝錄〉三輯共二十篇採訪紀錄,組合成「白睿文訪談錄」的第四和第五部。「中國及海外卷」受訪者包含閻連科、王安憶、方方、麥家、劉慈欣、韓松、高行健、哈金、張翎、虹影、薛憶溈、盧新華。
透過深度訪談,讓讀者追隨作者們的閱讀和寫作的旅程,了解他們天馬行空的想像力是從何處而來,聆聽他們作品中從沒有說出的祕密。本書收集的對談錄不是集中而是雜散,受訪的作家來自不同的地方,代表不同的輩分,作品也呈現不同的視角和文類,包括政治小說、同志小說、歷史小說、科幻小說、後現代小說、紀實文學、懸疑小說……等等,同時還包括彼此殊異的文學觀,但放在一起,足以見證華人作家的多元性和眾聲喧嘩。
作者簡介:
白睿文(Michael Berry)
1974年於美國芝加哥出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現代中國文學與電影博士。現職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亞洲語言文化教授兼任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當代華語文學、電影、流行文化和翻譯學。
著作包括《光影言語:當代華語片導演訪談錄》、《痛史:現代華語文學與電影的歷史創傷》、《鄉關何處:賈樟柯的故鄉三部曲》、《煮海時光:侯孝賢的光影記憶》、《電影的口音:賈樟柯談賈樟柯》、《丑角登場:崔子恩的酷兒影像》、《畫外音:當代華語片影人對談錄》。編著包括《霧社事件:台灣歷史與文化讀本》、《重返現代》等書。
中英譯作包括王安憶《長恨歌》(2008)、葉兆言《一九三七年的愛情》(2003)、余華《活著》(2004)、張大春《我妹妹》與《野孩子》(2000),舞鶴《餘生》(2017)以及方方的《武漢日記》(2020)、《軟埋》(2025)、《奔跑的火光》等書。2023年榮獲古根漢獎、2021年榮獲台灣文化部文協獎章、2009年獲得現代語言協會(MLA)最佳翻譯獎的榮譽提名。曾擔任金馬獎評審(2010、2018)、紅樓夢獎評審(2012-2018)和香港「鮮浪潮」國際短片展(2013)評審。也曾為《新京報》和「中國電影導演協會」撰寫專欄。
章節試閱
〈方方:歷史記憶的軟埋與甦醒〉(節選)
以文學關懷女性的處境
2022年很多媒體在報導陝西「鐵籠女」的遭遇。幾十年以來,您的文學作品裡一直在探索中國女性在社會上的各種掙扎、剝削和悲慘故事。《落日》、〈奔跑的火光〉、〈閉上眼睛就是天黑〉等作品都在探索女性在當代社會的位置和命運。很多人以為隨著經濟改革,女性生活上的條件會自然提高,但看了〈奔跑的火光〉等作品之後,便會發現「金錢」有時候也會變成一種枷鎖。幾十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一直在加速。通過您的文學創作,您如何綜合經濟發展」跟「女性的命運」之間的張力?
是的。我的確關注女性的命運。在中國,有著幾千年重男輕女的歷史。近一百年的婦女解放運動使女性命運有了莫大的改變,但沉重的歷史負擔和深刻的社會烙印,想要完全去掉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城市婦女和農村婦女之間的距離仍然相隔千年。如果將金錢或是拜金,視為一種枷鎖,我以為這個枷鎖其實是沒有性別亦沒有國別之差的。它幾乎可以成為所有人的枷鎖。而在貧困落後的中國鄉村,我想當婦女開始重視甚至追逐金錢時,其實是她們嘗試擺脫命運、為自己而活著的開始。對於中國婦女來說,經濟獨立是她們人生走出黑暗的最初一步,也是至關重要的一步。至少在現階段,金錢尚不是枷鎖,而是她努力跟上時代步伐的墊腳石。經濟發展,只會改變女性的命運,它們之間應該不存在張力。
(……)
〈奔跑的火光〉的創作背景很有趣,是當時為電視欄目《命案十三宗》擔任編劇,在其過程中您到了監獄跟十三位殺人犯進行面對面的採訪。《命案十三宗》是您自己提出的一個項目,還是高群書導演提的案子?可以介紹這個節目的背景嗎?
在此前,我曾經與高群書導演合作過一次。不過那次是我應一位朋友之約幫忙修改電視劇本。高群書是那部電視劇的副導演。因為合作愉快,他從北京回到石家莊,到監獄採訪了一些殺人犯,便產生拍一部類似紀實電視劇的想法。他從已知的案例中挑選了十三個犯人,邀請我參與編劇。因為之前有過合作,加上那時的小說稿酬很低,我也需要電視劇稿酬來改善生活,所以便答應了。這部電視劇是系列劇,其實就是一案一劇,共十三部,按劇情需要來確定每個案例需要拍幾集。十三個犯人,是他們篩選過的,也得到了監獄方面的同意。我到了石家莊後,便投入了採訪。他們全程錄影,後來播出的電視劇,每個案子開頭都有提問,基本上都是我的聲音。
採訪一結束便進入編劇環節,他們的時間要求非常急。幾乎幾天就要拍一部劇。當時我尚是《今日名流》雜誌的社長兼主編,雜誌正面臨一些問題,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我完全不可能幾天完成一個案子的劇本。而且我的寫作習慣也不適應如此快速地完成一個作品。在寫完第一部後,我表示實在趕不過來。好在我採訪過程有著完整的錄音和錄影,他們就另外請人寫了劇本。這部劇什麼時候拍完的以及什麼時候播出的,我都不知道。之後我斷續看過一、兩集,並沒有看完。
當您第一次踏入監獄進行採訪,您有什麼樣的感觸?
剛開始多少有些緊張不安。我不僅是第一次走進監獄,更是第一次接觸犯人。尤其是我採訪的第一個犯人,是一個年輕的東北男人,殺過兩個人。他是所有犯人中唯一的一個不是在偶然中殺人的犯人,他在殺第二個人的時候是有過精心策劃的。在採訪此人時,剛開始,獄警和攝影師都同在房間裡,但隨著採訪時間變長,天氣很熱,室內又沒有空調電扇,他們待不下去,都跑到室外去聊天。於是房間裡就只剩下我和犯人兩個人。
這是一個即將被槍斃的犯人,與我面對面坐著,我們之間的距離大約只有兩公尺左右,他如果要挾持我,是一件很輕易的事。我腦子冒出這個念頭後,就一直有恐怖感。一邊提問,一邊不停自己對自己作心理建設,強行鎮定自己,向他發問。這段時間大約有四十分鐘以上,後來有人進來後,我才鬆了一口氣。
這是唯一的一次,到後面,房間裡有空調,攝影人員就再沒有出去。採訪人數多了,基本上就和其他採訪沒什麼太大差異了。儘管那些人都是殺人犯,但其實在生活中也是普通不過的人。
採訪過程中您遇到什麼樣的挑戰?從精神上直面這些慘案和悲劇,一定是跟普通的「採訪」很不一樣吧?
最大的挑戰就是我上面講述的那一次。而且那是我採訪的第一個犯人。
以前留在我印象中的殺人犯就是比較兇殘的人。但是實際上我採訪的這十三個人中,大多在日常生活中反而都活得比較窩囊,有的人甚至十分軟弱無能。而且很奇怪的就是,有好幾個在殺人時,就是順手拿身邊的水果刀捅人,然後就一刀斃命。我和高群書他們還為此探討過幾次,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不過,他們也都是在為自己殺人找開脫的理由。唯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在〈水隨天去〉小說中的原型人物: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小男孩。他為了所愛的女人殺了她的丈夫。他得知我也採訪了那個女人,採訪結束時,他反覆強調,這件事是他一個人做的,與那個女人完全無關。甚至還可憐巴巴地問我,你見過她,她還好嗎?我好想她。坦率地說,那天我的心情是很複雜的。直面人性中的陰暗,會讓人有很不舒服的感覺。
(……)
小說〈奔跑的火光〉中的英芝跟原型的真人真事有什麼不一樣?可以談談這個改寫的過程嗎?您是否把您採訪的不同人物的性格或細節放在一起,來塑造新的人物?
〈奔跑的火光〉是我的這一系列小說中,最接近原型的一部,並沒有把其他採訪的人物放進小說,而是將原來故事中的人物進行了一些改造,並且把故事發生的場景放在了南方。像小說中的,英芝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婚前有孕後,不得不嫁人。丈夫婚後,比較貪玩,賭博、無事業,也不幹農活,她生了孩子後,公婆對她也不是太好。她不想與公婆住在一起,想要蓋一幢自己獨立的房子。此外,她的私生活不檢點,在外面有相好。受丈夫家暴後,逃了出去,被娘家人勸了回來。回到婆家後,仍然被家暴,於是再次逃跑。逃跑之後,在船上混了一段時間,又回到娘家。娘家人告訴她,她的丈夫來這裡燒過家裡的房子。她的丈夫聽到她回到了娘家,又拎著汽油追到她家。被她家裡的幾個兄弟制服後,將她的丈夫捆在樹上。她的丈夫不停地罵她,她一怒之下,將丈夫拎來的汽油潑到他身上,想都沒有想就點著了火。大火將繩子燒斷,她丈夫帶著全身的火追逐她,而她母親在半路遇到,將她丈夫攔了下來,結果她丈夫轟然倒下並且把她母親燒成重傷,搶救後還是死亡……等等,這些小說中很重要的情節遞進,都是原型人物真實發生的。
但是,其中的生活內容,以及人物如何走到那一步、遇到哪些事、和第三者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相遇,以及生活場景和發生矛盾的細節等等,卻是我虛構的。這就是我前面所說,我不瞭解北方鄉村的生活,我把人物放入了南方的鄉村,並且我按人物生活中應該有的邏輯,給了他們各自不同的性格。當然,有些我認識的人物性格我放了上去。像鄉村的唱歌班子,是我陪雜誌社司機回鄉參加他家親戚婚禮時所看到的。於是我對他們進行了一些採訪。鄉村唱歌班這個是我以往素材的積累,我覺得很契合小說中的人物,也能很好地展現當代的鄉村生活。而這個是原型人物生活中所沒有的。
〈奔跑的火光〉所呈現的「道德觀」比較複雜,您完全拋開所謂「黑白分明」的寫作策略,而呈現的人物充滿了矛盾和複雜性。您自己怎麼看英芝這個人物?
的確,英芝這個人物是很複雜的。尤其在農村,女人的處境經常是很尷尬的。有老話這樣說,嫁出去的女,潑出去的水。女兒離開父母家,如同水潑出去一樣,不會再回得來。所以,一個家庭,女兒總是外人,如果家裡有什麼祖傳秘方,也是傳媳不傳女的。可是嫁到別人家去的女兒,離開自己生活了十幾年或二十幾年的地方,換到一個全新的環境裡,僅靠一紙婚書,不可能讓她內心很快與新家融合起來。女人到二十歲左右的時候就被從原來的土地上拔出來放到陌生的地方,尤其是放入一個大家庭中,她要融入卻並不是件容易的事。至少她的心靈深處,很難認同這就是自己的家──除非她的小家不和公婆共住一起。但在中國農村,嫁出去的女兒多是和夫家的大家庭混居在一起。在這樣的背景下,女人看上去有了家,但在內心中她們卻是沒有家園的。甚至,她會在整個世界都找不到家園的感覺。潑她出來的娘家不要她們了,而婆家在短時間內又融不進去。這是她們的一段真空時間。在這時間裡,她們的內心裡空空蕩蕩。
英芝就是處在這種狀態之下的女人。中國一句老話,叫作「多年的媳婦熬成婆」,也就是說,你只有等你的兒子結婚娶了媳婦,你才算熬出頭來。很多媳婦就是這樣熬著,但英芝卻不願意這種長久的等待。她是新型的女性,期待自己有獨立的空間。她想有一幢屬於自己的房子,想要有自己獨立的小家庭。為了這個目的,她什麼事都可以做,並且什麼都敢放棄,甚至操守、尊嚴、名譽等等。她用盡辦法,進行抗爭。最終,她還是失敗了。她被公婆欺凌,被丈夫毆打。她逃出去流浪,也回到娘家。而娘家的人,卻覺得你應該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你還是應該回去跟他生活。她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最後選擇了殺夫。一把火把她的丈夫燒死了。
這是一種慘烈的反抗。是兩敗俱傷的結局。在我眼裡,英芝是中國鄉村中正在成長的新型女性,她們在蛻變、在抗爭,只是因為各種侷限,包括她們自己的侷限,導致這種抗爭的失敗和慘烈。二十多年過去了,中國鄉村的英芝已經少了很多。
從初版到現在,二十五年已經過去了。您曾經寫過一篇短文〈我們生活中有多少英芝?〉;2022年徐州「鐵鍊女」的報導震動全中國,我看了之後也不得不想到英芝。在這二十五年以來,中國女性在社會上的位置經過什麼樣的改變?
中國女性的命運,城市和鄉村是必須分開來說的。在城市,女性基本獨立,她們的生活方式和心態與西方其他國家大體已相近。究其原因,還是城市女性受教育範圍廣、受教育程度高。而在農村,女性地位的改變速度要慢得多。究其原因,還是得歸結到受教育程度低上面。這是一個綜合性的困境。除了農村重男輕女的觀念嚴重之外,貧窮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農民家庭貧困數多,在財力不足的情況下,供孩子上學,優先的仍是男孩。目前儘管已經比英芝生活的年代進步了很多,但是鄉村女性還處於蛻變的過程中。像鐵鍊女這樣的情況,尤其是女子在鄉村受虐,村民們視而不見且不救助的情況,也並不算少。中國重男輕女的舊傳統維繫時間太久,鄉村女性完成蛻變還得多久,真不知道。
《武漢日記》與真假倒錯風波
在《軟埋》裡,保留歷史記憶的器具就是青林父親當年留下來的日記──日記就是歷史記憶的載體。沒想到您自己在2020年武漢封城期間也是因為一本「日記」而引起一場風波。很微妙,前者是個虛構的故事,但有人攻擊您說,《軟埋》這部小說是「對土改的反攻倒算」;後者反而是個真實紀錄,但有人攻擊它是「造謠日記」、「道聽塗說」。剛好兩本書都被顛
倒:小說被讀成歷史,歷史被讀成小說,而兩本書都圍繞著「日記」。您如何看《軟埋》和《武漢日記》被攻擊後的這種「真假顛倒」的荒謬關係?
您的這種理解非常獨特,也非常奇妙。尤其是這一句:「剛好兩本書都被顛倒:小說被讀成歷史,歷史被讀成小說。」果真就是這樣。兩本書的風波,都在我意料之外。我完全沒有想到一部小說和一部疫情紀錄會引發如此的爭議。其實,細想也很簡單,因為率先攻擊《武漢日記》的那波人,正是之前攻擊《軟埋》的人。後一場風波,只不過是前一場風波的延續而已。兩場風波提出的命題均是無中生有,甚至是構陷和誣衊。在中國,有相當一部分人,他們擁戴專制,臣服權力,習慣鬥爭,對所有與他們觀點不同的人,均不包容,並扣以政治大帽。他們反文明反民主反人道反常識,像土改運動那樣的做法,以及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社會,是他們所贊同並想要的。而這些,正是我在反思並且極力抵制的。我與他們的判斷完全不同,所以在我看來,他們批判我的作品,是件很正常的事。而中國官方卻與他們相呼應,以行政手段封禁我的書,連帶著剝奪我所有作品的發表權和出版權。在一個是非顛倒的社會,他們有這樣顛倒的認知,也就不足為怪了。
需要多說幾句的是:與其他國家的作家相比,中國作家的寫作要多一重任務,那就是他們得不斷地嘗試題材的邊界。四周都是雷區,你不知道哪裡埋有炸雷。大家小心翼翼地試探、戰戰兢兢地摸索,也許能僥倖繞過或是擴大寫作的區域,但更可能一個不小心就引爆了雷區。我這兩部作品,大概都是引爆了雷區吧。
我們當初認識是因為我翻譯您2016年的長篇小說《軟埋》。這本書引起不少的爭議,後來因為一系列攻擊帶來一場政治風波,本書最終在中國境內遭禁。後來2020年的《武漢日記》又引起更大的一場社會和政治上的風波。經過這些事情之後,是否讓您重新思考文學的社會意義?經過這場政治洗禮之後,您依然相信文學的力量嗎?
我個人是處於風波中心,其實最初我也非常不解。因為所有攻擊我的內容,以及強加於我的罪名,都不存在。《軟埋》是虛構作品,它主要寫人在歷史事件中的命運,並沒有去評價歷史事件本身;《武漢日記》是非虛構作品,是現場的即時記錄,它本就是有所聞有所感,無一謠言。我完全不明白,這樣的作品為什麼會引發如此大一場風波。當然,像前面說的,這兩部書的批判者是同一批人。我推測,在他們批判《軟埋》時,我進行了激烈地反抗,這個反抗也為之後批判《武漢日記》埋下了伏筆。當武漢爆發疫情後,大約在我記錄了十來天時,就有人開始對我的記錄進行攻擊了。而第一個正式撰文批判我的人,便是一個曾經寫過九篇文章批《軟埋》的人。
我不需要思考文學的社會意義。文學經歷千年,一直有著它獨特的魅力,無論世事如何變化,它的社會意義一直都在那裡。只是人們如何閱讀它而已。至於我的個人是否相信文學的力量,以前不曾思考過這個問題,或者說,不曾深刻思考過。但經歷這次疫情,反而有了新的感受,那種以前從未有過的感受。記得武漢正處於疫情中的時候,一位作家朋友給我打電話說:「你知道嗎?人們像追電視劇一樣每夜追著閱讀你的日記,文字從來享受沒有過這樣的待遇。」當時的我,還不知道我的紀錄有這麼多人閱讀。我非常驚訝。後來,我聽說每天有幾千萬人半夜等著讀方方日記,甚至有過專業統計,說當時的閱讀者上億。我真是驚呆了。直到現在,還有無數陌生人見到我,開口就會說,「那時候,我們每天夜晚等著你的日記發表,只有看到你的日記,才會安心。」也有說,「我們靠著你的日記,度過最艱難時光。」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那應該是我一生的榮耀。我對文學力量的相信,正是來自這些讀者。我的文字安撫過他們,並給予過他們力量。這就足夠了。
(……)
〈方方:歷史記憶的軟埋與甦醒〉(節選)
以文學關懷女性的處境
2022年很多媒體在報導陝西「鐵籠女」的遭遇。幾十年以來,您的文學作品裡一直在探索中國女性在社會上的各種掙扎、剝削和悲慘故事。《落日》、〈奔跑的火光〉、〈閉上眼睛就是天黑〉等作品都在探索女性在當代社會的位置和命運。很多人以為隨著經濟改革,女性生活上的條件會自然提高,但看了〈奔跑的火光〉等作品之後,便會發現「金錢」有時候也會變成一種枷鎖。幾十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一直在加速。通過您的文學創作,您如何綜合經濟發展」跟「女性的命運」...
作者序
〈總序 談中得來〉
二十多年以來,除了學術研究和文學翻譯之外,我的另外一個學術方向就是文化口述歷史。初始的動機是因為我發現我所研究的領域特別缺少這方面的第一手資料。當時除了記者針對某一個具體的文化事件或為了宣傳一部新作品以外,比較有深度而有參考價值的口述資料非常少。但不管是從研究的角度來看或從教學的角度來考量,我總覺得聆聽創作人自己的敘述,是了解其作品最直接而最有洞察力的取徑。當然除了作品本身,這些訪談錄也可以幫我們理解藝術家的成長背景、創作過程,以及他們所處在的歷史脈絡和面臨的特殊挑戰。
當我還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便已經開始與各界文化人進行對談或訪問。一開始是應美國《柿子》(Persimmon)雜誌社的邀請,他們約稿我訪問資深翻譯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中國作家徐曉等人。我後來在紐約經常被邀請替很多大陸和台灣來的作家和導演擔任口譯。跟這些創作人熟了之後,除了口譯我也開始私下約他們談;這樣一個長達二十多年的訪談旅程就開始了。我當時把我跟侯孝賢、賈樟柯等導演的訪談錄刊登在美國各個電影刊物,包括林肯中心電影社主編的《電影評論》(Film Comment)雜誌。後來這些訪談很自然地變成我學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光影言語:當代華語片導演訪談錄》是我出版的第一本對談集,該書收集了我跟二十位資深電影人的對談錄。後來又針對侯孝賢導演出了一本長篇訪談錄《煮海時光:侯孝賢的光影記憶》。實際上,從1998年至今,我採訪各界文化人的計畫一直沒有間斷,從導演到作家,又從音樂家到藝術家,一直默默地在做,而且時間久了,就像愚公移山一樣,本來屬於我個人的、一個小小的訪談計畫,漸漸變成一個龐大的文化口述史項目。之前只刊登有小小的一部分內容,它就像冰山的一角,但大部分的口述資料一直未公開曝光,直到現在。
這一套書收錄的內容非常廣泛,從我跟賈樟柯導演的長篇訪談錄到崔子恩導演對中國酷兒電影的紀錄,從中國大陸的獨立電影導演到台灣電影黃金時代的見證人,從電影到文學,從音樂到舞蹈,又從建築到崑曲。希望加在一起,這些採訪可以見證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社會和文化轉變。它最終表現的不是一個宏觀的大歷史,而是從不同個人的獨特視角呈現一種眾聲喧嘩,百家爭鳴的文化視野。雖然內容很雜,訪談錄的好處是這個形式平易近人、不加文飾,可以深入淺出,非常直接地呈現創作人的創作初衷和心路歷程。從進行採訪到後來的整理過程中,我始終從各位前輩的創作人身上學到很多,而且每當重看訪談錄總會有新的發現。因為秀威的支持,這些多年以來一直放在抽屜裡的寶貴的採訪資料終於可以見天明。也希望台灣的讀者可以從這些訪談中獲得一些啟發。
生命一直在燃燒中,人一個一個都在離去。我們始終無法抓住,但在有限的人生中,可以盡量保存一些記憶和歷史紀錄留給後人。這一系列就是我為了保存文化記憶出的一份小小的力。是為序。
〈推薦序 當代作家,眾聲喧「華」〉
文/王德威
白睿文(Michael Berry)是當代英語世界裡最重要的學者之一。他的專著《痛史:現代華語文學與電影的歷史創傷》(A History of Pain: Trauma in Modem Chinese Fiction and Film, 2016)縱論20世紀中國與華語世界的暴力與傷害,以及文學與電影作為見證不義、救贖傷痕的方法,出版即贏得廣泛關注。行有餘力,白睿文致力翻譯兩岸四地名家作品,從王安憶《長恨歌》到余華《活著》;從張大春《野孩子》、《我妹妹》到舞鶴《餘生》,再到近期方方的《軟埋》、韓松「醫院三部曲」,都出自他的筆下。除此,白睿文長期關注當代華語世界電影及通俗文化,推介賈樟柯、侯孝賢、張藝謀作品不遺餘力。他的識見與活力遠遠超過一般認知的學院型教授,堪稱一位眼光獨到的公共知識分子。
白睿文還與作家、學者、導演多有往來,每每把握機會,與他們深度對談,從個人作品到時代觀察,從成長經驗到工作甘苦,包羅廣闊但又不脫本行專業。這些對話不僅帶有鮮活的個人風采,也銘刻了一時一地的現場感;更重要的,為一個劇烈變動的文字與媒體時代,留下珍貴紀錄,饒富歷史興味。白睿文與侯孝賢的訪談專著《煮海時光:侯孝賢的光影記憶》(2014),與有關賈樟柯電影的兩本著作《鄉關何處:賈樟柯的故鄉三部曲》(2010)和《電影的口音:賈樟柯談賈樟柯》(2021)堪稱認識這兩位導演的最佳入門資料。《光影言語:當代華語片導演訪談錄》(2007)則呈現兩岸三地二十位導演──謝晉、田壯壯、陳凱歌、李安、蔡明亮、楊德昌、許鞍華、陳果、陳可辛……──的對話,儼然是當代華語影壇點將錄。
是在這樣的語境裡,《字裡行間:華語作家對談錄》的出版更顯別具意義。這部對談集分為三部分,〈中國文學的寫實與魔幻〉、〈華文創作的國際視野〉、〈島嶼談藝錄〉。二十位背景、年齡、風格、立場各異的作家各就所長,暢所欲言。其中包括諾貝爾獎得主高行健,卡夫卡獎得主閻連科,當代科幻風雲人物劉慈欣、韓松,華裔英語小說第一人哈金,台灣文壇中堅駱以軍、吳明益,雲門創始人林懷民,還有「永遠的白先勇」。
這部訪問集意義獨特,不僅因白睿文有緣結識當代中國與華語世界的重量級作者,傾聽他們的願景與挫折,暢談文學的前世與今生,更因訪談所涉及的知識與言語造詣,遠超過此前的電影導演訪談錄。電影訴諸聲光色相,而文學是文字方塊的結晶。如何「繪影形聲」、有賴無中生有的想像力,以及觸類旁通的歷史感。這對成長於中文語境裡的讀者而言,已經是項挑戰,更何況白睿文這樣的非華裔學者。
《字裡行間》呈現作者對現當代中國文學脈絡的全盤掌握,對受訪作家、作品的深入傾聽、閱讀,以及對作家、作品,與他們所置身環境的「同情的理解」,在在令人驚豔。白睿文的中文了得,聽說讀寫俱佳,既能與作家閒話家常,也不避敏感話題。環顧當下漢學界,具有如此能量者幾希!
其次,白睿文訪談的作家來自四面八方,突顯了他對當代中文文學開闊的視野與包容力。20世紀中以降,海峽兩岸分為不同傳統,各自經歷起伏;久而久之,學界文壇各自為政,少有交集。白睿文這一輩學者因緣際會,不僅來往兩岸四地,學習、感受不同語境裡的文學脈動,也妥為利用「華夷」兼容的背景,從外部提供閱讀視角,鬆動內部的定見或成見。
訪談錄的軌跡將讀者帶向法國的高行健,加拿大的張翎;上海的王安憶,花蓮的吳明益;「西夏旅館」裡的駱以軍,外太空以外的劉慈欣。白睿文穿梭來往不同的世界,也啟發了不同的視界。將這三部訪問集合而觀之,我們不禁感嘆,當各地學者、讀者為文學的身分、認同、正統爭辯的不亦樂乎時,白睿文這樣的「老外」放眼天下,早已提出「眾聲喧『華』」才是文學的硬道理。
第三,在國族和身分辯證以外,白睿文和受訪的作家頻頻觸及「文學何為?」的命題。這自然是大哉問,但也是任何文學作者和讀者無從規避的話題。當代文化傳媒千變萬化,文學的影響看似式微。弔詭的是,文學失去了上世紀──尤其是五四──的焦點位置,或文化、政治建制的青睞,反而獲得了空前解放。作家馳騁在文字建構與解構的天地裡,言說那不可說的,看見那不可見的,想像那不可想像的,如此「肆無忌憚」,卻令人心有戚戚焉。他們證明了「文字」這最古老的傳媒魅力依然無窮。王安憶談日日寫作有如鍛煉,白先勇談《紅樓夢》歷久彌新的靈感啟發,虹影談歷史經驗與文字想像的奇妙置換,韓松談科幻的幽暗辯證法,陳思宏談文字永遠都在「鬧鬼」……,凡此皆令我們理解文字的千變萬化,招魂或驅魅的力道一如既往。
2013年,共和國領導人提出「講好中國故事」作為治國指標,不禁令人莞爾:曾幾何時,文學虛構敘事──尤其是講「好」故事──成為一切價值的樞紐:「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要圍繞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多個視角進行深入研究……」。但什麼是「好」的故事,如何「講好」,耐人尋味。如果將「中國」二字換成「台灣」,彼岸「講好故事」的公式在此岸不是如出一轍?
白睿文訪問對象中不乏「講不好」故事的作家。旅法的高行健以《靈山》、《一個人的聖經》探索一代中國人歷經種種傷痕,如何重新安頓自己的心路與身路歷程;旅美的哈金見證天安門事件後選擇以英文敘說那不能說的中國故事。兩人因此無緣再踏上曾經的祖國土地。另一方面,閻連科因為《為人民服務》、《炸裂志》等一系列的荒誕「神實主義」作品,遭到全面封殺。而方方則因為《軟埋》、《武漢日記》等反思歷史、暴露現狀的書寫,成為國民公敵。這些作家對中國深情款款,卻對一黨一派的政治難以苟同。他們藉文學觀察,思考,批判,也因此遭到放逐或迫害。比起共和國、民國或更早的文人前輩,他們所經受的考驗未必更為深痛,但所代表的文學氣度和信念,卻同樣歷久而彌新。
據此,白睿文的訪問錄促使我們再思「當代」文學的定義。「當代」指涉日新又新的此刻當下,或中國共產論述對1949之後歷史階段的命名。但受訪作家所示範的「當代」感更指涉一種敏銳的、具有批判力的時間意識,而這樣的時間意識恰恰來自作家面對歷史大勢或主流,種種的「不合時宜」(untimely)。唯其因為小說家審時度勢,洞若觀火,他們創造的世界總是夾處在多層時間皺褶中,也許來得太早,也許太遲;也許還沒到來就已經過去,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沈從文《邊城》語。)
這樣的「當代」觀讓我們想到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對歷史和時間的看法:歷史過去的某一個時刻,因緣際會,與此刻當下相遇,並產生了一種爆炸性過去所蘊藏的力量,居然在某一刻的「今天」、「現在」爆發出來,賦予我們新鮮的、震撼的「革命」感。阿岡本(Giorgio Agamben)的論述也可以帶來啟發:所謂當代感,就是時間皺褶中所發生的「不合時宜」的現象;就是從直面現實,在光明中看到黑暗,而在黑暗中反而看見不能逼視的光束的能量。更有意義的是魯迅所言:當代作家緊緊逼視他的時代,「自在暗中,看一切暗」(〈夜頌〉),他們的作品乃能發散灼熱的「黑暗之光」(beam from darkness)。
於是,白睿文從作家對談中看到如下奇觀:劉慈欣《三體》預言外星三體人入侵,人類文明必將覆亡;吳明益從「複眼人」無所不在的透視──或窺視──裡,幽幽訴說人類命運的殊途同歸;盧新華漂流海外,依舊舔舐四十年前文革難以癒合的傷痕,舞鶴徘徊霧社泰雅族抗暴事件遺址,思索「餘生」的意義;麥家企圖從無數密碼及風聲中打通「歷史的暗道」;王安憶藉著上海的不斷蛻變,探勘海上文明不變的內核;龍應台《野火集》曾燒遍中文世界,多年後化為無限滄桑的《大江大海》,方方爬梳家族往事,辯證歷史記憶的軟埋與甦醒……。
中國的、台灣的、海外華人作家的「故事」繼續衍生,講不完,也完不了。他們戳穿大人先生的表面文章,直面不能聞問的內裡。他們穿梭不同時空,打造最複雜的生命情境,拆解什麼是中國,什麼是台灣的宏大命題。於此同時,他們叩問救贖歷史、信仰,和愛的可能。
* * *
1996年我在台灣中央研究院客座訪學,一次參與臺灣大學的文學會議,會後一位美國大學生上前自我介紹。他年紀輕輕,一口新學的國語,自稱人人叫他「小白」。那是我和白睿文第一次見面。兩年後他錄取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班,正式進入現代文學領域。
小白學習中文充滿機緣巧合,但他的敏銳好學卻是一以貫之。他申請哥大博士班的資料之一正是余華《活著》英譯,當時他二十五歲不到,中文功力已經十分傲人。小白的博士論文處理兩岸三地歷史座標點,像是霧社事件的霧社、二二八事件的台北、文革知青下鄉的雲南、六四天安門廣場等,藉此探勘中國現代性的傷痕地圖。他明白政治之外,倫理──正義、悲憫、反思──才是文學的使命。日後他對當代文學電影的關照,無不出於這一信念。也因為向來的堅持,這些年儘管遭受大大小小的阻力和挑戰,他始終一如既往,無怨無悔。
白睿文人如其名,睿智而文雅,工作極其努力,處處與人為善。如今小白也不小了,已經成為學界領軍人物之一,但骨子他還是那個文藝青年,還是對文學與電影由衷熱愛。二十七年過去,我們的師生緣分轉為更深厚的友誼,多麼令人珍惜!謹藉《字裡行間》出版,聊志閱讀所得,並祝福小白「永保初心」。
*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現任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著有《想像中國的方法》、《如何現代,怎樣文學?》、《眾聲喧嘩以後》、《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被壓抑的現代性》、《歷史與怪獸》、《後遺民寫作》、《一九四九:傷痕書寫與國家文學》、《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可畏的想像力:當代中文小說31家》、《危機時刻的知識分子》等書。
〈前言:字裡行間〉
有時候小說的藝術更像是在變魔術,作家把我們日常生活中天天在使用的語言變成另外一種載體,而這種載體可以傳達的不只是「對話」、「人物」和「故事」,從「字裡行間」還可以傳達「七情六慾」與各種「情感」和「哲理」。這些無法用語言形容的「感觸」都是小說家的魔法所在。
如果作者是魔法師,這本書好比《綠野仙蹤》(The Wizard of Oz)裡桃樂絲揭開隱藏魔術師的大幕時,突然間看到歐茲魔法師不過是普普通通的一個人,而且跟桃樂絲一樣,也是一個逃亡者。作者也算是逃亡者,在寫作的過程中逃亡到另一個世界,而讀者像這個旅程中的乘客。有一點不同的是《綠野仙蹤》的魔法師是個騙子,作家也是騙子嗎?雖然他們一直不斷地塑造各種各樣的人物、變造各種各樣的故事和傳說、講述各種各樣從來沒有發生過也不可能會發生的事情,但是在「字裡行間」中傳達的情感或許是真實的,而且不論變出來的故事多麼地神奇或離譜,它們還是會帶動我們的哭泣和笑聲。揭開大幕之後,這本書試圖提供一個空間,讓我們這些「乘客」竊看魔術師是如何逃到另外那個世界:追隨他們的閱讀和寫作的旅程,了解他們天馬行空的想像力是從何處而來,聆聽他們作品中從沒有告訴過我們的祕密。
因為我是在一個非漢語的語境長大的,本書所採訪的部分作者都是在大學年代才開始進入我的視野。我在讀大學時就讀了盧新華的〈傷痕〉,它收錄在一本薄薄的《傷痕文學英譯讀本》,後來在台灣留學期間先後開始讀白先勇、林懷民、龍應台、虹影、高行健和王安憶的作品。像發現新大陸一樣,我興奮得不得了,天天拚命地閱讀。因為小時候的閱歷跟華文文學完全脫離了關係──都是在讀一些英美、歐洲和俄國的小說──這種拚命的閱讀經驗也算是一種「補課」。因為要「補課」,我就很有系統地讀各個時代、各個地區的作品,從鴛鴦蝴蝶派到五四小說,從現代派到鄉土派,從反共小說到紅色經典,從尋根到先鋒,從通俗小說到後現代,無所不讀。但無論如何還會覺得落伍,不斷地在「補課」,甚至於現在,幾十年之後,在某種意義上,還在補課。
也許除了閱讀作品以外,另外一種「補課」的方式,是找機會與作家深談其作品的背後故事。每當有機會與作家坐下來談談他們學習、閱讀和創作的過程、聆聽他們的文學旅程,我總是受益匪淺。不知道具體是什麼時候決定把這些談話錄下來,但它無意中變成了持續二十多年的一個長期的訪談計畫。我從來沒想過,自己大學期間所仰視的、高高在上的「大作家」,都變成我日後採訪的對象。
不管是作家的背景和輩分,或作品的風格和類型,本書收集的對談錄不是集中而是雜散,其中還包含很多不同的視角和文類,包括政治小說、同志小說、歷史小說、科幻小說、後現代小說、紀實文學、懸疑小說……等等。等到要為此書設計一個結構的時候,內容的跨越性和多元性便變成了一個難題。本來想過按作家出生的年份來結構,但最後還是決定按照地區來劃分。《字裡行間》便分成兩卷,包含三篇:〈中國文學的寫實與魔幻〉;〈華文創作的國際視野〉以及〈島嶼談藝錄〉。雖然地域性還是有其缺點,比如說長期生活在美國聖塔芭芭拉但一直被許多人當作「台灣作家」的白先勇老師和旅德的台灣作家陳思宏,應該放在「台灣篇」還是「國際篇」?多年生活在英國但一直在中國內地文壇特別活躍的虹影,應該放到「中國篇」還是「國際篇」?我為了出版方便給每一位作家一個地域性的「標籤」,也許實質的意義並不大。文學本來應該是無邊界的,它的意義不在於固定的地域性,而是在把讀者從一個實實在在的地方,帶到一個未知的地域,或許是「外太空」,或許是個「荒原」;或許是過去,或許是未來……,但這些想像中的文學地域也算是一座一座的橋梁,不斷地帶著我們從一個世界到另外一個世界。或許在文學世界的跨越上,可以把這本訪談集當作一個小小的指南書。
本書的作家來自不同的地方,代表不同的輩分,而且其作品也呈現不同的類型和文學觀,但放在一起,可以見證華人作家的多元性和眾聲喧嘩。鑑於採訪的對象如此不同,我採取的一些採訪策略則是一致的:我幾乎都會請他們談他們的文學啟蒙、影響他們的作家和作品、如何開始寫作……等等。這樣從某一種意義上,也是「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讓這訪談集成為一本有關藝術家的自我成長的文字素描。或許他們整體的經驗,也可以給年輕一代作家(或想成為作家的青年)提供一種精神糧食。
除了學術研究和口述歷史以外,將近三十年以來,文學翻譯也變成我非常重要的一個「副業」。特別可貴的是,本書也收錄我曾經翻譯過的四位作家──王安憶、方方、韓松以及舞鶴。因為曾經跟他們的作品「共生」了一段時間,訪談時更是別有滋味。這四篇對談,都特別針對我曾翻譯過的作品──就是說跟王安憶談《長恨歌》、跟方方談《軟埋》與《奔跑的火光》、跟韓松談「醫院三部曲」、跟舞鶴談《餘生》。從譯者的角度來說,有機會跟原作者深談所喜愛的作品,是特別難得經驗,也很高興有機會跟讀者一起分享。
本書大部分的對談都是以中文進行的,但其中的幾篇是原先用英文交談而後來翻譯成中文。用英文對談的包括白先勇與陳毓賢談《紅樓夢》的前半(後半轉成中文)、白先勇談〈謫仙記〉和《最後的貴族》、林懷民、龍應台、哈金和陳思宏的部分內容(陳思宏那章是由兩個對談組成的,第一個是中文,第二個是英文,在編輯過程中,訪談的內容與順序經過一些融合和調整)。特別感謝這些章節的譯者。為此書擔任聽打和翻譯有侯弋颺、陳培華、張峰沄、郭雅靜、白睿文、潘星宇、陸棲雩、周繹凡。除了擔任幾篇訪談的翻譯以外,侯弋颺也為整本書擔任編輯助理一職,他把全書所有的內容都看了,進行修改和潤色。特別感謝弋颺為此書所付出的時間和精力。這是我跟秀威出版社合作的第四部書,特別感謝主任編輯尹懷君和編輯部經理鄭伊庭一路上的支持。最後特別感謝王德威教授為此書寫的序文,和接受採訪的所有作家。
雖然我的本行是文學評論,有時覺得所有的評論、理論、分析和談話都是多餘的,要懂得作者,只能從作品本身入手,所有的答案都在作品裡。但正是因為如此,有時候聆聽作者的現身說法,可以呈現另外一層意義,也可以改變我們對作品的一些看法,增加我們對作品的欣賞、揭開那塊布幕。透過這本書,希望讀過的讀者可以從其中對討論的文學作品有一種新的認識,更希望還沒有讀過這些作品的讀者會受到刺激和啟發,然後找原著來看看,也許從這些小說的字裡行間會有新的感受、新的發現,對文學,也對自己。
〈總序 談中得來〉
二十多年以來,除了學術研究和文學翻譯之外,我的另外一個學術方向就是文化口述歷史。初始的動機是因為我發現我所研究的領域特別缺少這方面的第一手資料。當時除了記者針對某一個具體的文化事件或為了宣傳一部新作品以外,比較有深度而有參考價值的口述資料非常少。但不管是從研究的角度來看或從教學的角度來考量,我總覺得聆聽創作人自己的敘述,是了解其作品最直接而最有洞察力的取徑。當然除了作品本身,這些訪談錄也可以幫我們理解藝術家的成長背景、創作過程,以及他們所處在的歷史脈絡和面臨的特殊挑戰。...
目錄
總序 談中得來
推薦序 當代作家,眾聲喧「華」/王德威
前言:字裡行間
【中國卷。文學的寫實與魔幻】
閻連科:為文學服務
王安憶:書寫上海
方方:歷史記憶的軟埋與甦醒
麥家:文學的暗道
劉慈欣:中國文學科幻夢
韓松:科幻的治療法
【海外卷。華文創作的國際視野】
高行健:身分與創作
哈金: 在非母語的語境下尋找寫作的自由
張翎:我的文學旅程
虹影:從小說到電影
薛憶溈:加拿大的深圳人
盧新華:揭開〈傷痕〉
總序 談中得來
推薦序 當代作家,眾聲喧「華」/王德威
前言:字裡行間
【中國卷。文學的寫實與魔幻】
閻連科:為文學服務
王安憶:書寫上海
方方:歷史記憶的軟埋與甦醒
麥家:文學的暗道
劉慈欣:中國文學科幻夢
韓松:科幻的治療法
【海外卷。華文創作的國際視野】
高行健:身分與創作
哈金: 在非母語的語境下尋找寫作的自由
張翎:我的文學旅程
虹影:從小說到電影
薛憶溈:加拿大的深圳人
盧新華:揭開〈傷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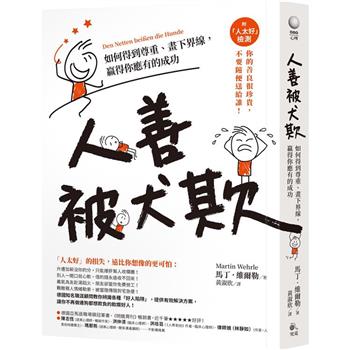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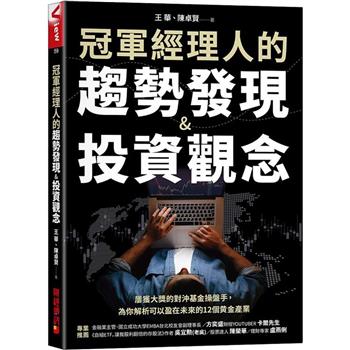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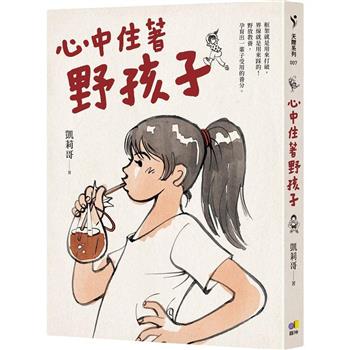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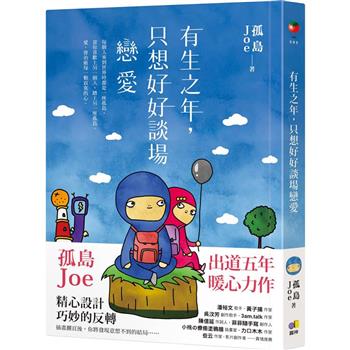






 你在媽媽肚子裡的樣子 [精美書盒典藏版](1:1真實比例小寶寶立體書,呈現媽媽懷胎九月的胎內樣貌)](https://www.books.com.tw/img/001/101/92/001101926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