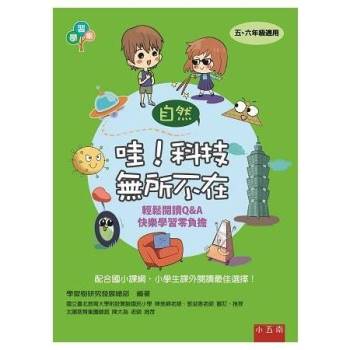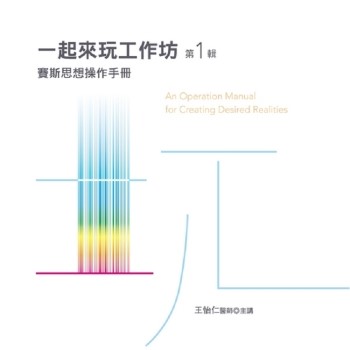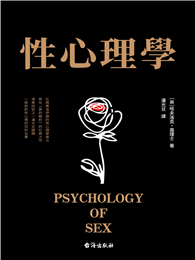一、一部迷離惝恍的書
在我國傳統典籍中,《周易》一書最為窔奧難理。它從書名取義到畫記符號、數目布列和文辭著錄等,都疑竇滿檔,很費究詰,不知折煞多少人在為它窮呼浩嘆,沒有了時。
所以會引出這種困折現象,大概跟詮釋範式無以有效建立以及短見各有因襲而日久沈溺等變數相關。前者(指詮釋範式無以有效建立),乃緣於去古敻遠,《周易》的履歷早已非解會者所能參與,以致大家只能憑空想像而漫無準的;後者(指短見各有因襲而日久沈溺),這則是先行解會者旁通無門,只好據地揣測或強為增衍,不意造成繼起者學樣懶怠於思辨而自陷雲霧莫辨窘境!
正由於解人難得,致使《周易》的面目始終模糊一片,可說近三千年來一部最現迷離惝恍且形制堪稱甚大的書。這種大,不是基於它篇幅有什麼可觀的量大,而是因為它涉義廣漠到足夠被人尋繹不盡而體現一種能無限延異的質大。也因此,先出的釋繹書如《繫辭傳》所以為易道「廣大悉備」1,就得反過來看:那是解會者把它說大了,《周易》原先的樣子還不可知(又如何肯定它有什麼廣大悉備呢)!但話說回來,解會者本就有權力依便賦予《周易》的意涵,而展演出理解某個對象必有先備經驗/方法意識等為前提以及權力欲望/文化理想等深層發用此一多重因素的約制樣態
在這種情況下,要說《周易》有多麼的窔奧難理或具體詮釋範式闕如,也就顯得不夠真切(實際上是大家將它引到那迷離惝恍的境地裏去了)。倘若有人想從新把它導向一條不同的思路,那麼只要所說的易義妥適且井然有序(不違認識條件和邏輯法則等),理當會獲得有相似經驗或相同背景者的賞鑑而自成一種新的詮釋典範。
依照這個理則,如果要說這是從眾作蕪雜中逸出而為一種最新解密的工作,那麼本身便僅僅是尋求相互主觀性下的自我限定以及期待他人前來認同的籲請促發而已;此外就無所謂《周易》本來面貌如何或應該怎樣解會才算正理一類問題存在。換句話說,在我這裏也只意在顯露一種新的詮釋策略(可不可取則留給讀者去研判裁決),而不敢必定可以通到《周易》被造時的原始心靈(以獲得反向的相互主觀性)。整個的自信在於:這一新的詮釋策略,大有解開《周易》所隱藏一段應有或理中合有的祕辛作用,很可以激勵世人另啟慧眼且據為發微或昌皇致效。
二、在減法和加法中看《周易》
上述所謂的祕辛,是指《周易》表面還未顯象也未經解會者參透條陳的部分,並且連帶溯及它可能深具的神妙性。此一解密作法,似乎又有要強通到《周易》被造時的原始心靈,而明著違反自我所設定詮釋的範限。其實不然!《周易》被造時的原始心靈不可知,所可知的是我們根據理則而探向那隱象終於得出一幅比較便於尋繹的圖畫,因此將它備列於同屬神妙性事物的領域。這時相關「未經解會者參透條陳」的宣稱,就只是對比詮釋下一種新發現的展示罷了,毋須受到膠柱鼓瑟式的指責。
從既有的文獻來看,通行本《周易》(王弼注本)所結穴的書名/畫記/數字名目/文辭等成分,大多得反常俗而改採減法先試予對待,看它究竟體現了什麼式樣,才知所詮釋的取徑。也就是說,《周易》一書在早期被敘及時,並未見偌多部件及其相互關係;倘若把增衍的部分減去,那麼我們將會發現古來解易能者所不察的層面竟然遠超出大家的想像(而這正是理解《周易》恰切的起點)。
首先是書名《周易》,全稱僅見於《左傳》、《國語》和《周禮》等(顯然那只是為了區別異代而沒有其他用意),先秦諸子所引則都不冠周字,可見周字是後人添加上去的(不大可能是先有全稱而被徵引時剛好都改為略稱);而這一添加,往後就多出了不少釋義爭議(詳後相關章次)。
其次是通行本畫記有連線(—)和斷線(--)二種且數量各為六,並非盡是通例;尤其是斷線部分,安徽阜陽所發掘竹簡《周易》和長沙馬王堆所發掘帛書《周易》就分別作和╯╰ ,形狀全異且有離有續(續指的是)。這如果把它納進來看覷(至今尚未見有人先比較三個版本後再論畫記的取義),當會發現歷來解易者窮為對兩種畫記分屬陰陽的揣測頗有疑問。至於另以為六畫記(並稱它為六畫卦)是從三畫記(並稱它為三畫卦)疊加演變而來的,則又是望文生義,盡屬無稽附會(詳後相關章次)!
再次是通行本六畫記都有搭配九、六和初、二、三、四、五、上等數字名目(名目指以初代一和以上代六等),這在《左傳》、《國語》、《論語》、《尸子》、《荀子》、《莊子》、《戰國策》、《呂氏春秋》和《禮記》等書所引《周易》(或《易》)繇辭中全然未見,則又可知此內多有衍增的痕跡(既然那些數字名目都是衍增的,那麼通行本乾坤二卦末尾所著錄的用九/用六等文辭可知也是添加的)。
再次是通行本都有篇題,而解易者也多據以為闡說全書的結構;但從竹簡《周易》和帛書《周易》的殘卷來看,不僅沒有篇題,而且卦序也大不相同,這豈不顯示通行本在獨為傳承過程中又被賦予了不少東西(包括作易的旨意及其排列組合的用心和指涉的寓意等)?
此外,向來有關畫卦/重卦/繫辭等誰屬問題,所見議論紛紜,以及通行本眾多異文且跟他本相比又宛如兩個系統等(光乾坤二卦名,就有帛書作鍵 和漢石經坤作w等無法為說易者所能面對通行本那樣定要解會),這不啻是在將通行本一系的詮釋進路悉數加以打破,而任由喧呶眾說嬉移流散無以終結!
以減法來看《周易》,所該裁切的就是上述那些添加衍增的部分(至於有所附會或強著意見乃屬解易者所為的說數,就暫且不計入了)。這樣《周易》就酷似殷商的甲骨卜辭4:單一的畫記形同兆坼,畫記旁(下)文辭猶如卜人的占斷,合而為一可意會的筮占形態。這恰是秦始皇焚書「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5而《周易》屬類得留所能還歸或保本的形式處;否則一如通行本那般多出難以勘驗的部件(諸如九、六、初、二、三、四、五、上和用九/用六那些東西,都不便直接跟筮事係聯),就得大費思量了。
即使如此,在理解《周易》時也不能僅是將它減卻成上面那樣簡易版(也就是只存畫記和文辭二式),還得有加法介入來充實它的內涵而構成另半對待《周易》的方式。原因就在那居關鍵地位的文辭(畫記乃隨機取用而不具關鍵性。詳後相關章次),它所結撰的模式以及被整合成書和希冀發揮什麼功用等,都需要加碼給予詮解(《周易》文本並不自我後設說明此中義例),因而得出一個已賦義可知曉的《周易》作品6。由於這種加法的對待方式是從原文辭(扣除乾坤二卦末尾所著錄的用九/用六等文辭)蘊意而摩想演成的,有別於上述所見傳易者的任易增添部件,所以它就得自擇殊異性的另為註記,才不致發生或造成混淆的事。而這則要等到後面相關章次再加以詳論,現在只先點到為止。
三、《周易》當是筮占的遺留
就《周易》所著錄文辭儘多吉凶悔吝的占斷7來說,乃屬甲骨卜辭一脈而自擇筮式(占媒不用甲骨而另採筴策),所成就各卦理當都是筮占的遺留。據此前人有所謂伏犧畫八卦、周文王演為六十四卦(並繫辭)和孔子作十翼(包括《彖傳》/《象傳》/《文言傳》/《繫辭傳》/《序卦傳》/《說卦傳》/《雜卦傳》)等「人更三聖,歷世三古」一類繁事8,則是無端在塗附枝蔓,終究難窺該筮占的底蘊(被強為走調旁牽的緣故)。
恰因《周易》各卦都是筮占的遺留而不雜羼其他非關筮事的東西,致使體現於減卻樣態的整體情況就多有可說處:第一,原筮例想必甚多(一如《尚書》和《詩經》等著作裒集前存篇無數那般),在彙編為《周易》一書過程中勢必得汰除重複且擇要以充篇幅,而正好湊成六十四卦數(緣於各卦一律是六畫註記,甚巧有乾坤震艮離坎兌巽等成相同三畫疊象,馴致前人普遍誤以為先有八個三畫卦的存在)。
第二,《周易》成書前後,雖然不知道有多少人參與編纂及其採為易教用途,但可以猜想的是人各有執本且付諸被參鏡行動,才會發生《左傳》和《國語》等所載依據《周易》範本去占筮卻常見未符通行本繇辭的案例9,因為那些案例都已明列在其他未定本中(該未定本所取例或是筮事相同且定名一致卻因占辭殊異而被採擷以互別苗頭),不教有心人就近借鑑也難!
第三,通行本《周易》所留存已被論者發覺的某些疑點,在前二項說法底定後便有機會給予適當的解釋(形同是在補充前二說)。例如有人取帛書《周易》跟漢熹平石經、王弼注和朱熹本義等版本相比較,以為此本具有較原始的形式,而懷疑後來的本子可能是在這個基礎上加工改造的10。這只是推測,可靠性如何不得而知(也許那是兩個系統,各有所承罷了11)。旁證則在卦名,通行本所見的,異文頗多12,可知通行本絕非本來面貌;至如帛書本卦名,也多跟通行本不同且頻用假借字13,顯然帛書本確是自有承繼而不宜被測定為通行本的源頭。此外還有卦爻辭,自《左傳》、《國語》以下,所引易辭多少都跟通行本有些差異,這當是古時尚未有定本所致(如上所述);但連同帛書本也沒得近前跟那些引例相印合,可知在帛書《周易》前同樣有更早的本子而無從任人作橫向的牽繫。
總括來說,《周易》為筮占的遺留且被編纂成書,原則上是大可確定的事。而它的屢經修訂(從部件的增衍和著辭的更易等跡象來研判),也反映出此書纂成後並不盡孚傳易者所望必一再斟酌改定而後快的心理。依此前人所出的「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或「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14一類屬失察且又太過冠冕堂皇的話,也就可以別為看待(詳後相關章次)而毋須再強拉來拼湊繹理《周易》的形貌意態,畢竟那些都無助於對優先筮占一事確切或有效的掌握解會。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周易》一次解密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46 |
中文書 |
$ 246 |
中國哲學 |
$ 246 |
Others |
$ 252 |
易經 |
$ 252 |
社會人文 |
$ 252 |
哲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周易》一次解密
《周易》一次解密
本書談《周易》之【總解】【分解】【析辨】【運用】【注釋】詳細內容闡述盡在書內。
本書,於理序(而非敘序)上先將《周易》所體現筮占儀節作一番徹底的耙梳尋繹,然後把相關占理的文化性及其可藉為探勘占事祕境的參考座標特徵予以全幅朗現。
筆者在減法和加法中看《周易》→《周易》當是筮占的遺留→編纂成書後《周易》衍為占筮的範本→詮釋及其演繹《周易》的流變→試為歸整筮占模式以解開《周易》的謎團→從新認知《周易》所體現精神在當今的意義等系列有關課題的總解密及從《周易》可綰結的體例→依體例所作《周易》六十四卦的疏解→白話詩證《周易》等系列逕涉文本的分解密工作。
從筮占的遺留,到被編纂成書且採作占筮的範本,再到被增衍成分而演為通行本形態,《周易》一書已歷經多重的變遷。後人不察此中曲折,只就後者入手而解者紛紛,導致原筮占的流程及其所體現的意蘊神態儘付闕如,大不便於《周易》在並世學問中取得有利的發言位置。這就有待本書來從新計議,先將筮占的來龍去脈釐個清楚,然後才據以為說釋文本,終而匯合我國傳統文化一起開啟匡世的偉業。
作者簡介:
周慶華,文學博士,大學教職退休。著有《語言文化學》、《走訪哲學後花園》、《閱讀社會學》、《文化治療》、《語文符號學》、《轉傳統為開新:另眼看待漢文化》、《後宗教學》、《解脫的智慧》、《跟君子有約:在全球化風險中找出路》和《酷品味:許一個有深度的哲學化人生》等七十多種。
章節試閱
一、一部迷離惝恍的書
在我國傳統典籍中,《周易》一書最為窔奧難理。它從書名取義到畫記符號、數目布列和文辭著錄等,都疑竇滿檔,很費究詰,不知折煞多少人在為它窮呼浩嘆,沒有了時。
所以會引出這種困折現象,大概跟詮釋範式無以有效建立以及短見各有因襲而日久沈溺等變數相關。前者(指詮釋範式無以有效建立),乃緣於去古敻遠,《周易》的履歷早已非解會者所能參與,以致大家只能憑空想像而漫無準的;後者(指短見各有因襲而日久沈溺),這則是先行解會者旁通無門,只好據地揣測或強為增衍,不意造成繼起者學樣懶怠於思辨而自陷雲...
在我國傳統典籍中,《周易》一書最為窔奧難理。它從書名取義到畫記符號、數目布列和文辭著錄等,都疑竇滿檔,很費究詰,不知折煞多少人在為它窮呼浩嘆,沒有了時。
所以會引出這種困折現象,大概跟詮釋範式無以有效建立以及短見各有因襲而日久沈溺等變數相關。前者(指詮釋範式無以有效建立),乃緣於去古敻遠,《周易》的履歷早已非解會者所能參與,以致大家只能憑空想像而漫無準的;後者(指短見各有因襲而日久沈溺),這則是先行解會者旁通無門,只好據地揣測或強為增衍,不意造成繼起者學樣懶怠於思辨而自陷雲...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序:藏在中文裏的神祕世界
《周易》本是西周時代筮占的遺留,畫記及其繇辭各自庋藏於官府,後經專人編纂成書而採作占筮的範本。時移境遷,相關筮占的源頭已被淡忘,傳易者又在畫記上增添數字名目以炫人耳目,並且大肆衍義,儼然是一部刻意寫就的著作。中間因為倖存於秦火之後,被經生獨攬為瓌寶,或據以說象數,或兀自解義理,或好事牽連河圖洛書,從此皇皇然張揚於世,以迄於今。
像這類紛紜說數《周易》的現象,本應許為是詮釋的常態而毋須給予訾議什麼;但當有意無意的離題解會逐漸掩蓋過原筮占的光芒,致使有關占理所體現的...
《周易》本是西周時代筮占的遺留,畫記及其繇辭各自庋藏於官府,後經專人編纂成書而採作占筮的範本。時移境遷,相關筮占的源頭已被淡忘,傳易者又在畫記上增添數字名目以炫人耳目,並且大肆衍義,儼然是一部刻意寫就的著作。中間因為倖存於秦火之後,被經生獨攬為瓌寶,或據以說象數,或兀自解義理,或好事牽連河圖洛書,從此皇皇然張揚於世,以迄於今。
像這類紛紜說數《周易》的現象,本應許為是詮釋的常態而毋須給予訾議什麼;但當有意無意的離題解會逐漸掩蓋過原筮占的光芒,致使有關占理所體現的...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藏在中文裏的神祕世界/5
【總解】/9
一、一部迷離惝恍的書/9
二、在減法和加法中看《周易》/11
三、《周易》當是筮占的遺留/15
四、編纂成書後《周易》衍為占筮的範本/18
五、詮釋及其演繹《周易》的流變/22
六、試為歸整筮占模式以解開《周易》的謎團/26
七、從新認知《周易》所體現精神在當今的意義/31
【分解】/37
一、《周易》可綰結的體例/37
二、依體例所作《周易》六十四卦的疏解/43
乾/44坤/46屯/49蒙/51需/53訟/55師/56比/58小畜/60履/62泰/64否/67同人/69大有/71謙/73豫/74隨/76蠱...
【總解】/9
一、一部迷離惝恍的書/9
二、在減法和加法中看《周易》/11
三、《周易》當是筮占的遺留/15
四、編纂成書後《周易》衍為占筮的範本/18
五、詮釋及其演繹《周易》的流變/22
六、試為歸整筮占模式以解開《周易》的謎團/26
七、從新認知《周易》所體現精神在當今的意義/31
【分解】/37
一、《周易》可綰結的體例/37
二、依體例所作《周易》六十四卦的疏解/43
乾/44坤/46屯/49蒙/51需/53訟/55師/56比/58小畜/60履/62泰/64否/67同人/69大有/71謙/73豫/74隨/76蠱...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