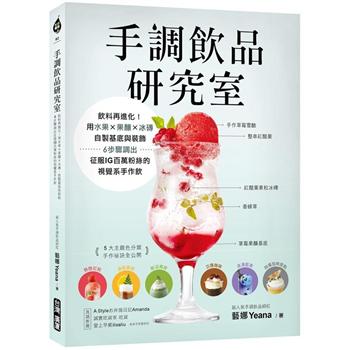推薦序
先除「迷信」再讀史
譚家齊
香港小學的中國語文課程,曾經有一篇可圈可點的課文,大意如下: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少年時代,於鄉下跟玩伴到寺廟中遊玩。在得意忘形之際,這幫頑童駭然發現殿宇中的神像面目威嚴,便都害怕起來了,更準備逃離寺廟。遊戲時間似乎要就此結束,但天不怕地不怕的國父為讓眾人釋懷,竟跳上神壇並併發神力,將神像的手臂折斷,聲稱「偶像」連自己的手也保不住,大家對它又何必敬畏呢!神像沒有反抗,是否即代表這個神靈是虛幻的呢?這則課文竟沒有指斥國父破壞家鄉的文化遺產,反而藉此誇讚這位基督教徒破除了「迷信」,從小便展示了革命領袖的本色。前輩學者已指出此故事疑點不少,而且相關行為也有充滿爭議性,最終在課程中消失了。不過,故事主要的教訓卻烙印在好幾代人的心裡,似乎成了香港以至整個大中華地區的精英價值:將傳統信仰標籤為「迷信」,視之為中國要進入現代社會必須「破除」的障礙。
在這種氛圍下成長的我,在小學至大學本科時代,竟不自覺地將不同的宗教信仰等同於「迷信」。雖然未敢如國父般跳上神壇,但往往對熱情投入於自身宗教的親朋戚友有所保留,甚至我自身信仰了基督新教,也是以極為理性的方式去「了解」教義,更視聖經及其他基督教文獻為「研究」的對象。因為在我的骨子裡,就是要拒絕「迷信」。
不過,究竟甚麼是「迷信」呢?我似乎沒有找到答案,因為如果視野偏狹,所有的宗教都是迷信。若是胸襟夠廣,則「迷信」就根本不存在了。這個結論,是我在牛津大學修讀博士課程時體會回來的。當時我最勤出席的課程,是中國考古學權威羅森夫人(Dame Jessica Rawson)的研究生討論會。每個參與的同學都是學有專攻的,會就不同的考古學及藝術史課題作深度的報告,還會被教授、客席學者與「天不怕地不怕」的同學尖銳地詰問。有次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同學,對漢代黃泉世界概念與墓葬關係作報告,提到那些宗教觀念是「迷信(Superstition)」,羅森教授竟當頭棒喝,厲聲責問那些概念有何不對,我們憑什麼說人家是「迷信」?
其實從歐美的史學史角度來看,「迷信」確是一個過時的標籤。早在一九六○年代開始,西方的史家在研究前現代的歷史時,已指出不同信仰的神學系統,甚至其中法術、魔力、神蹟等對世界運作的闡述,其實都是現代科學出現以前,對各種自然與人文現象的「技術性」解釋。例如在傳染病觀念未形成之前,解釋染疫者是受惡靈的侵害。那些宗教術語當然有別於科學語言,但都是在技術限制下盡量忠於事實的描述,不可一概說是欺騙百姓或胡思亂想的結果。以為掌握了科學,便會指出不用科學語言描述的世界觀是迷信;以為自己的信仰就是真理,便會指責其他的宗教是迷信。自己不解當然是迷,但自己不解自己便不必去信,何必辱罵其他能解能信的人為「迷信」呢?此外,既然有人能解,為何不嘗試問問人家的理解如何,也問問為何他們能接受有相關的信仰。有了這種「同情地理解」定體悟,便開闊了對歷史人物了解的新天地。
我一直相信歷史研究對今人最大的貢獻,是分析過去的人物在面對他們的處境時如何做選擇。受了現代科學、經濟學洗禮的我們,易以「最大利益」的「理性」框架,套入古人的思維來了解他們的抉擇。但是祖輩的信仰跟我們往往不同,他們眼中的最大利益或許超越了物質與現世。如果對人的了解缺少了宗教信仰的維度,就難免一知半解了。當然,要解決這限制是知易行難的,因為這是根深柢固的包袱,並不只能怪孫中山先生。
我們常說香港是中西文化的匯萃之地,那麼中西文化對本地的宗教發展,是否也有積極的推動作用呢?這要視乎站的是精英文化還是普羅文化的立場。中國的精英文化是高度理性的,天道是沒有喜怒哀樂的規律,而孔子也「不語怪、力、亂、神」。另一方面,西方的有識之士如果不是自我感覺良好的無神論者,就多是秉持「在禮貌的社群中,不談政治與宗教」的原則,因為這樣大概能避免出現不禮貌的爭辯。所以除了系統研究宗教的學者外,中西的精英多慣於將鬼、神及信仰推到邊緣位置,不得已才觸及宗教的話題。流風所及在探索古人時,便盡量不以宗教為史事解釋的核心了。
當然,中西匯萃也包含了不受精英束縛的普羅文化。開埠以來世界各地的移民與訪客,便將不同的宗教信仰也帶到香港這片彈丸之地,在擁擠的街坊中樹立各種聖域與寺廟。也許普羅大眾自有謙卑的心腸,不敢相信真理就在自己的手中,而香港的低下階層多視各種宗教都是「導人向善」的,因而不同宗教的信徒,通常也能和而不同地共處,甚至追求多教的融合,聽取不同的神諭與陌生的心聲。只是這個街坊的香港,在以政治家和大商家為主軸的歷史書寫下,只有模糊的面貌,往往隱沒於時代的洪流之中。
德維以宗教角度研究歷史起家,但言行時有刻意凡俗的傾向,所以他會告訴你被視為「痴漢」的困境,或者對「蘿莉控」的同情。正因為出聖入凡,更能走出精英的框框而進入普羅的世界,去探望及聆聽一個個有血有肉的靈魂,去了解鬼、神、天父如何跟他們渡過人生的喜怒哀樂,去分析他們的信仰如何指點迷津,幫助作大小的抉擇。德維與幾位同是有心人的伙伴,走入街坊的深處,為我們搜集一塊塊細碎的拼圖,以香港的不同宗教為經,以多個宗教信徒具體的信仰經驗為緯,為我們編織出一部以普羅為主角的香港故事。為大眾寫史的好處,是因為我們不常為立法的問題或企業併購的問題而煩惱,所以街坊對生活瑣事的切身經驗,可能是更有用的歷史知識。
先破除對「迷信」的執著,也不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並且尊重與理解有別於自身的信仰,再盡量走進普羅之中,嘗試去體會他們人生的抉擇,並以通俗易懂的語言來書寫。這樣的「採風」編纂過程,會不會成為歷史研究的「新常態」呢?但願這部《街坊眾神》,能給我們有血有肉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