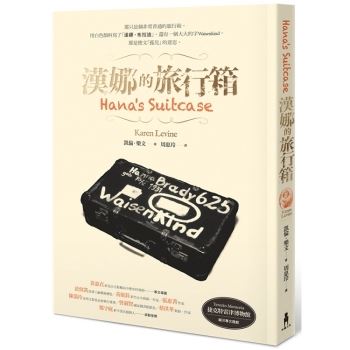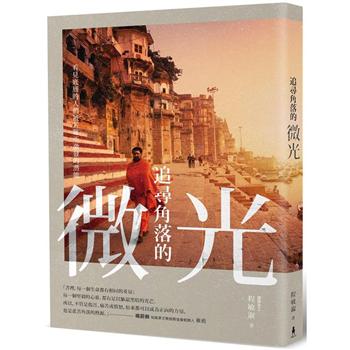一、海潮聲
「唉呀!……此乃絕景!」
十兵衛以精簡的用字發出讚嘆。
儘管熊野路沿途風景如詩,但行至此處,見到四周的景致,不只是十兵衛而已,任誰都不由得發出讚嘆之聲。
山茶溫泉向北十六里地——湯崎七湯,根據《日本書紀》的記載,此處有天皇曾經親臨過的牟婁溫泉 。南方則有朝著大海延伸的寬闊岩梯,當地居民稱之為千疊地 。不過,其實那些岩梯相當於千疊的十倍寬。白褐色的砂岩石臺,與拍擊著岸石的靛藍海浪相互映襯,景色壯麗至極。
「哇!好美,美極了!」
彌太郎宛如小鳥、小猢猻似的,又如陀螺、龍捲風般,在岩石之間縱身飛躍。
「叔叔,你們再像先前那樣,每個人都結成人鏈。」
「做什麼?」
「再全部翻滾下去,這裡的岩梯啊……有值得一滾的價值!」
「胡說什麼!」
柳生眾苦笑說道。
「哇啊!哇啊!」
彌太郎大聲叫嚷,不知又奔至何處去了。
「危險!你要去哪?彌太郎,等等——」
阿廣高喊,隨即慌張地追了過去,阿雛和阿縫則緊追在後。
「這小鬼,真拿他沒辦法。」十兵衛笑道。
只要一覺醒來,雙眼睜開之後,便再也靜不下來的彌太郎,到了這樣的地方,儼然當成自家地盤似地活繃亂跳,怎能停得下來。簡直是個拿他沒辦法的包袱。可是,幸虧有這頑皮的小鬼,才讓這次殺伐之旅不那麼沈悶凝重——另外——
彌太郎有時也成了盾牌,讓十兵衛得以防著那名美艷嫵媚的癡女。
十兵衛每夜都會抱著彌太郎睡,碰到狀況發生,偶爾會掐他屁股,讓他放聲大哭。十兵衛想到彌太郎近日來的辛苦,心想即使是為了彌太郎,也不能胡來。
在那以後——又曾有過幾個令人厭惡的夜晚,不過那些事卻無法向柳生眾透露。十兵衛對此苦悶不已。柳生眾白天也會照顧癡女,到頭來,真不知他們是為保護三名少女而來,或是專程來照顧這名癡女。
——還有另一個包袱!
十兵衛思及此處,轉身一看,瞧見阿品正背對著海,佇立在岩岸的邊緣,仰望著緩緩斜上陸地的白色岩梯。
秋日的陽光,照耀在她的臉上,白蠟般的精緻臉龐,毫無表情可言,更透露出空虛寂寞的哀愁——她此時的哀傷神情,讓十兵衛斷了棄之不顧的念頭。
「師父,咱們往那邊瞧瞧吧。」
「那裡有什麼?」
「在那附近,似乎有個叫三段壁 的奇景。」
「嗯。」
在說話的同時,無意間,十兵衛轉身朝阿品眺望的方向望去。在秋日湛藍天空之下,他看見遠處層疊岩石的彼方,忽然有奇怪的人影出現。
雖然身影很小,卻可辨出是一對男女。或許是那女子的鮮紅衣裳,吸引了癡女的目光。不過,最令十兵衛詫異的是,另一道人影,竟是頭戴網代笠的禪僧。
當十兵衛「咦?」一聲地看過去時,兩道人影倏地隱沒在岩石的另一端。
十兵衛心裡忖度著,這可真是詭異,禪僧與和女人一道,實在是極為罕見的情形。
十兵衛方思及此,便受到小屋小三郎的催促:「師父,請往三段壁的方向前進。」
於是,在金丸內匠、戶田五太夫和三枝麻右衛門等人的簇擁之下,一行人朝著那個方向去了。
「阿品小姐,往那邊去吧!」
「走吧!不過很危險哦!」
「沒錯,由我來背妳。」
一如往常地,磯谷千八、逸見瀨兵衛、小栗丈馬與伊達左十郎幾個,在後面怪聲怪氣地爭吵起來。──
「咦?要去哪?」
「危險!」
今日不知何故,癡女竟甩開了眾人的手,沿著比十兵衛等人更近海的斷崖邊緣,往三段壁的方向奔了過去。柳生眾等人也慌張吵鬧起來,顧不得腰際鈴鐺胡亂作響,紛紛張開雙臂急追而去,——以他們身後大海的洶湧波濤為景,眼前形成了一幅壯麗又滑稽的剪影。
「啊,危險!」
彌太郎從反方向奔了過來,手中拽著一截長繩。
「傻姊姊,危險啊!」
彌太郎認真地生氣起來。他雖然只叫阿廣「姊姊」,不過也叫其他女子阿雛姊、阿縫姊或者傻姊姊。
十兵衛朝著彌太郎走近。
「這繩子作什麼用的?」
「我找到的,用來測量海到底多深。」
「哦,那有多深?」
「很厲害!師父,好深,真的好深——這海呀,可是深到地獄底層哦!」
三名少女佇立在斷崖邊緣,海風輕拂著髮絲。讓十兵衛不禁暗嘆起她們的絕妙身姿。
十兵衛心想,此地便是著名的紀州白良濱的三段壁?高度約莫十五丈 左右。在這讓人望之暈眩的絕壁之下,翻騰而來的靛藍波濤,捲起了如白雪般的浪花,潮浪聲隨之轟然而來。
「這繩子雖然看上去不怎麼樣,不過至少也有個六十尺 長。投入這海裡之後,感覺還不及一半深呢!」彌太郎說道。
聽到此處,阿雛等人也笑了起來。
「傻姊姊,那樣危險。」彌太郎面有憂色地說道。「那麼,倒不如這樣。」說著,他把繩子纏繞在阿品的身體上,另一端則繫在自己的腰際。
「如此一來,我就安心了。」彌太郎語畢之後,動了動鼻子。
「你這麼做,兩個人都危險。」
三枝麻右衛門拉住繩子中央笑道。
不論如何,這也證明了彌太郎擔心她的安危——十兵衛點著頭沿著斷崖走去。
繞了山崖之後,發現它與對面斷崖之間,有著寬約二十尺,深不見底的裂縫,在遙遠的另一端,兩處斷崖才連接起來。在這裂縫之下,不斷翻騰的怒濤,正如彌太郎所形容的,發出彷彿來自地獄底層的呼喚。
「原來如此,不愧是奇景!」
十兵衛依然一如往常,以精簡用字感嘆眼前美景。正當他緩緩踱回之時——突然停下了腳步。
十兵衛見到一名男子,從方才走過的千疊地的方向走來。那是個戴著網代笠的禪僧,身長約莫五尺,軀體異常寬大,那個模樣,簡直像是在棋盤上放著斗笠。
那人是方才見到的禪僧,不過身邊卻未帶著女人。取而代之的,是方才未見到的物品──長槍。
那名禪僧左手持槍,緩緩地走了過來。槍尖則是沾染了腥紅。
柳生眾察覺到十兵衛的異樣,也轉身凝望著那個方向。片刻之後,其中的小栗丈馬,終於忍不住喃喃說道:「那……那是什麼人?」
一直凝神注視的十兵衛,低聲說道:「那人……恐怕是寶藏院。……」
那時仍在七十餘里距離之外的禪僧,理應聽不見這邊低聲細語。
「貧僧確實是寶藏院!」
在怒濤的轟鳴聲當中,吼聲竟不可思議地穿透過來。
「柳生十兵衛,聽到這個名號,是否覺得有些懷念啊?……在我生前,總是陰差陽錯,沒能和你見上一面。因此,無法化解的怨念,如愛慕之火般越發熾烈起來。——那是我的長槍,對你的劍的無盡眷戀。——」
然後,迴響起「唔、呵、呵、呵」,這種難以名狀的低沈笑聲。
在那陣陰森而豪快的笑聲停下來之後,寶藏院開始咆哮道:「依據約定,寶藏院沒要其他人插手,只有我一人獨自前來。十兵衛,說完這些話之後,其他也就沒什麼好談的——快拔劍!」
二
如今,禪僧的身影清晰可見。
他紮起墨黑色的衣袖,將之纏繞在背後,那是奈良寶藏院流的獨特衣袖。不過,臉卻無法看清。他除了頭戴網代笠,下方還圍著赤黃色的頭巾,因此只能看見他的眼睛。
不,精確來說,因有網代笠遮掩的緣故,按理也看不清那雙眼睛。然而,柳生眾卻在被那銳利的視線盯視之後,身子倏地動彈不得。
——寶藏院!
——奈良寶藏院!
他們只感全身僵硬,僅有胸口隨呼吸劇烈起伏。
奈良寶藏院距柳生莊不到兩里,這個著名練槍的道場,可說是無人不知。非但如此,柳生眾之中,也有人數度前往觀摩。那裡有檜木製的地板、壁板、一尺見方的柱子,簡直與能劇舞台無異。只是,到處都有如雲朵般的班駁污漬。那是擦拭不去的血跡,再加上置於正面的愛宕山勝軍地藏 與春日赤童子像 ,予人詭異的壓迫感。在京都附近,究竟有多少劍法道場,無法仔細計算,不過,有著這種陰森淒涼氣氛的道場,必然不會有第二處。
原本,在十數年前加入寶藏院的二代住持胤舜,他們未能親自得見。只知道現在三代住持的胤清。胤清這號人物,已是足以讓人瞠目結舌的厲害人物,不過,據說其武藝遠遠不及胤舜。
雖然眼前自稱胤舜的人物,極有可能是冒充者,而且,先前在田宮坊太郎現身時,已令他們半信半疑。不過,仔細凝視此人之後,他們感受到了強烈的衝擊,心中對他的真實身份的疑慮,霎時煙消雲散。
那禪僧佇立於層疊的白褐色斷崖上,衣擺隨風飄動,在秋天烈日之下,長槍光芒耀眼,那威風凜凜的模樣,足以讓人誤認魔神勝軍地藏再世,又像是春日赤童子的化身。
那支長槍的槍尖,已經有血光閃耀,或許是沾上了何人的血。
然而──時間似乎經過了很久,可是,那只不過是浪濤拍岸之後,至下一波浪濤再次作響之間的事。
柳生眾正欲起身動作時,
「別動!」十兵衛對著他們喊道。「眾人給我退到那邊等著。」
語畢之後,他接著和那禪僧交談起來:「誠如大師所言,先前總是緣慳一面,可謂相見恨晚,其中的悔恨與感懷,十兵衛也能感同身受——」
秋日的陽光,照耀著十兵衛倏地拔劍出鞘的刀身。
「不過,一切也正如您所願,這代表初次見面的敬意。」
十兵衛說完之後,又大聲斥喝道:「待著別動!不知天高地厚的傢伙!——對方可是亡父但馬守的莫逆之交!放尊重點,全都給我退下!」
那威猛勁烈的吼聲,讓柳生眾老實地退至一旁,再也不敢恣意行動。
不過,十兵衛這一番話,並非只是單純對胤舜聊表敬意。其實,他心裡也很希望與胤舜對陣一次,而且,對於這位父親的知交,他也的確懷抱著他人難以想像的懷念。
十兵衛還有其他想說的事,當然也有許多想問的事。然而——
胤舜沒等他說完想說的話,一手已然揚起,「唰」一聲地扯開了網代笠的繫繩。網代笠被強勁的海風吹走,露出了和田宮坊太郎相仿,讓人倒抽涼氣,令人毛骨悚然的赤黃色頭巾,見到那塊三角形頭巾的瞬間,十兵衛的內心已斷定,兩人必須以槍與劍之間的交擊,作為初次寒暄的禮節。
「禮節真是周到啊,十兵衛。不愧是但馬的兒子。看來與傳說中你的截然不同,似乎是個孝順的兒子——」
在寶藏院還冷笑著的同時,長槍在半空中迴了一圈,「趴噠」一聲,擺出橫槍身前的架勢——雙方依然相隔六十尺左右,但十兵衛已經全身肌肉緊繃。
寶藏院胤舜的本領,十兵衛先前已有耳聞。與世間傳說不同的是,胤舜其實曾敗給父親但馬守兩次。他的父親曾經說過,與其說胤舜是個武術家,倒不如說是政治家。這又和世間對胤舜的認知不同。所以,十兵衛雖然心知胤舜確有驚人的本領,不過畢竟曾敗給父親兩次,因而覺得對方實力或許未達頂尖。
不過,事實卻非如此!
如今與其對峙的寶藏院胤舜,全然出乎十兵衛的意料之外!那道五尺高的墨黑身影,瞬間變幻至七尺高,在下個瞬間又猛然縮小,消失在長槍的另一端。
聳立在十兵衛面前的槍尖,發出猶如星芒般的寒光,又交雜著赤紅烈日般的炙熱光芒。
寶藏院的這枝長槍,方才沾上了女子的鮮血。來自和歌山地底秘室的那名女子,成了替他長槍開鋒的祭品。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魔界轉生(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20 |
二手中文書 |
$ 264 |
日本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魔界轉生(下)
【媒體推薦】 日本亞馬遜五顆星推薦! 本作曾多次改拍成同名電影、漫畫、電玩,以及舞台劇,精彩可期! 【書籍簡介】 紀伊大納言德川賴宣,接獲幕府將軍家光病危的消息以後,傾全藩之力作為政治豪賭,供養自魔界甦醒的妖魔劍豪,目標直指江戶幕府--魔人們所擘畫的大陰謀,已進行到最後關頭!在這關鍵時刻,柳生十兵衛挺身而出,對抗魔人們覆滅天下的奸計,他的獨眼,散發出銳利目光,仗著身上孤劍,從柳生谷一路戰至伊勢船島。悲壯慘烈的大死,即將進入最高潮! 【作者簡介】 山田風太郎 1922年出
章節試閱
一、海潮聲「唉呀!……此乃絕景!」十兵衛以精簡的用字發出讚嘆。儘管熊野路沿途風景如詩,但行至此處,見到四周的景致,不只是十兵衛而已,任誰都不由得發出讚嘆之聲。山茶溫泉向北十六里地——湯崎七湯,根據《日本書紀》的記載,此處有天皇曾經親臨過的牟婁溫泉 。南方則有朝著大海延伸的寬闊岩梯,當地居民稱之為千疊地 。不過,其實那些岩梯相當於千疊的十倍寬。白褐色的砂岩石臺,與拍擊著岸石的靛藍海浪相互映襯,景色壯麗至極。「哇!好美,美極了!」彌太郎宛如小鳥、小猢猻似的,又如陀螺、龍捲風般,在岩石之間縱身飛躍。「叔...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山田風太郎
- 出版社: 尖端出版 出版日期:2007-08-08 ISBN/ISSN:9789571036526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76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日本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