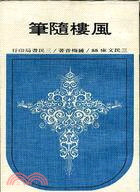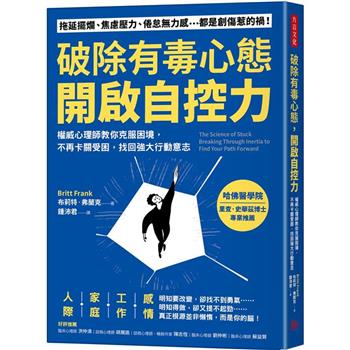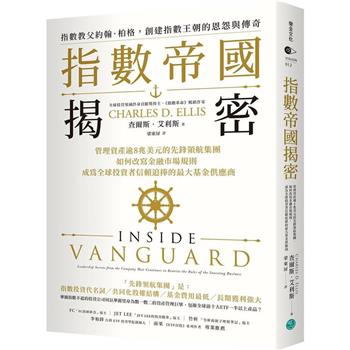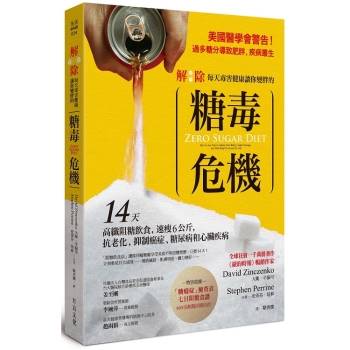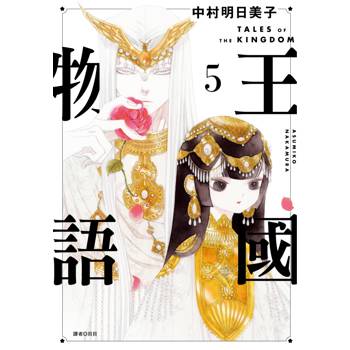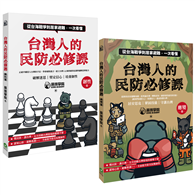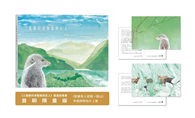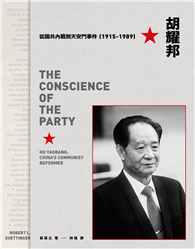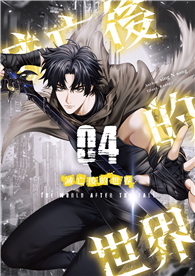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風樓隨筆(平)-三民文庫055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三民網路書店 評分:
圖書名稱:風樓隨筆(平)-三民文庫055
- 圖書簡介
這又是多才多藝散文作家鍾梅音女士的散文集。綜合它的內容,有三大部門:談文論藝說人生。談文方面:她評介了兇手、松窗憶語、漂鳥集、珍妮畫像、悔罪女、和智慧的燈六本文學作品。論藝方面:計有繪畫、攝影和音樂,最重要的是她提出了欣賞現代藝術的秘訣。說人生:主要的有十項母訓,愛情「婦女觀」,作者追求永恒的目標,有她獨特的方法,認定讀良書,結益友,看好畫,聽佳樂是人生四樂 。
- 作者簡介
鍾梅音
1922年生福建上杭人國立廣西大學文法學院肄業 - 序
前 記
沒有一本書的校對工作像「風樓隨筆」這樣辛苦,從臺北校到曼谷。因為在我啟程前一直忙得團團轉,朋友們誇我在一個半月裡成就了別人半年才能辦好的事,乍聽沾沾自喜,豈知這只是透支精力的結果,一到曼谷我就病了,這本小書直到病後才得校完。現在我是坐在一排很敞亮的窗前寫這篇小文,在曼谷一處很整潔的住宅區,樓雖不高,視界很遠,在遼闊的碧空下,滿眼綠樹裡點綴釐高高低低的漂亮屋頂,鳳凰木與九重葛,還有吊蘭,遠遠近近都是賞心悅目的花卉,平心而論,這正是我夢寐以求的住所,比我故居可愛得多。然而,我卻非常懷念鄧「風樓」上的日子。風樓之名不知幾時起的?由於過去兩年中,一家人分了三處,淒清的環境,淒清的心情,使我對於曠野的風特別敏感。更兼樓高風厲,當風聲穿過高壓電線,五音並奏時,真教人一夜華髮生。每當聽風聽雨,長夜不能入寐,我就起來讀書、寫稿。在這風樓上,我寫了不少字,一本「我從白象王國來」,還有一部份是關於音樂的欣賞,已刊入「黃友隸藝術歌曲選」,因為內容比較「專門」,這本隨筆中只選了一篇「顧曲餘談」。其餘的也都是隨筆小品,包括若干舊作,談藝術、談教育、談婚姻、談讀書,甚至談「吃」,還有十封給女兒的信。從內容與稿末註明的發表時間,可以知道我對音樂的興趣固然不自今日始,我談畫的見解也有一些非今日所能及。大約入學問之途愈深,去創造之途卻可能愈遠,因為創造最需要的還是敏銳的厘覺,當我們集中注意力於知識時,留給創造的活動空間就變小了。然而創造有時而窮,所以,藝術家與作家如果不肯向庸俗投降,將終其一生都在痛苦的追尋與掙扎中,只有極少的天才可以例外。我從未立志做一位作家,但在臺灣的二十年中,最初由於遣興,以後又為現實所迫,先後寫過文章不下百餘萬字,雖然自律甚嚴,不合意的仍然很多。除了「海天遊蹤」「我從白象王國來」「黃友棣藝術歌曲選」版權屬我,交大中國圖書公司總發行外,三民書局以鍥而不捨的精神,已把我在臺灣期間所寫的散文全部搜括了去,「風樓隨筆」是最後一本──已出版的有「摘星文選」「我祇追求一個圓」「夢與希望」總共四本,都曾經我親自淘汰,親自校對,我所承認的,也只有這些版本,不敢說全無謬誤,不敢說都值得為它們浪費時間,但已盡了我的力量。今後我是否還寫呢?自己也不知道。我最快樂的書,完成於最痛苦的心情中,卻是事實。感謝寫作,無論如何,它不失為一處逃避風暴的安全港,在那世界裡,可以忘情於物外,使現實成為可以忍受。記得童年時,偶然與小伴兒推開鄰家側門,望見一片荒園,叢草沒脛,幾枝瘦怯怯的桃金孃在夕陽下搖曳,蟲兒嚶嚶在鳴,我怔怔地看了半嚮,只覺空氣中有一種甚麼力量把我懾住了,那時沒有機車,沒有市聲,只有一片的靜……我心裡有說不出的喜歡;從那時的景物看現在,才發現我們這一代人巳跑了有多遠!當我開始校對這書時,太陽神十號正作繞月飛行,拫據太空人發射回來的電視畫面,月球醜陋不堪,美麗的想像全部粉碎。若月球上也有我童年時所見的荒園,一定被人驚為仙境;我之念念不忘,就正因它出現在我寂寞的童年;風樓歲月令人懷念,亦復如此。所以,窗外縱有萬紫千紅的美景如畫,我仍愛那風樓,愛那淒清歲月,愛那些工作,更愛我曾住過廿載之久的臺灣,而這幾本小書,就正是我報答這塊土地的禮物。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六月廿九日於泰京曼谷 - 目次
前 記
詩人的畫
白色的畫家
歡樂童年
藝術的陶冶
評聯合彩色影展
現代畫的欣賞
繪畫應往何處去?
評「兇手」
「松窗憶語」跋
「善」與「美」的結合
珍妮畫像
悔罪女
論華嚴女士「智慧的燈」
寫給女兒
贈你們一支慧劍
青春──是世上最大的財富
健康──是美滿幸福的鎖鑰
愛美──是端正品格的潛力
興趣──是平衡情緒的良藥
書籍──是啟迪智慧的泉源
毅力──是邁向成功的礎石
語言──是表達思想的工具
感情──是善惡之間的火種
漫長的路
教吾兒作文
談「吃」
木瓜之喻
談今後的女子教育
漫談健康與教育
迎接「劃時代的三八」
戀愛與結婚
我看婚姻制度
女明星為甚麼要自殺?
永恆的目標
顧曲餘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