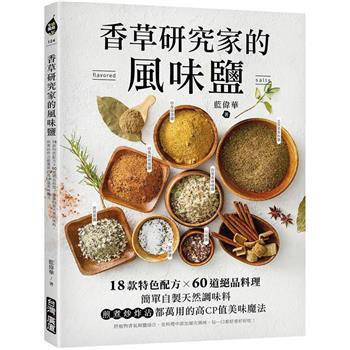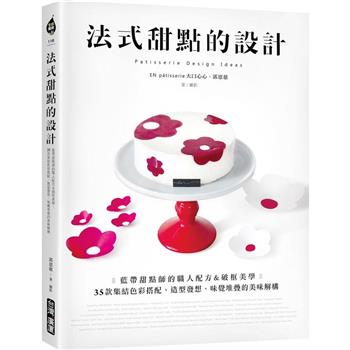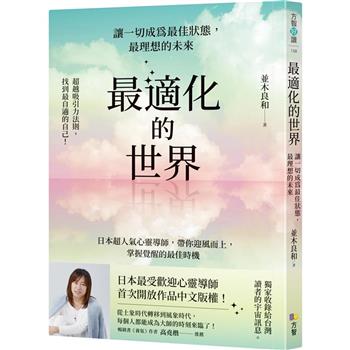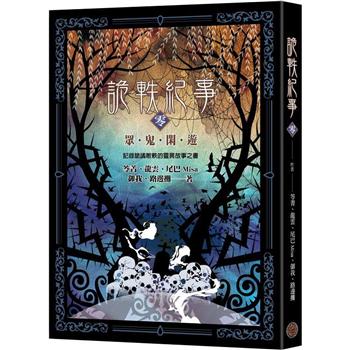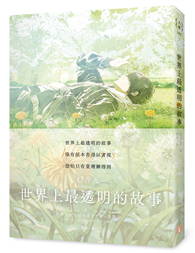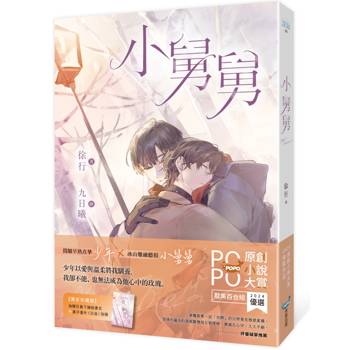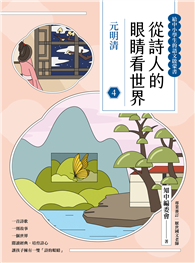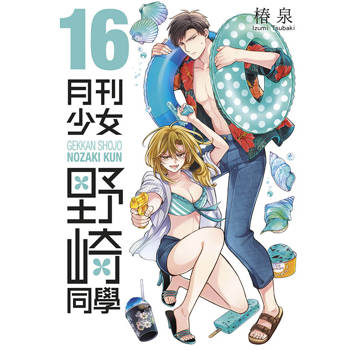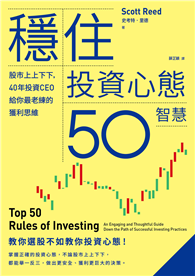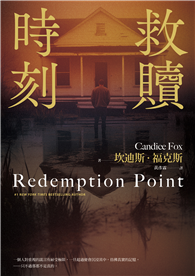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我與文學(三版)(美好年代典藏版)的圖書 |
 |
我與文學(三版)(美好年代典藏版) 作者:張秀亞 出版社: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06-2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76 |
二手中文書 |
$ 300 |
新書推薦79折起 |
$ 300 |
Books |
$ 323 |
文學作品 |
$ 342 |
小說/文學 |
$ 361 |
中文書 |
$ 361 |
現代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你是否終日為生活所需而忙碌?
你有多久不曾留意身邊的人事物?
「美文大師」張秀亞女士以美善的心靈、細膩的情思、優美的文字寫成這本《我與文學》。它將開啟你的心靈,讓你以新的眼光來看待身邊的一切,發現日常的美麗輪廓。
我有一個時期,曾企圖自室內走到戶外,如今,我才發現在戶外停留得太久了,我要回到屋簷下,回到心靈的內室裡來,諦聽他人以及自己靈魂的微語──那才是人類真正的聲音。
|美好推薦|
攝影作家|蔡傑曦
作家|Kaoru阿嚕 阿飛 知日謙 彼岸的鹿 黃繭 游知牧 溫如生
|系列緣起|
當代臺灣女性創作者在文壇一片璀燦,往前推至戰後的五O年代,顛沛來臺的外省移民第一代婦女,在臺灣女性書寫未臻成熟的時期,墾闢前路。而張秀亞女士便是在數點繁星當中閃耀的一位。家國的動盪讓許多生命出現凹折,宏大敘事不足以關照個人生命,張秀亞女士用小敘事突圍,在「自己的房間」創造臺灣女性書寫早期範式,《北窗下》在臺灣出版獲得廣大迴響,直到八O年代再版次數衝破二十三次,締造傳奇。她是西潮之下的摩登新女性,在老文青的少年時代,人人持卷,愛不釋手。
但傳奇女子轉過身來,是生離丈夫、獨自攜幼來臺的顛簸動盪。主外兼主內,揀選柴米油鹽,安頓撕裂的心肺並非從容簡單;她推著自己往前、專注生活的細節,將那些細瑣幽微的美好投入筆端,奠定自己的美文書寫風格。她成為自己的光照、成就整個美好年代。
一個甲子過去,適逢張秀亞女士逝世二十周年,編輯部輯選其經典著作,以饗讀者。看她專注於那些曾經斷裂的日常,在生活的細微處滌塵去垢,她亦或是他;妳亦或是你,在我們的年代,都能創造出屬於我們的美好年代。
|系列特色|
★五本書的初版日期橫跨1958-1978年,見證張秀亞女士20年的創作生涯。
★展讀張秀亞女士善感的靈魂與極致的微物書寫,發現平凡日常的美麗輪廓。
★邀請于德蘭女士記敘母親的寫作情思,讓讀者更貼近一代美文大師。
作者簡介:
張秀亞(1919年―2001年)
河北滄縣人。筆名陳藍、張亞藍、心井。北平輔仁大學西洋語文學系、歷史研究所史學組畢業。曾任重慶《益世報》副刊主編,來臺後曾任靜宜英專(今靜宜大學)、輔仁大學中文系及研究所教授、輔仁大學英文系與德文系大學部教授,並曾在美國西東大學擔任講座。作品領域寬廣,涵蓋新詩、小說、散文、評論、翻譯、藝術史,曾獲婦聯會新詩首獎、中國文藝協會首屆散文獎章、中央婦工會首屆文藝金質獎章、中山文藝獎首屆散文獎。著有詩集《水上琴聲》,小說集《藝術與愛情》、《那飄去的雲》,散文集《北窗下》、《牧羊女》、《水仙辭》,評論集《寫作是藝術》等,共八十餘種。
作家|Kaoru阿嚕 阿飛 知日謙 彼岸的鹿 黃繭 游知牧 溫如生
──美好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列)
∣系列緣起∣
當代臺灣女性創作者在文壇一片璀燦,往前推至戰後的五O年代,顛沛來臺的外省移民第一代婦女,在臺灣女性書寫未臻成熟的時期,墾闢前路。而張秀亞女士便是在數點繁星當中閃耀的一位。
家國的動盪讓許多生命出現凹折,宏大敘事不足以關照個人生命,張秀亞女士用小敘事突圍,在「自己的房間」創造臺灣女性書寫早期範式,《北窗下》在臺灣出版獲得廣大迴響,直到八O年代再版次數衝破二十三次,締造傳奇。她是西潮...
民國二十四年在初中讀書時,我即曾試著向當時天津《益世報》的〈文學週刊〉投稿,到今年正好是三十年,(偶發舊篋,微黃的紙色,見出時光的留痕。)這本書也恰好是我的第三十本文集,可謂巧合!
在這裡,我要向三民書局的劉經理道謝,由於他的盛意,這部散文集得以出版,而我正好用以做紀念我寫作「小小三十年」的里程碑,也可以用來作為我這格子紙上的蹉跎者以後寫作的分水嶺。書名也是出於劉先生的建議:以集子中的一篇的題目作為書名,這個題目「我與文學」,雖並不見得能概括這個文集的性質,卻多少說明了這個文集的意義...
母親手中的筆 ― 追求美的最高境界/于德蘭
重讀母親的《我與文學》/于德蘭
前記/張秀亞
【第一輯】
春天的聲音
貓
雨夜
月圓
春
水松
文竹
風鈴
海棠樹
小城‧老屋
夏日小箋
歌
呼喚
我愛雲
楓葉
田園
小花
白色的節日
池畔
秋
初秋隨筆
深秋
落雪的日子
雪地上
山與水
寂寥
杏黃月
星影搖搖
旋轉的燈柱
沉默
知音
【第二輯】
詩‧生活
吾師
我的一位老師
寄給薔
致友人書
有寄
小箋
黃鳥‧小孩
愛之火
歸
馬槽邊的小羊
快樂痛苦
笑
【第三輯】
一年來
我與文學
讀書偶得
月夜讀畫
讀畫記
圖繪感情的畫師
散文的抒情
文字的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