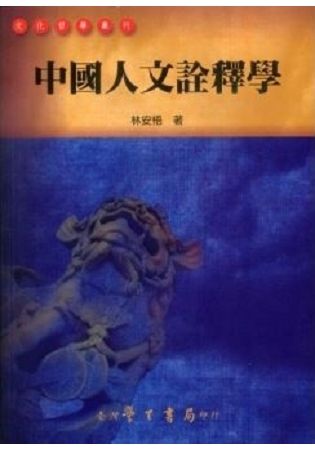「人文」是「由人而文,由文返人」,而「人」則生於「天地」間。
「方法」是「由法而方,由方返法」,而「法」則可溯於「道」。
「論」與「學」,是「道」之經由「人」「文」,如其「方」「法」,而訂定之,所以成之﹔時刻迴返,時刻開顯,剎那生滅,永不停歇。
「詮釋」是「話語的進入」,進一步使得「話語瓦解」,因之而有「意義的釋放」。再者,由於「意義的釋放」,調適而上遂於「道」,就在這「存有學的探源」活動中,才有「道的光照」。
有了「道的光照」,才有「意的趣向」,才有「象的顯現」﹔進而才有「形的構造」,才有「言的執定」。「道」、「意」、「象」、「形」、「言」這五個層次是彼此迴環相生,相續不已的歷程,如船山學所說,他們是「互藏以為宅,交發以為用」的,這裡隱涵著獨特的「詮釋學的迴圈」(hermeneutical cir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