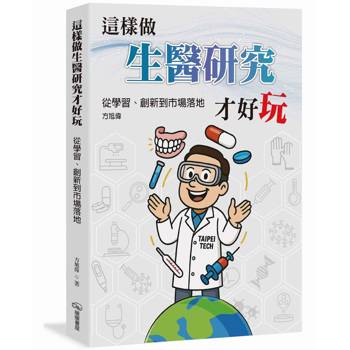『新本格派』代表作家法月綸太郎出道二十年最負盛名的代表作!
『是誰殺了我的兒子?!』我多想理直氣壯地如此大聲吶喊。
可是一旦揭穿了這個秘密,
多年來我拚命保護的一切就將瞬間化為烏有!
我好害怕,比什麼都害怕……
『山倉史郎,是你殺了茂!』富澤路子幾近瘋狂的控訴在我腦海裡不斷回響著……沒錯,是我殺了她的兒子茂。若不是我沒能及時交付贖金,可憐的茂也不會被撕票;若不是綁匪抓錯了人,現在躺在太平間裡的應該是我家的隆史;若不是七年前我一時鬼迷心竅背叛了妻子,跟路子上床,茂根本不會誕生在這個世界上!茂其實是我的私生子,然而此刻我卻僅能望著他的『父親』哭喊兒子的背影。我的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憤怒──到底是誰?竟然如此殘忍地殺害一個孩子!我發誓,一定要揪出這個可恨的兇手……
一件『綁錯人』的擄人勒贖案,讓無辜的孩子富澤茂代替同學山倉隆史而死,也牽扯出兩個家庭間複雜的感情糾葛。而整件事的始作俑者山倉史郎在自責與罪惡感交織之下,決定自己來追查兇手。原來,隆史是他的養子,而死去的茂才是他的親生兒子!
他的心中浮現出一個可疑的人物──隆史的親生父親三浦靖史。然而,三浦卻有很明確的不在場證明,而且他的證人還是推理小說家兼名偵探法月綸太郎。儘管如此,山倉卻並未就此抹去對三浦的猜疑,他甚至認為,法月綸太郎也可能是三浦的共犯……
作者簡介:
法月綸太郎
Norizuki Rintaro
1964年出生於日本島根縣松江市。就讀京都大學時,加入推理界人才輩出的『推理小說研究會』,和綾辻行人、我孫子武丸等人都是『新本格派』推理作家的代表人物。
1988年,他以《密閉教室》入圍江戶川亂步賞,因此獲得推理大師島田莊司的大力推薦而出道。1989年發表以『法月綸太郎』為主角的《雪密室》和《誰彼》,從此展開了『法月綸太郎』偵探系列,如《為了賴子》、《一的悲劇》、《再一次的紅色惡夢》、《法月綸太郎的冒險》等。其後,他以《二的悲劇》(皇冠即將出版)入選『這本推理小說真厲害!』1995年度10大最佳推理小說以及『探偵小說研究會』1975~1994年本格推理小說BEST 100,2002年則以〈都市傳說〉榮獲第55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短篇小說獎,2005年再以長篇《去問人頭吧》贏得第5屆本格推理小說大賞。
在他的作品中,常反映了身為作者内心的苦惱;而擔任『偵探』角色的法月綸太郎亦常融入事件中,與當事人同喜同悲,他也因此獲得了『煩惱作家』的稱號。
章節試閱
ong第一章
開端── 替換物語綁架事件
1
好幾條的水滴痕劃過車窗。不知不覺,外頭已經下起雨來了。在墨色的夜中,一條條模糊的街燈拖著淡淡的尾巴一個接一個地掠過車窗。
『請問……現在開到哪裡了?』
富澤耕一詢問前座的警官。他的側臉照映在玻璃上,聲音則微弱如耳語。
警官只簡短回答了『東大和市。』沒有更多的說明。富澤瞄了我一眼,卻也沒說什麼,將背靠向中間的位子。
我看了看手錶。
現在接近凌晨三點半。從久我山的家中出發至今已經過了將近一個小時。然而,由於來到不熟悉的地方,所以對於還需多久時間才能抵達目的地,真的是毫無頭緒。
跌傷的傷口,直到現在才開始在身體各處隱隱作痛。輕輕將手按在右耳上,發現先前撞到的地方燙燙腫腫的。我將頭靠在玻璃上,讓肌膚獲得冰涼的刺激。然而,即便這麼做,也無法弭平內心的自責。
『茂──』
左後方傳來絞緊喉嚨般的抽泣聲。那是富澤的妻子──路子的聲音。之後,不斷傳來斷斷續續的呻吟聲。富澤耕一回應這個聲音,彎著上半身,緊緊握住路子的手。我死命壓抑想要摀住耳朵的衝動。這次換前座的刑警半轉向我。他是杉並署的竹內警部補。我們眼神交錯,他沒有說話,再度將目光移回前方。最後,路子垂著頭,安靜了下來。
我再次將眼神瞥向窗外。深夜,車輛稀少,好一陣子只聽見雨刷刷開雨水的聲音。這輛車並沒有鳴警笛。
『竹內警部補──』
開了約五分鐘,帶著雜訊的男子聲音從警察無線電裝置中傳了出來。竹內拿起麥克風回覆。
『我是青梅署的搜查員,已經找到孩童的遺體了。』
在無線電宣告事實的這一刻,車內的空氣彷彿凍結了。富澤耕一的身體有如脈搏鼓動般痙攣了起來。由於我和他在狹窄的後座中促膝而坐,因此他的震動直達我的骨子裡。我沒有勇氣在這個時候看路子的臉。
『在哪裡?』竹內以低沉且平淡的聲音詢問對方。
『就如兇手所說的,在青梅養老院附近的工地上,孩童的特徵也都符合。遺體將立刻送往青梅東醫院。』
『醫院的位置是?』
『從青梅署往南五十公尺,位在同一條路上。』
『了解。我們大概在十五分鐘後就會抵達醫院。孩子的父母也在車上,所以麻煩告訴他們盡速準備確認身分的手續。我希望盡速完成。』
『了解。』
一句短促的回答後,無線電便斷線了。
『他剛才說找到遺體了,他說找到孩童的遺體了。』路子突然發出有如高燒時呻吟般的聲音。
富澤耕一猛然抱緊妻子,將她的額頭按在自己的手臂上。
『說不定是搞錯了。山倉先生,拜託你跟我妻子說明一下。』
他突然叫了我的名字。
我無法回答。如果為了一時的心安而附和了他,將成為天大的謊言。老實說,我老早就預料到這個最壞的結果。
『富澤先生,富澤太太──』此時我聽見竹內的聲音。他透過後照鏡看著他們。『看來應該就是你們的孩子,我想你們最好做好心理準備。』
我內心複雜的情緒交錯。竹內所說的雖然不無道理,但有必要在這個時候強調嗎?這或許並不是單純的辦案程序而已。
因為竹內的一句話,路子開始哽咽。富澤耕一也不知該如何安慰妻子,只能眼神呆滯地望著車頂。
我開始後悔和他們兩人一起行動。這不是因為身體上傷口的疼痛。我自以為要求同行是出於一種責任感的行為,然而這個心情背後卻緊跟著無法逃脫的罪惡感。
自從離開久我山的家到現在,我不斷試圖將自己和富澤夫婦的悲傷情緒切割開來,卻也因為這個念頭更加深自己的罪惡感。簡直是惡性循環。然而,最壞的結果還等在後頭,而我有義務目睹那個場面。
汽車左轉離開青梅街道,似乎進入了市中心。穿過建築中的公寓大樓旁,青梅警察署出現在熄了燈的商業大樓之間。外頭太昏暗,無法判讀,不過正面的牆上掛著防治犯罪的標語布條。
經過大樓前,再前進約五十公尺,車頭燈照亮了『青梅東醫院』的招牌。用螢光塗料所畫的箭頭指示著夜間入口的方向。車子從未開的正門前倒退,左轉進眼前的道路。
夜已深,而且還是雨中,夜間入口周圍卻擠滿人群,在那裡形成五顏六色的雨傘花朵。不用詢問身分,也知道他們肯定是聞訊趕來的媒體先鋒,有如獵犬般的傢伙們。
駕駛座的警官猛按喇叭破壞人牆,總算開了進去。竹內回頭告訴我們:
『到了。請下車。』
我打開自己這方的車門,單腳踩在淋濕的水泥地面上。帶著相機的人們擠到後保險桿處。探出頭的同時,所有閃光燈不斷閃爍,我不禁舉起手遮眼睛,然而光線依舊令人暈眩。
人群中,有人對著我伸出麥克風,他誤以為我是孩子的父親。我打算先替富澤夫婦開路。
『孩子被兇手殺害,您作何感想?』
『吵死了!』我怒斥他,猛力甩開他的手,似乎撞到什麼東西而發出怪聲,但我沒去理它。
富澤夫婦相擁,低著頭,總算下了車。停車場上此起彼落的聲音掩蓋了路子的啜泣聲。竹內撥開一堆相機,在媒體群中保護兩人。這樣的場面,讓他們兩人簡直和落網的重刑犯沒兩樣。我們胡亂衝向建築物中。
外頭的喧鬧彷彿是一片虛幻,院內沉寂在寒冷的寧靜之中。幾個表情嚴肅的男人沉默地往來各樓層。身穿魚骨紋西裝外套的男子一看見他們,立刻叫住竹內。
『你就是杉並署的人?』
『我是竹內警部補。』
『我是青梅署刑事課課長,松永。』兩人交換了同行才能理解的眼神。
『他們是被害者的父母。』竹內並沒有介紹我。
松永向富澤夫婦再次道出自己的名字,並說明自己是該案的負責人,接著表達制式的哀悼之意。富澤耕一打斷他的話。
『還不確定那就是我兒子。遺體在哪裡?』
『在地下室的太平間。你們可以馬上過去確認嗎?』
富澤點頭。不論結果如何,他似乎想盡早解決這件事。路子的臉頰濕透了,猶如沒有知覺的人偶般沉默。
『那麼,走吧!』竹內說。
松永課長帶領我們往前走。走下角落的樓梯後,一行人便擠成一團,走在充滿消毒藥水味的樓下走廊。沒人開口,唯有腳步聲響徹整個空間。
走廊深處,一扇陰森的門上平凡無奇地寫著『太平間』幾個字。松永打開門,請我們進去。
路子在門前裹足不前。富澤抱著妻子的肩膀,催她一起進去。路子沒有反抗,遵從丈夫。我也打算跟著兩人進去,卻被竹內擋住了。
『你不行。你不能進去。』
『為什麼?』
『你不是孩子的家屬。』
竹內只說了這一句,便讓我吃了閉門羹,無法表達異議。走廊只留下我一人。
不到三十秒,耳邊傳來了路子嚎啕大哭的聲音。果然,不會錯了。哭聲持續了好一陣子。我咬緊牙根佇立在門前,試著將路子的哀號刻入自己的耳朵裡。門突然開啟,松永課長的臉出現了。
『這孩子還這麼小,竟然白髮送黑髮,教誰都受不了呀!』
我點頭。這時,松永似乎突然對我的身分感到好奇。
『我忘了問你,你跟家屬到底有什麼關係?』
『──山倉史郎,兇手原本計畫綁架的是他的兒子。他住在他們家附近。』在我開口之前,竹內已搶先說明。他也剛回到走廊。
松永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看著我。
『你可真走運呢!要是兇手沒出錯,現在躺在那裡的就是你兒子了。』
從松永的語氣聽來,他顯然早已知道我今天的失誤,所以話中帶刺。腫脹的頭部發疼。本想反駁,卻在開口前又有人插進來了。
『──都是因為你。』
那是路子的聲音。她擋在敞開的門前,用哭腫的眼睛瞪著我。雖然哭得妝都花了,她也不在意。
『都是因為你,茂才會──』
『別說了。』富澤耕一從背後抓住妻子的襯衫袖口,試圖安撫她。『不能怪山倉先生,那不是他能控制的情況。要怪就怪兇手。』
『才不是。』
路子甩開丈夫的手,以堅定的步伐走向我。兩名警官被路子的氣勢震懾住了,從她的面前逃開。我靜靜佇立著,在伸手可及的距離下接受路子的責難。
『是你殺了茂。』
『路子。』富澤耕一制止她。
路子不理會丈夫,雙手抓起我的襯衫,歇斯底里地拉扯。我只能任由路子擺佈,因為我無法動彈。
『是你殺了茂!』
她像是失去平衡的風箏一樣,忽然晃了一下,下一瞬間就突然倒在地上。我身上的襯衫釦子被她扯了下來,空虛地滾落在地上。路子的臉碰到地毯,像個孩子般啜泣,不斷不斷地重複著同一句話:
『是你殺的──』
是我殺的?
沒錯,的確是我殺的。不論理由為何,是因為我,才讓一個無辜孩子的生命消逝。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我無法辯白。不,我根本不打算辯白。一個堂堂男子漢,怎麼會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呢?
我不會原諒奪走富澤茂年幼生命的兇手。同時,我也無法原諒我自己。因為我不得不承認,內心深處躲藏著另一個自己,期待茂的死亡。
富澤茂,是我的兒子。
2
凌晨四點半。青梅署二樓,我被要求獨自待在六個榻榻米大的冷清房間裡等候。這是只有鐵桌和幾張摺疊椅的充滿灰塵的房間。地板的地毯裂開了,露出地毯與水泥的縫隙,裡面積滿黑黑的塵埃。看來,連清潔人員都放棄它了。
富澤夫婦也在這個署裡的某個房間裡,由警方向他們說明必要的手續與今後的事宜。原本我也打算列席,但因為路子拒絕,於是我就這樣被迫獨自度過空虛的時間。
我發現窗外有一排鐵柵欄的影子,想必這裡原本是偵訊嫌犯的地方吧!從青梅署玄關被人一路帶往這裡時,我應該抗議警方的無禮對待,然而,我在肉體上、精神上都早已筋疲力盡,連向竹內或松永那些傢伙發火的力氣都沒有。
或許我也有點希望獨處吧!在醫院太平間的那一幕似乎嚴重打擊了我。
桌上擺著骯髒的鋁製菸灰缸,但我打從兩年前就戒菸了,就算這裡有菸灰缸也派不上用場。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其他解悶的辦法,只好像個破布般靠著椅背,緊盯著入口。
等待的時間太久,反倒加深內心的不安。那是一種近似愧疚的焦躁感。為何獨留我一人?我猜不透青梅署的用意。簡直就像只有我被排擠在外似的,令人忐忑。
話說從頭,富澤夫婦會捲入這個事件是因為兇手出錯所導致的結果。兇手的目的在綁架山倉家的兒子。因此就往後的辦案方向而言,我的存在比富澤夫婦重要。
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忽視我,是因為青梅署人手不足嗎?還是因為目睹孩子的死亡,所以警方聯手懲罰我?總覺得應該是後者。然而,這個可能微乎其微,我也不得不感慨自己一定有問題。這也算被害妄想的一種,或許是身體上的疲勞與疼痛的傷口正在腐蝕我的正常思考?
我並不是沒想過走出房間尋找電話,聯絡家人。或許只要聽聽妻子的聲音就能夠多少安撫情緒,趕走毫無根據的妄想。然而我沒有這麼做,是因為路子。她指控我的吶喊聲至今依舊在我的腦袋裡回響。
『是你殺了茂。』
這聲音依然停留在耳裡,我無法跟和美說話。
如果現在跟和美說話,在雙重罪惡感的折磨下,我可能會脫口說出茂是我兒子的真相。我害怕自己會這麼做,而且比什麼都害怕。
因為太害怕這個可能性,所以我產生一種預感,認為自己真的會在妻子面前說出這個事實。光想到這些,我就起雞皮疙瘩。自白的恐懼化為一種強迫的行為,增長我的不安與焦躁。
我告訴自己,只要在這個房間,別說是打電話了,就連想起妻子都不可以。把腦袋放空吧!然而,越想把她從腦海中趕走,心裡卻越加想念和美的身影。好比肺渴求氧氣一樣,我無法抗拒這個反應。
和美。
我的妻子。
這種說法雖然平庸,不過我非常愛我妻子。她絕對不是那種會引人注目的亮眼美女,然而柔和緊緻的端正五官散發著樸實隨興的美。她那不虛偽的微笑保留了少女般的清純,她的擁抱蘊含著自然流露的體貼與溫暖,只要觸碰她,我的情緒便立刻和緩了下來。我有一點不好意思把這稱作愛情,但毫不保留的互信關係繫絆著我們。和美是無可取代的、最理想的伴侶。
然而和美卻一直深信自己是個醜陋的女人,除非為了錢,否則不會有人想要和她在一起。直到與我結婚為止,這種想法一直伴隨著她。
『欸,門?專務的女兒啊!你應該知道吧?不是次美小姐,而是不起眼的大姊。』
她篤定外界是以這樣的眼光看待自己。我剛認識她的時候尤其嚴重,她對任何事都相當消極,容易自閉。
和美會這麼想的原因之一應該和她妹妹有關。次美是個人人稱讚的大美女。她腦筋動得快,有別於內向的姊姊,個性活潑外向,言行大膽。她曾被一家半職業性的劇團相中,拔擢為主角演了好幾齣戲,愛慕她的男人總是大排長龍。儘管如此,她的女性緣也不差,我猜是她爽朗的個性為她加分不少。和美拿這個妹妹與自己相比,永遠抱持著毫無根據的自卑感。
然而令我不解的是,在我之前,難道沒有任何人發現她的魅力嗎?她不過是和妹妹完全不同類型的女人罷了。由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先入為主的錯誤觀念是如何蒙蔽了男人的眼光。不過也幸虧這樣我才能夠得到和美,因此我沒有理由批評他們。後悔不已的,是除了我以外的那些男人。
不過,最早發現和美的魅力的人似乎是次美。我會跟和美交往,其實是因為得到了次美的幫忙。就這一點而言,我非常感謝次美。現在談起她已經成了過去的往事,因為很遺憾的,次美已經過世七年了。
我和路子發生關係正好也在同一年。正確來說,那是在次美過世的前兩個月。當時我已經跟和美展開了婚姻生活。
想起當時,我不禁厭惡自己。我並沒有對和美失去感情,而我做出這種背叛妻子的行為,正是導致這個事件的原兇。『鬼迷心竅』這句話真正的可怕之處,只有實際體驗過的人才懂吧!對我而言,除了鬼迷心竅之外,無法解釋與路子之間發生的事。
當然,妻子根本不曉得我與路子之間的事。萬一和美知道了,我們這個家庭勢必分崩離析,我絕不能夠讓這種事發生。這是我一個人的痛苦。它將否定、侮辱和美人生的一切,而我有義務保護妻子與家庭。就算有人譏笑這是出於男人的自私心態,但我還是必須拚了命保衛這個秘密。
我必須克服自己的軟弱,停止自憐自艾的情緒。從今以後不論發生任何事,我的心必須穿上鎧甲。這不是為了我,而是為了和美的幸福。
走廊上逼進的腳步聲打斷了我混亂的思緒。連個敲門聲也沒有,門就被打開了,接著竹內警部補走了進來。一如往常,一臉不悅的表情。
『久等了。請跟我來。』
只有嘴巴還算慇懃,但他的態度依舊傲慢。我刻意不應答,起身跟著他離開房間。因為坐太久,感覺自己的臀部像個乾黏土般失去彈性。
走到走廊上,我看見富澤耕一。他的臉色暗沉,呈現不健康的土色,雙眼似乎也混濁成褐色。那不是因為走廊的照明昏暗,因為我可以清楚看見眼睛底下的黑眼圈。
我若無其事地環顧四周,卻沒有路子的身影。
『接下來,我會去看發現我兒子的那個工地,』富澤聲音沙啞地說:『如果方便,山倉先生能不能跟我一起去?』
預料之外的要求。
『為什麼會想找我一起去?』
『茂的事情造成你很大的困擾。你不但幫忙籌贖金,還在那麼危險的情況下,遵從兇手的指示……』
『請別這麼說。如果我更注意一點,茂也不會有這種下場。』
『我並不是在責備你,』富澤急忙揮揮手。『我打從心底感激你。我當然感到很痛心,但這跟你沒有關係。拜託你,為了我兒子陪我去一趟。』
看來這是富澤的肺腑之言,這反倒更加折磨我。
『──可是如果我一起去,你太太不會答應吧!』
『我太太不會去,她現在躺在四樓的醫務室。』
『怎麼了?』
『她因為不舒服而昏倒了,不過不用擔心。可能是因為打擊太大,所以情緒一時無法平復吧!她已經打了針,稍微睡一下,應該可以恢復正常。』
富澤的回答透著點空虛。孩子都死了,還能恢復正常嗎?當事人應該有更深刻的感觸,他的外表卻絲毫不見這樣的跡象。他現在暫時麻木自己的感情,將悲傷擱在一旁,試圖撐過這一關。我十分同情他。如果我的同行多少能讓富澤的情緒振奮一些,我也沒有拒絕的道理。
『好的。』我對富澤說。
我們下了樓梯,走出玄關,不理會留在停車場的記者們便快速坐上車。
我坐進青梅署的車。不是警車,而是普通的豐田『皇冠』轎車。駕駛座上坐著青梅署的刑警,他姓宮本。富澤和我坐在後座,竹內像先前一樣占據了前座。
『就算你不肯,我也要硬把你拉過來。』車子行駛沒多久後,竹內對我說:『這個事件的主角是山倉先生。請你別忘了這個事實。』
這種事不用別人提醒,我自己最清楚。然而,現在的我沒有資格說出這句話。頭上的腫塊又隱隱作痛,我只能咬緊牙關忍住羞愧與窩囊的情緒。
ong第一章開端── 替換物語綁架事件1好幾條的水滴痕劃過車窗。不知不覺,外頭已經下起雨來了。在墨色的夜中,一條條模糊的街燈拖著淡淡的尾巴一個接一個地掠過車窗。『請問……現在開到哪裡了?』富澤耕一詢問前座的警官。他的側臉照映在玻璃上,聲音則微弱如耳語。警官只簡短回答了『東大和市。』沒有更多的說明。富澤瞄了我一眼,卻也沒說什麼,將背靠向中間的位子。我看了看手錶。現在接近凌晨三點半。從久我山的家中出發至今已經過了將近一個小時。然而,由於來到不熟悉的地方,所以對於還需多久時間才能抵達目的地,真的是毫無頭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