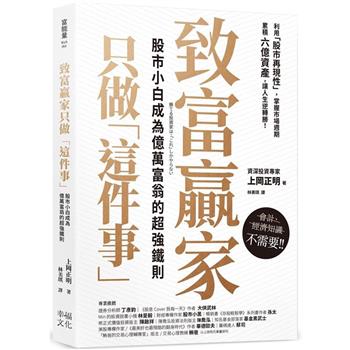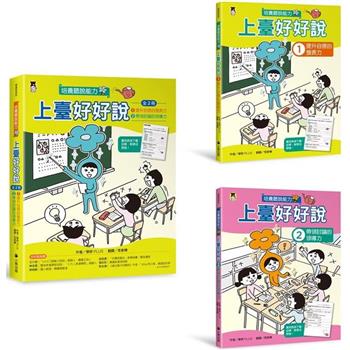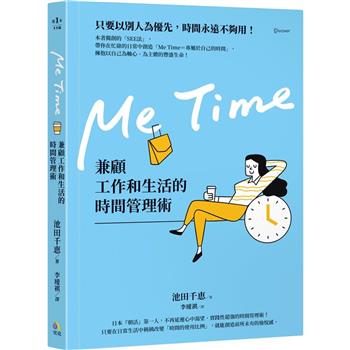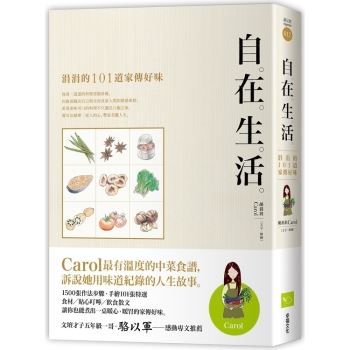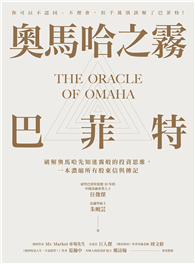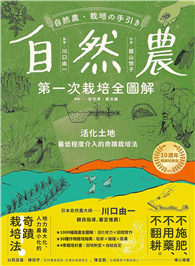導讀
島田莊司的舊情綿綿
推理作家、評論家 / 既晴
Ⅰ
一九九○年,是島田莊司才剛發表過融合本格與社會兩大流派的吉敷竹史探案傑作《奇想、天慟》(1989)、出道也即將屆滿十年的轉折期。
這一年,他總結了以往多方嘗試各種風格、各種題材的作家第一期,累積了豐富、多樣的創作經驗,於十月推出巨篇大作《黑暗坡的食人樹》(1990),朝「新.御手洗」時期前進,展開一年一部巨篇的創作長跑。
當然,既是決定在「本格Mystery」專注開拓更遼闊的未知可能,島田莊司就必須放下曾經割據他寫作時間的其他作品。例如,以輕鬆幽默風格為基調的「說謊也無所謂」系列,在推出兩部單行本以後就宣告落幕,電視台的「造假節目」導演輕石三太郎、打工者隈能美堂巧的身影再也不能復見;在《綢緞美人魚》(1985)裡的前賽車手、私家偵探「我」,僅僅登場一次──而這也是島田唯一一部冷硬派作品;更不用說取得角逐直木獎資格的《夏日、十九歲的肖像》(1985)中所呈現的青春懸疑氛圍,這條特殊的寫作路線也僅有此作。
尤其是以寫實風格為主的警界主角們,像是札幌警署的牛越佐武郎、東京警署的中村吉藏,都曾經活躍在強調社會性動機的罪案搜查中,這兩位踏破鐵鞋、一步一腳印的篤實刑警,曾經是島田表現社會派寫作功力的最佳代言人,也隨著島田創作方向逐漸回歸幻想至上、解謎至上的原初理念而逐漸淡出。
事實上,在島田作家生涯的前十年裡,創作數量最豐碩的系列,自然非吉敷竹史探案莫屬。儘管是跟從當時推理文壇上的寫實主流路線,捨去了天縱英明的名偵探,但在島田熱愛謎團的堅持下,從《寢台特急1/60秒障礙》(1984)裡最早的「都市傳說」風格,進展到《出雲傳說7/8殺人》(1984)的「日本神話」主題,吉敷探案仍然洋溢出一股不同於業界同類的怪奇色彩。
而在第三部作品《北方夕鶴2/3之殺人》(1985)裡,前妻加納通子突如其來的一通電話,更進一步地讓吉敷放下警務工作,遠赴北海道釧路尋找她的行蹤,而隨著離奇事件的不斷牽引,他也慢慢接觸到通子不可解的身世之謎,這可說是吉敷追查私人事件的開端,是系列中的異數。
這樣的特殊設計,開啟了吉敷探案的新可能──吉敷不再只是高大帥氣、充滿正義感、熱血奮戰的警界精英,屬於常人的七情六慾、喜怒哀樂,他也是一樣不缺。島田賦予了吉敷這樣的背景,至此,吉敷也從風靡女讀者的雄性洋娃娃,蛻變成更立體、更圓熟的角色。
然而,前妻加納通子的身世之謎,並未在《北方夕鶴2/3之殺人》裡全數解明。就在島田進入「新.御手洗」時期的前一刻,他發表了本作《羽衣傳說的回憶》(1990),做為此系列暫時放慢步伐的頓號。故事裡,加納通子再次現身,也帶來新的事件──不過,與前次完全不同,加納通子這次並未主動現身,而是吉敷在謬思女神的召喚下,偶然找到了通子的居所。
對台灣熟悉島田莊司的讀者來說,《羽衣傳說的回憶》可能會令你對島田的印象大為改觀。裡頭沒有窮凶惡極的殘暴壞蛋、沒有錯綜複雜的龐大謎團,也沒有神乎其技的推理論述──也許我們該說,這樣的印象,來自於過去島田以本格為主要範疇的選譯作品,但是,這並非島田作品的完整面貌。
跳開推理小說的框架來看,也許我們該說,其實這是一個熟男熟女懷念昔日美好、冰釋陳年誤會的情愛小說。
Ⅱ
在島田莊司的創作理念中,「謎團」當然是最核心的關鍵字,隨之而延伸的,則是謎團的表現型式、推理解謎的手段,以及透過解謎的曲折過程,揭露闡明關於人類、關於社會、關於文明的各項論述──換句話說,在島田的作品群中,不管是幻想或是寫實、是本格或是懸疑、牽涉到的相關論述的篇幅佔有多少比例,「謎團」仍舊是中心的書寫對象。
島田這種始終強力擁抱「謎團」、遵循古典格律的的創作姿態,固然是他今日鮮明搶眼、別無分號的正字標記,不過,這無疑也可能會增加讀者認知的侷限度。當讀者單單對其驚天動地的詭計設下了過高的期待,便不容易看清楚他在本格推理以外的經營。
在目前台灣已經翻譯的幾本吉敷竹史探案中,儘管表現手法各有側重,依然全是屬於謎團特質強烈的作品。在《北方夕鶴2/3之殺人》後直到《奇想、天慟》之間,吉敷探案其實經歷過相當程度的轉變,這也是吉敷探案至今之所以能與御手洗探案並肩齊立,成為島田作品中系列雙璧的主因。
御手洗潔,一如過去再三提及的,他永遠是島田心目中神探理想的典型投影,只會隨著島田創作思維的演化而變換形象──相對之下,吉敷竹史的誕生,當初卻是島田為了順應時代的閱讀潮流,才接受了編輯的意見。考慮到年輕女性讀者的市場,並且與辦案勤懇的十津川探案作出區隔,吉敷一開始是以男模般的偶像姿態降臨的。
不過,在御手洗沉潛養晦、吉敷大幅活躍的八○年代裡,島田作品中所碰觸到的社會議題愈來愈多,導致創作的走向也愈來愈趨往純正的社會派路線,於是,最早設定的怪談類殺人事件,也在吉敷探案裡漸次減少,島田的健筆反而藉由一樁樁毫不起眼的芝麻小案,讓讀者目睹現代社會的種種異象,吉敷在搜查的過程中,更表露了愈來愈多的苦惱、憤怒、沉重、無助、掙扎、悲傷等內心衝突的情緒,終於走出了與御手洗潔探案截然不同的格局。
翻開《羽衣傳說的回憶》,也許能得到一個更特殊的閱讀體驗。在本作中,不僅可以見到島田跳脫傳統的解謎格式,也沒有採用懸疑或幽默的表現方式,他更嘗試將謎團的主從關係予以互換──所謂殺人事件的謎團,甚至不是故事主軸,而成了依附於情節進展的小插曲。做為吉敷竹史系列的其中一部作品,本作卻不是讓吉敷解決重大犯罪事件,而是讓他在探尋加納通子的旅程中,逐漸發掘出個人內心真實的私密情感。
此外,《羽衣傳說的回憶》也不是類似《御手洗潔的舞蹈》(1990)裡〈近況報告〉中暢談御手洗潔與石岡和己兩人的室友生活瑣事,屬於增添神探風采的外傳式小說。加納通子的身世之謎,在本書裡還是出現了更多的真相。
Ⅲ
總體而言,若考慮到加納通子的角色定位,吉敷竹史探案就不能單純地認定為「警界精英吉敷竹史的辦案事件簿」。特別從《羽衣傳說的回憶》裡描述,吉敷之所以能成為才智與勇氣兼備的名警探,可說是源自通子的影響。這個系列,在吉敷全力以赴的警務工作以外,也不時穿插著他與通子之間的纏綿悱惻、藕斷絲連,毋寧應擴大視為「吉敷竹史的警探生活紀錄簿」。每每能夠一舉破解重大罪案的吉敷,碰上通子的問題,就會變得多愁善感、方寸大亂,剪不斷、理還亂,與御手洗面對玲王奈時決絕的冷調態度大異其趣。
截至目前為止,通子登場的故事共有──依照時間軸排序,分別是《北方夕鶴2/3之殺人》、《羽衣傳說的回憶》、《飛鳥的玻璃鞋》(1991)、《龍臥亭殺人事件》(1996)、《淚流不止》(1999)及《龍臥亭幻想》(2004)六部作品。其中《飛鳥的玻璃鞋》提到了本作故事的後續,至於「龍臥亭」兩作,因為主角偵探是石岡和己,加納通子的現身僅是驚鴻一瞥。
我們必須得在吉敷探案的唯一巨篇《淚流不止》裡,才能讀到島田以絕大的篇幅來敘述通子的半生。而關於她的謎團,屆時也終將全數揭露。
總導讀
新本格推理小說之先驅功臣島田莊司(三次增補版)
推理評論家 /傅博
●《占星術殺人魔法》是新本格推理小說的先驅作品
說到日本之新本格推理小說的發軔時,誰都知道其原點是一九八七年,綾□行人所發表的《殺人十角館》。但是少有人知道黎明前的那段暗夜的故事。凡是一個事件或是現象的發生,都有原因的,不是平空而來的。新本格推理小說的誕生也不例外,現在分為近、遠兩因來說。
一九五七年,松本清張發表《點與線》和《眼之壁》,確立社會派推理小說的創作路線,之後,新進作家都跟進。之前以橫溝正史為首的浪漫派(又稱為虛構派)推理小說(當時稱為偵探小說),隨之衰微,最後剩下(魚占)川哲也一人孤軍奮鬥。
但是稱為社會派推理作家的作品,大多是以寫實手法所撰寫之缺乏社會批評精神,甚至不少作品變質為風俗推理小說,到了一九六○年代後半就開始式微,於是第一波反動勢力抬頭,就是幾家出版社之浪漫派推理小說的重估出版。
最初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桃源社創刊「大浪漫之復活」叢書,收集了清張以前,被稱為偵探作家之國枝史郎、小栗虫太郎、海野十三、橫溝正史、久生十蘭、橘外男、蘭郁二郎、香山滋等代表作,獲得部分推理小說迷的支持。之後由幾家出版社分別出版了「江戶川亂步全集」、「夢野久作全集」、「橫溝正史全集」、「木木高太郎全集」、「濱尾四郎全集」、「山田風太郎全集」、「大坪砂男全集」、「高木彬光長篇推理小說全集」等精裝版不下十種。
另外,於一九七一年四月由角川文庫開始出版的橫溝正史作品(實質上是文庫版全集,達一百卷),與角川電影公司的橫溝作品的電影化之相乘效果,引起橫溝正史大熱潮,合計銷售一千萬本。象徵了偵探小說的復興,但是沒有出現繼承撰寫偵探小說的新作家。此為遠因之一。
遠因之二是,一九七五年二月,稱為「偵探小說專門誌」以重估偵探小說、發掘偵探小說之新人作家、推動推理小說評論為三大編輯方針的《幻影城》創刊。
《幻影城》於一九七九年七月停刊,在不滿五年期間,以特輯方式,有系統地重估了偵探小說,確立了從前不被重視的推理小說評論方向,並舉辦「幻影城新人獎」,培養出一批具「新偵探小說觀」的新進作家,如泡(土反)妻夫、竹本健治、連城三紀彥、栗本薰、田中芳樹、筑波孔一郎、田中文雄、友成純一等。
《幻影城》停刊後,浪漫派推理小說復興運動也告一段落,只泡(土反)妻夫等幾位幻影城出身的作家,以及《野性時代》出身的笠井潔陸續發表偵探小說而已。代之而興起的,就是被歸類於推理小說的冒險小說。一九八○年代,日本推理小說的第一主流就是冒險小說。
近因是帶著《占星術殺人魔法》登龍推理文壇的島田莊司的影響。
《占星術殺人魔法》原來是於一九八○年,以《占星術之魔法》應徵第二十六屆江戶川亂步獎的作品,雖然入圍,卻沒得獎。改稿後,於八一年十二月以《占星術殺人魔法》,由講談社出版。
占星術是把人體擬作宇宙,分為六部分,即頭部、胸部、腹部、腰部、大腿和小腿。各由不同行星守護。又每人依其誕生日分屬不同星座,特別由星座守護星祝福其所支配部位。
一九三六年幻想派畫家梅澤平吉,根據上述占星術思想,留下一篇瘋狂的手記,被殺害陳屍於密室。手記內容寫道,自己有六名未出嫁女兒,其守護星都不同,如果各取被守護部位,合為一個完美的處女的話,生命實質上生命已終結,其肉體被精練,昇華成具絕對美之永遠女神,變為「哲學者之后(阿索德)」,保佑日本,挽救神國日本之危機。
之後,六名女兒相繼被殺害分屍,屍體分散日本各地,好像有人具意識地在繼承梅澤的遺志。但是梅澤的手記沒人看過,何來有遺囑殺人呢?兇手的目的是什麼?四十年來血案未破,成為無頭公案。
四十三年後春天,事件關係者寄來一包未公開過的證據資料給占星術師兼偵探的御手洗潔,請他解決這一連串的獵奇殺人事件。名探御手洗潔如何推理、解謎、破案之經過,請讀者直接閱讀本書,這裡不饒舌,只說本書是一部蒐集古典解謎推理小說的精華於一書的傑作。
故事記述者石岡和己是名探的親友,完全承襲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御手洗潔根據四十年前的資料做桌上推理,是沿襲奧希茲女男爵的安樂椅偵探;書中兩次插入作者向讀者的挑戰信,是踏襲艾勒里.昆恩的「國名系列」作品;炫耀占星術、分屍的獵奇殺人,是繼承約翰.狄克森.卡爾的浪漫性和怪奇趣味。
本書出版後毀譽褒貶參半,否定者認為這種古色古香的作品,不適合社會派(實際上是寫實派)的推理小說時代,卻不從作品的優劣作評價。肯定者即認為是一部罕見的本格推理傑作。這些肯定者大多是年輕讀者。
處女作是作家的原點,至今已具三十年作家歷的島田莊司,其作品量驚人,已達七十部以上,非小說類之外,都是本格推理小說,而大多作品都具處女作的痕跡。
● 島田莊司的推理小說觀
在日本,小說家寫小說,評論家寫評論,各守自己崗位,工作分得很清楚;不像台灣的作家,人人都是天才,詩、散文、小說、評論樣樣寫,產品卻都是垃圾一大堆,但是有例外。現在日本推理文壇,也有例外,二位作家──島田莊司和笠井潔,卻是雙方兼顧的作家。
笠井潔的評論注重於理論與作家論(有機會另詳說),島田莊司的評論大都是宣揚自己的「本格mystery」理念。
那麼島田莊司的本格推理小說觀是怎樣的呢?我們可從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島田莊司所發表的長篇論文〈本格□□□□□論〉(收錄於講談社版《本格□□□□□宣言》一書裡)可獲得解答。
島田莊司的推理小說觀很獨自,把八十多年來的日本推理小說,大概按時代分為三種類,以不同名稱稱呼,意欲表達其內容的不同:清張(一九五七年)以前的作品群稱為「探偵小說」,即偵探小說也。清張為首的社會派作品稱為推理小說。自己發表《占星術殺人魔法》以後之推理小說稱為「□□□□□」,即mystery的日文書寫。以下引用文,一律按其分類名稱書寫,筆者的文章原則上統一為「推理小說」。
島田莊司對「本格」的功用定義如下:
──「本格」並非為作品的優劣之基準而發明的日本語。同時也非要衡量作品的社會性價值的尺子,只是要說明作品風格,並與其他小說群做區別分類之方便性而登場的稱呼而已。
繼之說明本格的構造說:
──「本格」就是稱為推理小說這門特殊文學發生的原點。並且具有正確地繼承這種精神的作家,在歷史上各地區連綿不斷地生產本格作品,而且從這些本格作品所發散出來的精神,也不斷地引起本格以外之「應用性推理小說」的構造。
島田莊司認為推理小說的原點是「本格」,由本格派生出來的作品就是「應用性推理小說」,他故意不使用「變格」字樣,他說:
──在前文使用過的「應用性推理小說」,就是指具有愛倫.坡式的精神,屬於幻想小說系統以外之作家,運用自己獨特的方式撰寫的犯罪小說。
島田莊司一面承認二次大戰前,被稱為「本格探偵小說」的作品就是「本格」,而另一面卻認為部分作品是非本格作品,但是沒有具體舉出作品名說明。
而二次大戰後,部分人士所提倡的「推理小說」名稱,他認為是「本格探偵小說」的同義語,在「推理小說」上不必冠上「本格」兩字。至於清張以後的「推理小說」,是從「本格」派生的,屬於「應用性推理小說」,所以「推理小說」群裡沒有「本格」作品。
──現在因這些理由,「本格推理小說」這名稱,在出版界廣泛使用。可是,現在所使用的這語言,是否對上述的歷史,以及各種事項具正確的理解,然後才合理的使用,這就很難說了。
島田莊司認為清張以後的冒險小說、冷硬推理小說、風俗推理小說、社會派犯罪小說都是從「推理小說」派生出來的。(前段引文的「這些理由」、「上述的歷史」、「各種事項」就是指推理小說的派生問題)。因此「推理小說」本身要與這些派生作品劃清界線,方便上稱為「本格推理小說」而已,實質上並不具「本格」涵義。由此,島田的結論是「本格推理小說」原來就不存在,名稱是誤用的。
──那麼,「本格」或是「本格□□□□□」是什麼?
──已經理解了吧。「本格mystery」不是「應用性推理小說」,是指極少數的純粹作品。從愛倫.坡的〈莫爾格街之殺人〉的創作精神誕生,而具同樣創作精神的mystery就是。
最後,島田莊司認為愛倫.坡執筆〈莫爾格街之殺人〉的理念是「幻想氣氛」與「論理性」。所以島田的結論是,「本格□□□□□」須具全「幻想氣氛」與「論理性」的條件。
島田莊司的這篇論文,饒舌難解,為了傳真,引文是直譯,不加補語。
● 島田莊司的作品系列
話說回來,島田莊司,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二日出生於廣島縣福山市,武藏野美術大學商業設計科畢業後,當過翻斗卡車司機,寫過插圖與雜文,做過占星術師。一九七六年製作自己作詞作曲的LP唱片〈LONELY MEN〉,一九七九年開始撰寫小說,處女作《占星術殺人魔法》就是根據自己的占星術學識撰寫的作品,出版時是三十三歲。一九九三年移居美國洛杉磯。
以《占星術殺人魔法》登龍文壇之後,島田莊司陸續發表本格推理小說已達七十部以上,非小說約二十部。以偵探分類,可分為三大系列,第一是「御手洗潔系列」,第二是「吉敷竹史系列」,第三是「犬坊里美系列」與一群非系列化作品。這是方便上的分類。島田所塑造的配角,如牛越佐武郎刑事、中村吉藏刑事,在各系列露面。現在依系列,簡介島田莊司的重要作品,書名下之括弧內的「傑作選X」為皇冠版島田莊司推理傑作選號碼。
一、御手洗潔系列
御手洗潔,這姓名很奇怪。「御手洗」在日本是實有的姓名,但是很少。當一般名詞使用時,是「廁所」之意。「御手洗潔」即具清潔廁所之意。作家往往把自己投影在作品的登場人物,不一定是主角,有時候是旁觀者。日本的「私小說」主角,大多是作者的分身。在島田作品裡,這種現象很明顯,不只是御手洗潔,記述者石岡和己也是島田莊司的分身。
據島田的回憶,小學生的時候被同學叫為「掃除大王」,甚至譏為「掃除廁所」,理由是「莊司」的日語發音souji與「掃除」同音。所以把少年時的綽號,做為名探的姓名。御手洗潔的本行是占星術師,島田曾經也是占星術師。石岡和己是御手洗潔的親友,並非作家,記述御手洗潔破案經過的《占星術殺人魔法》以後,改業做作家。島田也是發表《占星術殺人魔法》後成為作家的。
御手洗潔也是一九四八年出生。勇敢、大膽不認輸、具正義感、唯我獨尊、旁若無人的言動等性格,也是與島田莊司共有的。
01《占星術殺人魔法》(傑作選1):
一九八一年二月初版、一九八五年二月出版第二次改稿版。「御手洗潔系列」第一集。長篇。初版時的偵探名為御手洗清志,記述者是石岡一美。不可能犯罪型本格小說的傑作。
02《斜屋犯罪》(傑作選15):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初版。「御手洗潔系列」第二集。長篇。北海道宗谷岬有一座傾斜的房屋流冰館,連續發生密室殺人事件,辦案的是札幌警察局的牛越刑事,他不能破案,向東京救援,被派來的是御手洗潔。島田莊司的早期代表作,發表時也只獲得部分推理小說迷肯定而已,但是對之後的新本格派的創作具深大影響,就是「變型公館」的殺人。如綾□行人之《殺人十角館》等「館系列」,歌野晶午之《長形房屋之殺人》等信濃讓二的房屋三部曲,我孫子武丸之《8之殺人》等速水三兄妹推理三部曲都是也。
03《御手洗潔的問候》(傑作選12):
一九八七年十月初版。「御手洗潔系列」第三集,收錄密室殺人之〈數字鎖〉、具向讀者的挑戰信之〈狂奔的死人〉、寫一名上班族的奇妙工作之〈紫電改研究保存會〉、綁架事件、密碼為主題之〈希臘之犬〉等四短篇的第一短篇集。
04《異邦騎士》(傑作選2):
一九八八年四月初版。一九九七年十月出版改訂版。「御手洗潔系列」第四集。長篇。以御手洗潔探案順序來說,是最初探案。一名失去記憶的「我」,尋找自己的故事。屬於懸疑推理小說。《占星術殺人魔法》之前的習作《良子的回憶》之改稿版。
05《黑暗坡的食人樹》(傑作選5):
一九九○年十月初版。「御手洗潔系列」第六集。長篇。江戶時代,橫濱黑暗坡是刑場,有很多陰慘的傳說。樹齡二千年的大樟樹是食人樹,至今仍然有悲慘事件發生,與黑暗坡的藤並一族的連續命案是否有關?本書最大的特色是全篇充滿怪奇趣味。四十萬字巨篇第一部。
06《水晶金字塔》(傑作選18):
一九九一年九月初版。「御手洗潔系列」第七集。長篇。一九八四年在澳洲的沙漠,發現一具被燒死的屍體,從其駕照得知,他是美國軍火財團一族的保羅.艾力克森。他是美國紐奧良南端的埃及島上的巨大玻璃金字塔的建造者。建造這座金字塔的目的是什麼?與他之死有關係嗎?一九八六年來到這座金字塔拍外景的松崎玲王奈,首日看到狼頭人身的怪物,牠與傳說中之埃及的「冥府使者」很相似。之後不久,保羅之弟李察.艾力克森,陳屍在金字塔旁的高塔之密室內,死因是溺斃。兄弟之不尋常死亡意味什麼?四十萬字巨篇第二部。
07《眩暈》(傑作選9):
一九九二年九月初版。「御手洗潔系列」第八集。長篇。故事架構與處女作有點類似,一名《占星術殺人魔法》的讀者,留下一篇描寫恐怖的世界末日之手記:古都鎌倉一夜之間變成廢墟,出現恐龍,死人遺骸都呈被核能燒死的現象,而由一對被切斷的男女屍體合成的置錯體復醒。「幻想氣氛」十足的四十萬巨篇第三部。
08《異位》(傑作選19):
一九九三年十月初版。「御手洗潔系列」第九集。長篇。在《黑暗坡的食人樹》與《水晶金字塔》登場過的好萊塢日籍女明星松崎玲王奈,於本書成為綁架、殺人嫌疑犯。玲王奈最近時常夢見自己的臉噴出血的惡夢。有一天有名的女明星失蹤,當局懷疑是玲王奈的作為。不久,被綁架的幼兒都被殺,全身的血液被抽盡,恰如傳說上的吸血鬼之作為。難道玲王奈是吸血鬼的後裔嗎?御手洗潔會如何推理,為玲王奈解圍呢?四十萬字巨篇第四部。
09《龍臥亭殺人事件》(傑作選10、11):
一九九六年一月初版。「御手洗潔系列」第十集。長篇。御手洗潔一年前到歐洲遊學,岡山縣貝繁村之龍臥亭旅館發生連續殺人事件時,他不在日本,探案的主角是石岡和己。岡山縣在日本是比較保守的地區,橫溝正史之《獄門島》的連續殺人事件舞台,就是岡山縣的離島,一九三八年日本最大量(三十人)的殺人事件舞台也是岡山縣。本書是目前島田莊司的最長作品,他花了八十萬字欲證明其「多目的型本格mystery」(多目的型是指在一個故事裡有複數的主題或作者的主張)。如在下冊插入四萬字以上的「都井睦雄之三十人殺人事件」,原來這事件與故事是沒關係的。「多目的型本格mystery」的贊同者不多。
10《俄羅斯軍艦幽靈之謎》(傑作選23):
二○○一年十月初版。「御手洗潔系列」第十四集。長篇。一九九三年八月,即御手洗潔赴歐洲一年前,他收到松崎玲王奈從美國轉來一封她首次到美國拍「花魁」電影時,影迷倉持百合寄給她的舊信,內容說,前個月九十二歲的祖父倉持平八的遺言,希望在美國的玲王奈向住在維吉尼亞州之安娜.安德森.馬納漢轉達:「他對不起她,在柏林,實在對不起。」但是他卻不透露對不起的理由。他又希望她能夠到箱根之富士屋飯店,看到掛在一樓魔術大廳暖爐上的那一張相片。
於是御手洗帶石岡來到富士屋。此相片攝於一九一九年,箱根蘆湖為背景,一夜之間湖上出現一艘俄羅斯軍艦時的幽靈相片。直接關係者都已死亡的歷史懸案,御手洗如何解決?
11《魔神的遊戲》(傑作選6):
二○○二年八月初版。「御手洗潔系列」第十五集。長篇。五、六十歲的女人連續被殺分屍事件,在御手洗潔遊學英國蘇格蘭尼斯湖畔發生,掛在刺葉桂花樹上的「人頭狗身」的怪物意味些什麼?
12《螺絲人》(傑作選20):
二○○三年一月初版。「御手洗潔系列」第十六集。長篇。本書採取橫排與直排交互排版的特殊方式,可說是作者之新嘗試,是否成功讓讀者判斷。故事發生於瑞典與菲律賓兩地,發生的時間相差也有一段距離。全書分四大章,第一、第三章橫排,是御手洗的手記,寫他在瑞典的醫學研究所接見一位年齡與自己差不多的失去部分記憶的中年人馬卡特的經過。
第二章直排,馬卡特撰寫的幻想童話〈重返橘子共和國〉全文,主角艾吉少年出遊,來到巨大橘子樹上的鄉村,博學、長壽的老村長,有翼精靈……第四章橫直排交互出現,御手洗根據這本童話,推裡馬卡特失去部分記憶的原因,因此發現在菲律賓發生的事件。
13《龍臥亭幻想》(傑作選13、14):
二○○四年十月初版。「御手洗潔系列」第二十集。長篇。龍臥亭事件八年後,當時的本事件關係者在龍臥亭集會。在眾人監視的神社內,業餘的年輕巫女突然消失,三個月後,從地震後的地裂出現其屍體。之後,發生分屍殺人事件。這樁連續殺人事件與明治時代的森孝魔王傳說有何關係?吉敷竹史在本書登場,與御手洗潔聯手解決事件。
14《摩天樓的怪人》(傑作選21):
二○○五年十月初版。「御手洗潔系列」第二十一集。長篇。一九六九年御手洗潔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助理教授)。住在曼哈頓摩天大樓三十四樓的舞台劇大明星,因患癌症,臨死前向他告白,於一九二一年紐約大停電時,她在一樓射殺了自己的老闆。這棟大樓曾經發生過複數的女明星在房間內自殺,劇團關係者被大時鐘塔的時針切斷頭,又某天突然吹起大風,整棟大樓的窗玻璃都破碎,本大樓的設計者死亡等事件,都與住在這棟大樓的「幽靈(怪人)」有關。她要御手洗推理,告白後即去世。幽靈的真相是什麼?
15《利比達寓言》(傑作選25):
二00七年十月初版。「御手洗潔系列」第二十三集。收錄兩篇十萬字長篇。表題作《利比達寓言》寫二00六年四月,在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共和國莫斯塔爾,四名男人同時被殺害,其中三名是塞爾維亞人,三人之中兩名的頭被切斷,另一名是波士尼亞人,頭同樣被切斷之外,胸腔至腹部被切開,心臟以外的內臟全部被拿走。此外四名的男性器都被切斷拿走。
北大西洋條約機構(NATO)之犯罪搜查課之吉卜林少尉來電,要「我」(克羅地亞人。御手洗潔的朋友,本事件紀錄者)連絡在瑞典的御手洗潔,請他到莫斯塔爾來解決這次獵奇殺人事件。
另一長篇是《克羅埃西亞人的手》,同樣是蘇聯崩壞後,獲得獨立的小獨國內的民族糾紛為題材的本格推理小說。
二、吉敷竹史系列
島田莊司發表第二長篇《斜屋犯罪》後,風評與處女作一樣,毀譽褒貶參半。島田認為「本格mystery」尚未能被一般推理小說讀者接受,須擬出一套戰略計畫,推擴「本格mystery」。島田的策略之一,就是撰寫擁有廣大讀者的旅情推理小說,先打響自己的知名度,然後再回來撰寫「本格mystery」;另一策略就是到全國各所大學的推理文學社團宣揚「本格mystery」。島田的兩個策略,算是都成功了。他在京都大學認識了綾□行人、法月綸太郎、我孫子武丸等人,鼓勵他們寫作,並把他們的作品推薦給讀者,而確立了新本格推理小說。
另一面,島田莊司從一九八三年開始,以短篇寫御手洗潔系列作品,長篇寫旅情推理小說,而塑造了離過婚的刑事吉敷竹史。其離婚妻加納通子偶爾會在「吉敷竹史系列作品」露面,是一位重要配角。他們離婚前的感情生活,作者跟著故事的進展,借吉敷的回憶,片段的告訴讀者。
所謂的「旅情推理小說」大多具有解謎要素,但是它與解謎要素並重的是,描述地方都市的人情、風光。故事架構有一定形式,住在東京的人,往往死在往地方都市的列車內或地方都市。辦案的大多是東京的刑事。
吉敷竹史是東京警視廳搜查一課殺人班刑事,一九四八年出生,與島田莊司、御手洗潔同年,只從年齡來說,就可看出吉敷竹史也是作者的分身,所以其造型與寫實派的平凡型刑事不同。
長髮、雙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厚嘴唇、高身材,一見如混血的模特兒。這種素描就是島田莊司的自畫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