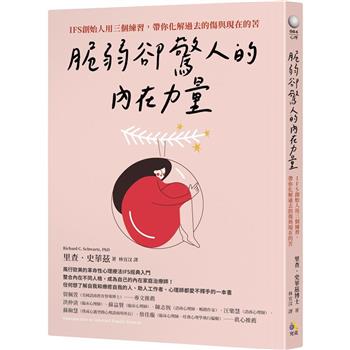溫馨懷舊有如「幸福的三丁目」,令人既感動又感傷!六段美好的時光剪影,一串令人永難忘懷的青春歲月!不只是東京,任何地方,任何時空,年輕的味道大概永遠都是這樣吧!青春結束了,人生才要開始……這句話,如果久雄還是當年那個十八歲的小夥子,一定不會同意。記得第一天到東京的時候,陪他來的母親感嘆地說:「十八歲了,真好,正青春呀!」他長這麼大,還是第一次聽母親講出心底話。母親依依不捨地離去那一刻,久雄覺得自己的人生終於開始了!這裡可是離家三百多公里遠的東京呢!接下來一年,他將獨立生活、準備重考大學,還會交一個和偶像明星
作者簡介:
奧田英朗 一九五九年生於岐阜縣。曾從事雜誌編輯、企畫、廣告創意人、文案等工作,一九九七年以《盂蘭盆的森林》出道成為作家。二○○二年以《邪魔》榮獲「大藪春彥賞」,二○○四年以《尖端恐懼》贏得「直木賞」,二○○七則以《家日和》榮獲第二十屆「柴田鍊三郎賞」,二○○九年再以《奧林匹克的贖金》獲頒「吉川英治文學賞」。另著有《最惡》、《持續勃起》、《一郎二郎》、《六宅一生》、《粉領族》、《無理》等書。
譯者簡介:
陳嫺若
東吳大學日文系畢。從事翻譯和編輯的工作多年,譯作有《喜樂京都》、《東京下町職人生活》、《一隻貓的巴黎研究》(以上為馬可孛羅出版)、《東京歸鄉》(臉譜,即將出版)、《周極星》(經濟新潮社)等。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推薦序〉
那個時代的你我他
【作家】張國立
「時代」是個很大、令人敬畏的名詞,摸不著也猜不透,等到有天發現它存在的時候,已經過去,所以「時代」幾乎像個過去式,能發現「時代」是現在式且是未來式的,幾乎都是偉人。對平凡的小人物,其實正因為「時代」往往代表過去,才產生若干意義。
例如我成長於六○、七○年代,那時除了聯考、把馬子、吸膠之外,有趣的事情很少,加上沒錢,美軍電台(後來的ICRT)播放的搖滾樂就成最直接的娛樂,於是我跟著排行榜、跟著Rolling Stone(滾石)、Simon and Garfunkel(賽門與葛芬柯)走,每年底的年終排行是大事,一缸子同學窩在某痞子的房間裡聽收音機,每一首都代表過去一年中某段時間的回憶,像Lobo(灰狼羅伯)在一九七一年唱他的成名作〈Me and You and a Dog Named Boo〉時,我十六歲,剛結束為期兩週零三天的莫名其妙戀情,聽著歌便想起女孩媽媽在電話裡對我講的:
「阿呆,她忙著補習,你不要再打電話來了。乖,你不是也要考大學嗎?」
許多瑣瑣碎碎的小事累積成「時代」,包括他們的時代和我們個人的時代,因此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凌晨台北突然起了陣狂風驟雨時,蔣介石死了,而我呢?那晚跳了起碼七小時的舞,努力想跟某個堅強的女孩跳三貼卻不幸失敗,因此那個時代,對很多人出現不同的意義,即使第二天我跟很多人一樣,對蔣介石的死得表現出哀悼、傷心,腦袋中想的卻是如何再約那個女孩出來,同時我母親獨自坐在她房內兩眼無神地說:
「回不了大陸了。」
奧田英朗寫的《東京物語》可以算是「啟蒙式」小說,也就是寫出作家年輕時的世界,最有代表性的包括美國沙林傑的《麥田捕手》、日本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另一位美國大師約翰厄文的《蓋普眼中的世界》等等。這種類型的小說特別強調時代,他們把那個時代的點滴當成小說的背景,一幕一幕的換,讓讀者有參與了那個時代的感覺,非常「幸福的三丁目」味。
「時代」有趣的地方在於每個人的「時代」可能有若干的交集,即使奧田英朗是日本人,我是台灣人。例如小說一開始提到松田聖子於一九八○年唱的成名作〈藍色珊瑚礁〉,那年我正躲在軍營裡數饅頭,距離退伍的日子沒幾天了,於是也感染上歌曲中的青春、快樂。也是那一年,我瘋狂地迷戀上一個叫劉藍溪的女孩,她唱著〈野薑花的回憶〉,與聖子同樣的清純可愛。很多年後,當松田聖子鬧出不少性醜聞時,劉藍溪則剃度出家。兩個美麗女孩成為我的一九八○年人生背景。
當然,一九八○年約翰藍儂被刺殺,全球的年輕人都一再嘶吼出他生前的名作〈Imagine〉時,這更是許多人的共同時代背景。
終於我明白,時代與個人,像河水與游泳的人,我們得跳進河裡才能游泳,努力往前游,水變得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游。看見從身旁流走的樹葉,看見其他也在河中的人有的超越我,有的被我超越,他們和我幾乎都沒有關係,甚至連水都和我越來越沒有關係,可是得當心別給亂流拖進去。
而且「時代」沒有記憶我們,它靜靜地流過去,我們卻始終忘不了「時代」,它令我們想起許多不該遺忘的人生歲月。
八○年代是段好日子,Bee Gees(比吉斯)和約翰屈伏塔的「Staying Alive」(「龍飛鳳舞」)把迪斯可帶入高潮,台北車站對面的希爾頓飯店每天下午有茶舞,票價低廉,我擠進裡面才首次明白年輕是種盡情流汗、忘記明天的享受。台北酒吧一間間地開,告別午夜十二點起警察憲兵能在街上要我拿出身分證的戒嚴時代;女孩的裙子由短而長再變短,頭髮吹高又拉直再吹出劉海。原來滿街都是愛情,看我能否於酒後的混亂之中抓住一二。
由戀愛到失戀再戀愛,羅貫中在《三國演義》裡開宗明義說的「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說的也是男女關係囉?台灣經濟起飛,每個人都說,只要努力一定賺得到錢。去美國念書,因為那裡滿地是黃金;留在台灣工作,因為處處是機會。
沒有了蔣經國,台灣得照樣走下去;沒有了鄧小平,大陸的開放仍是不歸路。「時代」也是無情的,吞噬浪花,河水繼續向前翻滾。你,我,他,隨著奧田英朗偶爾回頭看看人生的背景看板,「人生的意義只發生在回顧的時候,而我們卻總是瞻望未來」。
放慢點腳步,讓自己喘口氣,順便一起哼哼〈Imagine〉:
你也許說我活在夢裡,
不過我絕不是唯一的,
希望有天你能加入我們,
然後世界必能合而為一。*
*編註:這四句歌詞出自約翰藍儂的歌曲〈Imagine〉,原文為──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名人推薦:〈推薦序〉
那個時代的你我他
【作家】張國立
「時代」是個很大、令人敬畏的名詞,摸不著也猜不透,等到有天發現它存在的時候,已經過去,所以「時代」幾乎像個過去式,能發現「時代」是現在式且是未來式的,幾乎都是偉人。對平凡的小人物,其實正因為「時代」往往代表過去,才產生若干意義。
例如我成長於六○、七○年代,那時除了聯考、把馬子、吸膠之外,有趣的事情很少,加上沒錢,美軍電台(後來的ICRT)播放的搖滾樂就成最直接的娛樂,於是我跟著排行榜、跟著Rolling Stone(滾石)、Simon and Garfunkel(賽門...
章節試閱
〈那天聽的歌1980/12/9〉
1
站在沙丁魚罐頭般的電車內,一扭身,Sierra Designs外套的防風布料就互相摩擦,發出蟲鳴般的咻咻聲。眼前的粉領族似乎面露不悅,為了避免誤會,田村久雄把皮包抱在胸前,再次轉過身子,朝向別的角度。
暖氣開得太強了,他的額頭已滲出汗來。外套裡還套了一件圓領羊毛衣,體溫沒處可散,可以感覺到汗水凝成一滴在背上往下滑。久雄用吊環支撐著快要傾斜的身體,微微地嘆了口氣:早知道還是應該在公司打地舖。
為了工作在公司打地舖已經沒什麼大不了。他不小心考進的這家「新廣社」廣告公司,全體員工都帶著睡袋上班,早上進門時,總會有一、兩個人躺在地板上。想到公司連老闆一共只有五個人,頗像是非法勞工的營房。
昨晚,他無論如何都想到澡堂去一趟,他已經四天沒洗澡了,公司內部雖然是大廈住家的格局,但浴室改成暗房了。一個十萬火急的文案工作讓他思緒阻塞,但自己再這麼悶頭空想,也激不出什麼好點子,他用這個藉口說服自己,於是坐上末班電車回家去。
然而,現在他後悔了,雖然可以好好洗個澡,但昨天的困境依然沒有改變。久雄總是會把事情往好處想:泡在澡盆裡,就會閃出什麼好點子吧!躺在床上瞪著天花板,就會想到什麼絕妙好詞吧!然而,這種靈感從來沒有發生過,幾乎屢試不爽地,到了早上又帶著鬱悶的心情困在電車裡。
他必須想出來交差的文案,是新型卡式錄放音機的宣傳標語,中午之前一定要送去發包的廣告商那裡,讓他們審閱。發包的廠商叫「威斯特」,是一家擁有百名員工的廣告公司,簡單地說,新廣社就是威斯特的下游公司。
久雄會在新廣社成為廣告文案員,完全只因為這是份沒人能做的工作。公司竟然敢用他這個大學沒讀完、也沒有經驗的大少爺來做這種事,他著實佩服老闆的勇氣。老闆是個設計師,今年才三十幾歲,一句話裡一定要加上「不管怎麼樣」,每天平均睡眠只有四小時,算是個能人。
半路上經過轉運站,車廂內變得更嘈雜了。久雄被擠到通道中央,他旁邊站的是一個學生打扮的男孩,隨身聽的耳機裡流洩出刺耳的噪音。前面的中年上班族毫不掩飾地皺起眉頭,久雄也在心裡喊著「吵死了」,雖然他愛音樂勝過吃飯,但是對去年開始大流行的隨身聽卻很感冒。
久雄轉過頭去,掛在走道上方的週刊廣告映入眼簾,斗大的標題寫著「太陽族以來的震撼,《無來由、水晶》作者果然是一橋大學生」等字樣。「這傢伙也很礙眼。」久雄其實根本不看小說,此時似乎把他當成了出氣筒。
還是回頭想文案吧!只要一台就能對錄的新型雙卡錄放音機,得替它想廣告文案。
久雄閉上眼睛,腦中的思緒翻轉著。
「我們的音樂故事」。
一路上就只想到這幾個字,大概不能用吧!久雄想。音響產品不喜歡太輕的文案,他已經可以預見將會有人嘲諷他:「你以為你是系井重里嗎?」
廣告文案這個時髦的頭銜雖然讓他有點輕飄飄的,但事實上,他只是最下層的雜工罷了,每天有做不完的雜務,甚至可以說,每天都得利用雜務的空檔才能做些自己分內的工作。
車內廣播告知即將到達惠比壽站。久雄穿過人群走上月台,霎時,他呼出的氣成了一團白霧。
經過驗票口,儂特利對面的漢堡店,大白天的卻已打開聖誕節的應景霓虹燈。
年底的時光過得特別快吧!前兩天才想起十二月到了,今天卻已經是九號了。
看樣子,今年自己又要過個沒有情人的聖誕節了。久雄宛如大猩猩般吐著白氣,重新將圍巾圍上脖子。
「田村,把JBL的音箱從『搖擺生活』搬到『音響夥伴』去。」老闆準備要出門時交代說。
「現在就去嗎?」久雄抬起了頭,望向裡面的房間。
老闆看著茶几上的黑板,頭也沒抬地淡淡答道:「特急件。」
「可是我現在得把文案趕出來。」他帶點抗議地說。昨天大家吩咐的雜務太多了,教他何時才能專心寫文案呢?
「音箱比較急,跟健二一起去。」
抗拒無效,只好答聲「是」。健二是老闆的弟弟,年紀差了一大截,雖然負責會計的工作,但是其他的事當然也得幫忙。
「田村,你開車。」一回頭,健二拿車鑰匙在他眼前晃了晃。「我昨天晚上只睡兩個鐘頭。」
久雄把脖子轉得卡卡響,過了一會兒才接過鑰匙。
從停車場開出小貨車,前往位於芝區的「搖擺生活」編輯部。他要把出借到這裡的試聽用音箱,搬到神保町的「音響夥伴」編輯部去。為了讓雜誌社多寫一點客戶的產品,有時他們也得充當廣告業主的搬運工。
「健二,今天路上很塞哦!」久雄從高駕駛座俯視著令人心煩的長長車陣說。
「快到年關了嘛!」坐在副駕駛座的健二玩著魔術方塊。「哎,不行,花了半天才拼出兩面。」
「你昨晚只睡兩小時,不會是在玩這個吧!」
「才不是哩!我在趕完稿。」
收音機裡放出松田聖子的〈藍色珊瑚礁〉,健二跟著哼唱。
「佐藤昨晚也熬通宵嗎?」
「嗯,他被老闆罵了。」
「真衰啊!」
「誰叫他工作遲交。」
設計師佐藤負責當老闆的出氣筒,而且老闆罵他的方式並不尋常,一旦開罵,連三個月前的舊帳都要翻出來,足足可以罵上三十分鐘。久雄從沒看過佐藤回嘴。
第一次看到佐藤被罵的場面時,他心想,如果哪天輪到自己的話,他就馬上辭職。
幸運的是,久雄從沒被罵過。老闆罵人也是看對象的吧!
「啊,對了。」健二抬起頭,「昨晚森下打電話給你。」
「昨晚?我回去以後?」
「對啊!十二點之後,他問說:『田村還在嗎?』」
與他同年的森下是個攝影師,剛從攝影學校畢業,新廣社只發給他簡單的工作。
「結果呢?」
「我答不在,他說:『那就算了。』」
「哦?」
「你家裡好歹也裝支電話嘛!」
「給我獎金的話就裝。」
「會發啦,冬天發吧!」
「真的?」
「嗯,大概十萬左右吧!」
久雄的心情稍微好一點了。他的薪水只有十二萬,每個月都過得很拮据。
「森下好像要去美國。」久雄一邊開車,一邊點了根菸。
「之前就聽他說了,不是說要去洛杉磯拍衝浪照片嗎?整個夏天都聽他在吹牛。」
「他是跟我說過,要在那邊住一陣子。」
「那傢伙光說不練啦!」
健二有一搭沒一搭地轉著魔術方塊,收音機裡的音樂,不知何時變成了「Y.M.O.樂團」的〈科技都市〉。
從「搖擺生活」編輯部抬出JBL4343,搬進小貨車裡,那大型音箱有冰箱那麼大。除此之外,他還見過三百六十公斤的轉盤,和一台令人懷疑裡面到底放了什麼、重如墓碑的擴大器。新廣社的客戶都是有專業樂迷傾向的重量級音響公司,拜他們之賜,他這個上班族卻得經常肌肉痠痛。
「接下來換你開吧!」久雄說。健二學人家演戲那樣嘟起嘴,一言不發地坐進駕駛座。接下來是到神保町的「音響夥伴」。
「我得想想文案。」
「西条先生那裡的?」健二說。他一發動車子,就猛地衝了出去。
西条是威斯特的製作部長,總是邊摸著鬍子,邊拉長尾音說:「還是不夠好耶……」
「那個大叔就是喜歡挑毛病。」健二苦笑著低聲說。
馬路上越來越塞了。收音機裡放的全是流行歌曲,他轉到美軍電台,車裡流淌出久雄喜歡的外國搖滾樂。
「這是誰?」健二問。
「史提夫佛伯特(Steve Forbert)。」
「你果然很清楚。」
久雄把魔術方塊放在儀表板上。
「田村,你能拼幾面?」
「一面。」
健二不屑地笑了。
沒時間理他了,真的得快點想出文案。
仰頭看到宛如刺穿灰色天空的東京鐵塔,久雄暗忖著「ONE AND ONLY」這個句子不知過不過得了。
不行,那個錄放音機還沒有新潮高級到那種地步,他兀自搖了搖頭。
車流好像不會動了,心情漸漸變得焦慮起來。
搬運音箱的工作浪費了上午兩個小時後,才回到公司。
一打開門,就聽到老闆的斥罵聲在狹小的辦公室裡響起。
「佐藤──!我要說幾遍你才懂?!」
佐藤像個小孩一樣看著地上,臉色發青地捏著完稿。
「照相打字一個字多少錢你知道嗎?為什麼不會先用影印?!」
看樣子起因大概是照相打字稿被刮傷了。
老闆叱責佐藤時,整個公司籠罩在低氣壓中。坐在佐藤旁邊的海野小姐一定很受影響吧!海野小姐是公司裡唯一一朵紅花,她雖然也是設計師,但仍是兼職的身分,所以她也從沒被罵過。
儘管如此,為什麼佐藤不說話呢?再怎麼說,他也太懦弱了。
「田村先生,」海野走到他面前,像是找理由逃出隔壁房間的風暴,「威斯特的西条先生打電話找你。」
「糟了,是催稿嗎?」
「不清楚耶!」海野似乎還不想回到位子上,徵求他同意地問:「來杯咖啡吧?」然後便逕自走向流理台。
不管怎麼樣,他得趕快把文案趕出來。時鐘指著上午十一點。
他快速翻著昨晚找來的一堆雜誌,尋找可以從其他廣告或標題擷用的字句,尤其是才剛創刊的《BRUTUS》給了他很多好點子。
喝著海野泡的咖啡,他一刻也沒停地繼續翻找。
「喂,田村,有空閒晃的話,來幫我做完稿。」
「我沒在閒晃!」他帶著抗議說,瞪了隔壁的健二一眼。
雜誌全都翻遍了,也找不出一絲靈感,他把之前想到的文案全都排在桌上,沒有一個像可以過關的樣子。
「田村,電話,森下找你。」海野叫他。
搞什麼?!忙得天翻地覆的時候來電話。他嘴裡嘟囔著,拿起眼前的話筒。
「喂,田村啊?我啦!」電話另一頭響起森下慢條斯理的聲音。
「幹嘛?」
「昨天晚上你很早就走了哦?」
「什麼早!我搭末班電車回去的!」
「哦……因為你不在公司就找不到人嘛!」
「閒話少說,找我什麼事?」
「家裡還是牽一支電話比較好,有時候休假……」
「別廢話了,說重點。」
「你發什麼脾氣嘛!」
「我沒發脾氣啊!」
「這還不叫發脾氣啊?」
久雄大大嘆了一口氣。「我現在在忙。」
「是哦。」
森下滿不在乎的回答令他感到無力。
「拜託你,快點說重點好嗎?」
「哦,好。我之前也跟你說過,我接下來要去美國。」
「何時?」
「過完年後。」
「真的要去嗎?」久雄有點吃驚。
「嗯,我已經存了三十萬了,其他的到那邊再想辦法。」
「你去美國,是為了拍衝浪的照片嗎?」
「對啊,我自己也會帶板子去。」
「是哦……那加油吧!」
「會啊!我會加油。」
靜默了一會兒。
「……那下次再告訴我細節,掛囉!」
「等等,所以……」
「什麼啦?」
「你別那麼兇嘛!」
「我哪有兇?!」
「田村,你很容易就生氣耶。木村也這麼說。」
「我知道啦!快說重點好嗎?」久雄看看時鐘,上午已經快結束了。
「之前在居酒屋,你不是差點跟他吵起來嗎?」
「你在說什麼?」
「木村啊!」
「別再廢話,你到底想講什麼?」久雄忍不住又提高了音量吼道。
「好嘛好嘛,我是要問你,護照要去哪裡辦?」
「……我哪知道啊?」
「什麼?田村,你不知道嗎?」
「你才奇怪咧,都要去美國了還不知道?我這輩子還沒坐過飛機咧!」
「這種事有什麼好炫耀的。」
「誰在炫耀啊!」久雄靠在椅背上,扯起頭髮。
「有沒有別人知道呢?」
「你等等。」
久雄把話筒遞給隔壁的健二,他只說了句「森下」,連解釋的力氣都懶得花。
莫名其妙地浪費了一段時間。久雄看著稿紙,調整姿勢準備集中精神。
再寫一次新產品的特色吧!
對錄方便,減少音質耗損。高科技的設計……
所以音質耗損少啊,那就主攻這點吧!
「聲音 更鮮活」。
他大大寫了下來,把紙拿遠點看,字面的好壞對文案也很重要。
「欸,森下好像要去辦護照耶。」健二在一旁說。
「他要去美國,當然要辦護照啦!」
他站起來再仔細端詳一次。
「你想他真的會去嗎?」健二說。
「誰知道?」
「我賭一萬他不會去。」
「我也是。」
「怎麼這樣?那就沒法賭啦!」
反正先送到西条那兒讓他看一次,只要把先前想的幾句文案混在裡面一起帶去就行。給他看五句,至少會滿意一句吧!
他打電話表示自己這就過去。
威斯特公司步行就能到,就在隔著山手線對面的代官山大廈一樓,從新廣社的窗口抬頭便能看見。他們的燈一整年沒關過,老闆每遇到什麼事,就刺激他們說:「喂,威斯特還沒下班哦!」
久雄套上防風外套,小跑步往威斯特走去。
他走上橫跨山手線的天橋。
他喜歡在這裡看著從底下經過的電車,但大多時候,經過此處的心情都是沉悶的。因為接下來要去的,絕不是什麼令人快樂的地方。
2
「田村,看過『克拉瑪對克拉瑪』嗎?」西条手肘撐在桌上,撫著鬍鬚,用清亮的聲音說。
「嗯,我看過。」
「達斯汀霍夫曼不是有一幕在做法式吐司嗎?早餐的時候。」
「嗯,我記得。」
「法式吐司是用那種方法做的嗎?」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吧!」
聽不懂他在說什麼,西条總是從八百里遠的話題開始說起。
「在盤子裡倒入牛奶和蛋,然後把吐司浸在裡面,等到吐司看起來好像濕濕爛爛的時候,再把它拿去煎。」
「哦。」久雄不知他想說什麼,只好附和了一聲。
而且文案全被封殺。西条只看了一眼,便直截了當地說:「每個看起來都不太好。」
「然後,我家的老婆說,做法不對吧!我剛開始也同意她的看法,應該不是這麼做才對……可是後來想想,我們根本不知道正確的法式吐司做法呀,更何況也沒看人做過。這麼一想,我才恍然大悟。總之,在日本,法式吐司根本不是家常菜,而是在外面吃的大餐。田村,你沒有在家裡做過吧?」
「是的。」
久雄連在外面都沒吃過,不過還是應和一下。
「該怎麼說呢?日本和西方的距離。」西条抽出一根萬寶路,濾嘴那端在桌上敲了敲。「法式吐司在他們那邊只是一種簡便的食物吧,給孩子吃的,我們日本人卻把它當成大餐。簡單地說,我們自己的理解未必正確,有些部分太小看了它,有些又太誇大了。」
他到底想說什麼?
「廣告也是這樣。」西条用Zippo打火機在香菸上點了火,「我們不知不覺地被既定的訊息束縛了,音響也是這樣。」
他吐了口菸,眼睛看向遠方。
「並不是因為它是音響,才要做這個廣告。」
「是。」
「試著打破這個觀念,讓消費者耳目一新一下。」
久雄不明白他在說什麼,但還是默默地點點頭。
「音響是奢侈品?」
「這個嘛……至少對我來說是的。」
「已經不再是了。」西条沒理會久雄的回答。「隨身聽都出來了。這款WW─402錄放音機只因為雙卡就是高級品嗎?它應該已經是很平民化的款式了吧!」
「是,您說得對。」在對方的強勢語氣下,久雄立刻見風轉舵。
「說起來,的確有些為音響發燒友設計的高價商品,但是這種錄放音機就是法式吐司呀!而且不是日本人眼中的法式吐司,是西方人的。」
西条的語氣聽起來雲淡風輕,卻很篤定。
久雄看向窗外,灰雲低垂於天際,肚子已經唱起空城計。
這一套跳躍式的訓話,每次都要來上一回,但今天跳得尤其遠。「克拉瑪對克拉瑪」裡的梅莉史翠普成了八○年代的受害者象徵,走平民風在未來會受歡迎。最後西条摸著下巴的鬍子,丟下一句:「那就到這裡,傍晚前再想一想。」
久雄用手掌搓搓臉,打消正要形成的呵欠。他很想說:你愛怎麼講都行,但能否給一點具體的指示?
看來他得盯著時鐘絞盡腦汁到傍晚了。一想到這點,久雄的心情憂鬱起來。
「田村,出問題了。」一回到公司,健二習慣性地拍拍他的肩,一副事不關己的口吻說。
「啥?」
「『音響夥伴』來電說JBL4343的保護罩不見了。」保護罩就是包覆在喇叭前面的網子,「他們說沒有罩子沒法拍照。」
「可是從『搖擺生活』搬出來的時候,沒放進車裡啊!」
他把對方交給他的東西直接放進車裡,因為常看到沒有保護罩的照片,所以也沒覺得有什麼奇怪。
久雄與健二面面相覷,互相進行無言的牽制。
「田村,你一個人去吧!」健二很有節奏地繼續習慣性動作。
「猜拳。」久雄右手比出猜拳的手勢。
「不行啦!我今天一定要把完稿做好。」
「我也是啊!文案還沒想出來。」
「怎麼?沒通過啊?」
「遇到那個人,第一次哪過得了。」
「話是沒錯……」健二閉上嘴。「等下銀行的人要來,你如果可以幫我應付他們,我就可以跑這一趟。」
「奸詐。」
久雄皺起臉。健二伸出手輕輕拍著他的臉說:「炸豬排飯,大碗,我已經叫了。」
「你請客哦!」
「我知道啦,所以吃完趕快去吧!」
雖然表面上好像是得到安撫,但位子比人低,沒有拒絕的餘地。
老闆好像出去了,佐藤設計師吐著菸,放鬆地在午休。對他而言,老闆不在就好像是上天的恩賜。
久雄趁著豬排飯來之前的幾分鐘,不敢鬆懈地繼續想文案。
早上才喝一半的咖啡還放在桌上,他啜了一口潤潤喉。
呃,叫什麼來著?法式吐司。
手臂抱在胸前,靠在椅背上。
「品味音樂,就要像法式吐司。」
應該不是這種東西吧!他長嘆一聲。
想了兩、三個,還是沒什麼好靈感……
〈那天聽的歌1980/12/9〉
1
站在沙丁魚罐頭般的電車內,一扭身,Sierra Designs外套的防風布料就互相摩擦,發出蟲鳴般的咻咻聲。眼前的粉領族似乎面露不悅,為了避免誤會,田村久雄把皮包抱在胸前,再次轉過身子,朝向別的角度。
暖氣開得太強了,他的額頭已滲出汗來。外套裡還套了一件圓領羊毛衣,體溫沒處可散,可以感覺到汗水凝成一滴在背上往下滑。久雄用吊環支撐著快要傾斜的身體,微微地嘆了口氣:早知道還是應該在公司打地舖。
為了工作在公司打地舖已經沒什麼大不了。他不小心考進的這家「新廣社」廣告公司,全體員工都帶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