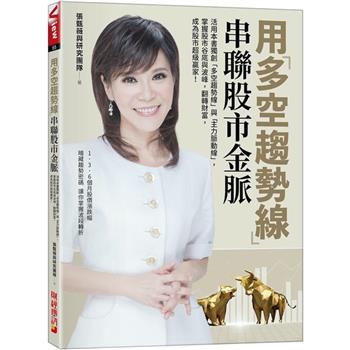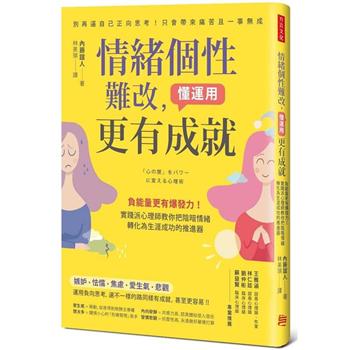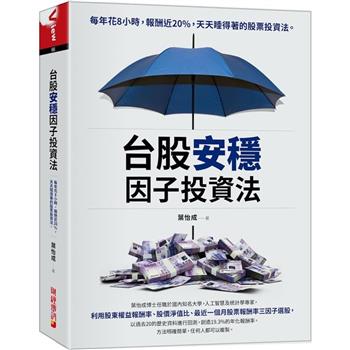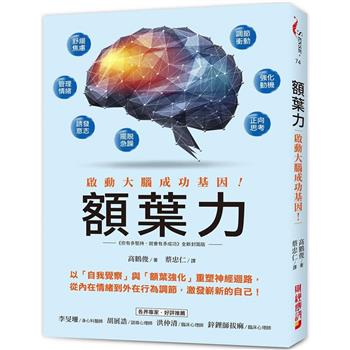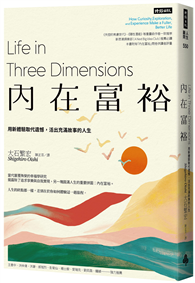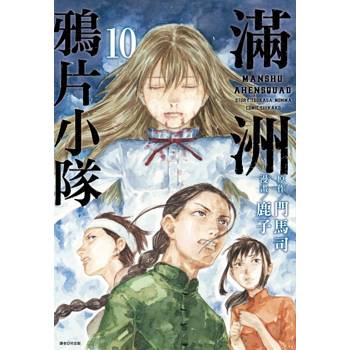之一 天馬奔騰在府城
四、五十年代的臺南市,工商發達,經濟繁榮,是臺灣少數有著文化涵養的地方。其中傳統戲曲的傳揚和演出極為興盛,平劇亦躬逢其盛,在全臺首學之地開花結果,帶動往後數十年表演薪傳,留下璀燦動人的文化底蘊。
這股風潮是外來的軍人和公務員帶來的。其實,當地士紳學者對平劇亦皆愛好,「顧劇團」留臺表演期間,全臺各地對傳統戲曲的喜歡,已達瘋狂程度,一方面基於脫離日治、仰慕中華文化之故,另一方面源於當時戲劇演出乃為唯一文化活動,所以並不因平劇為「外來劇種」而排斥,甚而成為人人學習與爭看的娛樂。
當時娛樂少,學戲、唱戲頗為時髦,不少當地人士加入劇社學習,表演得有聲有色、融洽和樂,很難想像隔了三、四十年後臺灣會有挑撥族群不合情事上演,再次挑動原已撫平的族群仇恨之根;當初學戲的臺籍人士,恐難以想像!
人文化成的力量本就沛然莫之能禦,從文化看政治,即證「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了。
現座落於二級古蹟臺南地方法院對面的實踐堂及其旁的社區活動中心,即見證了這段文化遞嬗、融合和傳揚的歷史。
.
民國四十四年在臺南出生的我,懂事之後,比較記得清楚的地方是現今的實踐堂和其周圍之地。那時從我們住的安平路到那裡,都要坐三輪車,小孩蹲在大人腳前,看著車伕用力地踩踏前行,一會兒發著口哨聲驅趕著,一會兒用著剎車的鐵桿碰觸車體發出聲音,就像喇叭一樣,一路送我們到達那個地方。
當時那是一座公園,聽人們稱它為「忠烈祠」,我只知道樹木長得高壯,有多個高大的銅馬和銅麒麟立於其內,但前頭群聚的小販弄得滿地泥濘,令人生厭。
我們一家人到那裡是陪爸爸票戲。所謂「票戲」,是票友到票房唱戲,說的真確些,是一群不是平劇專業演員的人,定期到一個場所聚會練唱的意思。
那時候的娛樂極少,平劇演出機會較多,南臺灣比不上北部要角如雲,但非專業演員認真排練,自娛娛人,很得當地民眾激賞。父親加入的劇團名為「天馬平劇隊」,全是空軍各單位的官士兵組合而成,練唱和聚會的場地在忠烈祠內。
小時候的我,不懂得什麼是忠烈祠,隨著爸媽穿過群聚小攤,從一座有著半圓形拱門式的邊門進到內裡。裡頭是座中國式建築物,有廊柱、翹瓦,和一般所見民居大不相同。
我始終不明白的是,還算佔地寬廣的建築物,為何要從一道窄門進出?直到回想起這段記憶,我才驚覺,原來建物的前方早被違建戶佔得滿滿,所以當我們由邊門進入後,能看到一座天井花園,那是這棟建物的前埕。花崗石地板每在下雨過後,留下青苔水漬和岩面輝映成趣。
進入大廳後是一張方桌,就像民初電影中的場景一樣,只是朱紅大柱十分顯眼。平劇演出時的道具都擺在這裡,有桌椅和刀槍劍戟等物,因為空間大,看起來不覺擁擠,左右各有些房間,後方則是一臺壓麵機。
天馬劇隊成員有的未婚,住在此地,有的可能是退伍軍人之類,所以壓麵機的主人肯定沒工作,就以製麵為生。我常跑到大廳後,看他操作。那位伯伯先將麵粉和水,不斷揉和,再將麵糰捍平,放入機器,愈壓愈薄,到一定程度後送入機器內,就能軋出各種粗細的麵條了。
至於伯伯在劇隊的角色,倒是忘得一乾二淨,連姓什麼都不復記憶。記憶最深刻的是趙慧珠姑姑,她是父親的乾姊,先生宋向榮是黃埔出身,官居要職,卻因感情不睦而分居,四十年後才又復合,直至宋伯伯九十高齡辭世。
.
趙姑姑聽說是科班出身,青衣花旦均見長,是劇隊中的要角。住在入口邊門的對面,通常那裡男賓止步,她卻常招呼我和姊妺進她房間,空間雖不大卻雅緻舒適,有時拿些蘋果送我們,在當時是最高級的水果了。
趙姑姑與媽媽以姊妹相稱,有時亦到家裡來坐。她是古典美女,五官勻稱,扮相極美,連我們小孩子都說漂亮。趙姑姑說話很好聽,可有些天津腔,和一般北京話有些不同,在劇隊裡很受尊敬,倒不是她先生是大官之故,而是她永遠微笑待人,舉止非常優雅。
那時劇隊的成員很多,小孩子哪記得到名字,碰到人就「叔叔、伯伯」的叫一聲就行了,尤其是文武場(樂隊)的人來來去去,很難記得住誰是誰?倒是唱的人和一般住在那裡的人,看久了通常會留下一些記憶。
演員中最出名的是謝景莘伯伯,爸媽都喊他「謝眼鏡」,因為他戴著厚重的近視眼鏡。謝伯伯唱老生,嗓音清越,天馬劇隊連年獲獎,主要功臣就是他。每回謝媽媽都跟著來,是劇社中公認的兩枝花,另一位是我媽媽。
謝景莘是機械官,我爸爸則是醫院的檢驗科主任,是公認最年輕的帥哥,他卻唱老旦,也是戲裡吃重的角色。其實,爸爸熱愛平劇,各種角色都難不倒他,還勇於嘗試演老生、小生、丑角,是演戲全才。
提起全才,就不得不佩服一個劇隊能擁有各式各樣的人才。光樂隊就要十來人,各種樂器都要有人使用,合奏起來的效果才好。我經常看見拉胡琴的一停下來就撥弄三弦,吹鎖吶的可以吹笛子等等,好像每個人都身懷絕技似地,隨時都能應付各種狀況。
司鼓的文武場是指揮,我記得姓「查」,人高馬大,脾氣不小,對其他成員出錯,往往不給好臉色。敲鑼打鼓的很吵人,我也不想去記他們的姓,只有一位汪子懷伯伯打小鑼,因日後有機緣住得很近,始終不會忘掉他的大名。
汪伯伯戴眼鏡,身形瘦小,當時戴眼鏡的人不多,很好認。他敲鑼很認真,專注的神情彷彿和外界一點關聯都沒有。其他的樂隊成員來來去去,都不復記憶了。
演員中,唱花臉的是劉志發,個頭不大,結實精壯,嗓如洪鐘。最吸引我們注意的是男扮女裝的角色,那是李金河伯伯;其實,李金河在那個年代算是高大帥氣,西裝頭油亮得很,不知怎會扮演女性角色?直到日後看了四大名旦的照片後,才發覺李伯伯和他們長得一個樣。
當時,另一位有名的乾旦程景翔伯伯也常來劇社,和李金河同樣是很帥氣的男生。李伯伯對我們小孩子很好,不時拿些糖果給我們吃。他一直未婚也常到家裡走動,不過,儘管他演女生維妙維肖,當時,我從未將李伯伯當做女生來看。
.
李伯伯住在劇社內,當時的他好像是聯隊的士官長,另一位住在他隔壁房的是許伯伯,大名早已忘了,只知道所有的人都叫他「老許」。老許像是總管,很少看他唱或拉琴,倒是聲音滿場飛,不管是在劇社或是上臺公演,他的聲音緊扣著動作,讓「天馬」不致真的飛上了天。
老許伯伯是山東大漢,人高馬大卻不胖,聲音渾厚帶著山東腔,對我們也滿好,好像也是聯隊的士官長。菸抽的很兇,只要爸爸一到劇社,他馬上奉上菸,倆人就自顧自地抽將起來。
還有兩位和我們家關係很密切的人,都會在那裡穿梭招呼著,他們的任務是演出時的「檢場」角色。檢場是演戲時搬道具的人,角色不重卻需要「戲精」才能勝任;因為每齣戲演員上上下下,何時該有桌椅或何時要有物品在手,都要靠檢場的協助,所以,檢場是最重要的螺絲釘角色。
兩位檢場,一未婚一已婚,一胖一瘦,一黑一白,一多話一不言,真正絕配。未婚的是靳樹霖叔叔,是聯隊的士官長,瘦黑精壯,話講個不停,老媽封他個「話癆」之稱。談起任何東西,頭頭是道,很少有他不知道的東西。
靳叔叔做得一手好菜,始終未婚,爸爸徵得我姊姊同意認他為乾爹,他高興得不得了,對姊姊疼愛有加,也和我們家走得更近了。
由於母親生大哥時得了心臟病,每當犯病時,就由靳叔叔到家裡幫忙。幾乎一個多禮拜時間,他都要由住處騎腳踏車到我家照顧我們,洗衣、做飯,忙到晚上才再騎車回去。媽常對我們說要飲水思源,永遠不能忘了靳叔叔的這分情。
日後,我退伍返鄉,每月都要開車送爸爸去高雄榮總診治,就會繞到靳叔叔住處接他一起就診,那時他已中風不太能言語,我從他的眼神中看到的是感謝之意,我都會恭敬地扶著他,跟他說:「這是我應該做的,請不要放在心上。」我也常載爸爸去他住的地方為他打營養針,直到他離世為止。
這段軍官與士官融洽相處、感情濡沫的事,也在另一位檢場周清賀叔叔身上看得到。老媽也給周叔叔起了個綽號「啞吧」。周叔叔是聯隊的士官長,退役之後做旗袍,在水交社眷村頗為出名,也靠著他的巧手養活了一大家子「七仙女」。
周叔叔像彌勒佛般笑臉迎人,很少講話,和父親頗為投緣,常以義兄弟相稱,他所生女兒俱喊我父親為「大丈」。從小看病就直奔我家,父親所開之葯都能讓她們快速轉好,兩家人感情甚為融洽,只是周叔叔也已過世。
.
那時的劇隊在忠烈祠維持了多久,沒有印象,可能是我日漸長大,不再跟著爸媽去的緣故。只依稀知道忠烈祠拆遷,那裡蓋了一座室內籃球場,那是我高中時候的事。有次和同學一起入內打籃球,感覺新奇無比,因為我們從來都是在室外的水泥地上打球,能在室內地板上鬥牛,真是件新鮮事。
運動廠館剷平了忠烈祠記憶,而後市政府又把體育館拆了改建成地下停車場,只剩下國民黨市黨部所在的實踐堂和其旁一棟建物而已。民國八十七年我回到臺南市,二棟建物還在,實踐堂早已封閉,只供特定團體教學之用,其旁的二層樓建物則是「藝光國劇隊」租借使用。
我常開車載著父親每週六到劇社票戲。成員大都是上年紀的人,我都不認識,父親也從不說。外觀斑駁老舊的建物重複上演著各齣戲的片段,和其旁老榕樹下聽著歌仔戲的老人家,對照成趣,卻不干擾,而自得其樂。
劇社內廖秋碧阿姨常聽爸媽提起,是我比較知道的人物。她雖是本省人卻熱愛平劇,以老生戲為主,是臺灣少見本地坤生演員,嗓音圓潤著稱。兩岸開放後,廖阿姨至北京學戲,連獲幾項獎譽,可稱臺灣奇女子。而後因整修,劇社遷至社區活動中心,再遷回原址。
父親年逾八旬,耳背目不明,已不能票戲,母親則早離開了我們。每看著父親房中唱戲的照片,勾起我片段記憶:從「天馬」到「藝光」的歲月,是父親休閒娛樂的記憶,也是我思念母親、感懷童年的時刻。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千緣萬履(POD)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21 |
中文書 |
$ 252 |
文學作品 |
$ 266 |
現代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千緣萬履(POD)
本書是作者以報導筆觸描述自己成長經過。
寫出故鄉府城舊時風情和眷村生活風味;
寫出軍校生成長蛻變汗水和基層軍官領導統御之道;
寫出青年期至壯年期奮進的心路歷程;
寫出投入社會盡心於雜誌與文字工作的志業軌跡。
作者簡介:
胡鼎宗
民國四十四年生於臺南市。政戰學校新聞學系畢業。
從事雜誌工作四十年。曾獲「國軍文藝獎」(報導文學類)、「府城文學獎」(散文類)。
出版人物專訪、文史專書、雜文勵志等專冊十三本。於《南市青年》主編任內退休。
章節試閱
之一 天馬奔騰在府城
四、五十年代的臺南市,工商發達,經濟繁榮,是臺灣少數有著文化涵養的地方。其中傳統戲曲的傳揚和演出極為興盛,平劇亦躬逢其盛,在全臺首學之地開花結果,帶動往後數十年表演薪傳,留下璀燦動人的文化底蘊。
這股風潮是外來的軍人和公務員帶來的。其實,當地士紳學者對平劇亦皆愛好,「顧劇團」留臺表演期間,全臺各地對傳統戲曲的喜歡,已達瘋狂程度,一方面基於脫離日治、仰慕中華文化之故,另一方面源於當時戲劇演出乃為唯一文化活動,所以並不因平劇為「外來劇種」而排斥,甚而成為人人學習與爭看的娛樂。...
四、五十年代的臺南市,工商發達,經濟繁榮,是臺灣少數有著文化涵養的地方。其中傳統戲曲的傳揚和演出極為興盛,平劇亦躬逢其盛,在全臺首學之地開花結果,帶動往後數十年表演薪傳,留下璀燦動人的文化底蘊。
這股風潮是外來的軍人和公務員帶來的。其實,當地士紳學者對平劇亦皆愛好,「顧劇團」留臺表演期間,全臺各地對傳統戲曲的喜歡,已達瘋狂程度,一方面基於脫離日治、仰慕中華文化之故,另一方面源於當時戲劇演出乃為唯一文化活動,所以並不因平劇為「外來劇種」而排斥,甚而成為人人學習與爭看的娛樂。...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自序/往事不如煙
我自己的感覺:年齡越大,越念舊。而且很怕記憶之鏈突然中斷,那些美好事物將隨風而逝,於是起了動筆念頭。
論年齡,我還不到寫回憶錄的時間,就算寫了也毫無賣點;能有機會記錄成長都市的舊時風情,以及個人的人生風景,可能是內容雖老調卻不重彈,涵括了些人文意味在內。
不過,個人眼界甚小,生活的吉光片羽,哪堪與時代洪流相比?野人獻曝,留存斯事,自得其樂而已。
緣分難得,步履惟艱。每個人都有可茲敘說的春秋往事,千言萬語反覆吟唱,引為至寶;思索再三,本書即以「千緣萬履」定名。
感激所有在成長...
我自己的感覺:年齡越大,越念舊。而且很怕記憶之鏈突然中斷,那些美好事物將隨風而逝,於是起了動筆念頭。
論年齡,我還不到寫回憶錄的時間,就算寫了也毫無賣點;能有機會記錄成長都市的舊時風情,以及個人的人生風景,可能是內容雖老調卻不重彈,涵括了些人文意味在內。
不過,個人眼界甚小,生活的吉光片羽,哪堪與時代洪流相比?野人獻曝,留存斯事,自得其樂而已。
緣分難得,步履惟艱。每個人都有可茲敘說的春秋往事,千言萬語反覆吟唱,引為至寶;思索再三,本書即以「千緣萬履」定名。
感激所有在成長...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卷一 古都拾零
之一 天馬奔騰在府城
之二 南空院的安平追想曲
之三 想我眷村哥兒們
之四 粼粼運河水 悠悠鐵房情
之五 新町.幫派.夢
之六 明德感恩 輝映榮光
之七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卷二 軍旅流光
之一 蝙蝠山勢下洗禮
之二 榮湖畔砲聲隆隆
之三 飛駝上身練文筆
之四 重慶南路增見識
之五 文化大樓見真章
卷三 文海漫遊
之一 古都青年真本事
之二 學校文藝培根苗
之三 在地雜誌展實力
之...
之一 天馬奔騰在府城
之二 南空院的安平追想曲
之三 想我眷村哥兒們
之四 粼粼運河水 悠悠鐵房情
之五 新町.幫派.夢
之六 明德感恩 輝映榮光
之七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卷二 軍旅流光
之一 蝙蝠山勢下洗禮
之二 榮湖畔砲聲隆隆
之三 飛駝上身練文筆
之四 重慶南路增見識
之五 文化大樓見真章
卷三 文海漫遊
之一 古都青年真本事
之二 學校文藝培根苗
之三 在地雜誌展實力
之...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