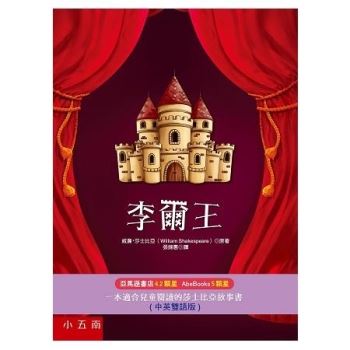推薦序
違章建築的手記──讀郭啟宏小說《稻草人長大了》
紀大偉
舊日的小說家杜斯妥也夫斯基寫了《地下室手記》,喃喃托出封閉空間裡的藝術家孤寂。卡夫卡如是,魯迅如是。當前的小說家,我認為,卻寫出了「違章建築的手記」,不再困守舊時代的封悶地下室。
台灣都會人最熟悉的違章建築之一,就是頂樓加蓋──人們甚至忘記頂樓加蓋是會被拆除的非法空間,反而視為理所當然。奇才作家邱妙津的短篇小說〈柏拉圖之髮〉裡頭,主人翁住在大都市的頂樓加蓋空間,而非地下室。主人翁以寫「垃圾文學」(通俗小說)維生,住處外面的屋頂空地也堆滿垃圾。頂樓加蓋是台灣都會「流動」人口的最愛──流動人口包括從鄉鎮前往城市求職求學的人,收入不穩定的藝術家,離家出走或被父母趕走的青少女。這些流動人口租不起一般公寓,更無法購屋,只好改租便宜的頂樓加蓋。同時,頂樓加蓋這種空間也剛好隱喻了這種「流動」的房客,如身分流動,慾望也流動的〈柏拉圖之髮〉主人翁──正如頂樓加蓋既屬於建築物之內的單位,又屬於建物之外的違章建築,小說主人翁既屬於社會之內的一分子,卻又是被社會排擠的非法怪物。社會邊緣人,正好住在頂樓加蓋這種邊緣空間。
邱妙津畢竟是留在二十世紀的小說家。眾小說家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更加流動不歇,不安於室──不但不住地下室,也頻頻從頂樓加蓋出走。頂樓加蓋未必一定貧窮,反而可能閒錢拼貼而成的後∕後現代色情酒吧。違章建築不只在台北發芽,也在上海以及其他「全球化都會」茁壯開花。在跨國企業盛行的這個時代,人才和錢財不再只從鄉鎮奔赴城市,更從城市飛往其他城市。青年作家郭啟宏的新作,《稻草人長大了》,就是一部「違章建築手記」。《稻草人長大了》是廣納眾聲、野心勃勃的長篇小說,描繪了龐大家族的正史與密史,誠然不只是跨國違章建築的寫真。但書中找得到具體的非法空間,以及心靈的非法空間:書中具體的非法空間就留待讀者自行發掘,我在此不打算洩密;至於小說裡心靈的非法空間,我倒有閒話可說。
什麼是小說裡頭的心靈非法空間?簡言之,「外遇」是也。《稻草人長大了》充滿多種外遇:除了一般認知的婚外情之外,還有形形色色的不法之戀。這些外遇可能在床上發生,可能不必上床就發生,也可能不敢發生。《稻草人長大了》甚至挑戰了「外遇」的定義:外遇之所以為外,就該發生在正宗家庭之外;可是,如果桃花開在家庭堡壘之內,那麼外遇是不是該改稱為「內遇」呢?
法國著名哲學家德希達在《書寫學》(浯f Grammatology荂^中,討論了「危險添加物」(dangerous supplement)這個觀念。德希達將危險添加物說得玄奧,不過此添加物其實正像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添加物一樣平凡常見。如,食物之中添加維他命是好事,但維他命一旦劑量失控卻也可能危害健康。又如,文明社會的飲水都打入了化學藥劑,這些添加物為了消毒飲水或防止蛀牙,卻也可能傷身。危險添加物,就是芸芸眾生又愛又恨,想排除卻又無法釋手的怪物。我先前提及的具體非法空間(違章建築,含頂樓加蓋)和心靈非法空間(外遇),也可視為危險的添加物。違章建築是合法建築的危險添加物:它寄生在合法建築的裡面或外面,可能會被取締,可能會阻礙火災逃生路線,可是合法建築的屋主總是想要收養一點非法空間。就算屋主果真循規蹈矩,沒有偷建任何違章建築,他們卻也無法完全壓抑興建違章建築的幽微慾念。外遇也是危險添加物:對於合法的婚配關係來說,外遇是野花而不是家花,是威脅家庭秩序的寄生物。大概所有的人都承認搞外遇等於玩火;大概也沒有人可以保證外遇的火苗是可以完全壓住的。
我甚至認為:合法家庭是外遇的受惠者。多虧外遇,合法立案的家庭才得以在風雨中倖存。許多人早已知道,維繫既有家庭的弔詭祕方之一,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任憑另一半進行外遇──另一半有了外遇,在家的時候反而更加聽話(大概是出於罪惡感,想要贖罪),所以家庭的平衡感才得以維持。不過,除了這種幾乎成為常識的弔詭之外,我還要指出別的弔詭。除了「目前」和外遇並存的家庭可能因為外遇而「受惠」,「曾經」被外遇威脅的家庭也算是外遇的受惠者。這種「擺脫」外遇陰影的家庭,是改邪歸正的,是浪子回頭的,也因此更讓人津津樂道──可是我要問,要不是當初被外遇威脅了,那麼怎麼可能有改邪、歸正、回頭的起點?如今歷劫歸來,慶幸之餘,恐怕還要感謝當時的劫數(即外遇)呢──如果不曾有劫,要如何歷劫?此外,甚至和外遇絕緣的家庭(過去沒有,目前沒有,以後也不會出現外遇的家庭)更是外遇的受惠者。這種家庭被譽為正直幸福的典範──但我要說,正是因為其他「比較不幸福」的家庭和外遇打得一身腥,這種「健康正常」的家庭才得以脫穎而出。沒有壞人墊底,怎麼看得見(社會上,以及文學電影中的)好人?
以上我說了一串不道德的話,都因為年輕小說家郭啟宏交出一部不道德的外遇小說。然而,不道德的小說家特別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