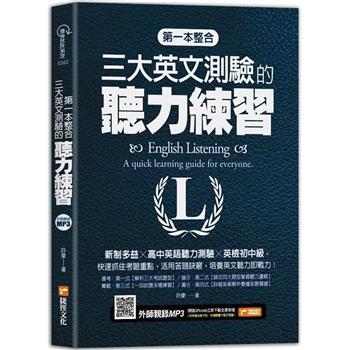本書特點
★慶祝九歌出版社創立三十週年,並反映在此期間(1978-2008)台灣文學之特殊表現及其成就。首創《台灣文學30年菁英選》為台灣本土文學做一完整紀錄,並立下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本集依文類分詩、散文、小說、評論四卷,書名分別為《新詩30家》、《散文30家》、《小說30家》、《評論30家》,除新詩一冊外,餘皆分為二冊。
★本集所選作家為戰後世代(1945年台灣光復以後出生者),各卷作家以出生年為序,皆不重複。
★主編序言,暢談三十年文風與社會變遷的關係。所選各家皆有作者小傳、風格特色、鑑評及照片,便於讀者閱讀賞析之用。
★選收作品,含長短篇散文各一加編者短評,更涵蓋作者寫作風格及該篇作品特色。
台灣現代散文歷久不衰,名家輩出,寫作者大膽嘗試翻新技巧,兼容詩歌小說的質素,包羅多元的內涵,無拘無束,造成一派繁華景象,亦完全符合了「散」字本義的「自由」。器識涵養充足、思考見解深刻、技巧章法整備,此為入選三十家的共同優點;而各家自成的人格特質、人生閱歷、生活態度、關心焦點、書寫方式,則各自形塑了獨特的文風。
上冊入選散文家菁英:
奚淞、蔣勳、顏崑陽、邱坤良、廖玉蕙、阿盛、王溢嘉、龍應台、凌拂、舒國治、林文義、林清玄、周芬伶、龔鵬程、劉克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