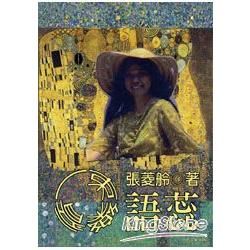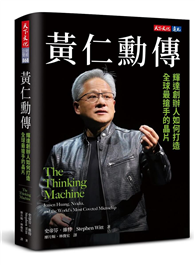代序
張菱舲
我在漫漫季節之間踱著。廣場對街,轉角之處,我瞥見Philip Glass灑著音符,從我詩裡走來。我在他面前幽然顯現,將長長的髮絲撒向秋天。 攬楓色或閃金的陽光,撒秋天成網,網層層摺疊的玄想或意象。逐漸曖昧的年紀,逐漸清晰的夢。山色更濃,水意更淡。
如果清晨有雨,大城在我面前展現無限延長的街道,溼溼的通向海灣,在波浪裡消融。午間,陽光像是偶然,微微一笑,滑過大城嚴肅莊重的琉璃,一閃而過,投影我,網我秋意的髮絲成網。
網盡楓色或閃金的陽光,颯然成詩。風色從詩頁詩行裡溜進溜出,颯然而涼。 我在漫漫的季節之間踱著。在廣場對街,轉角上,見到我詩裡的Philip Glass從詩裡走來,揮手灑著音樂,像一座古希臘神的恆美,在楓色金光的意境裡,微微淒然的白晝,我在街的對岸,將長長的髮絲撒秋天成網,網向淒涼。網滿一裙兜,捧一盈握的音符。懾人的節奏。在秋色裡燃起,焚大城漠然漠然的眼神。
山色更濃,水意更淡。我在廣場對街轉角之處,見秋天走來,揮手灑著音符,盈我滿握,颯然望我。
那時,海灣曾昇上來,在兩柱垂長的塔形之間,探頭窺望,昇起潮汐,澆熄一城焚然的秋意。
焚然的樂意。溼而且涼。淒然響起大城漠然的眼神,網我,網我長長髮絲的網。 我就在那一瞬間,瞥見秋天,從廣場對街,轉角之處,從我詩裡走向我。於是我幽然顯現,掩映滿面,在漫漫季節之間流浪。
我將見到真實之中,我詩裡的意象顯現,網我長長的髮絲成網,網意象成真象。 我將在真實之中,見到那意象。也許是在白晝,或黃昏某些曖昧時光,我將見到那意象在真實之中顯現,而我將在那時,幽然出現在面前,像一瞥秋天。
後記
山在心中呼嘯 萬噸凝結的風
「那只是一片片透明的感受,一種情緒的突發,如菱舲自述中,『常常有很美的光閃過……抓住時,也不過是一點微弱的影子』。既使只是一點微弱的影子也己夠讀者咀嚼迷醉了。你不一定完全嘹解她所述說的每一件事。但你必能感到那片氣氛,常是很柔、很淡、很美的,如秋水倒映的一抹昏黃的光。過了很久也忘不了。她只盛一盤朦朦朧朧的夢給你……像些無言的淒涼,如此的飄忽不可捉摸──你只能用『心』去體會。」這是林懷民早在上一世紀描述菱舲的詩散文。如今吟詠她的散文詩,林懷民當年的先見銳識仍然鮮明。而這本詩集與之前出版的幾百首詩中和她「外太空的狩獵」的長篇史詩等,還有更多深層藝術性的討論,有待知音掘鑿。她的詩文中那種豪情氣勢,極至的反衝張力,絲絲吟詠的剛柔,那些無言的淒涼,含在淡淡飄浮的輕煙薄霧或崖岩表層感到的微顫之下,帶給讀者的是表層抑壓不住,隨時待發的滾燙岩漿。
假如現代藝術是複雜內涵的一種單純表現,這本一九九一年,同是中英對照中文詩篇的合集,同樣是菱舲層層疊疊向陽向陰、錯綜複雜思路情感單純表現的一種現代藝術。聆聽Philip Glass的經典之作「Music in Twelve Parts」,是千變重複著萬化的單純表象,既無起始也無終結。在顯微鏡裡聆聽,是重重疊疊、層層錯綜編織精細精緻的複雜網構。是精巧設計的無數細緻勾花lace片片交織。是萬花筒中無窮無盡排列組合的面面圖案。似同?異,華麗非凡。在整整維持了四個小時沒有間斷的高潮時,突然驟逝。忽然一片靜寂,沉默,禪意。菱舲的詩文在重重疊疊的感傷之後,是重重疊疊的感傷。是層層疊疊交錯編織錯綜的複音瓣複瓣音。是精緻的華字麗句層層重重疊疊編織繁花如泣汀汀如雨晶然的和聲。主題重複變奏變調海縲迴旋賦格形式的唱和。是幽幽如簫的樂音,絲絲剛柔的吟詠,不息綿綿永恆的音韻。是光影互疊起伏千浪千年輪迴的歌聲,撩撥千鍵,千弦撩原,燃亮千弦千鍵,燦然揮灑。Philip Glass創造了音樂的另一種語言,菱舲創作了語言的另一種樂音。早在三十多年前,當Philip Glass還少為人知之時,就連藝術鑑賞家還未肯定他之前,菱舲就肯定了他,也肯定了自己。
藝術是沒有完成的一日,所謂的完成也僅是在有限之中暫時的完成。而最好的藝術是完成於受者的不同心靈思路、不同詮釋、不同的自我感受中。因而千變萬化,無止無盡。如果通常一本詩集合集三十到五十首出版,到如今菱舲出版的這本《一束樂音─語蕊》應該是通常的第十本或是第十五本詩集了。但是藝術重質不重量,作曲甚豐,生前享有盛名與莫札特同時的A. Salieri,如今有誰問津?反之,A. Thomas以一首歌劇Mignon就留名史頁,Pagliacci(小丑),Cavaleria Rusticana(鄉村騎士)都僅以短短一首歌劇永恆。而愈是創新愈有深度的著作,愈需長時間的消化掘發。只是我們等不到那時見證了。
唯弦對這本詩集熱心的指點指教,幫助了我的整理,深深致謝。同時感謝十分謙遜自稱凡夫俗子的蔡先生。本來九歌預排在幾個月前出版此書,因我來不及整理而拖延,就想到菱舲,一切憑自己的毅力。曾被Stanford Harvard Yale MIT競相爭取入學的大孩子們,也曾是菱舲鍾愛的「兩個小傢伙」,也謝謝他們。幾年來我因忙於阿姨的遺作而犧牲了無數次他們相邀親情相聚的時光,他們都能諒解並支持。如今菱舲之前出版的五本遺作已由國會圖書館、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學院等珍藏。然而,當Philip Glass問及並得知菱舲就住隔街咫尺之近的紐約時,他禁不住深深的大聲長嘆。一時不清楚是一種安慰呢?無比的遺憾?還是更加的悲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