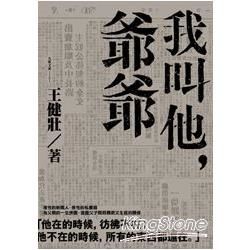代序
那一段我們在眷村的青春歲月 張力
一九六.年代,健壯和我同住左營的一個海軍眷村,他家三一.號,我家三一四號。村子眷舍十戶一長棟,我們兩家分屬不同棟。要去他家,得在進村之後的第一個十字路口左轉,經過防空洞,向前幾步右轉,才到那裡。就讀高中時,我常走這條小路到健壯家,健壯也常出現在我家門口,高坐二十八吋的自行車上,左手扶著門柱,等我同去球場打球,或是到海軍的中山堂、中正堂看電影。
健壯家所屬的那一長棟眷舍,雖是我們這個小型眷村的一部分,卻是毗連另一個全是從渤海灣長山八島遷來的魯籍移民村落。那裡地勢較低,大雨時不免積水。走進健壯家的前院,常會立刻聽到王家除了王伯伯之外的幾個大嗓門吆喝開講;直直穿過兩間房,通到較寬敞的第三間,窗外就是後院。有趣的是,他家的後院緊貼一堵清道光年間修築的城牆。這道牆很厚實,沒法為後院鑿個門。那一長棟房子都是以高牆為界,牆的另一頭也有一長串捱著城牆搭建的房舍。城牆之上滿是雜樹野草,遮住了城垛。甚至在所謂城門洞的北門城樓上,長期住著一位老兵,我們經過城門洞,有時瞧見老兵在城樓上淘米洗菜晾衣服。日漸傾圮的城牆和城門,給城裡城外的孩子留下共同的記憶。如今這座「鳳山縣舊城」已被定為國家一級古蹟,經過整修之後乾淨清爽,每次舊地重遊,竟令我有些不能習慣。
對我而言,看到這堵牆就意味著回到家了。就讀大學時,連續幾班夜行列車都會在清晨時分停靠小站左營,收假回來的海軍官兵下車後換搭計程車返回軍艦或防地,還趕得上早點名。我則是沿著站前的勝利路步行,先經過右手邊健壯畢業的初中,之後再貼著城牆往前走,同時想起另一個版本的鄭成功傳說:有人告訴過我鄭成功就葬在城牆底下,恰好城牆有一小孔,我曾有好幾年深信不疑民族英雄就在裡面躺著。城門洞前一口水井位居十字路口當中,那時還有居民來此汲水,我也曾學他們甩動繩索,讓鐵桶沉入水中,再一手接一手拉至井口。
我不知道健壯當年就坐在後院牆頭的樹蔭下,讀著文學書籍。但我是從他那裡漸漸接觸到文學。其實,陳芳明就住在左營大路上的台電收費站隔壁,而再過去幾步的勝利路口一家腳踏車店的樓上,就是葉石濤的家,當時我們毫無所知。對我們而言,左高地區給了我們另外一些文學機緣。海軍出版的《海訊日報》(後來改名為《忠義報》)是一張四開大的報紙,只有四個版,每個週三、週日各有一版提供學子投稿,不論是高雄中學的青年或是中山國校的小朋友,文章刊登後一律可領五元稿費,這筆稿費正好夠在中山堂或中正堂看兩場電影。健壯的散文常以不同的筆名出現在報紙上,我知道其中一個,也曾向他求證另一個筆名是不是他,他笑而未答,至今仍是我的疑問。書店是接觸文學作品的好去處,然而學校在近火車站的三民區,主要書店卻在鹽埕區,頗有一段距離,但是青春年少的我們只要一想到可以先經過五福三路的省立女中,就會精神振奮,不覺路途遙遠。我們總是先到大眾書局,書局門口靠牆處直立擺放幾乎聯號的「文星叢刊」(有幾種已遭查禁)。書局為客人準備的包書紙上印著「貧者,因書而富;富者,因書而貴」和「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兩句話。往前幾步,又在百成書局瀏覽一陣子。繼續右轉大勇路,就看到大業書店。這家極有特色的書店在進門處的小桌子上,陳列各種詩集,已經成名的幾位出身左營軍中的詩人作品,以及他們的《創世紀》詩刊,一定在其中。健壯在那裡買到紀德《地糧》,也對著我談.弦、葉珊的作品,當年的我似懂非懂。怎麼也沒想到後來我竟有機會和兩位前輩詩人共事多年。
高雄市救國團每年春秋兩季各舉辦一次青年寫作比賽,獲獎作品刊於《高青文粹》,這是一份不太注重宣揚黨國意識的機關刊物。健壯是比賽的常勝軍,每次他都拖著我參賽,我也只好屢敗屢戰。有時我讀著他的作品不免納悶,為甚麼他寫的散文和詩,看似風花雪月,卻還是有其道理,而我絞盡腦汁仍像是無病呻吟?漸漸地,我的文章也在《忠義報》和《高青文粹》上出現,才開始領略到寫作的樂趣和意義。這時健壯的作品,已在左高地區以外的文學刊物上攻佔版面。
風起雲湧的一九七.年代,我們幾位在高中因寫作而熟識的朋友,因先後到台中台北求學,交往更為密切。一九七.年夏天健壯先行北上,國卿和我卻有著不得不「留」在南部的理由。我開始單獨騎著自行車上下學,不能再和健壯並駕齊驅來往於左高之間的中華路上;初時感覺有些落寞,但不久就適應了。我們藉著書信往返,瞭解彼此的近況。有一次健壯到中央研究院的胡適紀念館參觀,選了一張印有「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的胡適墨寶明信片,寫上幾句話寄給我,令我對陌生的台北又多了一份嚮往。想不到三十五年後,胡適紀念館的經營是我主管的業務之一。
我們差距的一年當時看似漫長,如今想來只是瞬間。一九七一年八月下旬,國卿和我搭對號快到北部就學,已經插班台大歷史系的健壯,從他暫住的政大宿舍來台北車站迎接。出站之後,看到對面一排樓房的每家店面,張掛「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等字句的紅布條,氣氛有些奇特。那一年,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密訪中國大陸,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而海內外的保釣運動已經展開。某天晚上,在台大體育館前面健壯介紹我們認識了身穿新潮媚嬉裝的華民,國卿和我頓時感覺自己果然是南部來的老土。第二年國卿插班台大,我則轉考乙組進入政大,大家同住木柵,常有機會見面。住宿不成問題,所以就讀東海的阿擘也就更有理由北上找我們。
身處當時的社會中,我們或許還不能真確感受到時代的轉變。同為負笈在外的學子,我們同住木柵,遠離了家庭和父母的約束,享有更多的自由空間。我們還算是規矩之人,和很多年輕人一樣,著迷每週的西洋歌曲排行榜,關心自由盃、中正盃、亞洲盃,以及後來的威廉瓊斯盃球隊戰績,還有每年的三級棒球國內外賽事。離經叛道的事,至多就是蓄留長髮。由於治安機關視男子蓄髮有違善良風俗,每次我們到西門町或台北車站,總是提高警覺,躲著警察,甚至「跑給警察追」,以免被逮到強迫理髮。一天晚上,和我同住的國卿從外面回來,立刻叮囑我:「等一下看到阿壯不要笑,他被條子堵到,剪了頭髮。」不久健壯進來,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終於看到他久被頭髮覆蓋的雙耳。他坐在書桌前,對著鏡子左瞧右瞧,不說一句話。好一陣子才說:
「我回去了。」我不僅沒有笑他,也不知道該說甚麼。
窮學生靠著有限的生活費,必須省吃儉用過日子,為了買書,自助餐的菜就越點越少。由於家母獨自住在台北,每隔一段日子,我去她那兒拎回一大袋煮好的菜餚,回到木柵和健壯等人分享,若有剩菜,再帶回自用。有一次,在大家殷切期盼之中我去取菜,卻因塞車回來遲了。剛進門就聽得眾人一陣數落,接著立即分而食之。這時我才明白所謂「嗷嗷待哺」的心情。
雖然過著窮困的日子,但是一九七.年代萌發的台灣生命力,不斷豐富我們的心靈。我們正好趕上《中外文學》的創刊、「雲門舞集」和張曉風劇作的演出,也經歷洪通素人畫作和朱銘雕塑個展造成的風潮。楊弦在中山堂舉辦「現代民謠創作演唱會」的當天,我搭夜車趕回高雄,擔任次日健壯和華民公證結婚的證人,以致未能現場經歷現代民歌的誕生的一刻。金庸的武俠小說當時是禁書,盜版商偷天換日安上的書名和作者名,並不會混淆我們的辨識力,而能立刻判定何者才是真正金庸的作品。此時的健壯繼續他的文學創作,和朋友編輯《主流》詩刊,也開始撰寫一系列評論文章。
健壯入營服役前,安排我續住他在木柵的雅房,這樣他就不必急著清空。留下的一些書籍雜誌,後來跟著我搬過幾次家,至今偶爾還能找到他簽了姓名(或筆名)、購買日期的書。雅房靠近公車終點站,房門只是虛應故事掛著一個號碼鎖,散居各地朋友常來投宿。健壯在政戰學校受訓的幾個月,休假時常回他的舊居。之後他分發到曾在八二三砲戰期間防守金門烈嶼的王牌師當連隊輔導長,一九七五年五月的一個週末,他從台南的駐地來台北,說起蔣中正過世那幾天,部隊進入一級戰備,他接到指示,要連上弟兄作交代後事的準備,似乎兩岸戰爭一觸即發。不少年輕士兵憂心忡忡,不知如何下筆,老士官卻興高采烈,喊著終於要反攻大陸了。這一段敘述令我印象深刻。
退伍之後的健壯又來舊居住了一段時間,歷經好幾次求職的碰壁。後來我們一起搬到景美山邊的一棟公寓三樓,他也終於找到工作,竟然是一份綜合性雜誌的主編。我知道他很當一回事地規劃編務,到處約稿,然而這一工作並不穩定,甚至領不到薪水。雜誌停刊後,他投入《仙人掌》雜誌的創刊和其後兩期的編務,終於一展長才,再因余紀忠先生賞識進入《中國時報》,擔任副刊主編。我也跟著健壯夫婦和來台北就讀的健聖,遷往羅斯福路五段一棟公寓的二樓。公寓後面有個「國軍軍犬訓練中心」,偶爾從陽台看到幾隻狼犬接受訓練人員的指令,認命地排隊、爬樓梯,或是繞圈子。幾個月後健壯開始跑立法院新聞,常向我們講述跑新聞的趣事。一九七八年夏天,健壯調到台中,夫妻倆隨著搬家公司的卡車離開台北,我默默地看著車子轉出巷口,頓時有種各奔前程的感覺。此後健壯在新聞圈裡堅持信念努力耕耘三十多年,一起長大的朋友都清楚,彼此也保持聯繫。然而我們處在各自的人生衝刺階段,共同分享的場景就減少了。
這本書裡的多篇文章,還有著父親各時期的身影。我稱為王伯伯的父親,一九一六年於安徽郎溪出生,十八歲自宣城中學畢業後,投身軍旅,有很長一段時間在紛亂的大時代中漂泊;我們那個眷村的長輩,包括先父在內,大多有著類似的經驗。王伯伯逝於一九九六年,此刻我已來不及向他請教一九三七年他所看到的首都保衛戰,戰時桂林的生活情形,後來如何在日軍發動的一號作戰中撤退,以及他的一九四九年經歷。王伯伯退休前在左營的造船廠服務,一九七二年的暑假我在廠裡短期打雜,每天的工作之一是騎著單車送待修艦艇的派工單到各個工場,經過王伯伯看顧的小辦公室時,就會停下來打個招呼,王伯伯總是微笑跟我聊幾句。
王伯伯是看著我們長大的,相信一向淡定從容的他會很高興我為健壯的新書寫了這篇序文。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