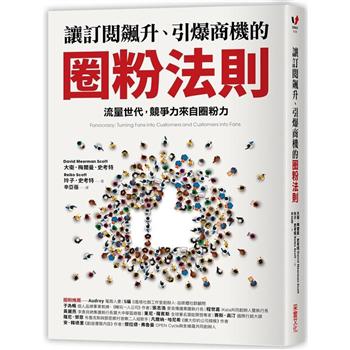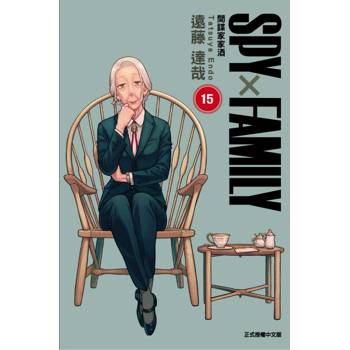這三兄弟齊聚在一間房裡形成有趣畫面。儘管三人髮色相近,但臉孔卻完全不同,尤其是班奈特,因為他有鬍子。唐納文和傑克的輪廓比較秀氣,儘管兩人都不及他們迷途的兄弟蓋伊迷人。傑克傾身向前,開始無所事事地翻閱弔唁卡。
當莫娜拿著裝滿各式食物的托盤走進客廳時,我想唐納文正要開口要求我說明。托盤大小和下水道蓋子差不多,樣式非常簡單,可能是純銀的,而且邊緣明顯地失去光澤。除了像是奇威的鹹餅乾外,冷盤內容還包括一晚花生,和一碗未去核的綠橄欖。在她離開,關上門前,無人開口說話。
傑克前傾,「這什麼鬼?」
此時正吞下一口馬丁尼的班奈特大笑。呼哧一聲他嗆到了,我看見琴酒從他的鼻孔流出。他連忙用手帕掩口咳嗽,傑克對著他微笑。我敢打賭,作小孩時,他們必定會飯吃到一半,突然張開嘴巴,向彼此展示口中嚼爛的食物。
克莉絲蒂立刻以不贊同的眼神看著他們。「伊妮德晚上休息,你們可以停止挑剔嗎?莫娜是護士,她是被雇來照顧爸爸的,而非侍候你們兩個。她肯留下來,是我們運氣好,你們也很清楚此點。這屋子裡,除了我以外,沒有人願意盡舉手之勞。」
「謝謝你說得這麼白,克莉絲蒂。你還真他媽的討人喜歡,」傑克說。
「別吵了,」唐納文說。「我們可不可以先聽她說,再來解決這事?」他抓了一把花生,一次吃一顆地轉而注視我。「你可以說給我們聽嗎?」
我花了幾分鐘詳述我是用什麼方法找到蓋伊‧馬雷克的。沒有提達希‧帕斯可,或者加州忠誠保險,我只透露循著他的身份證找到進一步資料的過程。我承認我有些誇大,好讓事情聽起來較實際上困難「根據我的瞭解,你們的兄弟已經洗心革面。他擔任禧年福音派教會的管理人。我想他還替馬賽拉其他的人做雜務工。他說他是鎮上唯一到府修繕的人,因此他能賺取夠他花用的錢。他的生活很簡單,但他過得還不錯。」
唐納文說,「他結婚了嗎?」
「我沒有問,但似乎沒有。他從未提起老婆。他的住處是教會提供的,以工作代替租金。那地方很怪,不過他似乎還蠻能適應。我承認這些判斷都只是表面的,所以我並未就此停止調查。」
班奈特用牙齒啃咬橄欖的肉,並將果核放在紙巾上。「為什麼是馬賽拉?那是一個又髒又破爛的地方。」
「他離家的那天,這個基本教義教會的牧師在101號公路上讓他搭便車。從那時開始,他基本上都待在馬賽拉。他加入的教會似乎很嚴格。不准跳舞、打牌,和那類的事。他說他偶爾會喝杯啤酒但不嗑藥。這種好轉變已經持續十五年。」
「聽起來你相信他,」班奈特說。「我不知道那麼短的時間內,你能看出多少。你在那裡多久,一個小時?」
「差不多,正確地說,我不是業餘的。我接觸過吸毒者的案子,所以相信我,他看起來不像。同時,我也能看出別人是否在撒謊。」我說。
「沒有冒犯之意,」他說。「只要扯上他的事,我就變得多疑。他向來很會演戲。」他喝完他的馬丁尼,握著高腳杯的腳。最後一點琴酒在邊緣形成明顯的荷葉波紋。他伸手拿酒壺,又替自己斟了杯酒。
「你還和誰談過?」唐納文問,重申他的存在。很明顯地,他再次主導整個場面,並且要確定班奈特依然記得此點。就後者來說,他似乎更關心他的馬丁尼,而非談話。我看見他臉部的緊張線條逐漸舒緩。提問是為了展現他的自制力。
我聳聳肩。「我在鎮上逗留了一會兒,並且向一間雜貨店的老闆娘順便提起蓋伊。那個鎮上的居民不超過五六百。我想那裡的每個人都知道別人的事。她沒有任何反應,也沒有這樣那樣地批評他。牧師和他的妻子似乎真的很喜歡他,而且對 他改變的程度頗感驕傲。他們可能在說謊,演戲,但我不覺得。大多數的人都不善於即興表演。」
傑克拿起一塊餅乾,把沾著餡料的奇威餅乾立起,像在舔奧利奧夾心般地吃著。「所以,現在情況怎樣?他重生了?他受洗了嗎?你認為他會打心底接受我們的主耶穌嗎?」他的譏諷令人生氣。
我轉而瞪著他。「你對耶穌有什麼意見嗎?」
「我為什麼會有意見?那是他的人生,」傑克說。
唐納文換了個坐姿。「還有別人有問題嗎?」
傑克突然把餅乾塞進嘴裡,邊嘎吱嘎吱地嚼著時,還邊用餐巾擦手指。「我想這很好啊。我的意思是,或許他不想要錢。要是他真是這麼個好基督徒,或許他會選擇精神生活而非物質生活。」
班奈特惱怒地打鼻孔裡哼了一聲。「他是基督徒和這件事一點關係也沒有。他一貧如洗,你沒聽她說嗎?他什麼也沒有,他身無分文。」
「我不知道他是否身無分文。我從來沒這麼說,」我插嘴。
現在換班奈特轉過來瞪著我。「你真認為他會拒絕這麼一大筆錢?」
唐納文也看著我。「好問題,」他說。「你對這件事的看法為何?」
「他從來沒有問起錢。當時,我覺得他對你們僱人找他的理由更感興趣。起初他似乎很感動,之後當他瞭解自己誤會了時,又很尷尬。」
「誤會什麼?」克莉絲蒂說。
「他以為會派我去找他是出於家人的在乎或關心。不過很快地,他便發現找他的目的是為了告訴他父親過世,而且通知他,在貝德的遺囑條款中,他是可能的受益人。」
「如果讓他以為我們感情很好,或許他會放棄金錢,改選愛,」傑克提議。
唐納文不理他。「他有說要去找律師談嗎?」
「沒有。我要他和泰莎聯絡,不過她並非負責遺產的律師,她不會就那方面的情況給他任何意見。假如他打電話給她,她會叫他去找律師,除非他已經有一個。」
唐納文說,「換句話說,你的意思是,我們還不知道他會怎麼做。」
班奈特開口,「我們當然知道。一點都不費解。他要的是錢,他不是個傻瓜。」
「你怎麼知道蓋伊要什麼?」克莉絲蒂突然惱怒地答。
班奈特立刻接口道,「金絲應該要他簽一份放棄聲明。讓他簽切結書。趁他還沒機會多做思考前,把一切解決。」
唐納文說,「我問過泰莎是否可以這麼做,我建議我們擬一份棄權聲明,心想可由金絲帶去,不過泰莎反對。她說棄權聲明毫無意義,因為他以後還是可以主張他的權利,因為他沒有合適的代表替他處理,或者他受到不當影響,也或者他當時情緒過於激動而沒有想清楚之類的屁話,都能讓這份聲明無效。我想想她說的也有道理。告訴一個人他父親死了,接著掏出一份棄權聲明?這不啻在一頭公牛面前揮舞紅旗。」
克莉絲蒂再次開口,「金絲有個好主意。她指出因為兩份遺囑的簽署時間只間隔三年,第二份遺囑的見證人可能和第一份相同。要是我們能找出這些見證人,說不定其中有人會知道條款。」
「像是秘書或者律師助理?」唐納文問。
「有可能。也或者是職員/打字員充當見證人。某些人必定曾經參與文件的準備工作,」我說。
「要是真有這麼一份的話,」傑克說。
唐納文在思考時,嘴角下彎。「值得一試。」
「為了什麼目的?」傑克問。「我不是說我們不應該做努力,但很可能還是沒有任何好處。你可能是個不清楚遺囑內容的見證人。再說,要是第二份遺囑是把一切留給蓋伊呢?那麼我們就真的麻煩了。」
班奈特不耐煩。「喔,拜託,傑克。你到底是站在哪一邊?至少見證人可以證明有第二份遺囑的存在。我聽老爸說過六次蓋伊一毛錢也拿不到—我們全聽他這麼說過—所以哪會有什麼不同?」
「怎麼不會?遺囑在老爸手裡。他把它保存在樓上的一個檔案夾裡。你怎知道他最後不會反悔。想想要是他死前撕了呢?大家都沒有隱瞞 他,他完全知道自己還有幾天可活。」
「他會告訴我們。」班奈特說。
「不一定吧。」
「天啊,傑克,我告訴你,他說蓋伊一毛錢都拿不到。我們已經聽過一百次了,而且他非常堅定。」
「他說什麼並不重要。你知道只要扯上蓋伊,他是怎麼處理的。他從來都沒有堅持立場過。被迫嚴守規則的是我們,不是他。」
唐納文清清喉嚨,並且發出尖銳叩擊聲地把他的玻璃杯放下。「好啦,你們兩個別吵了。這對我們一點幫助都沒有。我們已經受夠這些。我們還是等著看蓋伊會怎麼做吧。我們或許不會有麻煩。現在什麼都還不知道。泰莎說,如果他沒有先與她聯絡,她會聯絡他,我可能親自寫封短信給他,我們就從那裡著手。」
班奈特直起身。「等等。誰授權讓你負責的?我們怎麼不討論討論?這畢竟關係到我們大家。」
「你要討論?好啊,繼續講,」唐納文說。「我們全都清楚你的想法。在你眼裡,蓋伊是個討厭鬼。你對他敵意很深,而那種敵視態度,會讓你直接把他逼至絕境。」
「你對他的瞭解不會比我多,」班奈特說。
「我不是在談他,我是在談你。什麼理由讓你這麼確定他要錢?」
「因為他憎恨我們。這就是他當初為何離開的原因,不是嗎?他會做任何事來報復我們,有什麼方法比這麼做更好?」
「你不瞭解,」唐納文說。「你不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麼事。他完全不可能對我們懷有任何敵意。你在那邊挑釁,他當然也會繼續防備。」
「我從沒對蓋伊做過什麼。他幹嘛要恨我?」傑克開心地說。兩個哥哥之間的激烈爭辯似乎讓他覺得很有趣,我懷疑他是否經常煽動他們。
班奈特又冷哼了一聲,他和傑克眨眨眼。某種氣氛在他倆中間閃現,但我不確定是什麼。
唐納文再次以警告的眼神打斷兩人。「我們可不可以回到正題?還有人有新的意見要提供嗎?」
「唐納文掌控整個家庭,他就是王,」班奈特說。他看著我,眼睛有點水汪汪的,就像那些喝多的人一般。不到十五分鐘,我就已經看他灌下兩杯馬丁尼,誰知道在進客廳之前他還喝了多少?「那個人認為我是個白癡。他可能假裝支持,但其實在撒謊。他和我的父親從未真正供應我足夠的錢去做成任何事。而且當我失敗—當一個事業做垮時—他們會很快指出我是怎麼個管理不善。爸爸一直在扯我後腿,而就我來說,現在蓋伊出現,並堅持他那份遺產又是同樣的情況。誰會關心我們的利益?不是他,」他說,彈出拇指指著唐納文。
「等等。住口!這又是從何說起?」
「我從來不是真心在為自己爭取,我早該在很久之前就堅持,不過我還是出錢參與計畫,參與你和爸爸捏造的故事。『嘿,班奈特,這點錢給你,好好利用這筆小額的款子,替自己闖番事業,並且累積出更多的財富。你不能指望我們負擔整個企業的經費。』諸如此類,一遍又一遍,這就是他們對我說的話。」班奈特說。
唐納文斜眼看他,搖搖頭。「我簡直不敢相信,爸爸給了你好幾十萬,而你全敗光了,你覺得自己可以有多少次機會?開始時,這城裡的哪家銀行願意給你半毛錢—」
「胡扯!全是胡扯。我像條狗般地工作,你很清楚。該死,爸爸也有很多事業做失敗。你不也是。現在卻搞成我得坐在這裡,他媽的為我的每個動作受審判—就只為了拿那一點創業基金。」
唐納文不可置信地看著他。「你合夥人拿出的錢又在哪兒,那也是你吹牛的。你一心只想做大人物,卻不願意腳踏實地地幹。你所做的事大半都是詐欺,你心裡很清楚。要是你不知道,那下場會更慘,因為你就準備去吃牢飯吧。」
班奈特伸出一根手指,重複地對著空中戳,彷彿那裡有個電梯按鈕。「聽清楚,我是願意承擔風險的投資人,我是願意承擔風險、放手一搏的人,你卻從未站在第一線上頭。你老是撿安全的做。你是爹地的小男孩,乖乖待在家中,爹地說什麼就做什麼的小寶貝。現在你卻想以成功者自居。哼,真他媽的幹,去你的。」
「注意幹這個字,有女士在場,」傑克語調平板地說。
「閉嘴,你這小混蛋,沒人在和你說話!」
克莉絲蒂朝我的方向瞥一眼,然後舉起手說,「嘿,夥伴們,可以晚點再吵嗎?金絲不必坐在這裡聽這些。我們是請她來喝酒不是來看戲的。」
我聽出她話中的暗示,藉機站起身。「我想我該告退,讓你們好好討論。我真的認為你們不需要擔心蓋伊。他看起來是個好人。這就是我觀察的主要結論。我希望所有事都能圓滿解決。」
一大段笨拙的廢話接踵而生:替火爆場面道歉,慌亂地解釋貝德的死讓大家都很緊繃。我個人卻認為他們是一群粗魯的鄉巴佬,要不是我酬勞還未拿到手,我才懶得和他們說那麼多。然而事實上,他們向我保證,絕無意冒犯,我也向他們保證,沒人會那麼認為。看在錢的份上,我撒謊的功夫可以不比他們任何人差。我們一一握手,眾人感謝我撥冗前來。我也謝謝他們的酒,然後告辭。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金色預謀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78 |
二手中文書 |
$ 246 |
中文書 |
$ 246 |
英美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金色預謀
★紐約時報暢銷作家——蘇‧葛拉芙頓,經典推理鉅作
★好評如潮「字母天后」系列第M集
★本系列主角金絲‧梅芳,完美調和了邏輯推理的冷硬果決與女偵探的柔性風貌
★作者蘇‧葛拉芙頓與莎拉‧派芮斯基、梅西‧米勒並稱美國三大冷硬派推理女傑
★系列作品譯為26種語言、風行全球28國
★丁學文、九把刀、李家同、杜鵑窩人、既晴、景翔齊聲推薦
★「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齊聲推薦
★《美國人物雜誌》──蘇‧葛拉芙頓設立了一個讓同業無法跟隨,更別說超越的高標準
富豪馬雷克先生去世,四個兒子繼承了龐大的家產,然而放浪不羈的第四子早在多年前離開家族,被家人視為家族之恥。然而為了解決遺產的分配,勢必要請四子出面,於是女偵探金絲‧梅芳受雇追查四子的下落,受委託的事小,馬雷克家族因此事而浮上檯面的種種謎團,才是對金絲而言最具挑戰性的工作……
作者簡介:
蘇‧葛拉芙頓
1940年出生於美國肯塔基州路易維爾市,是一位相當傑出的電視劇作家及小說家。葛拉芙頓的創作天賦,在早期小說及長篇劇作中已初現端倪,80年代末期甚且將克莉絲蒂的英國作品改編為電視劇集。
1982年推出的金絲‧梅芳探案系列,每部作品皆按英文字母的排列順序命名,創新的手法,一直為推理小說迷所津津樂道。葛拉芙頓運用人物側寫手法,有效地拓展了偵探小說的視野,讓人物回歸為小說的第一主題,同時也使曲折的情節有更進一步的深化空間。其作品筆觸果斷、情節多變,讀來令人大呼過癮。
她的小說被譯為26種語言版本,發行全球28個國家,至今銷售記錄達數百萬本之多,堪稱偵探小說界的暢銷大師。
章節試閱
這三兄弟齊聚在一間房裡形成有趣畫面。儘管三人髮色相近,但臉孔卻完全不同,尤其是班奈特,因為他有鬍子。唐納文和傑克的輪廓比較秀氣,儘管兩人都不及他們迷途的兄弟蓋伊迷人。傑克傾身向前,開始無所事事地翻閱弔唁卡。
當莫娜拿著裝滿各式食物的托盤走進客廳時,我想唐納文正要開口要求我說明。托盤大小和下水道蓋子差不多,樣式非常簡單,可能是純銀的,而且邊緣明顯地失去光澤。除了像是奇威的鹹餅乾外,冷盤內容還包括一晚花生,和一碗未去核的綠橄欖。在她離開,關上門前,無人開口說話。
傑克前傾,「這什麼鬼?」...
當莫娜拿著裝滿各式食物的托盤走進客廳時,我想唐納文正要開口要求我說明。托盤大小和下水道蓋子差不多,樣式非常簡單,可能是純銀的,而且邊緣明顯地失去光澤。除了像是奇威的鹹餅乾外,冷盤內容還包括一晚花生,和一碗未去核的綠橄欖。在她離開,關上門前,無人開口說話。
傑克前傾,「這什麼鬼?」...
»看全部
推薦序
推理文壇中的女性圖像 ◎景翔(推理評論家)
在推理文學的世界裡,儘管在創作者和系列主角兩者數量上都還沒有完全到「男女平等」的地步,但女性始終都占有一席之地,卻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創立「謀殺專門店」的詹宏志先生在他為其中一本推理小說寫的導讀裡,就洋洋灑灑地列出一大串卓然有成的女作家。從他所謂「上古開創時期」,比福爾摩斯更早出現的史上第一位推理小說女作家安娜‧凱薩琳‧格林(Anna Katharine Green 1846-1935)開始,二十世紀從第一個十年的瑪麗‧蘭哈特(Mary R. Rinehart 1876-1958),往下數到二○年代...
在推理文學的世界裡,儘管在創作者和系列主角兩者數量上都還沒有完全到「男女平等」的地步,但女性始終都占有一席之地,卻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創立「謀殺專門店」的詹宏志先生在他為其中一本推理小說寫的導讀裡,就洋洋灑灑地列出一大串卓然有成的女作家。從他所謂「上古開創時期」,比福爾摩斯更早出現的史上第一位推理小說女作家安娜‧凱薩琳‧格林(Anna Katharine Green 1846-1935)開始,二十世紀從第一個十年的瑪麗‧蘭哈特(Mary R. Rinehart 1876-1958),往下數到二○年代...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蘇‧葛拉芙頓 譯者: 劉韻韶
- 出版社: 小知堂文化 出版日期:2007-03-01 ISBN/ISSN:9789574505432
-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84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英美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