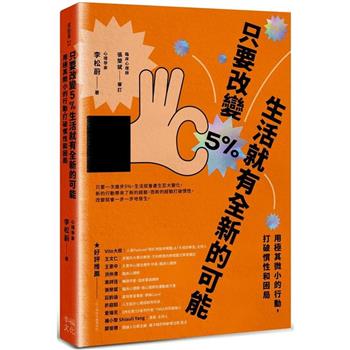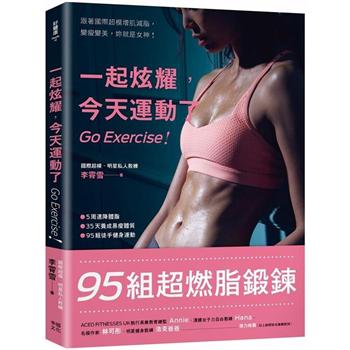【導論】
十八世紀日本禪林與東亞漢文學之交涉:
以京都相國寺派大典顯常《小雲棲稿》為考察中心
一、 前言:問題的所在
十八世紀的東亞海域諸國,呈現錯綜複雜的交流與互動局勢。伴隨盛清帝國時代的來臨,漢字文化圈(sinosphere)內各國,一方面仍秉持固有的華夷心態凝視(gaze)中邊關係,而社會內部形成的慕華心態與相應的雅俗觀,卻就此達到巔峰。與此同時,周邊國家紛紛出現對中國文化強勢影響的反思與批判聲音。 如向與中國有一衣帶水之稱的日本,正從古典學問的復權、和漢‧雅俗對立的文化奠基期, 步入「雅俗融合」的爛熟階段。 斯時,以江戶荻生徂徠(1666-1728)為首之古文辭學派興起,不僅打破近世以降京都五山禪僧確立的宋學思想之藩籬,並黜斥德川初期漢學者依傍宋儒明經之傳統。而在文藝理論上,其所標舉明代李攀龍(1514-1570)、王世貞(1526-1590)復古學派之旗幟,為漢文壇帶來耳目一新的家風;並在門下高足服部南郭(1683-1759)等人的推波助瀾下,一躍成為文藝思潮之主流。 儘管在徂徠身後不久,「反徂徠學」之聲浪日益高漲,難以否認的是,整個十八世紀的學術話語權幾乎未曾離開對其思想的探論。 最顯而易見的,即是「上方」與「江戶」兩大地域文化性格雖共構整個近世日本文化之主體,展現雅俗融合內在的複數性,然而東西文運發展始終與古文辭學派之消長,密不可分。
隨著江戶文壇巨擘徂徠、南郭之相繼凋零,十八世紀後半(1751-1788)的京都,始迎來「藝苑之秋」的局面。 堪稱「振起五山文學頹勢之碩英」 的臨濟宗相國寺派禪僧大典顯常(1719-1801),既是見證這個時代轉變的重要人物,亦是接續新舊文化的中介者(cultural mediator),在近世日本文化史上佔有舉足輕重之地位。大典禪師道號梅莊,法諱顯常,又號大典、蕉中、東湖,亦有稱竺常。生於享保四年,卒於享和元年。近江神崎人,八歲從父入京都,先是於黃檗山華藏院薙髮,翌年復投相國寺慈雲庵獨峰慈秀(?-1756)門下,正式出家。此後,更就當時著名的學僧大潮元皓(1678-1789)、布衣儒者宇野士新(1698-1745)學習漢詩文,宗範古文辭派。獨峰既歿,禪師旋以病故退隱山林,致力於筆耕,迨安永元年(1772)再歸慈雲。六年(1777),復依山中耆老勸請,董席相國寺第一百十三代住持。大典禪師學識拔群而名震禪剎,曾獲列碩學,幕府由是召為對馬以酊庵的朝鮮修文職,並於期滿後由五山之首的南禪寺授予紫衣。平生著述頗豐,在禪學理論、文學批評及詩文創作方面咸有造詣,詩壇宗匠六如慈周(1734-1801) 如是評:「其詩玄澹清婉,瑤臺之月,霜天之鶴。不假安排,優入唐域。而耳食之徒,尚且目之以太羹玄酒。」 現存作品中,收錄若干與王公侯伯、碩匠名士的應酬文字,反映禪師交遊廣闊,不挾方之內外,在京阪文壇上佔有一席之地。
歷來關於大典禪師之研究,國內外學界均未充分展開論述,除臨濟宗相國寺派學僧小畠文鼎的《大典禪師》(1927)一書外,罕有其儔。是書立基於堅實的文獻基礎上,從史學研究進路對大典禪師生平行誼進行詳細考證,從而關注其在佛教史、文學史與外交史上的特殊地位,洵為研究之良範。值得一提的是,近年隨著東亞文化研究在日發展的顯著化,大典禪師相關研究始以多元的觀照面向,在各個研究領域進行嶄新對話。如池內敏率先以日朝關係的角度,重新梳理禪師與朝鮮通信使的往來詩文書信史料,並提出其於外交上的重大意義,功不可沒。尤其,禪師筆談記錄《萍遇錄》的問世,成為理解江戶時代日人朝鮮觀至為重要的史料依憑。 而藝術史、文化史學者別自抱持著對伊藤若沖(1716-1800)、賣茶翁(月海元昭,1675-1763)的關懷,連帶注意到大典禪師詩文中對二人的評騭文字,特別是出自禪師之手的《賣茶翁傳》是為現今研究其人不可或缺的傳記作品。至於傳統文學方面的研究,過去中村幸彥聚焦在京學中的《唐詩選》課題,由是注意到禪師《唐詩解頤》對江戶詩學發展的重要性;筆者亦曾就當時《世說新語補》注選本的出版進行文獻勾稽,始知禪師三度箋注出版的《世說鈔撮》於近世的日本漢學界影響甚鉅。 又如由末木文美士、堀川貴司《江戶漢詩選(5)僧門—独菴玄光‧売茶翁‧大潮元皓‧大典顕常》(東京:岩波書店,1996)一書,提出其人其詩在江戶漢詩研究史上之價值,意義非凡。儘管如此,這種以單一議題(事件)而不以人為主的研究方法,仍難以宏觀俯瞰大典禪師在整個江戶文化史上的殊異性。
過去小畠氏曾對大典禪師著作進行全盤調查,在其所勾稽的78種書籍目錄裏,除23種屬有目無書外,尚有55種為傳世著作。而在現存著作中,僅就刊本來看,絕大部分的著述又集中在安永(1772-1781)、寬政(1789-1801)年間出版。其中,《小雲棲稿》的再版係大典禪師在世時,重新補刻校訂並付剞劂的最後一部詩文集,收錄其自寶曆九年(1759)就慈雲庵退院以降,迄於安永二年(1773)再返山庵以前,此間莫約十五年閑居郊野時期的作品。全書凡十二卷,勒為六冊,按體裁分為十八類,包括:五言古詩(6)、七言古詩(6)、五言律詩(175)、五言排律(15)、七言律詩(29)、五言絕句(147)、七言絕句(270)、賦(1)、序(20)、傳(2)、記(8)、碑碣銘(4)、論(3)、說(8)、銘箴(12)、哀文(3)、跋(5)、雜文(4)和書(51)等,頗具規模。是書脫稿後,禪師曾多次致函同窗片山北海(1723-1790),請求代為題序,相關尺牘內容悉收入《小雲棲手簡》初編中,唯其一者見於《小雲棲稿》:
不慧詩文有請梓行,依違不果,頃見促不已,遂授之云。近世文苑日靡,諸以彫蟲災梨棗者,月滋歲繁,不慧固腹非之,豈其尤而效之?顧以年過半百,才分已限,不如隨其所請,而為不朽計也。詩文總十有二卷,刻畫無塩,足下所諳知也。然所謂冠一言以寵光者,非足下其誰也!千萬冒凂。幸一下大手,事在面罄,先茲敘陳,冀為意匠地。
北海早年從遊士新門下,並由是結識同時期前來求教的大典禪師,二人始以詩文相交,終成莫逆。禪師自稱:「嘗從宇先生學文,乃與君相交四十年如一日也。道雖不同,於其所執,未嘗不相謀也,凡有著作,莫不相視,悅其同調。」 足見一斑。是以士新作為江戶中期關西詩壇的異軍突起, 起初信奉徂徠復古學說,後因與之意見相左,學風遂轉向折衷;此外,又於經學、「於詩文言必稽,事必核」, 故有稱古注派之流亞。由於其學問不從時流,世或目以為畸;雖然,亦不為意,輒稱:「道之弘而世之憂,君子所志,吾豈為道而遠人者乎!當今之時,毋論不得出而從政,移風易俗,即退而序詩書,循循然而善誘。舊染成體,圓方不相入,吾故不能與輕俊之士為伍也。」 頗體現儒士從善固窮以待來時的風骨氣節。對於年少發跡的禪師,士新敦勸其學優乃仕之餘,應心無旁鶩、誠心修道,切勿耽溺於翰墨遊戲:
車馬喧塵地,胡為君遠遊。江山千里路,海月一輪秋。
麗藻非逢問,明珠且莫投。不言分手暫,緇素更無儔。
又
千里兩都際,悠悠幾往來。悲秋非爾事,作賦讓誰才。
大海窺樓結,高山望雪催。禪心無住看,風景或徘徊。
上述引詩成於寬保二年(1742),甫屆弱冠的禪師始以五山與金地院僧諍事,隨慈照院住持天叔顯台共赴江戶幕府備詢,時士新有詩為贈。此詩詩意甚明,美其名曰送別,實少狀離情之辭,多作規箴勸諫之語。禪師雖為一介緇流,但留心辭藻,文才縱橫,早年以文事出入儒釋,寅緣公武,名聲顯赫,嘗自我解嘲:「不慧釋氏子,何以文為?乃習氣不除,間遊戲筆研,唯是瓦釜雷鳴,必見笑於大方之家。」 不僅嗜詩成性,且老而彌篤。全詩以「車馬喧塵地,胡為君遠遊」詰問破題,傳遞詩人對山林朝市本殊途的立場,告誡遠遊的禪師俗務經心之餘莫忘初衷,寓意深遠。往後,反覆道以「非逢問」、「且莫投」、「非爾事」諸語,不難想見其對禪師過早投身世海、恐放失心志甚為堪慮,乃就中叮囑,老婆心切不言而喻。凡此,或影響禪師日後一度放棄宗門中事、選擇隱逸修行的人生抉擇。
士新歿後,北海號召以浪華木村世肅(1736-1802)為首的蒹葭堂諸子集結混沌詩社,名聲「藉藉四方,諸以筆札來求者不絕,皆以敏捷應之,篇什浩翰盈箱」, 「海內知宇先生之業者,莫不知君,以故行束脩以上者,比比不絕」, 建旗鼓一方。當此之際,江戶漢詩壇一片繁榮,盛況空前。詩社蜂起,「人人各自振藻,家家自展技」, 別集、選集乃至以詩話為中心的詩學論著魚貫面世,而「以彫蟲災梨棗者」亦屢見不鮮。興許帶著對「文苑日靡」、詩家魚龍混雜的憂慮,以及懷抱著經世的文章實用觀,北海雖執詩壇之牛耳,終其一生卻未嘗以詩家自居,亦不曾刊行個人文集,一如其師。而身後由友朋門徒裒集刊刻的若干集子,今猶不獲,因此禪師詩文尺牘中的相關記載文字,便成為了解其生平不可或缺的依憑。儘管北海不以立言為己任,但對禪師聲名鵲起之際,選擇急流勇退、閉門潛心著述的作為,卻抱持肯定態度:
噫!古之學者身遇遣唐留學之盛,出庠黌、登臺闕而如彼,今也在庶士之與僧流而如此;則雖不當經世,無乃降者即升,而汙者即隆耶!禪師之所撰,集而刻成,以序屬余。觀其文溫雅純粹,其詩和諧清麗,而天機活動以斡旋之,猶丸之轉盤者,乃其道之所致乎。余雖不文也,有見東方之文全乎夏者,自宇子與禪師,則其所不敢辭也。
在北海的背書下,《小雲棲稿》出版伊始即在江戶文壇產生不小的回響,而禪師刻意將是書作為藝苑切磋談資,併有贈書舉動,亦使書稿廣為世人所熟知。在與儒者澤田君孝(1722-1774)的兩封書信中,禪師曾話及此事:「《小雲棲稿》既施四方,得入電矚褒賞之厚,令人愧死。今般謹具一部附貴地書院,亦准前見耳,幸冀收錄。」 又謂:「《小雲棲稿》如有討論,爾時必見邀,亦為一日雅集。」 可為一證。即便進入江戶後期,《小雲棲稿》依然是當時漢文學習的重要指導書,著名的昌平黌教授、漢詩批評家友野霞舟(1791-1849)云:
余閱《昨非集》,雖沈著有自得之境,然殊乏高筆,竊恠其名浮於實矣。讀《小雲棲稿》,似更長一格,蓋晚年所著也,因知禪師老而益精詣也。文最妥帖,絕無支離之病,當時推為巨匠亦非虛美矣。
《昨非集》成於寶曆十一年(1761),係禪師早年出版的著作之一,收錄自弱冠迄於寶曆九年(1759)離山隱居之初的詩文作品。書名「昨非」,係取陶淵明詩「覺今是而昨非」,蓋以「師之於文章自以為土苴緒餘,至其所道乃非世之所識也。且辭官剎,雲遊江海則是其志也。榮利不可繫、名聲不可拘,必矣。」 恰與編纂《小雲棲稿》時,對外宣稱「顧以年過半百,才分已限,不如隨其所請,而為不朽計」的創作心態,呈現鮮明對比。此時禪師業已褪卻年少時縱情文墨、流連光景的風發意氣,先是一變為著述固「非其志」 、不為文字所囿的沉著自得;在歷經十五年的雲遊生涯後,其境界再變為欲立文字以成「不朽計」的精益老練。《小雲棲稿》的成立,隱然象徵著禪師將作為陶冶性情的翰墨遊戲,昇華至以文字做佛事的淑世境地,可謂文字三昧參究與實踐下的結果。
今就東亞漢文學發展的基礎上,以中日漢文學交流為主線,通過對《小雲棲稿》的分析,將有助於釐清大典所處之時代背景、學思歷程、人際網絡與創作心態,從而探求其文藝風格的形成原因以及演進軌跡,乃至管窺十八世紀上方文壇之實態以及日本禪林文學發展的內在趨勢。其目的與重要性,約可從數端觀之:
(一)從通代文學史的角度看,出身京都五山名剎、深受幕府器重的大典禪
師,是儒林眼中的「緇衣禪僧」,叢林口中的「黑衣儒者」。 他是江戶時代少數
長於外典的儒僧,曾數度與儒者進行儒佛、心性、文道等命題之論辨,也曾著書
批判傳統五山宋學思想。尤其是為數不多對日中詩學發展胸有成竹的詩僧,於詩
禪論述有所發明,對江戶禪林文藝理論具有一定之啟迪。從斷代史的角度來看,大典禪師在文學創作上雖然接受徂徠學說的復古思想,卻非一味推尊擬古主義,而兼取法於漢魏唐宋,不拘一格,由是提出調整、流暢、圓熟的創作標準,可謂
別開生面。作為五山叢林文學之餘響,大典禪師同時揭開江戶中期上方文壇反古
文辭學派之序幕,無疑具有承先啟後之重大意義。
(二)從交流史的角度看,自一六五四年以福建高僧隱元隆琦(1592-1673)
為首的黃檗僧團東渡日本、於京都宇治創立萬福寺後,儼然成為日中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媒介之一。是時受到公武兩造青睞的渡日華僧,為鎖國時期的日本帶來明朝流行文化,其在異地留下為數可觀的詩文作品,不僅豐富江戶叢林文學之面容,而在日刻意培養的法門龍象,亦成為傳承黃檗家風與中華文化的幕後推手。大典幼入華藏院為沙彌,與家中兄弟妹共為黃檗僧侶;及長,從遊於檗門碩學大潮元皓之下習漢文,又與月海元昭以詩文、茶道相結為忘年交。此外,禪師座下白眉中,以才學見長的聞中淨復(1739-1829)、 萬浪玄達(1733-1800), 原來分別嗣法隱元之日籍法孫雷巖廣音(1699-1765)與玉柱寂撐;而平生與之相善、切磋文藝的法友如終南淨壽(1711-1767)、悟心元明(1713-1785), 也都是檗宗一時尊宿。大典禪師與黃檗宗派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映現自隱元東渡半世紀以來,日本漢文壇喧嘩繁盛的局勢,也是明清宗教文化從移植走向共生的具體證明。
(三)從江戶文藝思潮的角度看,伴隨著政局變化與經濟發展,江戶中期的社會達到史無前例的變貌與規模,呈現鮮明的世俗化趨勢。豐盈的物力拓展了中
下階層作家的創作視野與審美經驗,改變往昔上層階級(公家、武家與禪林)對雅俗品味的鑑賞標準。是時,上方町人握有經濟與文化之實權,一方面由富商集
資建立、以懷德堂為首的學問所、私塾,培養一批具有道德修養的「商人學者」,與藩儒分庭抗禮;另一方面,附庸風雅、競相誇富的雅痞(yuppie)社群,成為
文化場域的中堅分子,帶動文物商品化與雅俗共存的市場趨勢。受惠於這片曾孕
育絢爛元祿盛世之沃土,大典禪師不僅於茶藝、花道、篆刻、書畫、琴奕諸方面
頗有會心,而從他與學者、使節、僧侶或商賈等各種人物身分的對話中,還可以看見其對文化繁盛的謳歌外,所懷揣對世道轉變的憂慮,以及雅賞品味的堅持態度——儘管在實踐過程中(包含文學創作與鑑賞),他早已不自覺的將禪林文藝推向俗化一方。這種矛盾、焦慮的處境,絕不單是個人、偶然性的發生,更是十八世紀上方文壇與叢林知識分子共同面臨的時代課題。
緣於此,筆者擬立基於前賢研究之上,以京都臨濟宗相國寺派的大典顯常為考察對象,結合近世僧家文學、明清佛教與東亞交流三個層面,經由若干個案研究分析,嘗試捕捉十八世紀日本叢林文學發展之吉光片羽。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日本‧大典顯常《小雲棲稿》校注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40 |
文學研究 |
$ 270 |
日本現代文學 |
$ 270 |
文學作品 |
$ 279 |
中文書 |
$ 279 |
日本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日本‧大典顯常《小雲棲稿》校注
18世紀的東亞海域諸國,呈現錯綜複雜的互動局勢。向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正從古典學問的復權、和漢‧雅俗的對立,步入融合階段。自17世紀以隱元隆琦(1592-1673)為首的渡日華僧,為鎖國的日本帶來明朝流行文化後,不僅豐富江戶叢林文學之內涵,而在日刻意培養的門徒,時已成為傳承黃檗家風與中華文化的重要推手。堪稱「振起五山文學頹勢之碩英」的大典顯常(1719-1801),法接日本臨濟,在文學造詣上則深受中國黃檗禪的啟迪。本書通過對其生前重新補訂的最後一部詩文集《小雲棲稿》的斠理,希冀能夠映現自隱元禪師東渡近一個世紀以來,日本漢文壇喧嘩繁盛之面容,及明清宗教文化從移植走向共生的具體樣態。
作者簡介:
編者簡介
劉家幸,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博士後研究、花園大學國際禪學研究所客員研究員。曾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訪問研究員(2013-2014)、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外國人共同研究者(2018-2019)。主要研究領域為日本漢文小說、東亞佛教文化。著有博士論文《日本江戶漢文世說體著作之受容與生成》,單篇論文〈虛靈不昧托青蓮──黃檗四祖念佛獨湛感應書寫義蘊探析〉、〈峭壁空中湧聖泉:江戶禪林有馬湯山地景文學探析〉、〈明末清初渡日華僧高泉性潡《釋門孝傳》初探〉等。
章節試閱
【導論】
十八世紀日本禪林與東亞漢文學之交涉:
以京都相國寺派大典顯常《小雲棲稿》為考察中心
一、 前言:問題的所在
十八世紀的東亞海域諸國,呈現錯綜複雜的交流與互動局勢。伴隨盛清帝國時代的來臨,漢字文化圈(sinosphere)內各國,一方面仍秉持固有的華夷心態凝視(gaze)中邊關係,而社會內部形成的慕華心態與相應的雅俗觀,卻就此達到巔峰。與此同時,周邊國家紛紛出現對中國文化強勢影響的反思與批判聲音。 如向與中國有一衣帶水之稱的日本,正從古典學問的復權、和漢‧雅俗對立的文化奠基期, 步入「雅俗融合」的爛熟階段...
十八世紀日本禪林與東亞漢文學之交涉:
以京都相國寺派大典顯常《小雲棲稿》為考察中心
一、 前言:問題的所在
十八世紀的東亞海域諸國,呈現錯綜複雜的交流與互動局勢。伴隨盛清帝國時代的來臨,漢字文化圈(sinosphere)內各國,一方面仍秉持固有的華夷心態凝視(gaze)中邊關係,而社會內部形成的慕華心態與相應的雅俗觀,卻就此達到巔峰。與此同時,周邊國家紛紛出現對中國文化強勢影響的反思與批判聲音。 如向與中國有一衣帶水之稱的日本,正從古典學問的復權、和漢‧雅俗對立的文化奠基期, 步入「雅俗融合」的爛熟階段...
顯示全部內容
推薦序
《小雲棲稿》序
蓋嘗聞文與道升降,道與世汙隆,我東方則然乎哉!神代邈矣,自都橿原而降,其道也神,其文也侏離。西發東漸,是既混雜,侏離亦相半。自遣唐留學之制起,頗知文之不專侏離,菅、紀、橘、都之倫,由此其選也。然而知效李唐,而不知李唐沿襲六朝靡儷駢偶之習,何況秦漢以上!則我不知其升者降耶?抑其隆者汙也?保元以來,皇維廢弛,鐮倉氏霸於關東,而武弁是競。侏離之文濟美當世,而經世不與焉。肉食者不學,學而不及修文,於是立誠之後,使不立字家儼然握其柄,而顧其成也。直不專耳,是亦侏離也。
及物子唱業於東都,一...
蓋嘗聞文與道升降,道與世汙隆,我東方則然乎哉!神代邈矣,自都橿原而降,其道也神,其文也侏離。西發東漸,是既混雜,侏離亦相半。自遣唐留學之制起,頗知文之不專侏離,菅、紀、橘、都之倫,由此其選也。然而知效李唐,而不知李唐沿襲六朝靡儷駢偶之習,何況秦漢以上!則我不知其升者降耶?抑其隆者汙也?保元以來,皇維廢弛,鐮倉氏霸於關東,而武弁是競。侏離之文濟美當世,而經世不與焉。肉食者不學,學而不及修文,於是立誠之後,使不立字家儼然握其柄,而顧其成也。直不專耳,是亦侏離也。
及物子唱業於東都,一...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總序/萬金川 4
叢刊緣起 6
導論/劉家幸 11
凡例 72
解題 75
《小雲棲稿》序 76
《小雲棲稿》卷之一 78
《小雲棲稿》卷之二 103
《小雲棲稿》卷之三 129
《小雲棲稿》卷之四 154
《小雲棲稿》卷之五 182
《小雲棲稿》卷之六 208
《小雲棲稿》卷之七 233
《小雲棲稿》卷之八 253
《小雲棲稿》卷之九 267
《小雲棲稿》卷之十 282
《小雲棲稿》卷之十一 301
《小雲棲稿》卷之十二 317
《小雲棲稿》跋 333
叢刊緣起 6
導論/劉家幸 11
凡例 72
解題 75
《小雲棲稿》序 76
《小雲棲稿》卷之一 78
《小雲棲稿》卷之二 103
《小雲棲稿》卷之三 129
《小雲棲稿》卷之四 154
《小雲棲稿》卷之五 182
《小雲棲稿》卷之六 208
《小雲棲稿》卷之七 233
《小雲棲稿》卷之八 253
《小雲棲稿》卷之九 267
《小雲棲稿》卷之十 282
《小雲棲稿》卷之十一 301
《小雲棲稿》卷之十二 317
《小雲棲稿》跋 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