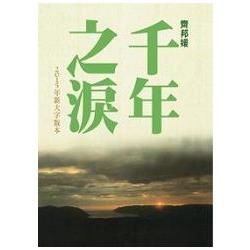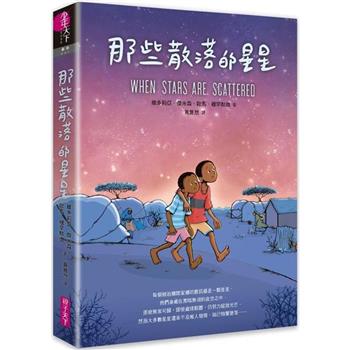我由一個間歇性的輕鬆讀者,進步到被朋友嘉許為當代臺灣文學的知音,其間積聚了重重因緣。最大的因緣是一九七三年開始編選且英譯了兩冊《中國現代文學選集》,自此以後,我開始以研究的態度,相當詳盡地研讀臺灣當代的新詩、散文、小說和評論,也陸續地寫了一些歸納的意見,想鼓舞臺灣四十多年的創作發出更響亮的聲音。收集在本書中的全是小說的評論。它們共同之處是所寫多是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人的苦難。只有〈閨怨之外〉和〈留學「生」文學〉兩篇是寫一九四九年到目前的文壇情況。
這些篇小說中特殊的時代性,中華民族特殊的困境,幾乎就全是我個人生長的背景。我出生在繼臺灣之後,被日本人佔領多年的東北。自幼年起全家即隨著一生追求拯鄉救國理想的父親漂泊過半個中國,直到定居臺灣,以此作埋骨之家鄉。我親嘗過戰爭的殘酷與恐怖,眼見過生生不息的希望、奮鬥和更多的幻滅。中國的憂患已融入了我的生命。文學對我,從來不是消遣,也不僅是課堂上的教材,它是我一生尋求事實的意義,進而尋求超越的唯一途徑。數十年間我幸得有認識西方文學的喜悅,也曾苦修過眾聲喧嘩的文學理論。卻因英譯而回歸到中國文學,不僅飽嘗遊子還鄉的歡愉,也在心靈上開拓了遼闊的領域。這些書中的人物、時代和境遇可說是這半世紀中華民族史詩的重要素材。而我自己似正在近距離看著這些有血有肉的書中人物歌哭中華民族的共同苦難,並試著找出這特殊的時代性和種族苦難的意義和希望。
泰恩(Hiooolyte Taine, 1828-1893)由法國人的觀點寫《英國文學史》,他說要藉一個豐富和完整的文學生長史分析時代性與種族性與文學的關係。在他之前,在他之後,西方文學理論發展出許多不同的流派,忙煞學院中人。但泰恩所持的文學三要素︱時代、民族、環境︱在重要的文學作品中仍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凡能傳世的作品都或隱或顯地具有這三要素,進而以藝術的創新方式衝破一時一地的局限。本書中所評介的小說能超脫所謂的「抗戰八股」、「反共八股」而不被時間淘汰,因為它們各以獨特的藝術風格,描繪出那個時代的面貌,有雄渾,有優美,有細膩……各擅勝場。能吸引住讀者注意力,讓人肯將數百頁讀完的,是它們的文字魅力。這種魅力來自作者力透紙背的感情。作者不僅有故事要講,還有他生命中一些重要的訊息要傳遞,有珍藏的情愫要傾訴……這種誠摯如此強烈,所以寫出的文字就充滿了抒情性。這些小說,大多數都可以稱之為抒情詩體小說。我認為這種小說的藝術形式和內涵都是極為珍貴的。陳紀瀅的《荻村傳》,《旋風》中的方鎮,《秧歌》中的上海近郊村莊,《未央歌》中的昆明,《蓮漪表妹》的北平和延安,《荒原》中的淮河平原,《城南舊事》中古城溫馨的一隅,《寒夜三部曲》中的蕃仔林……因文字的神奇力量,不受劇烈世變的沖激,向後世見證了一個他們所不認識的中國。
我不能說全然客觀冷靜地評論了這幾篇小說,因為他們曾深深地感動了我。英國詩人奧登說他無法客觀地評估哈代的成就,因為他曾經強烈地愛上了他的詩。讀文學作品的感動總引發我許多聯想:今昔之感,理想與現實差距之感,悲憤昇華為悲憫的智慧,和對人類前途的憂慮等等。這些蜂擁而至的聯想成了我評論的骨血,也助我衝出了各種理論的藩籬。這種純屬讀者反應的書評,古往今來,共鳴不少。《杜詩鏡銓》引王嗣奭評《無家別》說:「目擊成詩,遂下千年之淚」,也是我常有的感懷。杜甫此詩吟成至今,早逾千年,而中華民族仍在自掘的泥淖中啼飢號寒。此淚何日能止?
對於出書,我始終抱著虔敬的心情。一直希望能周全些,多評介幾本同樣重要的書,但個人的力量究屬有限,只有日後繼續努力。感謝隱地多年來溫文爾雅的鼓勵和無言的催促。在我蹉跎多年之後,文學評論書籍在今日書市只能靠強韌的生命力才能生存。對隱地出版文學書的理想和勇氣,我在感謝之外,有更多的敬意。
書後所附書目是鐘麗慧小姐費時費力所成,有了這份書目,這本論集對讀者會更多一些參考的價值。謝謝麗慧。感謝楊宗潤先生耐心的整理和修訂,使這些原來散載於報章雜誌的文章,在此以文字體例統一的面貌問世。
遲遲出書也有一些好處,既不必悔少作,又沒有太多重複自己的機會。人活著留些未竟的心願也好。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千年之淚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38 |
文學作品 |
$ 246 |
中文書 |
$ 246 |
現代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千年之淚
齊邦媛教授以研究的態度,發抒今昔之感、理想與現實差距之感、對人類前途的瞻望與憂慮,以鼓舞臺灣的創作者,希望他們發出更響亮的聲音。雖然本書評論的都是多年前的小說集,但好的小說可以打破時代的藩籬,帶給新一代不同的視野與想像。讀小說有助於認識人性,而讀這本文學評論,更使我們洞察人生。
作者簡介:
齊邦媛,一九二四年生,遼寧鐵嶺人,國立武漢大學外文系畢業,一九四七年來臺灣。一九六八年美國印地安那大學研究。曾任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助教、國立中興大學外文系主任。一九八八年從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任內退休,受聘為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名譽教授。曾任美國聖瑪麗學院、舊金山加州大學訪問教授,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客座教授,中華民國筆會英文專刊(The Chinese Pen)總編輯。編有《中國現代文學選集》詩、散文、小說卷三冊,《吳魯芹散文選》,《中英對照讀臺灣小說》,《最後的黃埔》,並主編《中國現代文學選集》英譯本上、下冊,《中華現代文學大系》小說卷五冊,另有英文評論譯述多種。著有:
《千年之淚》,一九九○年七月,三十二開,二二四頁,爾雅出版社印行。
《千年之淚》(補增大字版),二○一五年七月,二十五開,二七二頁,爾雅出版社印行。
《霧漸漸散的時候—臺灣文學五十年》,一九九八年十月,三十二開,三九六頁,九歌出版社。(本書版權到期,已由作者收回,即將由爾雅出版社重新排印發行)。
《一生中的一天》(散文),二○○四年五月,二十五開,二七二頁,爾雅出版社。
《巨流河》,二○○九年七月,二十五開軟皮精裝,六○一頁,天下遠見出版公司。
《洄瀾—相逢巨流河》,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五開軟皮精裝,三九二頁,遠見天下出版公司。
TOP
作者序
我由一個間歇性的輕鬆讀者,進步到被朋友嘉許為當代臺灣文學的知音,其間積聚了重重因緣。最大的因緣是一九七三年開始編選且英譯了兩冊《中國現代文學選集》,自此以後,我開始以研究的態度,相當詳盡地研讀臺灣當代的新詩、散文、小說和評論,也陸續地寫了一些歸納的意見,想鼓舞臺灣四十多年的創作發出更響亮的聲音。收集在本書中的全是小說的評論。它們共同之處是所寫多是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人的苦難。只有〈閨怨之外〉和〈留學「生」文學〉兩篇是寫一九四九年到目前的文壇情況。
這些篇小說中特殊的時代性,中華民族特殊的困境,幾乎...
這些篇小說中特殊的時代性,中華民族特殊的困境,幾乎...
»看全部
TOP
目錄
千年之淚
│當代臺灣小說論集
自序五
時代的聲音一三
千年之淚四五
與時代若即若離的《未央歌》六九
烽火邊緣的青春七九
︱潘人木《蓮漪表妹》
旋風中的繡花鞋九七
︱姜貴《旋風》
震撼山野的哀痛一 九
︱司馬中原《荒原》
轎走出《狂風沙》一二五
超越悲歡的童年一三七
︱林海音《城南舊事》
閨怨之外一四九
︱以實力論臺灣女作家的小說
留學「生」文學一九三
︱由非常心到平常心
人性尊嚴與天地不仁二二七
︱李喬「寒夜三部曲」
關於作者二五三
齊邦媛紀事二五五
│當代臺灣小說論集
自序五
時代的聲音一三
千年之淚四五
與時代若即若離的《未央歌》六九
烽火邊緣的青春七九
︱潘人木《蓮漪表妹》
旋風中的繡花鞋九七
︱姜貴《旋風》
震撼山野的哀痛一 九
︱司馬中原《荒原》
轎走出《狂風沙》一二五
超越悲歡的童年一三七
︱林海音《城南舊事》
閨怨之外一四九
︱以實力論臺灣女作家的小說
留學「生」文學一九三
︱由非常心到平常心
人性尊嚴與天地不仁二二七
︱李喬「寒夜三部曲」
關於作者二五三
齊邦媛紀事二五五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齊邦媛
- 出版社: 爾雅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7-20 ISBN/ISSN:978957639590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72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華文文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