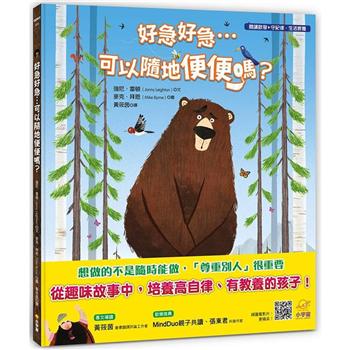暗戀的你、失戀的你、悲傷的你、幸福的你……
這本書,送給渴望被擁抱的你!
市川拓司繼《現在,很想見你》後,純度最高的「深愛三部曲」!
如果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小宇宙,
那麼,在我雙手環起的這個微小空間裡,
位於中心的妳,便是那無限大的存在……
可以這麼說嗎?
妳和我,是這個星球上獨一無二的組合。
或許,從我降臨這世界的那一剎那,妳就已經陪在我身旁了。
我的記憶裡充滿了妳的身影,呼吸中吞吐著妳的味道,即使妳只是安靜笑著,在只有我們兩人的小宇宙裡,卻是如此閃閃發亮。
因為圍繞著妳,我的一切一切才有了意義。
這樣的妳,竟然對我說:「離開我吧!我要還你自由……」
妳仍是安靜笑著,然而在妳眼裡,我卻讀不到一絲光亮。
離開了妳,我怎麼會自由呢?
離開了妳,我只會感到寂寞。
如果我真的離開了妳,那麼妳永遠都不會知道,遇見妳,對我來說有多重要。
可以這麼說嗎?
就算時光可以倒轉,我還是會再一次選擇,伸出雙手,緊緊擁抱妳……
作者簡介:
市川拓司Ichikawa Takuji
一九六二年生於東京,獨協大學經濟系畢業。天秤座,A型。
離開出版社的工作後,隨即騎著機車環遊日本一周,從此時開始寫小說。一九九七年開始在網路上發表小說作品,二○○二年以《Separation》正式出道。另著有《現在,很想見你》、《戀愛寫真》、《請你記得喔──阿格衣布星的故事》、《直到約定的那一天》、《如果全世界都在下雨》等。其中,《Separation》在網路上發表時,曾擁有高達十二萬的讀者,後來被改編拍成連續劇『14個月』;《現在,很想見你》更躋身二○○四年日本十大暢銷書,銷售超過一百三十萬冊,改拍成電影和電視劇亦大獲好評,市川的作品也從日本文壇到影壇掀起一股強大的純愛風潮,延燒至今。
文體深受約翰.厄文、符傲思、伊恩.麥克尤恩的影響。從小愛讀科幻小說,成為往後小說靈感的泉源,對於英美愛情電影,也十分喜愛。
一個月至少看五本書(不包含漫畫),但最愛的還是漫畫,欣賞的漫畫家有松本零士、內田善美和岩館真理子等,目前漫畫藏書已超過一千本。
譯者簡介:
王蘊潔
日本求學期間,對日本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進入寄宿家庭後,藉由廣泛閱讀和旅行,對日本的人文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得以在目前近十年的翻譯生涯中,盡可能呈現「原味」的日本。曾經翻譯的小說數量已經超過年齡,直逼體重,希望在有生之年可以超越身高。
曾經譯有《現在,很想見你》、《龍眠》、《白色巨塔(中)》和《博士熱愛的算式》、《14個月》、《分手後的寧靜午後》等。
個人部落格:綿羊的譯心譯意 http://blog.pixnet.net/translation
章節試閱
<我的手是為了妳存在>
在我最初的記憶中,已經有她的身影。聰美比我早出生三個月,從我降臨這個世界的那一剎那,她就已經陪在我身旁。
我母親和聰美的母親是閨中密友。雖然她們來自不同的地方,但來到這個城市後,親如姊妹,直到其中一方離開人世,始終情同手足。
她們具有相同的背景,都是外地農家的女兒,帶著模糊的夢想和明確的目的(也就是為了工作)來到這個城市。她們來到了這個城市的中心,或者說,來到象徵這個城市的大紡織工廠上班,在單身女子宿舍認識了對方。
雖然我覺得她們不需要像到這個地步,但她們幾乎同時生下了沒有父親的孩子。不,這樣的描述不夠精確,她們並不是處女懷孕,只是生下的孩子在法律上沒有父親。當時生下的,就是聰美和我。
開始懂事後,我們曾經懷疑:
「我們的父親是不是同一個人?我們是不是同父異母的姊弟?」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的母親斬釘截鐵地否認了。
「不是。」我的母親說。
「我們喜歡的男人完全是不同的類型。」
「不過,我們對男人的眼光都很差,這點倒是很像。」聰美的母親說道。
「你們在這個國家,應該有不少同父異母的兄弟姊妹,但你們兩個人絕對不是。」
我和聰美互看一眼,用力眨了眨眼睛。或許認為這樣會對我們的教育產生不良影響吧,母親沒有忘記補充一句:
「當然,他們也有優點。他們都很溫柔體貼、俊俏帥氣,否則我們怎麼可能喜歡他們。」
兩個年輕女孩礙於規定不得不搬離宿舍後,開始在廉價公寓裡一起生活。那是兩房的小公寓,她們把寶寶託給願意收零歲幼兒的私人託兒所,和之前一樣,繼續在工廠上班。在不斷有年輕單身女子從外地湧入的這個城市裡,和她們境遇相同的女人並不在少數。
再聊回我最初的記憶。
我在拉著厚實窗簾的昏暗房間內看電視,我很清楚,那是白天的事。室內的光線很微弱,我的內心充滿不安,彷彿置身夜晚的森林。突然,指尖感受到柔軟的觸感,我的視線順著自己的手臂望去,在微弱的光線中,看到一張白皙的臉。她正在對我微笑。看到她溫柔的眼神,我頓時備感幸福,不安隨即消失,平靜隨之而來。「博。」她呼喚著我的名字,聽到她的呼喊,我就興奮得渾身發抖。她用力握了握我的手,似乎在告訴我:「別擔心。」我相信她,輕輕點點頭,再度將視線移回電視──
那應該是四歲至五歲時的記憶。雖然還有更早之前的記憶,但每一份記憶就像水底的硬幣般晃動、模糊,無法順利用言語表達出來。所以,這是我最早的鮮明記憶。那是我們的母親外出工作時,我和聰美兩個人在家看電視的記憶。從那個年紀開始,我們就不再去託兒所。母親的薪水微薄,但託兒所的費用卻相反,就這麼簡單。聰美和我在沒有大人的房間內相互依偎,度過一整天。因為沒有聲音就會感到不安,所以電視一直開著。陽光灑進房間時,看不清電視畫面,因此一整天都拉上窗簾。昏暗的房間內,藍白色的光在我們的身體上閃爍舞動。我總是握著她的手,因為這樣可以消除我內心的不安。聰美雖然只比我大三個月,但當時我覺得她就像是比我大好幾歲的姊姊,代替母親保護我,她就是我白天世界的全部。
當我們上小學後,聰美和她母親搬到隔壁的房間,因為我們小孩子已經長大,四個人住兩個房間實在太擁擠了。而且那時候,我們母親的薪水稍微增加了一些。
在學校時,我也整天跟著聰美。雖然我們不同班,但每次一下課,我就衝去聰美的教室,拉著她毛衣的衣襬不放,直到下一節課開始上課為止。所以,她的毛衣或是開襟衫的右側下襬總是鬆垮垮的,而且都特別髒。
當然,這個舉動免不了遭到其他同學的嘲笑。男生的嘲笑毫不留情,女生則用巧妙的方式傷害我的自尊心。這令我感到痛苦不已,曾經暗自發誓要獨立,然而,要在沒有聰美陪伴的情況下度過一天,實在比登天還難。因為我的關係,聰美無法交到好朋友,在學校也遭到孤立。
雖然是我一味的依賴,但聰美並沒有露出絲毫厭惡之色。那時候,她比我高,心智也比我更成熟,因此很自然地扮演保護我的角色。
「對不起。」這句話成為我的口頭禪。
「你不必放在心上,」聰美每次都這麼對我說:「因為保護你是我的責任。」
「真的嗎?」
「對,所以別擔心,我會一直保護你。」
這句話好像是終身保證的合約般令我感到安心。當時,我的思考能力和食蟻獸差不多,絲毫沒有洞察未來的能力。我只是茫然地以為,那樣的生活會永遠持續到天荒地老。不,我甚至沒有想到這一點。總之,我只以為明天和今天差不多,明天的明天也將是平淡無奇的一天。我太遲鈍,完全沒有考慮到自己的成長,或是環境會隨著時間發生改變這些事,所以她的這番話令我欣喜若狂。因為我覺得我太脆弱,這個世界太嚴酷,如果沒有她,我將會立刻被撕得粉身碎骨。
我和聰美靠心靈的臍帶結合在一起。那不是紅色的細線,而是把我綁在這個世界邊緣的結實登山繩。
十一歲的夏天終於來了。
七月,第一學期末極為炎熱的這一天,成為區分以前和往後日子的分界線。
還記得那是第四節課快要結束的時候,我從教室窗戶看到一輛救護車駛進校園。其他同學聽到警笛聲,開始心神不寧,甚至有人特地走到窗邊看熱鬧。我們的班導師,一位上了年紀的男老師也忘了上課,手拿著課本,目不轉睛地看著學校中庭。我們的教室在二樓,可以清楚看到所有的情況。救護車一停在正門旁,警笛聲就停止了。救護員打開後方的車門,拉出擔架,兩個人抬著擔架消失在校舍。幾秒鐘後,教室的門突然打開了,包括我在內的大部分學生都忘記了時間上的矛盾,以為是救護員走進我們教室。所有人都倒抽了一口氣,教室內的空氣好像也變得稀薄了。
然而,站在門口的是一位年輕的女老師,她是聰美的導師。她向愣在講台上的老師點頭示意後,環視教室內,視線立刻停在我的臉上。
「田澤,你可不可以跟我來一下?」
我戰戰兢兢地點頭,挪開椅子站了起來,走到老師面前。她小聲地和我們班導師嘀咕了幾句,不知道說了什麼,然後用眼神示意我走去教室外。女老師和我一起走在走廊時說:
「聰美的身體不舒服,剛才叫了救護車,她很不安,一直叫你的名字,所以,你可以陪她嗎?」
「好。」我點點頭。那時候,我還沒有發現事情有多麼嚴重,還不知道被救護車送去醫院是多麼嚴重的狀況。
我走下樓梯,在正門的鞋櫃前脫下了室內鞋,換上運動鞋。女老師在我身後輕輕推著我走向救護車,我從後門坐進車內,女老師也一起上了車。
聰美已經在車上了。她戴著氧氣面罩,救護員正在幫她量血壓。她看到我,小聲地叫了一聲:「博……」她的臉色蒼白得嚇人,簡直不像是聰美。我坐在她身旁問:「妳怎麼了?」「有點……」她回答說,似乎很難過。
「有點不舒服……」
我點點頭,用手摸了摸她的額頭,發現好像陰暗處的水泥地那樣冰冷。她額頭上冒出的冷汗更加冰冷。
救護車發動了,車身用力搖晃了一下,聰美的臉痛苦地扭曲著。警笛聲震耳欲聾,簡直就像在我腦袋裡轟隆作響。
醫院應該很遠,過了好久好久仍然沒有到。聰美的情況越來越惡化,她的臉色漸漸發黑,呼吸也變得急促,宛如溺入空氣之中。救護員也顯得手忙腳亂,他們用聽診器尋找聰美的呼吸和心跳,不斷地確認連在她身上的那些管子另一端螢幕上的數字。比起聰美的狀態,救護員臉上的慌張神情更令我感到恐懼,好像發生了什麼很糟糕的事。此刻我感覺大地彷彿狠狠地傾斜,把承載著我們的整個世界都滑向某個地方。
聰美的情況越來越不妙,已經面無人色。她似乎十分痛苦,喉嚨發出「咻、咻」的異樣聲音。她用力閉上眼睛,淚水順著眼角滑落下來。
「聰美,聰美。」我情不自禁地呼喚著她的名字,我並不期望她會回答我,只想把她的意識叫回來。我擔心聰美會去一個遙遠的世界。
她突然張開眼睛,用含淚的雙眼凝望著我。當我們視線交會的那一剎那,我立刻知道我該做什麼。我把身體靠了過去,把雙手放在她胸口上。她立刻發出「呼∼」的聲音,用力呼吸了一口氣。接著,又用力呼吸了好幾次,順暢的呼吸完全沒有任何阻礙。
她的臉上漸漸有了血色,車內所有的人頓時鬆了一口氣。「沒事了。」有人說道。
「博,謝謝你。」
聰美呼吸急促地說,臉上露出淡淡的微笑。
就這樣,我們就無法分開了。我們相互需要,也成為彼此不可取代的人。
聰美去醫院檢查過許多次,沒有醫生可以做出明確的診斷。每個醫生都說出好幾個疾病的名字,但每個醫生都對自己的看法缺乏自信。那年夏天,聰美發作了三次,嘗試用過的每一種藥物都沒有效果。在最後的緊要關頭,只有靠我觸摸她,才能改善她的發作。其他人當然也曾經試過相同的方法,卻沒有明顯的效果。
在多次發作後,我漸漸掌握了訣竅。
直接用手觸碰她的肌膚,比隔著衣服更有效果;比起身體前側,把手放在她的背後,尤其是肩胛骨下方的位置時,她的恢復速度最快。而且,沿著肩胛骨邊緣慢慢滑動,又比手放著靜止不動更有效。沒有人能夠告訴我,如果她發作時我不在身旁,到底會發生怎樣的結果。好幾位醫生都只對我說:「既然只有你能夠治好她的發作,那你最好和她寸步不離。」他們認為聰美的疾病是某種心理上的原因所造成。
即使不需要醫生特別叮嚀,我也無意離開聰美。這好像在說,一切必須維持原來的樣子,可以名正言順地和她形影不離這件事反而令我竊喜。
之後,聰美每隔幾個月就會發作一次,也漸漸發現身體過度疲勞時容易發作,所以她盡量避免勞累,上體育課時,都在一旁看,晚上也早早就上床睡覺了。一旦發作,我立刻衝到她身旁。在學校發作時,她都在保健室等我。當我趕去保健室時,老師就會把我帶到她躺著的床前。
拉開簾子,我叫著她的名字:「聰美。」側躺的她抬起頭對我說:「對不起。」類似的情況發生了很多次。我拉起聰美身上的襯衫或是毛衣,把手放在她骨感的後背,用手指確認肋骨和脊椎的位置後,尋找那個不起眼的定點。我的手沿著肩胛骨邊緣摸到後,輕輕地開始撫摸。然後,她會重重地吐出一口氣,溫暖的血液再度開始在她冰冷的肌膚下流動。
「為什麼?」她曾經問我,「那次你為什麼會知道要摸我?」
「不知道。」我回答說:「只是有這種感覺,覺得應該這麼做。」
「好厲害,」她說:「好像神仙一樣。」
我當然不是神仙,有不少人聽到我們的事後,來上門拜託我撫摸他們的身體,最後無功而返,病人依然是病人,他們的疾病也完全不見好轉。所以,我認為自己就像一把鑰匙,我是鑰匙,而聰美是鎖。在這個星球上,我們是唯一的組合,是獨一無二、無可取代的關係。
不久之後,我們從國小畢業,一起進入國中。那一年夏天,我的身高終於超越了她。在第二年春天時,我已經比聰美高超過五公分了。
我不再像以前一樣整天圍著她打轉。我們又被分在不同的班級,就算下課,我也可以獨自忍耐五分鐘,我會在同學的吵鬧聲中看從家裡帶來的文庫本小說。即使屏住呼吸五分鐘,人也不會死。總之,在上課鐘聲響起之前必須忍耐。而且,有個男同學開始向我搭話。他很文靜,也喜歡看書,我們成了好朋友。
回家後,我和聰美還是如影隨形。在我們的母親下班之前,她都會留在我家。那時候,經濟景氣正處於顛峰時期,總有做不完的工作,無論我母親還是聰美的母親,都希望在我們讀高中前多賺點錢,所以每天都加班到很晚。我和聰美放學後,先去附近的超市買食材,她負責煮四人份的晚餐。如果我們的母親六點還沒回家,我們兩個人就會先吃晚餐。電視整天都開著,這樣感覺比較不寂寞。
她偶爾也會在這種時候發作。那是一年級第二學期期末考後一個寒冷的日子,天空好像隨時會飄雪。那一陣子為了應付考試,她太疲勞了,也可能是放學回家途中吹到了冷風。
那天的晚餐是聰美親手做的可樂餅,因為太好吃了,我連續吃了好幾個。聰美擔心地說:「你不要吃光,留幾個給媽媽啦!」吃完飯,她在廚房洗碗時發作了。
「博……」她努力從喉嚨裡擠出聲音叫著我的名字,「又來了。」
「嗯。」
我點點頭,起身走去廚房,從身後扶住她。我抓著她的雙臂,把她帶回房間。她的呼吸越來越急促,我讓她輕輕坐在榻榻米上,她像胎兒般背朝上縮成一團,露出的頸子宛如被漂白過一樣毫無血色,然後,漸漸變成了黑紫色。這已經是相當危險的狀態了。
我毫不猶豫地拉起她的白色運動衣,她在裡面穿了一件紅豆色的T恤。看到這黯淡的紅色,我忍不住退縮,內心一陣翻騰,我不禁停下了手。
在我猶豫的這幾秒鐘之中,她的症狀越來越嚴重。她的生命靠著只能勉強穿過針孔、氣若游絲般的呼吸維繫著。我下定決心,翻起她的T恤。她後背的肌膚已經變成了危險的顏色,我把手放在她宛如無機物般冰冷的背上,輕輕地沿著皮膚下的骨骼尋找最有效的那一點。她的背很單薄,很容易摸到她的骨骼。我把手指放在肩胛骨和脊椎之間,輕輕往上滑動。
「啊∼」她吐出一口氣。
「有效嗎?」我問她。
聰美微微點頭,當我探頭張望她的表情時,看到她微微隆起的乳房,慌忙把視線移開。
不起眼的隆起應該是這幾個月才出現的變化,所以我以前從來沒有注意到。
她並沒有注意到我的新發現,只專注於已經恢復的呼吸。電視中的主播正在播報某個國家有大象踩死人的新聞,據說該地區至今為止,已經有超過兩百人被大象踩死。我再度將視線移回她的胸前,隆起的部分就在好幾條從背後向胸前延伸的肋骨拱形前端。她的膚色已經恢復了紅潤。每次當我撫摸她的背時,她的肌膚就會慢慢溫暖,微微滲汗。然而,她嬌小的乳房仍然十分潔白,發出冷冽的光澤。
好像有什麼東西爬上我的脊背,我忍不住微微抖動了一下。
「怎麼了?」聰美轉頭看著我,我慌忙移開視線,可能被她察覺了。
「謝謝,我已經沒問題了。」
說著,她雙手抱在胸前坐了起來,背對著我把T恤和運動衣的衣襬拉好。她重重地吐了一口氣,身體靠在牆上。我也坐在她身旁。
「我覺得,」她開口說道:「每次你摸我的背,我就好像再一次誕生在這個世界。」
「是嗎?」
「對,小嬰兒在出生前不是也沒有呼吸嗎?我現在也有那種感覺。」
「我不太清楚。」
「嗯,我想也是,那是一種很特別的感覺。」
她把雙手放在從牛仔裙下伸出的纖細雙腿上。
「謝謝你。」聰美輕聲呢喃,「多虧了你,我才能獲得重生。全新的世界,全新的我。」
「我並沒有做什麼了不起的事。」
「不過,我真的很感謝你,雖然我無以為報。」
「嗯。」
「但是,如果……」
說到這裡,聰美突然陷入沉默。不自然的沉默讓我忍不住探頭看她的臉,發現她的臉頰染上了紅暈。難道是發作的後遺症嗎?
「什麼?」我問。
「不,算了。」她搖頭回答說:「算了。」她又重複了一遍,然後再度抬起頭,注視著我的眼睛。
「總有一天……」她似乎鼓起了勇氣。
「嗯?」
然而,最後她還是沒有把話說完。她的氣勢突然弱了下來,話語失速,沉入她的肺底……
<我的手是為了妳存在>在我最初的記憶中,已經有她的身影。聰美比我早出生三個月,從我降臨這個世界的那一剎那,她就已經陪在我身旁。我母親和聰美的母親是閨中密友。雖然她們來自不同的地方,但來到這個城市後,親如姊妹,直到其中一方離開人世,始終情同手足。她們具有相同的背景,都是外地農家的女兒,帶著模糊的夢想和明確的目的(也就是為了工作)來到這個城市。她們來到了這個城市的中心,或者說,來到象徵這個城市的大紡織工廠上班,在單身女子宿舍認識了對方。雖然我覺得她們不需要像到這個地步,但她們幾乎同時生下了沒有父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