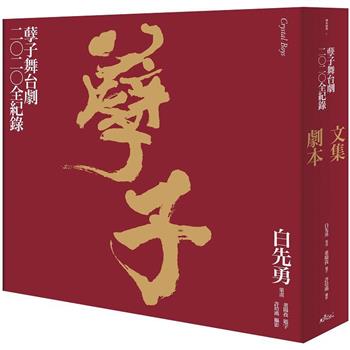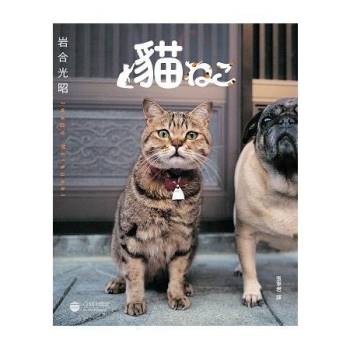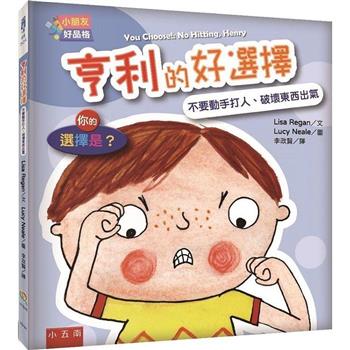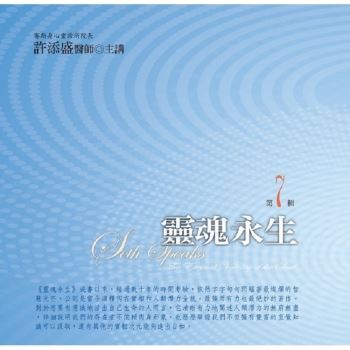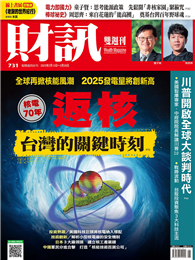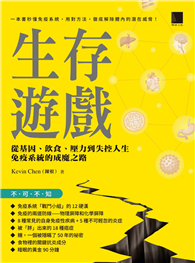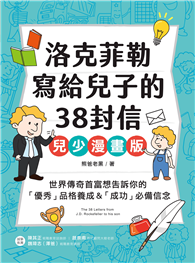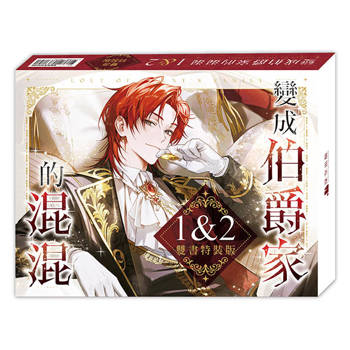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儒教的聖域的圖書 |
 |
儒教的聖域 作者:黃進興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7-15 語言:繁體中文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儒教的聖域
內容簡介
本書是黃進興教授以儒教為主題的重要研究成果的結集,為宗教文化史研究的又一力作。全書由五篇文章組成,主題集中,層次明瞭,邏輯清晰,著重聚焦儒教的聖域——孔廟,進而探究儒教的宗教性格,挖掘其濃厚的政治與文化意涵。通過作者深入淺出的分析,孔廟祀典與帝國禮制的動態整合過程得以勾勒,儒教豐富的文化面相也得以呈現。對於清末民初以來,廣為學界關注的儒家或儒教是否為宗教的問題,作者也旗幟鮮明的給出了自己的答案。除了具體問題的研究,本書還包含了作者在研究理路上的反思,尤其是對近年來孔廟文化研究的基本觀念和進路進行了檢討,可謂發人深省。帶著一份對傳統文化「同情的瞭解」探索孔廟,無疑是打開儒教聖域之門的一把鑰匙。閱讀本書,正是從作者手中領過這把鑰匙,並隨之去解開儒教的宗教之謎。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黃進興
一九七三年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一九七五年獲該校碩士學位,一九八三年取得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二〇〇八年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著有《哈佛瑣記》、《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聖賢與聖徒》、《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一個批判性的探討》、《從理學到倫理學:清末民初道德意識的轉化》等,其著作或有英文、日文、韓文等譯本。英文著作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刊行。
黃進興
一九七三年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一九七五年獲該校碩士學位,一九八三年取得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二〇〇八年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著有《哈佛瑣記》、《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聖賢與聖徒》、《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一個批判性的探討》、《從理學到倫理學:清末民初道德意識的轉化》等,其著作或有英文、日文、韓文等譯本。英文著作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刊行。
序
自序
上世紀著名的神學和宗教史家伊里亞德(Mircea Eliade, 1907-1986),於探討「宗教」的本質,曾特別關注神聖的空間、時間、神話等構成因素,而受到學界的注目。顯然,孔廟便是儒教的聖域,但我研究孔廟純出偶然,與伊里亞德的學說並無關聯。
初始,與友人懵懵懂懂參訪臺北孔廟,無意間卻打開了聖殿之旅。好奇心的驅使,讓我的孔廟探索,變成心靈的朝拜之旅(pilgrimage)。孔廟在歷史上曾遍佈東亞世界,中國之外,尚包括朝鮮、日本、琉球與臺灣,甚至南抵越南為止。雖說各地的孔廟另有它獨特的性格,但此一跨域的共通文化現象的確值得注意;它不僅是一個耀眼的宗教聖域,還具有濃厚的政治與文化意涵。
孔廟作為儒教的聖域,乃無庸置疑;只要略加一窺史料的記載,便了然於心。試舉一例,以概其餘:明弘治二年(一四八九年)所撰的〈重建清真寺記〉即明確地傳達了此一訊息。它言道:
愚惟三教,各有殿宇,尊崇其主。在儒則有「大成殿」,尊崇孔子。在釋則有「聖容殿」,尊崇尼牟(照原碑)。在道則有「玉皇殿」,尊崇三清。在清真,則有「一賜樂業殿」,尊崇皇天。
「大成殿」位居孔廟的主殿,其得與釋、道、猶太教諸殿宇相提並論,可見作為儒教的聖域,孔廟的宗教象徵樣樣俱全,毫不遜色。是故,聚焦孔廟以彰顯儒教的宗教性格,便成為我的研究重點。
拙作首選的論文,係新近刊行的〈象徵的擴張──孔廟祀典與帝國禮制〉。該文從宏觀的角度,比較完整地勾勒出孔廟祀典與帝國禮制的整合過程,盼能涵蓋較豐富的文化面相。之前,個人對孔廟的研究著重其緣起,尤其是儒生和人君的互動。本文則將焦點放在制度層面,特別聚焦孔廟制度在歷史上變易的動態過程。誠然,孔廟祭典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各有出入,但整體而言,則與帝國禮制的運作趨於一致。若說孔廟祭典是項「象徵」,那必然相當於英文語詞裏大寫的「Symbol」或複數的「symbols」,其緣由則是孔廟祭祀在中國綿延長達兩千多年,不止堆積並且衍生了許多附加的意義和功能。尤其在帝國中晚期,上至朝廷、下迄地方行政的運作,皆可見證孔廟祭典的擴張與提升。作為國家宗教的聖域,孔廟亦充分地顯現出官方壟斷與排他的特性。
次之,〈學術與信仰—論孔廟從祀制與儒家道統意識〉一文,則是由孔廟「從祀制」的運作來偵測儒家「道統意識」的具形化。牽涉其中的,當然是儒家主流思潮的呈現,但政治、社會力量的介入,亦不可忽視。
第三篇〈《野叟曝言》與孔廟文化〉,則是剖析儒家道統思想如何影響了該書作者的學術觀點及創作的取捨。換言之,孔廟的知識可以充作文學創作的資源。
第四篇〈清末民初儒教的「去宗教化」〉,旨在闡述儒教原是中華帝國時期的國家宗教,然而在清末民初卻一步步崩解為「非宗教」的過程。此一歷程適可佐證儒家或儒教是否為宗教,基本上乃是歷史的問題,而非哲學的析論。
末篇〈研究儒教的反思〉,則是檢討個人近年來研究孔廟文化的基本觀點和進路,可與第四篇合觀並讀。
總之,近年來孔廟研究的熱度,不敢說「蔚為風潮」,但絕對稱得上是「方興未艾」。國際上已刊行的論文與專著,不在少數。雖然個人研究孔廟起步稍早,但今日無論在深度與廣度都已見到他人清新可喜的成果,不由得萌生「道不孤,必有鄰」的喜悅。簡言之,過去二十年,個人僅專注於中國境內整體孔廟的探討,而對各地孔廟細緻的認識顯然有所不足,尤其不曾著墨跨地域、跨文化的比較研究,這些都尚待他人繼續努力,以增添一份對傳統文化「同情的瞭解」。
最後,我想以這本選集紀念甫辭世的芝加哥大學余國藩教授(Anthony C. Yu, 1938-2015),藉以表達我對他的懷念,並感謝他對我研究孔廟一路走來的鼓勵和支持。我與余教授在臺北雖然只有一面之緣,但相談甚歡,日後竟成忘年之交,常透過電郵筆談。近年,他尤其不厭其煩、再三催促我動手撰寫一本英文專著,綜合之前探討孔廟的心得,俾與西方宗教史家直接對話。余教授認為我聚焦宗教「神聖空間」的手法別有特色,容與西方比較宗教學界互相參照。但個人因另有其他研究課題刻在進行,分身乏術,一時只有辜負他的好意。唯一稍可補償的是,個人攸關孔廟的研究不久將有兩大冊日譯本刊行,聊可回報他的厚望。至於撰述英文專著一事,則猶待來日的努力了,盼時時以此鞭策自己。是為序。
上世紀著名的神學和宗教史家伊里亞德(Mircea Eliade, 1907-1986),於探討「宗教」的本質,曾特別關注神聖的空間、時間、神話等構成因素,而受到學界的注目。顯然,孔廟便是儒教的聖域,但我研究孔廟純出偶然,與伊里亞德的學說並無關聯。
初始,與友人懵懵懂懂參訪臺北孔廟,無意間卻打開了聖殿之旅。好奇心的驅使,讓我的孔廟探索,變成心靈的朝拜之旅(pilgrimage)。孔廟在歷史上曾遍佈東亞世界,中國之外,尚包括朝鮮、日本、琉球與臺灣,甚至南抵越南為止。雖說各地的孔廟另有它獨特的性格,但此一跨域的共通文化現象的確值得注意;它不僅是一個耀眼的宗教聖域,還具有濃厚的政治與文化意涵。
孔廟作為儒教的聖域,乃無庸置疑;只要略加一窺史料的記載,便了然於心。試舉一例,以概其餘:明弘治二年(一四八九年)所撰的〈重建清真寺記〉即明確地傳達了此一訊息。它言道:
愚惟三教,各有殿宇,尊崇其主。在儒則有「大成殿」,尊崇孔子。在釋則有「聖容殿」,尊崇尼牟(照原碑)。在道則有「玉皇殿」,尊崇三清。在清真,則有「一賜樂業殿」,尊崇皇天。
「大成殿」位居孔廟的主殿,其得與釋、道、猶太教諸殿宇相提並論,可見作為儒教的聖域,孔廟的宗教象徵樣樣俱全,毫不遜色。是故,聚焦孔廟以彰顯儒教的宗教性格,便成為我的研究重點。
拙作首選的論文,係新近刊行的〈象徵的擴張──孔廟祀典與帝國禮制〉。該文從宏觀的角度,比較完整地勾勒出孔廟祀典與帝國禮制的整合過程,盼能涵蓋較豐富的文化面相。之前,個人對孔廟的研究著重其緣起,尤其是儒生和人君的互動。本文則將焦點放在制度層面,特別聚焦孔廟制度在歷史上變易的動態過程。誠然,孔廟祭典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各有出入,但整體而言,則與帝國禮制的運作趨於一致。若說孔廟祭典是項「象徵」,那必然相當於英文語詞裏大寫的「Symbol」或複數的「symbols」,其緣由則是孔廟祭祀在中國綿延長達兩千多年,不止堆積並且衍生了許多附加的意義和功能。尤其在帝國中晚期,上至朝廷、下迄地方行政的運作,皆可見證孔廟祭典的擴張與提升。作為國家宗教的聖域,孔廟亦充分地顯現出官方壟斷與排他的特性。
次之,〈學術與信仰—論孔廟從祀制與儒家道統意識〉一文,則是由孔廟「從祀制」的運作來偵測儒家「道統意識」的具形化。牽涉其中的,當然是儒家主流思潮的呈現,但政治、社會力量的介入,亦不可忽視。
第三篇〈《野叟曝言》與孔廟文化〉,則是剖析儒家道統思想如何影響了該書作者的學術觀點及創作的取捨。換言之,孔廟的知識可以充作文學創作的資源。
第四篇〈清末民初儒教的「去宗教化」〉,旨在闡述儒教原是中華帝國時期的國家宗教,然而在清末民初卻一步步崩解為「非宗教」的過程。此一歷程適可佐證儒家或儒教是否為宗教,基本上乃是歷史的問題,而非哲學的析論。
末篇〈研究儒教的反思〉,則是檢討個人近年來研究孔廟文化的基本觀點和進路,可與第四篇合觀並讀。
總之,近年來孔廟研究的熱度,不敢說「蔚為風潮」,但絕對稱得上是「方興未艾」。國際上已刊行的論文與專著,不在少數。雖然個人研究孔廟起步稍早,但今日無論在深度與廣度都已見到他人清新可喜的成果,不由得萌生「道不孤,必有鄰」的喜悅。簡言之,過去二十年,個人僅專注於中國境內整體孔廟的探討,而對各地孔廟細緻的認識顯然有所不足,尤其不曾著墨跨地域、跨文化的比較研究,這些都尚待他人繼續努力,以增添一份對傳統文化「同情的瞭解」。
最後,我想以這本選集紀念甫辭世的芝加哥大學余國藩教授(Anthony C. Yu, 1938-2015),藉以表達我對他的懷念,並感謝他對我研究孔廟一路走來的鼓勵和支持。我與余教授在臺北雖然只有一面之緣,但相談甚歡,日後竟成忘年之交,常透過電郵筆談。近年,他尤其不厭其煩、再三催促我動手撰寫一本英文專著,綜合之前探討孔廟的心得,俾與西方宗教史家直接對話。余教授認為我聚焦宗教「神聖空間」的手法別有特色,容與西方比較宗教學界互相參照。但個人因另有其他研究課題刻在進行,分身乏術,一時只有辜負他的好意。唯一稍可補償的是,個人攸關孔廟的研究不久將有兩大冊日譯本刊行,聊可回報他的厚望。至於撰述英文專著一事,則猶待來日的努力了,盼時時以此鞭策自己。是為序。
二〇一五年十月
於臺北南港
於臺北南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