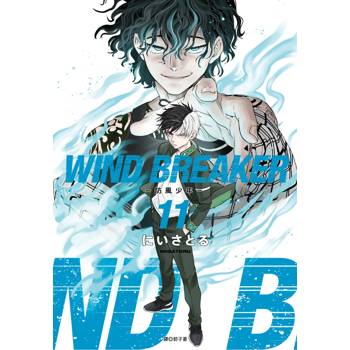原書序
羅澧銘
余少耽戲曲藝術,及長,更喜與藝人交遊,時聆菊部1 新聲,復領李謨2 雅教,耳濡目染,怱怱數十寒暑,亦既嗜之成癖矣!槧鉛之暇3,以顧曲遣有涯之生,讀李笠翁先生《閒情偶寄》4,胡翼南先生《梨園娛老集》5,心竊慕焉,不揣謭陋6,東塗西抹,發抒管見,撰《顧曲談》,刊《星島晚報》「娛樂版」,以就教於高明。猥蒙知音人士不棄,囑印單行本,因念是書在報章發表,將達三百續,當時拉雜成篇,絕無系統可言,弗若分門別類,分集刊行,大致別為「戲劇」、「歌曲」、「雜俎」三種,皆約略溯其源流,兼考證樂器出處,以供參考。
屬於「戲劇」方面,計有:〈粵劇源流與粵曲演變〉、〈十行腳色歌喉雜談〉、〈正本齣頭及其他〉、〈新春佳節應時戲曲談〉等篇。屬於「歌曲」方面,包括「樂器」計有:〈練聲方法與問字求腔〉、〈棚面師父十三手〉、〈地道粵曲— 南音〉、〈五十年來省港著名師娘〉、〈八大曲取材及唱工的變遷〉、〈歌壇滄桑錄〉,以及〈洋琴考證與玩奏技巧〉、〈梵鈴(小提琴)拉雜談〉、〈三絃在南北樂壇的地位〉諸篇。「雜俎」方面,計有:〈大八音班的技巧與組織〉、〈廣府、潮州及外國傀儡戲〉、〈「打
真軍」與「三上吊」〉各篇。
此外選錄「顧曲散評」四篇,標題:〈祁筱英復出— 提倡唱、做、念、打、藝術〉、〈吳君麗勤有功戲有益〉、〈薛派薪傳弟子林家聲〉,區區之意,竊以為:粵劇日走下坡,消失大部分觀眾,事實具在,固不必「諱疾忌醫」。挽狂瀾於未倒,植藝苑之新葩,尤須灌輸新血,發掘後起之秀,鼓勵之,扶掖之,責無旁貸,端在我輩— 站在觀眾地位,抱持擁護粵劇之熱誠。至於「壓軸」一文〈白雪仙示範《牡丹亭》〉,蓋余尤有說焉:余撰顧曲文章,只是側重後起人才,歷向對於「紅伶」甚少吹捧。一者:紅伶聲價重,地位高,藝術優越,自是份所當為,實無吹捧之必要;相反而言,對藝術不忠實,馬虎從事以「欺台」,更要仿春秋「責備賢者」之意,率直加以批評。二者:紅伶常自恃聲價重,地位高,喜諛詞,惡忠告,認輿論殊不足重輕,甚至變本加厲,蔑視社會人士,吾人又何必浪費筆墨?吹捧紅伶唯一例外,便是態度嚴肅認真,一切以藝術為前提,博採廣諮,有超羣軼倫之表現,則吾人職責所司,豈能膠柱鼓瑟7,一概而論,抹煞事實?比年來,白雪仙致力文藝術,頗起「示範」作用,「破例」以此文殿吾書,知音士女,儻不以吾為阿其所好乎?
本書出版,悼念卅五年亡友平愷薛覺先五兄逝世一週年(十月卅一日)9,並有感於粵劇田地,日就荒蕪,後繼難得其人!薛氏生平,對戲劇電影藝術之貢獻,蔚為「一代宗師」,僉稱10「萬能泰斗」,除獻身劇藝之外,更致力社會福利慈善業,興辦「覺先平民學校」,造福失學兒童;扶植藝苑俊秀,領導八和會館,栽培「八和」子弟;以至待人接物,亦悉本至誠,仗義輕財,存終存始,只求良心之所安,絕非「沽名釣譽」
者可比。舉一個例:逝世首夕,點演其首本戲《花染狀元紅》,病魔突擊,體力不支,照劇情演出,跪地起身時,雙腳搖擺不定,同場藝員,見神色有異,連忙上前攙扶,一再受其苛斥,定要唱完最後幾句「滾花」;煞科落幕,仍不肯「入場」,必須
向觀眾「謝幕」後,才算職責完成:生具藝術天才,死亦忠於藝術,其嚴肅認真之態度,誠堪為後輩楷模。聯想所及:本屆「八和」演「大集會」,十二月九日,新馬師曾、芳艷芬合演《胡不歸》〈慰妻〉,按照往昔伶人習慣,「大集會」多演本人「首本」戲,倍見精彩,但若干年來,「新馬」最喜歡點演薛氏之「開山」戲,以表示繼承「伶王」寶座(?),有志向上,本未可厚非。如能保持嚴謹作風,吾人站在觀眾立場,得飽耳福,亦正歡迎之不暇,可惜結果完全相反!「新馬」演戲歷向「兒嬉」,永遠忘記曲本(薛氏對於所有劇本曲白,一經演出後永不訛舛刪改),不論任何家絃戶誦之名曲亦一樣「爆肚」11,是晚之「慰妻」一闋,忘記得一乾二淨,加添許多「不乾淨」口白,整個戲之氣氛為之破壞,使人越聽越氣憤。新馬更有一種「無可寬恕」之惡習慣:與芳艷芬演《紅鸞喜》一幕,因對方是「道姑」一角,新馬便「借題發揮」,大談「道友」之「光榮史」,以誇示於觀眾之前(或許已忘記「吸毒」是犯法之勾當?),偶一為之,
吾無間言,而此君習慣成自然,差不多每套劇本,稍有機會便「扯科諢」12,殊屬討厭!又如前者演《拉車被辱》,及所演其他劇本,猥褻「口白」,衝口而出,弄到輿論譁然,提倡「粵劇清潔運動」,迎頭痛擊,此風稍戢13;近者故態復萌,余忝屬輿論界一份子,決不能安於緘默。因為演劇如球賽,必須全體鼎力合作,一個「破壞份子」,可能影響全體,尤其是演對手戲之藝員。余嘗冷眼旁觀,「新馬」參加「新艷陽」,好幾次「扯科諢」,俱為芳艷芬迅速「插白」,阻止其繼續說下去。芳艷芬是盡忠藝術之戲劇工作者,當不願意受其牽累。即如〈慰妻〉一幕,因新馬之「爆肚」亦為之興致索然,缺乏精彩;反觀次夕關德興與吳君麗合演《平貴別窰》,關德興演來「認真」,連帶吳君麗亦出色當行,試想以一個「初出茅廬」之吳君麗,怎可與「高據后座」之芬艷芬相提並論?但事實上兩相比較,吳君麗確能發揮情緒,給予觀眾良好印象,理由十分顯淺:對手演出「戲假情真」,自己如設身處地,定要「迎頭趕上」耳(雖然兩人演來仍有小疵:關德興有幾句曲白,應該「催快」,頗嫌其遲慢;吳君麗之中州音「念白」,未盡純粹;不過「情緒」甚佳,所謂「戲假情真」,才是「上乘工夫」)。一得愚見,貽笑大方;百爾君子,起而教之,則幸甚!
禮記羅澧銘序於香江14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中旬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顧曲談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顧曲談
雅好戲曲,亦精通戲曲的羅澧銘,對廣東粵劇、粵樂,興趣尤深。他既觀劇聽曲,又同時評論劇曲,下筆有理有據,而且旁徵博引,寫的都是高素質而認真的戲曲評論。上世紀五十年代,羅氏在《星島晚報》連載一系列戲曲專題文章,專欄名為「顧曲談」,取「曲有誤,周郎顧」的典故,以「行家」身分撰文,寫戲曲、音樂、掌故、名伶,內容豐富。後來他整理部分連載文稿,出版了《顧曲談》。
本書以《顧曲談》初版為底本,參考羅氏在原書序文中提及的分類標準,重新校訂,並為若干字詞作簡注,方便讀者閱覽。
作者簡介:
羅澧銘(一九○三—一九六八)
筆名塘西舊侶、蘿月、憶釵生、三羅後人、禮記。廣東東莞人,香港名中醫羅鏡如之子。羅澧銘十四歲隨何恭第習古典文學,並入讀聖士提反中學,十九歲出版四六駢文小說《胭脂紅淚》,翌年從商,仍筆耕不綴,常以「憶釵生」筆名發表文章。一九二四年八月與何筱仙、黃守一等人合辦《小說星期刊》。一九二八年八月與孫壽康合辦《骨子》,刊物以消閒為主,甚受讀者歡迎。一九五六年起,羅氏以「塘西舊侶」筆名在《星島晚報》連載名作《塘西花月痕》。羅氏多才藝,曾辦報、編雜誌、撰稿、出版,一生對文字不離不棄。
朱少璋
作家,現為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高級講師、「香港文學推廣平台」主任。香港新亞研究所文學碩士、香港大學哲學碩士、香港浸會大學榮譽學士及哲學博士。國際南社學會、廣東南社學會、香港作家協會會員。公餘熱衷參與文化藝術活動,多年來從事文學研究、文學創作及中文教學,近年着手整理編訂罕見文學材料,尤致力於廣東戲曲文獻及唱詞劇本的研究。
編訂/校訂作品包括:《小蘭齋雜記》(榮獲第十屆「香港書獎」)、《香如故──南海十三郎戲曲片羽》、《薛覺先評傳》、《顧曲談》等
作者序
原書序
羅澧銘
余少耽戲曲藝術,及長,更喜與藝人交遊,時聆菊部1 新聲,復領李謨2 雅教,耳濡目染,怱怱數十寒暑,亦既嗜之成癖矣!槧鉛之暇3,以顧曲遣有涯之生,讀李笠翁先生《閒情偶寄》4,胡翼南先生《梨園娛老集》5,心竊慕焉,不揣謭陋6,東塗西抹,發抒管見,撰《顧曲談》,刊《星島晚報》「娛樂版」,以就教於高明。猥蒙知音人士不棄,囑印單行本,因念是書在報章發表,將達三百續,當時拉雜成篇,絕無系統可言,弗若分門別類,分集刊行,大致別為「戲劇」、「歌曲」、「雜俎」三種,皆約略溯其源流,兼考證樂器出處,以供參考。
屬...
羅澧銘
余少耽戲曲藝術,及長,更喜與藝人交遊,時聆菊部1 新聲,復領李謨2 雅教,耳濡目染,怱怱數十寒暑,亦既嗜之成癖矣!槧鉛之暇3,以顧曲遣有涯之生,讀李笠翁先生《閒情偶寄》4,胡翼南先生《梨園娛老集》5,心竊慕焉,不揣謭陋6,東塗西抹,發抒管見,撰《顧曲談》,刊《星島晚報》「娛樂版」,以就教於高明。猥蒙知音人士不棄,囑印單行本,因念是書在報章發表,將達三百續,當時拉雜成篇,絕無系統可言,弗若分門別類,分集刊行,大致別為「戲劇」、「歌曲」、「雜俎」三種,皆約略溯其源流,兼考證樂器出處,以供參考。
屬...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目 錄
重刊《顧曲談》二三事 朱少璋 / i
原書序 羅澧銘 / xii
第一輯:歷史.源流
粵劇源流與粵曲演變 / 003
十行腳色歌喉雜談 / 006
正本齣頭及其他 / 010
新春佳節應時戲曲談 / 018
第二輯:歌曲.音樂
練聲方法與問字求腔 / 027
棚面師父十三手 / 030
地道粵曲—南音 / 032
五十年來省港著名師娘 / 037
八大曲取材及唱工的變遷 / 042
歌壇滄桑錄 / 059
洋琴考證與玩奏技巧 / 062
梵鈴(小提琴)拉雜談 / 069
三絃在南北樂壇的地位 / 076
第三輯:雜錄.散記
大八音班的技巧與組織 / 083
廣府、潮州及外國...
重刊《顧曲談》二三事 朱少璋 / i
原書序 羅澧銘 / xii
第一輯:歷史.源流
粵劇源流與粵曲演變 / 003
十行腳色歌喉雜談 / 006
正本齣頭及其他 / 010
新春佳節應時戲曲談 / 018
第二輯:歌曲.音樂
練聲方法與問字求腔 / 027
棚面師父十三手 / 030
地道粵曲—南音 / 032
五十年來省港著名師娘 / 037
八大曲取材及唱工的變遷 / 042
歌壇滄桑錄 / 059
洋琴考證與玩奏技巧 / 062
梵鈴(小提琴)拉雜談 / 069
三絃在南北樂壇的地位 / 076
第三輯:雜錄.散記
大八音班的技巧與組織 / 083
廣府、潮州及外國...
顯示全部內容
顧曲談 相關搜尋
走進宋畫,10-13世紀的中國文藝復興(南宋篇):在江南煙雨微茫中若隱若現,越過唐人直奔魏晉的宋人美學I NEED ART:關於我,Henn Kim的成年記述
傳承與開創,從臺灣到亞太—亞洲作曲家聯盟口述史訪談集(國際版)
神聖黑色的魔力:徹底改變人類文明、藝術、歷史的黑色故事
說故事的古典音樂導聆【古典樂派】:鋼琴家帶你入門200首名曲,聽懂巴哈到貝多芬的光明與黑暗
人像繪畫聖經:從不像畫到像,再打破框架!幫你練好基礎、開創風格的人像技法全書 ( 素描 / 插畫 / 電繪全適用)
現代藝術的拓路人:塞尚
韓秀帶你認識西洋藝術家(卡拉瓦喬、埃爾‧格雷考、杜勒、李奧納多‧達‧文西、林布蘭、塞尚)
走進宋畫,10-13世紀的中國文藝復興(北宋篇):建立在皇家畫院以外,由士人畫以至於文人畫擔待起來的北宋繪畫藝術
一出手就是名場面:從《樂來越愛你》到《寄生上流》,11大類型片背後的影像拍攝密技&布局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