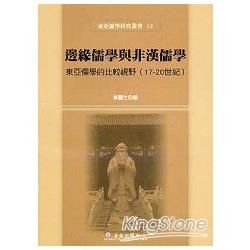引言∕黃麗生
壹
千百年來,隨著中國歷史的發展與變遷,儒學由中土傳佈於中國周邊的日、韓、琉球等國,對當地社會文化產生深遠影響;亦由內地流傳至蒙古、臺灣等邊區,近代以降更由華人移民傳至海外僑地。我們或可以「邊緣儒學」和「非漢儒學」來形容儒學在中原邊緣和域外地區的傳播及其總體效應。相對被視為核心∕主流的中原∕漢人的儒學,這些邊緣或非漢地區的儒學,長期未受到學界足夠的重視。事實上,正由於其所具「邊緣性」的獨特意義,恰可提供今人有別於過去的視角,掘發儒學研究新的問題意識與詮釋空間——例如儒學在邊緣地區的傳播,凸顯了哪些普世的價值?儒學在邊緣地區如何被吸納、呈現與回應?表現了怎樣的「風土化」特性?它與非漢民族原有的文化有何互動調融的關係?是否影響他們的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是否涉及亞洲歷史上權力結構的變遷與重整等等。這些課題不但是中國儒學本身的重要內容,亦與整個東亞儒學和文明發展的歷史環節,緊扣相連。
公元2000年,在紀念朱熹逝世八百週年所舉辦的學術研討會中,清華大學中文系楊儒賓教授曾以「邊緣-核心」的理論意義,提出「朱子學的邊緣與邊緣的朱子學」的談法與思考方向。楊教授以為:從儒學的觀點來看,儒學本有其核心的命題、意義與價值,但它需要不斷地再被詮釋以體現新生的活力;而往往這些再詮釋的角度,係來自於核心以外的「他者」(the others)。歷代偉大儒者的出現,如朱子、程伊川、王陽明,概與當時主流思潮對反,而重新復活了儒家經典。故來自於「他者」的力量,對儒學的發展實有重要意義。「他者」即是所謂的「邊緣」,「邊緣」可以是學問的邊緣,也可以是地區的邊緣,朱熹和王船山都是處於邊區的位置,而重新詮釋儒家經典,反而更能對當時的主流思潮提出有力的抗爭。此外,非漢民族的邊緣位置,也曾促使滿清雍正皇帝和日本儒者重新審思「夷夏之辨」的種種問題,其論述亦未必不符儒家原始本意,反而更凸顯儒家有其超越族群與性別的普遍價值。總之,「邊緣」的角度復活了儒家的經典;儒學的傳布和發展,也豐富了「邊緣」的價值。
公元2004年,國立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的計畫總主持人黃俊傑教授則進一步歸納「邊緣」提法的意涵,他認為「邊緣」的意義至少包括三種可能性,亦認為相對於中心的「邊緣」、相對於漢人的「非漢」應可為儒學研究的重要問題:
一、地理意義的邊緣,如位於中國周邊的韓國、日本、琉球、越南等國家地區以及相對於中原內地之邊疆地區如蒙古、臺灣等地。
二、社會意義的邊緣,如相對於漢人的少數民族、相對於中國主流社會的耶穌會士及其信徒、相對於一般儒生的民間宗教以及相對於馬來社會而居於少數的東南亞華人移民等等。
三、思想意義的邊緣,如相對於中原儒學之理、氣、心、性等課題,非漢民族吸納儒學時可能的轉化、對儒家夷夏之辨的反思以及其他的新論題等等。
貳
基於以上學術構想和問題意識,2004年當時的國立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計畫總主持人黃俊傑教授與「臺灣儒學與教育文化研究室」召集人陳昭瑛教授的支持與領導下,舉辦了「邊緣儒學與非漢儒學:東亞儒學的比較視野(17-20世紀)」(2004.3.16)與「邊緣儒學與非漢儒學:臺灣、內蒙古與東南亞的比較(17-20世紀)」(2004.5.24)兩場學術研討會,期由邊緣和非漢的角度出發,討論日、韓、蒙古、琉球、東南亞等地以及其它非核心儒學,並與臺灣儒學相參照——蒙古儒學是屬於中國內陸邊緣的非漢儒學;日、韓、琉球則屬於非中國之海洋邊緣的非漢儒學;東南亞華人的儒學屬於中國域外之海洋邊緣的漢人儒學;明末以降的天主教儒學與中國民間宗教的儒學亦皆有其非核心性。臺灣儒學較為特殊,其於明末迄於清代屬於中國海洋邊緣的漢人儒學;但1949年後,卻以創造性的轉化繼承以及獨特的時空地位,而躍昇儒學重鎮。藉由臺灣儒學與其他邊緣儒學和非漢儒學的探討和對比,一則凸顯儒學在不同「邊緣」傳佈發展的獨特內容與課題,呈現儒學研究過去較被忽視的面向與意義;二則重新審思儒學有其超越「邊緣與中心」、「漢與非漢」之普世價值的當代價值;並綜此二層,探索回應前述問題的可能性。
此兩場以「邊緣儒學與非漢儒學」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匯聚了各個「邊緣」儒學的面貌與課題,其貢獻之一是凸顯了從地域、族系或社會階層等不同「邊緣」的視角觀照與儒學關聯的多樣性。所探討的主題,就地理意義上的邊緣來說,包含了韓國、日本、琉球、臺灣、內蒙古、東南亞各地的儒學;就社會意義的邊緣而言,則涉及了耶穌會士、中國天主教人士以及東南亞華人移民、內蒙古漢人移民與儒學的關聯;就思想意義的邊緣來說,儒學除了在韓、日、琉以及蒙古等非漢民族中引發了不同層面之受容與轉化的問題外,亦在內蒙古和臺灣等邊區的漢人移民社會,表現出有別於中原主流儒學發展的過程與效應。這些論文的內容,多同時涉及不同層面意義的「邊緣性」,印證了本會議從「核心∕邊緣」、「漢∕非漢」的理論意義,以及以豐富的「邊緣」意涵開發儒學議題的構想,確有進一步拓展的學術價值。
上述兩場會議的各篇論文,在展現各個「邊緣」與儒學關聯多樣性的同時,亦強烈反照出儒學研究另一種議題的迫切性:這個「核心∕邊緣」、「漢∕非漢」對比架構所呈現之儒學非核心層面的多元豐富,是否仍存在著某些超越地域、族系或社會階層共通的普世價值?它應如何被當代理解、詮釋?這是循著「核心與邊緣」進路所必然出現的問題意識。吾人若能適予回應,不但可深化「邊緣」提法的理論意義,實亦助於釐清、充實所謂「東亞儒學」的內含及其現實意義。
兩場會議「綜合討論」的引言內容,即表現了類似的關懷,也使「邊緣」的切入點得到進一步的發揮。如蔡仁厚教授和楊祖漢教授都提到了歷史上儒學核心的移轉和流動,並指出:舊有的「邊緣」亦可能為新出的「核心」;時間空間的架構,可以人文價值加以轉換。其想法實與前述楊儒賓教授「由邊緣復活儒學生機」的提法相呼應,他們所強調的「人文價值」或「生機」內涵,都不可能不觸及儒學的普世價值。張啟雄教授則建議進一步思考:以儒學在東亞各地傳佈發展的歷史經驗為基礎,它是否可提供共同的價值資源以助創建東亞共同體的可能性?蒙古籍的寶力格教授亦指出:在全球化時代進行文明對話的潮流下,中國的各族或各地域有必要反思儒學的在地價值,以為向全世界發聲的根據;無論從世界觀或方法論上,儒家「和而不同」、「不同而和」的文化價值,尤待反思與總結。
參
本書各文即此兩場會議的部份成果。其中,□本雅史的〈談日本儒學的「制度化」:以十七至十九世紀為中心〉 指出:日本近世儒學的特質,在於儒學沒有充分的制度化,也就是儒學知識的再生產,並沒有在制度上被組織化。具體來說日本儒學具有兩點特性:第一,沒有科舉制度;第二,幾乎沒有採行儒教上的祭祀和儀禮。這使儒學在日本並未成為統治階級的獨佔物,而有自由發展的空間,進而展現出多樣化、個性化的知性特質。亦即在日本,儒學係以個人的修習與實踐道德為主軸,原本就未受到社會的特別期待;而日本政治的現實,也往往靠著與儒學理念相異的原理運作。
上里賢一的〈琉球對儒學的受容〉 則指出儒學傳入琉球,一是藉由日本僧侶(京都五山系)與薩摩儒者的媒介傳來,以「首里」為根據地,發展出以薩摩訓讀結合日本僧門學問為特色的漢學,並普及於琉球士族等各階層。二是因為中琉之間有密切的朝貢關係,而藉由冊封使、從客與官生、勤學等留學生直接從中國引進。來自中國的儒學傳播,又可從兩方面來理解:其一是明初「閩人三十六姓」定居在那霸一角的「久米村」後,已有自明朝前來的教授團進入,形成以「明倫堂」為中心的據點,培育三十六姓子弟為中琉往來貿易的人才;其二是琉球國派遣到中國的「留學生」。早期留學生主要是由王公貴族中選派的「官生」,後期則以出身於久米村的「勤學」為主。「久米村」與「首里」兩地,成為琉球儒學文化的中心,並在教育上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徐光台的〈明末耶穌會士對「理」的詮釋與影響:「理一分殊」與分科之理的遭遇〉 ,以耶穌會士對「理」的詮釋,討論儒學與耶教以及西方現代文明相遇的處境。該文認為:在儒學傳統中,自然知識處於較邊緣的位置;程朱理學「理一分殊」的觀念,雖認為萬殊的自然事物與道德行為都是一理的體現,但從自然知識的觀點來看,「理一分殊」下的一理存在著兩個問題:一是如何由分殊的自然事物來貫通形而上的一理;二是「理一分殊」合理化了「怪異」、「奇異」與星占等自然知識。在西學傳入以前,前者滯礙難行,後者則缺乏相競的學說予以批判。作者析論明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等耶穌會士來華傳教,藉由「格物窮理」之名引入西學,使原先似不相干的西學與程朱理學相遇——西學對「理」所涉及萬物起源的概念和詮釋,既挑戰一理,也引入分科之理的知識理念;而且以原理或原因來解說自然現象的思維,提供了一種與儒學競爭的自然哲學。
三位蒙古族學者,則從不同角度討論清代蒙古儒學發展的各種議題。 其中雲峰的〈清代蒙古族的漢文創作及其儒學〉指出:早在蒙古汗國和元朝時期,蒙古統治者就非常注重儒家文化,並出現了以漢文創作的蒙古族詩人、散曲家、雜劇家等;降至清代,再掀另一波蒙古族漢文創作的高潮。該文認為:清代中前期的蒙古族漢文作者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參加科舉考試的蒙古八旗子弟,其二是元末隱姓埋名的蒙古族裔以及蒙古盟旗王公子弟。他們的漢文創作及其儒學表現在幾個方面:一、治理邊疆民族地區的思想與實踐;二、對科舉考試及儒家經典的記載與研究;三、文學創作和文學評論等。迨至清代後期,大批儒家的經典、著作和漢文章回小說被譯介到蒙古地區,儒學影響也隨之深入蒙古社會。此時期蒙古族漢文作者,亦包括草原牧區的文人,並出現批判佛教、認同儒家入世主張和關心社會現實的思想。他們兼通蒙漢文,不但將蒙古文化融入漢文作品之中,亦對儒學傳播蒙古地區有積極影響;其儒學或闡述理學,或具有濃厚的民本思想,有的更以實際作為體踐儒家價值。
特木爾巴根的〈清代蒙譯儒學典籍及其流傳〉,首先簡述蒙元時期儒學在蒙古地區傳播的史實,說明蒙元提高儒學在國家意識形態的正統地位,大力推進儒學典籍的翻譯、詮釋和傳播,促使儒學普及於各色人種,並廣泛傳播於蒙古地區。次則闡述清代蒙古文人士子透過學校教育、科舉和社會交往等三種基本途徑接觸儒學典籍,並概述多種清代蒙譯儒學典籍的官刻本和民間鈔本,提供了主流儒學研究較為陌生的訊息。該文最後各種蒙古儒臣的著作為例,說明清代蒙古儒學由翻譯儒學典籍到闡釋撰述的歷史發展,凸顯了清代蒙譯儒學典籍在蒙古地區傳播的客觀事實,以及儒學對蒙漢民族文化交流的廣泛影響。
扎拉嘎的〈儒學蒙古化與尹湛納希的近代民族啟蒙思想〉,係以出身於蒙古草原的尹湛納希為例,呈現出晚清儒化蒙古知識份子最具思辨力和開創性的一面。作者指出:尹湛納希係透過小說形塑和理論著述的方式傳達自己的儒學思想和儒學詮釋;常以儒學為理論根據,批評草原的佛教傳統和清朝的蒙古政策,反思蒙古傳統文化和民族宗教問題;並將儒學「修身治國」的義理,轉換為追求蒙古民族發展和民族平等的理論。作者從「誠其意」和「去其辟」的民族平等觀、成吉思汗「生而知之」的形象與民族文化本源觀、儒釋比較的民族文化發展觀以及「孝」、「勿忘祖先」的民族自識觀等面向,析論尹湛納希的近代民族啟蒙思想,並以尹湛納希主張以「天、地、君、父」四大取代「三綱」的儒學改造思想探討儒學蒙古化的問題。
張崑將的〈從布袋戲「雲洲大儒俠」看儒學在台灣的常民化〉 ,從「儒學常民化」的角度,以庶民藝術布袋戲〈雲州大儒俠〉為中心,析論儒學價值內涵如何透過民俗文化,自然地融入於一般庶民生活中,呈現出明清以迄日據時代臺灣儒學發展的豐富議題。作者認為劇中「大儒俠史艷文」堪稱臺灣儒學價值常民化傳播的最佳代表,這位儒俠的角色轟動臺灣中下階層,相當反映出其對儒學價值的認同面向。該文分析布袋戲作為臺灣儒學常民化的各種表現特質:一、藉由善惡二元對立和高潮迭起的戲劇特性,凸顯人倫日用的道德價值和儒學義理。二、寓教化於表演藝術,將「士大夫菁英的儒學」轉化為「普羅的常民儒學」;三、將通俗文學方言化,有效引起大眾共鳴。作者並從劇中「儒俠」人物史艷文,分析常民儒學的忠孝仁義形象,兼論創造者黃海岱藉由布袋戲表現抗議殖民統治的民族意識,並謂其劇本所傳達「忠孝仁義」的儒家道德,係根植於中國文化的脈絡,大異於殖民統治者在日本文化脈絡下所宣揚的內涵。
鄭文泉的〈論儒家思想在當代馬來群島的轉化與難題〉, 係藉由東南亞華人在異地延續儒學命脈的苦心孤詣,討論存文保種的轉化與難題。該文旨在析論儒家思想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三國自戰後獨立以來的轉化,係對「仁」的思想涵意作出消極與積極兩種不同的詮釋與回應。前者以「共存共榮」的「平等」思想(消極詮釋)而散見於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二國華人之母語教育(華教)與孔教運動,是為「少數人的儒學」(Confucian-based of minority)。後者則於新加坡以「大一統」思想(積極詮釋)打造儒家政府,是為「統治者的儒學」(Confucian-based of government)。但二者均面臨了「族群儒學」(ethnic Confucianism)與「普世儒學」(universal Confucianism)的難題,如「普世儒學」僅限於新加坡一隅,而散佈群島各地的「族群儒學」又有不能表現「以天下為一體」之虞,同證儒者「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志,在當代馬來群島地區,尚有漫漫實踐之途。
肆
如前所述,「邊緣儒學與非漢儒學」的學術構想,不但凸顯了儒學在「核心∕邊緣」與「漢∕非漢」對照下的多元與殊異,實亦涉及超越殊異的共通價值內涵。唯整體而言,本書各文所呈現的,似較偏重儒學在不同「邊緣」顯發的多樣議題,而未及深入論述超越殊異的共通價值。但透過對比和歸納,我們仍可從下列角度略窺本書各文,如何在「邊緣儒學與非漢儒學」的框架呈現儒學超越殊異的共通價值:
一、認同儒學對普遍原理的肯定,如「仁」、「理」等相關的核心價值與平等思想。
二、對人之道德主體的肯定與期待,重視個人的誠意修身、道德實踐以及歷久彌新的應變動力。
三、對人文教化的重視,重視倫理德性的信念以及生活日用的規範。
四、重視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入世實用的精神。
五、對儒家經典的傳習與詮釋等。
「邊緣儒學與非漢儒學」的提法是一項新的嘗試,也是忠實呼應儒學傳播長遠歷史的必然產物。此一構想所激發儒學研究的新興面向與多元議題,多為學界主流過去所未及重視者。其對開拓、發展儒學研究領域的成效,是顯而易見的。本書在此構想下,將儒學研究的視野,從漢人本位擴及於非漢民族,從中國本土擴及於東亞周邊;其成果雖重在多元與殊異的面向,亦多少反映了儒學超越殊異的共通價值。唯學海無涯,「邊緣儒學與非漢儒學」的學術園地,畢竟仍有廣大開發、提昇的空間,有待學界同好共襄盛舉。本書的出版,不但是初步成果的結集,亦表達了對此園地持續耕耘的深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