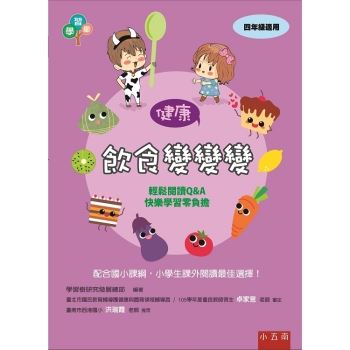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法國電影新浪潮(全新俢訂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05 |
二手中文書 |
$ 357 |
藝術設計 |
$ 420 |
電影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一個渴望改革的時代,一本黃色的電影雜誌,加上一群勇氣十足、叛逆的年輕人,將電影
推向今日新穎的多向度中。即使當時的批判讓他們的電影反而變成了主流而顯得諷刺,
即使昔日的革命如今已像是對失落影像的惋嘆,
他們仍是電影史上最熾熱的一段。
在一次論戰中,法國電影史甚至是全世界的電影就此改變……
1960年代初期,一群新的電影小子從巴贊老爹創立的《電影筆記》雜誌竄起。這群年輕人長年看片,累積了大量豐富的電影知識,犀利的評價成為當時許多電影是否賣座的關鍵。他們咒罵整個50年代的品質傳統,毒舌批判以古典文學為腳本的主流電影已淪為「爸爸的電影」,他們大聲疾呼眾人應用新的觀點及看法對待電影。《電影筆記》對電影的犀利評價,在當時也逐漸成為許多電影是否賣座的重要關鍵;而過去被大家貶抑為娛樂家的風格導演在此時都得以翻身,倍受世人注目。一如希區考克。
當這群新的電影小子從影評/影迷的角色轉換為導演之後,我們在每部電影中看見他們對過去崇拜的致意,以及他們帶有自傳色彩的人生倒映。《四百擊》裡的那個不學無術的叛逆少年正是楚浮的最佳代言人。導演的作品,和他的思維、他的成長背景開始變得緊密相扣了起來。
「電影即寫作」,新浪潮運動除了一改過去編劇電影在對白及布景上的過分講究外,亦成就了製片技術和製片方法的新思維。高達──一個真正抓住一整代電影人想像力的作者──對電影的想法是,「電影當然有開頭、有中間、有結尾,但不一定依照這個順序。」他為了追求這種疏離的效果,運用了許多美學上的新觀念。像是跳接(使觀眾覺得在時空上連結突兀),省略不交代細節,不斷地變動構圖框內的景物,以及不明確告知時空地點……。
本書將帶領你進入新浪潮的時空,從新浪潮運動的歷史背景談起。除詳述其流派、演變、成果,以及對於全世界的電影製作及美學上的影響,並對該運動的靈魂人物的「作品」及其「思維」做深入的剖析與探討,是一本易讀性與趣味性兼具的通論型書籍。
作者簡介:
焦雄屏(文/圖)
現任臺灣電影中心主任、吉光電影公司董事長、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研究所專任教授。台灣最著名的電影學者、製片人、前金馬奬主席。畢業於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系,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電影碩士,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電影博士班。於1980年代成功推動台灣新電影運動,同時也是「中時晚報電影獎」(「台北電影獎」前身)的創始人,主導「台灣電影年」全年活動。除了出版眾多電影史研究書籍、在國外推動台灣電影回顧展,亦擔任世界各大電影節的評審委員,所監制的電影多次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代表作有《十七歲的單車》、《愛你愛我》、《藍色大門》、《聽說》、《愛你一萬年》、《初戀風暴》等。著作包括《藝術電影與民族經典》、《閱讀主流電影》、《談影錄》等四十餘冊。
- 作者: 焦雄屏
- 出版社: 麥田 出版日期:2010-12-05 ISBN/ISSN:978986120472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16頁
- 類別: 中文書> 藝術> 電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