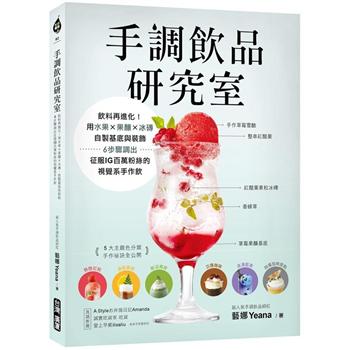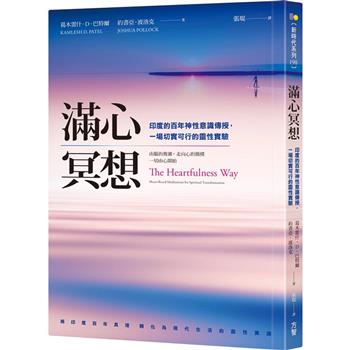我花錢買了一個人的命,我的情人的妻子的命
假如時間不能重來,我還會喜歡他嗎?還是不喜歡他了?是愛他,還是恨他?祝福他,還是詛咒他?極端的兩種感情在我心中呈現同等的強度,對他的恨竟和我對他的愛一樣強烈,一方面期待他幸福,一方面又忍不住詛咒他不幸。這時我已經知道,無論我對他如何百般期待、如何魂牽夢縈,也無法感動他了。他在我難以企及的地方睜眼醒來、用餐、說笑、鬥嘴、調整明日行程,和肚子裡的寶寶說話,與我不認識的女人相擁而眠。我被排除在他的人生之外,就像被囚禁在一個粗大厚實的膠囊中,伸長手臂也觸及不到任何東西,扯嗓喊叫也無人聽聞。
夏天早就過去,我前方的道路卻搖晃著,以致景致變形。路旁的住家庭院裡,不合季節的向日葵驕傲地抬頭盛開。
鋼鐵打造的囚籠是我與丈夫愛的城堡;背棄的暗影任我踩在腳下,日復一日無聲長眠。為了挽回瀕臨瓦解的婚姻,即使與世隔絕也無所謂,只要這愛的城堡裡只有「我們」二人……
太過執著的愛,讓我們生了病,令我們廢棄了生活。
你以為小說裡的世界荒謬至極、令人難以置信嗎?
然而,現實種種其實更駭人!
從小對親姊妹的妒恨;單身媽媽嚮往少年所給的空虛戀情;買凶殺死婚外情對象的妻子;猶如惡鬼般纏著獨子的病重老母……
腥色羶的社會新聞反映了我們心中蠢蠢欲動的病源:
在這世界的角落,有人緊抓著褪色的情感,有人貪索青春肉體,有人心中迴盪著害怕孤獨的呼喊。為了奪取小小的溫暖的安慰,以愛之名所犯的罪更是可怕!
真實卻恐怖,角田光代寫出令人不敢直視的「愛」的真面目。
作者簡介:
兼具芥川獎與直木獎實力、年年高踞暢銷榜的作家角田光代Kakuta Mitsuyo
一九六七年生於日本神奈川縣。早稻田大學第一文學部畢業。一九九○年,以《幸福的遊戲》獲海燕新人文學獎;一九九六年,以《朦朧夜的UFO》獲野間文藝新人獎;一九九八年,以《我是你哥哥》獲坪田讓治文學獎;《綁架旅行》於一九九九年獲產經兒童出版文化富士電台獎,於二○○○年獲路傍之石文學獎;二○○三年,以《空中庭園》獲婦人公論文藝獎;二○○五年,以《對岸的她》獲直木獎;二○○六年,以短篇小說〈禁錮的母親〉獲第三十二屆川端康成文學獎;二○○七年,以《第八日的蟬》獲第二屆中央公論文藝獎,此作並改編為同名日劇。另著有《明日遙遙》、《對岸的她》、《我喜愛的歌》、《森之眠魚》等。
三度入圍芥川獎、三度入圍直木獎的角田光代,作品橫跨純文學與大眾文學,與吉本芭娜娜、江國香織並列為當今日本文壇三大重要女作家。
譯者簡介:
鍾蕙淳
政治大學法律系畢業,東吳大學研究所肄業。譯有小說《空中庭園》、《她和她的生存之道》、《東京島》,散文《我喜愛的歌》等。
章節試閱
年關將近,房枝打電話給美枝子。原本擔心姊姊可能去參加婦女團體的聚會不在家,但電話鈴響八聲後,美枝子接了電話。
「你在家呀,房子太大,接通電話也要走很遠呢。」房枝開玩笑說。
「有事嗎?」美枝子的口氣冷淡唐突。
「沒什麼。只是久沒聯絡,想知道你近來可好?」
「還不是老樣子。」美枝子的聲音隱約帶著憂愁。
「可是你的聲音很沒精神耶,怎麼了?如果感冒不舒服,我可以幫忙買菜。」
「不用,我又沒著涼。」她的語氣不但陰沉,更帶著回絕房枝好意的冷漠。
「姊姊,之後有事想找你商量。」房枝很意外美枝子如此冷淡,情急之下話語脫口而出。「其實我們也在考慮買間房子。姊姊你們不是才蓋了新屋?到時你一定要傳授我們竅門,怎樣才能蓋像你家一樣棒的房子。」語氣帶著幾分諂媚,房枝把耳朵緊貼話筒,靜待美枝子的反應。
「房子?」美枝子問。聲音的背後鴉雀無聲。
「是啊,我老公有機會升遷,他說到時可以換間比較寬敞的新家,還要養隻狗。」
「聽起來不錯啊。」
聽到美枝子的回話,房枝如釋重負。
美枝子繼續問:「你想說的就這件事?」似乎想盡早掛電話。
「我想問你過年要怎麼過?要回正文姊夫家嗎?還是回娘家?如果要回去,我們約個時間……」
這時美枝子打斷房枝說:「我今年忙得很,沒辦法回去。我會寄賀年卡給爸媽,到時麻煩你代我向他們問好。」
就這麼幾句,美枝子便掛上電話。房枝一張臉糾結著,盯著發出嘟嘟聲的話筒。也許姊夫真有外遇,所以姊姊才遷怒於我。不過若真又碰上了,姊姊和以前一樣回娘家不就好了。該不會是上次在新宿碰面時,我說了什麼得罪了姊姊?房枝左思右想,就是毫無頭緒。想著想著,不僅感到自討沒趣,也漸漸怒火中生。姊姊那是什麼態度嘛!之前也不管我是否方便,逕自打電話過來。
房枝心浮氣躁地踩著涼鞋踏過枯褐色的雜草,將洗好的衣物拿到狹小的庭院晒。她使力拍整捲皺的襯衫、浴巾,一一晾在晒衣架上。雖然陽光普照,空氣卻寒凍冷冽,才一眨眼,指尖便已凍僵。她呵氣溫暖指頭,用夾子夾住丈夫的內衣和襪子。
房枝又想起方才的那通電話。在姊姊心情不佳的時候,還跟她說升遷、養狗的事也許不大妥當。或許這些話讓她有落井下石的感受。縱使嘴裡說不錯,也許在內心深處嫉妒著比自己幸福的妹妹。姊姊的性格表裡不一。她外表給人的感覺溫柔婉約,不過房枝想起小時候姊姊曾把爸媽為自己準備的七五三和服腰帶扔進後院的水田,就因為當天她自己無法穿漂亮的禮服。電話鈴聲從窗縫間傳來。房枝直覺可能是姊姊打來的,回到屋裡拿起話筒,聽到的卻是大志的聲音,說今天要加班。大志最近每週有三天加班。又來了?房枝急忙把就要說出口的話硬是吞了進去,心想升官前一定比較忙吧。
「你先睡不用等我。」大志說完便掛上電話。
放好話筒,房枝望著庭院嘆息。早知道大志不回來吃晚飯,就用不著出門買晚餐的菜,拿剩菜將就著吃就好了。晒在庭院的衣服在豔陽下隨風翻飛,遠方可見湛藍色的天空。房枝心中閃過美枝子手上的白色陽傘。
三年後,房枝終於搬到夢寐以求的獨棟洋房。時序進入八○年代,社會人心浮動。大志在川崎買了一棟成屋,雖然去車站要搭公車往返,可是房子十分寬敞,從前住的公寓房子根本無法比。房裡充滿新成屋的味道,讓房枝一早起來便覺得身心舒暢。誠如所料,大志在這三年從課長助理晉升為課長,公務也更繁忙,每天回到家幾乎都已過深夜時分。偶爾趕不上末班電車,大志說住公司附近的廉價膠囊旅館比搭計程車划算,直接在外過夜。想起房間變得寬敞卻必須時常獨守空閨,著實讓房枝感到諷刺。但若因此要她重新搬回市中心租屋,卻是絕無可能的事。
房枝終究沒有二度就業。每天送丈夫出門,帶著搬家後才飼養的雜種犬散步,做做家事。她厭煩成天獨自一人在家,剛搬來時,常招待高中同學或短大同學來玩,然而房枝發覺自己和朋友竟搭不上話。高中的朋友全都有了孩子,滿口育兒經;短大時期的朋友都是職業婦女,聚在一起總是對社會上依舊根深柢固的男女差別待遇猛發牢騷。和她們在一起,房枝覺得自己就像幽靈。膝下無子又沒工作的自己,在這個世界上似乎可有可無。偶爾幾個特別談得來的朋友相約吃飯,不過要前往市中心必須搭公車轉乘電車,太麻煩了。連續幾次回絕後,朋友便和她漸行漸遠。
遛完狗、晒好衣服、掃除完畢、準備好晚餐的菜,房枝眼睛瞪著電視上的八卦節目,心中想起姊姊美枝子。
究竟是怎麼了?曾經聯絡頻繁的美枝子,那年夏天後幾乎音訊全無,連過年也不回娘家。縱使房枝主動打電話聯絡,也總是一副拒人千里的冷漠態度,說沒幾句就掛電話。剛搬到川崎新家時,房枝也曾打電話通知,卻只換來一句「哦,是嗎」。姊姊沒有一聲道賀,也沒意思要到新家看看。雖然房枝認定美枝子是嫉妒自己,不過和她過去的態度相比,簡直判若兩人。就算絞盡腦汁回想是否自己做了要讓人絕交的糊塗事,但房枝始終想不出個所以然。
梅雨季剛結束不久,房枝決心走一趟姊姊家。她搭乘田園都市線在澀谷下車,走進東急百貨地下街買了盒蛋糕當伴手禮,又轉乘國營電車。
剛過正午不久,車廂裡坐滿放暑假的孩子。房枝在搖晃的電車中覺得只要當面和姊姊談一談,一定能知道原因。如果是氣自己,或許跟她解釋清楚便能前嫌冰釋。如果是遇到無法回娘家的處境,也要問個清楚。縱然有時彼此會羨慕嫉妒,不過再怎麼說,兩人總是絕無僅有的手足,更何況先前還聯絡頻繁,感情融洽。
走出車站,靠著腦海中的記憶進入商店街。就算盡量挑樹蔭下走,仍是走得汗流浹背。房枝想起最後一次去美枝子家時也是夏季。早知道就該早一點來,房枝為這疏遠的三年懊悔不已。
房枝焦躁不安。因為沿著記憶裡的路走,竟找不到那棟熟悉的房子。她遍尋不著那個作為標誌的紅磚牆和藍屋頂。印象中確實是在這呀,可是眼前只有一面像是把拼湊的鐵皮屋頂當防護牆的怪異牆壁。逐一確認附近人家的門牌,房枝拿出手帕頻頻按拭汗珠,快步朝一間酒坊走去。店裡空調令人瞬間舒暢。她買了一瓶PLUSSY維他命C飲料,轉開瓶蓋,邊喝邊問櫃檯後面的中年女性:
「請問,小林先生是不是住附近……」
素著一張臉的店員才聽到「小林」這名字便立刻皺著臉,一臉驚訝地望著房枝。
「是哪位小林先生?」
「小林正文先生,家中只有他和太太兩個人。」
「你認識他們?」
女人眉頭深鎖,讓房枝不知如何接話。這女人一定認識姊姊夫婦,可是似乎對他們印象不好。房枝擔心如果讓她知道自己是姊姊的親友,也許會招致對方不友善的對待。
「談不上親朋好友啦,只是以前和小林太太很熟……」不得已用這種說法說明和姊姊的關係,房枝心中感到歉疚。
「小林先生還是住在老地方,沒變。不過那家人真教人發毛,有時送貨到他們隔壁,還會從窗口罵人!上次他們還痛罵山本先生家的狗太吵,可是山本家和他家隔了一條街哩!」
這女人似乎有滿腹牢騷想一吐為快,一口氣講完又對房枝上下打量。
「最近連小林太太也不跟人打招呼了……如果你要去拜訪那位太太,拜託你跟她說一聲,不要在院子裡灑奇怪的藥品,大家都說臭得受不了。」
「唔。」房枝含糊地點點頭,將空瓶放在櫃檯。步出酒坊,熱氣一瞬間湧上。房枝站在店門前目不轉睛地凝視數十公尺外的奇異圍牆。在原有的紅磚矮牆上加蓋鐵皮牆面,上端圍上帶刺的拒馬鐵圈。從鐵皮接縫勉強看得見房舍,但當年嶄新的藍色屋頂如今舊得厲害。究竟發生什麼事了?因為酷熱而呆滯的頭腦無法思考。誠如酒坊的女人所說,那面彷如要塞般包圍著房子、東拼西湊搭成的鐵皮牆,令人不寒而慄。姊姊真住在裡頭嗎?
房枝朝著可能是姊姊家的那面牆走,連汗水也忘了擦。看不到門牌,曾經是大門的地方都被鐵皮給包圍。房枝駐足於這面難以一探究竟的圍牆外,思索著該如何通知他們自己的到來?
「幹嘛?」粗暴的嗓音從頭頂落下,房枝顫抖著身軀,提心弔膽地抬頭一看,鐵皮接縫間,可見在二樓窗前怒氣沖沖的正文姊夫。
「姊夫……」
許久未見的姊夫與從前判若兩人,削瘦的身軀像長滿了尖刺。他探出窗戶、火冒三丈的那張臉不僅冷漠,而且猙獰可怕,簡直就像能面似的。房枝有些恐懼。或許是認出房枝,正文的表情突然變得僵硬,他使力甩上窗戶。房枝仰頭盯著那扇窗,心想或許姊姊會從窗中探出頭來。這時,擋在大門外的鐵皮緩緩向外推開,姊姊白晳的小臉探了出來。
「小房!」
「姊姊……」
美枝子熟練地從鐵皮後鑽出來,並將鐵皮挪回原來的位置。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目瞪口呆的房枝不由得發問,但美枝子只是猛力抓著妹妹的手腕,強拉她離開自家門口。
「等、等一下,要去哪?」
「要來先說一聲嘛,你突然過來,嚇我一跳!」
「可是就算打電話,姊姊也……對了,你家怎麼回事?出了什麼事?」
「沒事、沒事,這裡不方便,我們還是找個地方喝茶好了。」
美枝子拉著房枝,踏著小碎步一路閃避人群前進,引來多名路人轉頭注視。她們經過肉店和玩具店時,甚至有人從店裡斜身探頭張望。雖然不知原因,但房枝隱約發覺姊姊夫婦在這個小鎮似乎小有名氣,也清楚這名氣似乎不怎麼光采。
車站前的咖啡廳裡,姊姊蜷縮在位子上,喃喃地逕自說個不停:「這附近最近治安不太好」、「闖空門的很多」、「還發生過強盜案件」。
「就算治安真的不好,你家也太誇張了。我剛剛去那家酒坊,他們在閒言閒語喔!」
「什麼?他們說了什麼?」美枝子這才抬起頭來,慌張問道。
「聽說你們灑藥?藥的味道很臭……」
「哦,我們聽了小房的建議,規畫了家庭農園。本來不想用農藥,可是夏天害蟲多,不用不行。你千萬不能信酒坊老闆的話,那人面善心惡,之前還滿不在乎地把一些無法回收的破玻璃瓶和廚餘扔到我家院子。」
房枝目不轉睛地端詳對面的姊姊。姊姊原本圓潤的臉頰和姊夫一樣瘦削凹陷,盤成單髻的頭髮增添許多白髮,原來溫和沉穩的氣質消失殆盡,她變成一個尖銳帶刺的中年女人。房枝滿心狐疑,想知道究竟是什麼讓姊姊變了樣,卻完全不得其解。
「究竟發生什麼事了?」房枝直接問道。「你好久沒回娘家了,爸媽很擔心呢。你又不跟我聯絡,就算打電話給你,沒說兩句話就掛電話。」
美枝子探頭看著自己面前的咖啡杯,細聲說話,音量小得幾乎被店裡播放的古典音樂掩蓋。房枝豎起耳朵仔細聆聽。
「我和我老公約好了,我們只能相互依靠,兩人同心協力走下去。那房子是我們的財產,我們必須守著房子一起生活下去。」
美枝子如同往昔般,以指尖沿著杯子旁的圓形水漬畫圈,臉上帶著淺淺的微笑。房枝見到她的臉上竟帶著前所未見的滿足。從前環繞在姊姊周圍的寂寞空氣,在笑容中已不復存在。但不知什麼緣故,房枝覺得毛骨悚然,露在短袖外的手臂瞬間冒出雞皮疙瘩。為了不被姊姊發現,房枝不動聲色地悄悄將手臂隱藏在桌下。
「你家又不是豪宅,何必搭蓋那麼高聳的圍牆呢?而且一看就不是請人做的,牆上到處是縫,看了真不舒服。」
房枝相信那棟奇怪的房子是讓她不寒而慄的主因,因此決定單刀直入問清楚。然而姊姊臉上的笑容並不因房枝的話而消失。
「沒關係,無論外界怎麼看,只要能守住家裡就好了。你說對不對?」美枝子抬起頭,對房枝微笑。
「姊姊不擔心正文姊夫的婚外情了?」
房枝突然想看姊姊的笑容崩潰,故意一派輕鬆地問。然而姊姊依舊笑容滿面地回說:「不擔心,我再也不擔心正文外遇了。」
年關將近,房枝打電話給美枝子。原本擔心姊姊可能去參加婦女團體的聚會不在家,但電話鈴響八聲後,美枝子接了電話。
「你在家呀,房子太大,接通電話也要走很遠呢。」房枝開玩笑說。
「有事嗎?」美枝子的口氣冷淡唐突。
「沒什麼。只是久沒聯絡,想知道你近來可好?」
「還不是老樣子。」美枝子的聲音隱約帶著憂愁。
「可是你的聲音很沒精神耶,怎麼了?如果感冒不舒服,我可以幫忙買菜。」
「不用,我又沒著涼。」她的語氣不但陰沉,更帶著回絕房枝好意的冷漠。
「姊姊,之後有事想找你商量。」房枝很意外美枝子如此冷淡,情急之...


 購買新書79折221元
購買新書79折221元
 購買二手書36折100元起
購買二手書36折100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