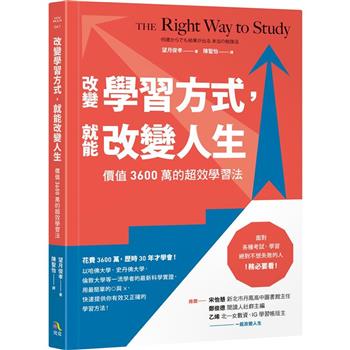代序
滲入體內的記憶
我從來沒想過要為自己長年來所從事的工作做個總整理。因為在心裡某個角落,我總覺得一這麼做便脫離了工作現場。
因此,我並不想要記住曾經做過的事。不如說,我反而覺得忘了比較好,有時甚至還會努力遺忘。在我心裡存在著一道公式:「先讓自己歸零,接下來就會一路順遂」。
是什麼樣的機緣造就了我這樣的想法呢?老實說,我連這個都不記得了,也許和學生時代讀過宮澤賢治的詩,或是受到寺山修司的影響有關吧。從他們身上我自有一番領悟:事情結束就是結束了,此刻正在發生的這個瞬間才是重要的事。
重要的是「現在」、「眼前」。「過去」已無所謂了。我和宮崎駿(以下稱宮兄)近三十年來幾乎每天都在交談,但從來不談過去。我們總是談論「現在」。談現在非做不可的事,以及大約一年以後的事。光是這樣要聊的事情就多得像山。
宮兄是有名的健忘。我想這也和他創作電影的祕密息息相關。既已做出一番成績,一般人應該會承繼過往並延續下去吧。首先就會往如何強化自己既有手法和技法來與人一較長短這樣的方向去思考。然而宮兄並非如此。他總是像新進導演般挑戰新的事物。這雖然是宮兄的作家性格使然,但也未嘗不是因為他對自己曾經做過的事已不復記憶的緣故?
作家吉行淳之介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會遺忘的記憶無足輕重」。換言之,記憶有兩種,滲入體內的記憶和會被遺忘的記憶。必須仰賴筆記或日記才不會忘記的事,忘了也罷。雖然剛才提到的吉行先生的話我也記得不是很清楚,但它在不知不覺中融入了我的體內,這才重要不是嗎?
若從製作人的立場來看,該用什麼樣的宣傳文案?在什麼樣的條件下合作?或是前例如何等等都至關重要。可是平常這類事情忘了也沒關係。必要時再問人,或是翻閱當時的資料,然後該想起來的自然會想起來。
有工具就信任工具。「記錄」即是為此而存在。因為「記憶」和「記錄」是兩碼子事。我相信人類的記憶容量有限,既然如此,我寧願將那容量盡可能留給珍貴的記憶。所以我決定少記自己曾經做過的事,減少到所需的最小限度。
我的身分使我有很多機會與人對談和聊天。在談話時我常常會以「我剛剛突然想到一件事」的說法來擴大或轉移話題。現實中也是如此。我有過好幾次聊著聊著便猛然想起什麼,或是經人一問才回憶起來的經驗。因為那「記憶」已滲透到自己的體內去了。那些「記憶」大半不是我刻意要記住的,而是不知不覺便成為自己的一部分。
正因為如此,我記憶中的人、時、地並不必然正確,說不定前後關係也會記錯。可是,重要的應該是記住了什麼內容吧。舉例來說,與其告訴你五十五加四十四等於九十九,二○五○加一○三○等於三○八○這樣正確的數字,還不如大致掌握一○○或三○○○這樣約略的數字來得重要,不是嗎?
我因為『Animage』月刊創刊而涉入動畫世界整整三十年,STUDIO GHIBLI起步至今也已二十年有餘。那麼,在這漫長歲月中,我所珍視的「記憶」、不知不覺間已成為我生命一部分的「記憶」究竟是什麼?接下來我將回憶那些往事並娓娓道來。
原諒我說話常常東跳西跳、翻來覆去。因為「突然想起」的事很多。我不知道這些事情對讀者而言是否有趣,能不能有所助益。只希望讀者能用各自的方法來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