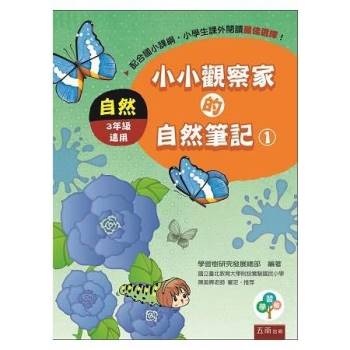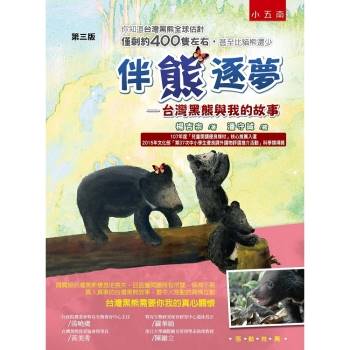一九九二年,我們從芝加哥的市中心搬到了科羅拉多州洛磯山脈(Rocky Mountains)的丘陵地帶。儘管我在這兩個地方的工作間,都位於地下室,實際上的差別可大多了。從芝加哥的地下室窗口望出去,我看到的是路過行人的膝蓋,以及鴿子和松鼠等小動物;現在,我卻可以從窗戶看見覆蓋白雪的山丘和美國黃松,以及一群又一群的狐狸、梅花鹿、麋鹿、北美臭鼬、土撥鼠、熊、山貓,有時候甚至還有獅子,經過我家庭院。
我們之所以搬家,部分原因是芝加哥真的太亂了,另外一部分則是因為我覺得需要換個地方,專心寫作。身為記者,以前我總是報導別人的故事;現在,是時候把注意力轉向裡面,寫一寫更多個人的反思。我需要檢視自己的信仰,並且把這趟旅程的每個步驟都記錄下來。至今,我還是很訝異,自己竟然可靠以此為生。對其他行業的人來說,他們必須在工作之餘,另外花時間來處理信仰的掙扎,我卻可以在這麼做的時候,還能得到薪水。
過程中,我始終保持著記者的身分。我覺得自己蒙召要以平凡天路客的角度來書寫。或許是因為自己成長於一間不健康的教會,我總是羞於代表某個建制型的基督教宗派或形式;我不曾被按牧,也不必捍衛任何機構的名聲。反之,我是一個自由作者,自由地探討我自己的問題,看看這些問題將把我帶到哪裡,而不用擔心隨之而來的後果。我尋求專家的意見,儘可能地學習,然後把我覺得有用的答案,以可讀的方式撰寫出來。
每一個觸及靈性議題的作家,多少都能明白梅頓(Thomas Merton)有過的感受。儘管他的書對於什麼是靈性的生命,總是有著十足的把握,實際上,梅頓常常被各樣的不安、懷疑,甚至是恐懼所困擾。我常常會有一個感覺,相較於自己的生命,我所寫出來的文字,可能有更長遠的價值;我也覺得,當我所談的事情愈屬靈,就愈不能傳達在我生命中的各種混亂。我發現,編輯文字,比編輯自己的生命要簡單多了。每一次,我收到讀者來信,說我的書是如何影響他們的生命,我都會忍不住想要抗拒:「是的,不過你並不認識我;跟我太太聊一聊吧!」文字給了我們這些書寫信仰的作家代言的權力,但是我們根本就不配。
我曾經在書中好幾次提到自己在一間基督教學校念書的日子,雖然文字中並沒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我始終都沒有發現,這樣做是如何讓那裡的人不高興,一直到我有機會重返校園,跟學校的某些老師或是行政人員交談。「你為什麼要這樣傷害我們?」一個教授問。「為什麼老是提那些負面的事情?我們曾經頒了年度最佳校友獎給你,你卻轉過身,一有機會就批評我們!」我試著只是傾聽,而非為自己辯護。我很清楚,他所回應的是文字不公平的特性。我所寫下的隻字片語,藉著書籍的出版,傳到了美國各地,表達出一個有限且不足的看法,讓他覺得相當困窘。
為什麼我們這些作家要這樣做?「著書多,沒有窮盡」,早在三千多年前,傳道書裡的教師就這樣說過。如今,單單在美國,每年新書的出版量就達到二十五萬種。如今我們依舊如此,生產出多而又多的文字,可能帶來安慰或是傷害。所有作品多多少少都帶著點傲慢。當我寫下這些句子,我是厚著臉皮相信值得你花時間好好讀一讀。我,一個你可能從未見過的人,竟要求你來注意我,把自己投入在我的文字和思想中。我要你聽我說話,卻又不給你機會交換身分。
我認為,作家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除了提供一個觀點,我們沒有別的東西。我所寫的每一件事,都從我的家庭、我在南方基要主義環境中長大,以及身為一個天路客的經歷中得到色彩。我只能帶著熱情來寫自己的故事,而不是你的。然而,我在教會、家庭,甚至是信仰路上蹣跚的步伐,不知道為什麼,竟能觸動讀著的回應,有如撥弄吉他琴弦引起聲音的共鳴。正如波西(Walker Percy)說過的,一個好的作家,可以幫助讀者發現他們早已知道,卻還沒意識到自己原來知道的事。
我曾經寫過自己在一間「有毒教會」成長的故事:那是一間堅守律法、充滿憤怒與種族主義的南方教會。我笑說自己正從那間教會「康復中」,慢慢明白過去許多被稱為絕對真理的事情,很可能其實是錯的。結果,當我開始寫作,我發現自己就像一個站在邊緣的人,更喜歡問問題,而不是提供答案。我早年的幾本書(《有話問蒼天》〔Whrer Is God When It Hurts〕、《無語問上帝》〔Disappointment with God〕),便反映了我在這方面的掙扎,以及我是如何定位自己。
我曾經用「邊界之人」,來形容那群落在信與不信之間,苦苦掙扎的人;我總是傾向聆聽他們的聲音。當中有些人接觸教會時小心翼翼,被耶穌所吸引,卻因為那群自稱耶穌跟隨者的人而離開;另有些人,因為過去不好的經驗而逃離教會,不過心中仍然渴望在那裡感受到慰藉。過去,我也花上不少時間在邊界地帶徘徊,很希望能向這群游離在邊界的人們致敬。
我並不是要為教會辯護,反之,我想要認同在些曾被教會傷害的人,為他們重新指出福音的好消息。耶穌說真理叫人得自由,祂來是要人得著更豐盛的生命。任何看法如果無法使你得自由,拉大生命的格局,那就一定不是耶穌的信息。聽起來不像好消息的,就一定不是福音。
文字就是我的工作,我會挑起一個字,反覆觀看,拆開再組合,並且反覆咀嚼。我就是這樣對待恩典一詞的。我注意到,恩典總是以不同的樣貌,出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體育版面(優雅的〔graceful〕運動員)、停車場(免費〔grace〕停車時段)、樂譜(裝飾〔grace〕音)。這個現象值得細心探究,因為恩典的每一個用法,總是正面且迷人的,和基督徒常常給人的負面形像並不一樣。人們認為基督徒是拘謹、愛論斷的。在我們的生命裡,恩典這個詞竟然傳達了一個與神心意正好相反的印象,實在是一件古怪的事。於是,《恩典多奇異》(What’s so Amazing about Grace ?)有了雛型。
我多麼希望,自己可以這樣說:「讓我來告訴你,我的十年計畫是什麼,在這後現代的文化裡,我有什麼傳福音策略。」事實是,我做不到。我只能從當下困擾著我的問題,跳到下一個困擾著我的問題。回顧過去,我發現有好些主題不斷重複出現,像是苦難和恩典。我也發現,自己的寫作逐漸從信仰的邊陲,往中心移動。看看我近年來的書名――耶穌、恩典、禱告――全都是信仰的核心。
如果有人在二十年前建議我寫一本關於禱告的書,我一定會放聲大笑。直到許多年後,我才意識到,自己想要談談這個主題。我說自己想要,並不代表我有能力:我還是一樣,以記者的身分進行接觸,帶著一長串的問題,去找那些可能有答案的人。與有權和掌管宇宙的神溝通,許多人卻覺得禱告是一件無聊、死氣沉沉的儀式。有可能扭轉嗎?我是不是真的相信禱告?我開始問類似的問題,最終寫成了一本書。
老實說,我其實是為自己來寫書。我把那些困擾著我、挑起我興趣的問題找出來,然後一頭栽進去,不知道自己會從什麼地方浮上來。未來也許有人會跟我一樣投入其中,只是寫作的當下,我是自己一個人,和問題搏鬥,驅趕著文字(它們就像一群小動物,老想著逃出去)。寫作給了我一個處理信仰方式,一個字接著一個字。而出乎我意料,這些文字最終也幫助到其他人的信仰。
在雪茄仍然是用人工捲成的年代,古巴那裡就有一個傳統,聘請一些人來為工廠的工人朗讀。大家無聲地工作,耳邊一個小時接著一個小時,聽著大聲朗讀出來的文學名著。工頭發現,這麼做不但有助於時間的經過,也提升了工人的士氣。雪茄工人非常喜歡《基度山恩仇記》(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到一個地步甚至寫信給了大仲馬(Alexandre Dumas),請他同意用這本小說來為雪茄命名――今天依然受歡迎的「蒙特克里斯托」(Montecristo)雪茄,就是這麼來的。我很懷疑,大仲馬寫作的時候,腦袋裡可曾想過古巴的雪茄工廠;文字的可傳播性,卻讓他橫渡了整個海洋,進入到另外一種語言,拜訪遙遠的國度。
文字讓作家得以跳過鴻溝,進入到另外一個人的意識中。作家與讀者間的往來,通常都是祕密發生的,連開始的人,都不知道確切的時間和地點。我從沒親眼見過有人在閱讀我的著作,但是讀者們卻信誓旦旦地告訴我,他們有讀過。我盼望自己所寫的東西,能夠成為懷疑者的同伴,為受苦的人帶來安慰,讓無法從教會中感受到恩典的人,找到恩典。
我曾經收到過一封來自印尼的信,以拼湊出來的英文寫道:「我讀了你的《耶穌真貌》〔The Jesus I Never Knew〕,這真是一個祝福。我反覆看了三次。好幾天的晚上,我都無法入眠,一直在想你寫的東西。你的書幫助我明白,耶穌並不只是一個在兩千年前活過,卻又死掉的人;祂更是一個在兩千年前死掉又活過來的人,直到今天,祂都還真實的能夠觸摸。」
一九九八年我到黎巴嫩,在那裡遇到了一個女士。她說,黎巴嫩內戰的時候,她讀了我的《無語問上帝》。她把書放在地下室的防空洞裡,當戰火來到公寓家的附近,她會拿著手電筒,走過漆黑的階梯,點亮一根蠟燭,讀我的書。我真的無法形容,聽到基督徒正為了信仰的緣故面臨死亡,中東最美的城市遭到摧殘的當下,我在芝加哥公寓寫成的文字,不知為何竟能為她帶來安慰,而自己感覺多麼的不配。
還有一個來自布魯特(Beirut)的女士,寫信告訴我,《恩典多奇異》怎麼幫助她改善對於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 L. O.)游擊隊的態度,他們侵占了她住的公寓。讀到這樣的信,我忍不住這樣對自己說,天知道我寫作的時候,心裡所想的其實是身體上慢性的病痛,絕對不會是遙遠地方的一場內戰,是要善待把音響開到最大聲的鄰居,而不是不請自來的游擊隊員。一次又一次,神讓我驚訝,使用我這個不完全的人帶著混雜動機所寫下的文字,結出我想都沒想過的果子。
朋友曾經對我說:「你寫的文字,出版的書,就像你的小孩。你儘可能為它們做出最好的安排,最終它們還是會離開你到別的地方去,活出它們自己的生命。」這說話再真切不過了。讀者手上的這本書,便是從過去幾十年我寫作的「孩子」那裡挑選出來的,包括了二十二本書、四十五篇不同的文章,以及一些從未出版過的文字。修訂它們的同時,我也再次為著自己有權參與文字的工作,為這些文字所帶來各種不可思議的連結,獻上深深的感恩。
「藉著閱讀,我們知道自己其實並不孤單」,電影《影子大地》(Shadowlands)裡,一個曾被魯益師(C. S. Lewis)指導過的學生這樣說。的確,我們這些寫作的人又何嘗不是如此,在深切的盼望中相信自己並不孤單。
楊腓力,科羅拉多,二○○九年春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微光:楊腓力365恩典故事集的圖書 |
 |
微光: 楊腓力365恩典故事集 上下 (2冊合售) 作者:楊腓力 出版社: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校園福音團契附屬校園書房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09-10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99 |
宗教 |
二手書 |
$ 416 |
二手中文書 |
二手書 |
$ 416 |
Others |
$ 510 |
中文書 |
$ 510 |
基督宗教 |
$ 522 |
宗教命理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微光:楊腓力365恩典故事集
用故事的力量點亮世界
從光鮮亮麗的美國超級教會,到遭共產政權逼迫的地下教會;從貧民區酗酒者的辛酸史,到原野上動物的一舉一動;從車禍現場的神蹟醫治,到終身未蒙應允的禱告。楊腓力踏破鐵鞋,挖掘恩典事件,以細膩的文筆,寫出真實又動人的恩典故事。
恩典大師楊腓力在《微光:楊腓力365恩典故事集》,給我們一個「恩典放大鏡」,讓我們在閱讀的過程中,看出神在我們生命中所留下恩典的痕跡,吸收神話語的屬靈養分,過豐盛的每一天。本書特色如下:
「暖心」的屬靈書籍。本書取自作者二十二本書、部分未發表的札記小品中的恩典故事,是作者四十年集大成之作,適合慕道友、初信者,以至所有渴望恩典的基督徒。
實用的靈修工具。三百六十六則短篇故事,每篇附有與故事主題相關的聖經經文和反思問題,幫助基督徒每天有規律地靈修、默想。
豐富的牧養素材。作者足跡遍及中東、印度、俄羅斯,見識信仰百態。他體會大都市的華麗與庸俗、洛磯山原野的生機與肅殺。這些素材都值得服事同工參考,使講台、團契聚會的教導生動有力。
邀請你在晨光初現之時,讓恩典故事陪伴你走過每一天恩典之路。
作者簡介:
楊腓力(Philip Yancey),《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雜誌特約編輯,美國基督教暢銷書作家,著作翻成二十五種語言,售出超過一千四百萬冊。他是一位記者,足跡遍及中東、印度、日本,記錄人情冷暖、信仰百態;他也是一位天路作家,透過溫暖的文字,陪伴讀者經歷信仰的甜美與辛酸。著作包括:《尷尬的上帝》、《恩典不虛傳》、《耶穌真貌》、《恩典多奇異》、《歡喜讀舊約》、《何必上教會?》、《盼望的線索》、《為何上帝不理我》、《恩典現場》、《禱告》、《另一世界的傳言》、《無語問上帝》(新北:校園)等。
章節試閱
一九九二年,我們從芝加哥的市中心搬到了科羅拉多州洛磯山脈(Rocky Mountains)的丘陵地帶。儘管我在這兩個地方的工作間,都位於地下室,實際上的差別可大多了。從芝加哥的地下室窗口望出去,我看到的是路過行人的膝蓋,以及鴿子和松鼠等小動物;現在,我卻可以從窗戶看見覆蓋白雪的山丘和美國黃松,以及一群又一群的狐狸、梅花鹿、麋鹿、北美臭鼬、土撥鼠、熊、山貓,有時候甚至還有獅子,經過我家庭院。
我們之所以搬家,部分原因是芝加哥真的太亂了,另外一部分則是因為我覺得需要換個地方,專心寫作。身為記者,以前我總是報導別人的...
我們之所以搬家,部分原因是芝加哥真的太亂了,另外一部分則是因為我覺得需要換個地方,專心寫作。身為記者,以前我總是報導別人的...
顯示全部內容
推薦序
推薦序
本書不是一本沉思性的文集,也沒有對某些理論提出探討性的反思。作者楊腓力的短篇文集是一種生活化與有互動特性的智慧之語。在一個忙碌、膚淺與疏離的時代,作者對世事的洞見與對人生的真情流露,感染讀者,使他們的生活多一份創意思考與活力投入。他像是一個朋友從自己的經歷和現實的生活,自然地分享他的所思所感。若能每天閱讀一篇,讀者會感到多了一個靈程同路人在身邊同行,並體會對談之歡欣。
此書的文字真誠樸實、生動活潑,作者能將發自內心的感受與視角如實地表達,又善用引起讀者同感的方式描寫自己的所見所聞。他能在...
本書不是一本沉思性的文集,也沒有對某些理論提出探討性的反思。作者楊腓力的短篇文集是一種生活化與有互動特性的智慧之語。在一個忙碌、膚淺與疏離的時代,作者對世事的洞見與對人生的真情流露,感染讀者,使他們的生活多一份創意思考與活力投入。他像是一個朋友從自己的經歷和現實的生活,自然地分享他的所思所感。若能每天閱讀一篇,讀者會感到多了一個靈程同路人在身邊同行,並體會對談之歡欣。
此書的文字真誠樸實、生動活潑,作者能將發自內心的感受與視角如實地表達,又善用引起讀者同感的方式描寫自己的所見所聞。他能在...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