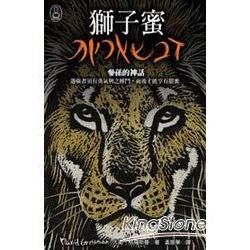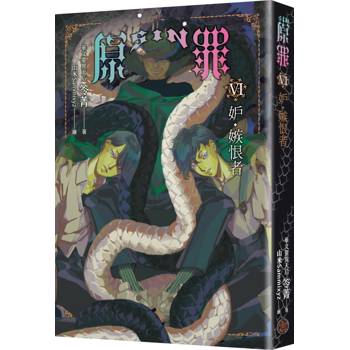解構參孫神話,走出猶太悲情
文∕南方朔
神話和史詩經常都是生存情境的隱晦寓言,只有透過睿智且深刻的解讀和詮釋,始能從古代的文本裡探索出新意,幫助人們走出糾纏得有如迷宮般的宿命。這是一種智慧事業,它帶領著人們超越狹隘,昇華心靈,離開那不應該存在的狀態。
而當代以色列主要作家大衛.格羅斯曼(David Grossman, 1954-)所著的這部《獅子蜜──參孫的神話》,就是神話及史詩解讀的新經典著作。作者以超凡的洞察能力和開闊的襟懷,透過解讀《舊約》〈士師記〉裡有關大力士參孫的神話,而連繫到今天以色列的情境。作者指出,參孫那種由於被背叛、被出賣的危機感所造成的過激反應,最後使他走向與他者同歸於盡的毀滅,而這點其實也就是今天以色列處境的原型。以色列面對生存上的危機,已習慣誇大所具備的力量之價值,使力量走向反面,過分地加以使用,於是原本應改善的生存環境遂變得更加惡化,慘痛的歷史經驗也就被不斷重覆,猶太人也因此永遠難逃「世界的陌生人」之命運。在格羅斯曼筆下,「參孫神話」其實早已成了猶太人心中的「參孫情結」。它是猶太人深層心理構造的成分,只有超越「參孫情結」,以色列始可為創傷的歷史打開新頁。當代法國思想家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曾指出過,「他者」其實是在我們自己的裡面,人經常都是自己把自己變成了陌生人,這種觀點倒是和格羅斯曼的論點相當。
人們皆知道大力士參孫乃是《舊約》〈士師記〉裡重要的史詩人物。根據希伯來古史,我們已知希伯來人乃是閃族的一支,原居阿拉伯半島南端,從紀元前三千年起即一路向西移動。紀元前十三世紀在摩西率領下過紅海,在西岸曠野流浪四十年,抵達約旦河東岸。接著約書亞率眾渡河,到了西岸迦南這應許之地,他們初到之時,當地原來的住民稱之為「哈比魯人」(Habiru),意思是,「從河那邊來的人」,這個稱呼後來音轉而成「希伯來人」(Hebrew)。
而希伯來人在之前十二世紀抵達迦南地區時,來自地中海克里特島及愛琴海各島嶼的人也到了這個地區,他們即非利士人(Philistines),意思是「海上民族」,今日所謂的「巴勒斯坦」即由他們所命名,意為「非利士人的土地」。非利士人比希伯來人先進,這也是希伯來人常受迫害的原因。在大約兩百年的時間裡,希伯來各部族主要靠「士師」(Shophetim)來領導,這個字指的是「裁判者」和「復仇者」,顯示出那個時代的希伯來人基本上仍處於部族階段,戰時各部族即以「軍事民主」的方式合作,士師形同指揮官,平時士師則為行政官和司法官。士師時代一直到掃羅稱王,進入王國時代而告終。
而《舊約》〈士師記〉就是士師時代的紀錄,在眾多士師裡,曾任職二十年的參孫,無疑是戲劇性最強的一個。
其實,力大無窮的參孫,在所有的士師裡,乃是最不像士師的人物,更像是個孤獨的復仇英雄。他並非父母親的精血所生,而是上帝的使者讓他的母親受孕。他曾搏殺獅子,而後獅子的屍骸被蜜蜂所居,他因而吃了獅子蜜。他兩度愛上非利士女子,但都遭背叛並對非利士人大開殺戒。最後他被出賣,頭髮被剃光,神力完全消失,眼睛也遭刺瞎,淪為推磨的奴隸,但後來頭髮長了出來,神力恢復,他靠著神力推倒了樑柱,殿內三千多人皆被壓死,他成了死的時候比活著時殺了更多人的復仇英雄。有關參孫的故事,一般人皆強調他的大力士特性,至於猶太人則著重在他的復仇性格上。猶太人的這種復仇性格,除了顯露在中古布拉格教士馬哈拉爾(Maharal)曾創造出一個對反猶人士進行暗殺活動的幽靈戰士勾勒姆(Golem)外——這個勾勒姆即瑪麗?雪萊(Mary Shelley)所著《科學怪人》的前身;以色列在和中東國家多次戰爭期間,也有過將部隊命名為「參孫之狐」,以及準備展開核子攻擊的「參孫方案」。參孫已成了猶太人「復仇有理」的心理依據。
而格羅斯曼的這部著作,即是企圖以深層心理分析和文本重新詮釋,來解構參孫神話,取消參孫的合理性。而當然這樣的解釋觀點並非他首創,稍早之前,以色列精神病學家伊蘭.庫茨(Ilan Kutz)、英國猶太作家琳達.格蘭特(Linda Grant)等早已有過類似的解釋,但透過格羅斯曼精湛細密的分析,他無疑的已將這個問題做了集大成的討論。在他的分析觀照之下,參孫其實是個缺乏愛、孤獨、渴望愛與認同,但卻自我扭曲,具有被女人背叛這種強迫心理需要的英雄,他狂暴的行為因此而有了理由,而最後則是自己與敵偕亡。參孫的這種心理情境,其實與今天以色列猶太人相似,被出賣背叛的恐懼,已使得以色列成了狂暴有如參孫的大力士,與敵俱亡的共同毀滅衝動則是它的終極後果。以色列必須擺脫參孫這個魔咒!
當代以色列的猶太人反思自己的歷史與現狀的日增,以色列已不能再像參孫那樣去過他們的生活,從這樣的角度看,解構參孫神話,並將它與現在連繫起來,未嘗不是猶太人自我反省的重要一步。人類必須揚棄許多悲情──被壓迫的悲情、被背叛出賣的悲情,這些悲情在自哀自歎下,所隱藏的其實是自我扭曲的自悲與自大,格羅斯曼對猶太神話與情結所做的睿智分析,不但對猶太人,就是對世界上許多其他的人,也同樣有振聾發聵的作用啊!
每個猶太孩子第一次接觸參孫的故事時,瞭解的都是「英雄參孫」——因此,他被古往今來各種語言的文藝作品和戲劇電影或多或少地塑造成這樣的形象:神話般的英雄、強壯的戰士、赤手空拳撕裂獅子的人、猶太人與非利士人的戰爭中超凡的領袖。毫無疑問,參孫也是《聖經》中最多姿多彩、也最有性格的人物之一。
而我從手中的《聖經》經文讀到的參孫,在某種程度上與人們熟知的參孫故事和他的形象有些出入。他並非一個勇敢的戰爭領袖(事實上他從沒有真正領導過他的人民),不能算是上帝的拿細耳人(我們得承認,他極其好色貪淫),也不僅僅是一台殺人機器。在我看來,除了以上這些之外,這是一個人的故事:他一生都在不停地努力適應著強加於他的宿命,但從來就沒有成功,而且直到最後似乎都沒能理解自己的命運。這是一個孩子的故事:他生來就被父母當作外人。這是一個強健男人的故事:他無時無刻不在渴望得到父母的愛——不僅如此,還有所有的愛,可他從來就沒得到過。
誠然,《聖經》中並沒有多少故事能像參孫的故事包含這樣多的戲劇和刺激的行為,情節如焰火表演一般,高潮迭起:與獅子的搏鬥;三百隻燃燒著的狐狸;和他睡覺的女人們;他愛上的唯一女子;還有生命中這些女人(從他母親到大利拉)對他的背叛;最後是他推倒三千非利士人聚會的大殿,與他們同歸於盡。但這暴力的、衝動的轟然巨響向我們展現了生活的一個章節:一個靈魂受苦、孤獨和躁動的歷程。世上沒有一個地方是這個靈魂真正的家園,即便它的肉體,也好似被重重限制的流放之地。對我來說,這個發現、這個身分認定,便是神話存在的地方。這個神話連同其中高大的形象和它所闡述的,還有那些超凡脫俗的事蹟,突然滲透進了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滲透進了我們最私密的時刻和深藏心底的祕密之中。
大衛.格羅斯曼
二○○五年三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