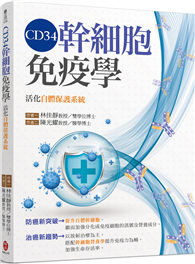第五章第二節 【「原意的」還是「更好的」、「不同的」理解?―朱熹、戴震孟子學之評議】
中國經解的歷史傳統參照西方詮釋學系統,透過中西對話的拓展交流,釐清解經傳統中「名實之辨」、「言意之辨」、「義理與考據之辨」的詮釋論題。中國經典悠久歷史,自先秦孔子「述而不作」編纂六經以來,歷代經解家踵武前修至清末,詮釋系譜始終附在經學的發展上,這代有解人的經註傳統,承續著「述而不作」的一貫宗旨,於是闡發義理成為經註發展的主流。「經典註疏」與「哲學建構」相互為體,解經中創新思想,朱熹與戴震即是此典型的思想家代表之一。 朱熹、戴震分別以「集註」、「疏證」方式追隨孔孟,企慕聖賢經典以聞道,探尋孟子「作者原意」與《孟子》視域融合的可能,召喚經典中的言外意蘊。所以,環諸二家研究的文獻所見,皆不離藉助講學、問答、書信、辯難等方式,對「經典註疏」進行義理的「哲學建構」。這特點呈顯中國經典的註疏傳統,「述而不作」與「寓作於述」的解釋體系是相合,因此詮釋者總在「述」中之「作」而逼近作者原意,詮釋並非作者「原意理解」的完全再現,而是融鑄詮釋者自得義理創造「更好理解」或「不同理解」。因此,在中國經典註疏傳統上,思想家圍繞「經典」展開經註,作為自身「哲學建構」背後的權威依據,所以經學家也多是哲學家,這則是中國哲學不同西方哲學的重要特點,而朱熹、戴震「經學與哲學」綰合治孟,亦是依循此解經的方式開啟繼承儒學道統之大業。就孟學詮釋史立場而言,朱熹與戴震的孟學詮釋使命,分別立足在不同的歷史時代氛圍,面對佛老思想挑戰、夷夏文化衝擊、異端之說混淆、聖人之道不傳的社會,感懷憂國從而進行文本的經註事業,力辨廓清「返歸孔孟」,這詮釋的開創性亦也成為一個歷史性的意義存在。因為,作為「詮釋者」的朱熹、戴震以歷史視域解讀《孟子》,自然探尋與《孟子》經典所寄寓的意蘊,借鑑經典「原意理解」出發,注入了自身「前理解」時代下更關注的期待視域。這期待視域始終環繞著當時的歷史氛圍、時代課題,依其不同的關懷解讀《孟子》經典,「述而不作」經解活動,「以意逆志」創造了朱熹、戴震「詮釋者」與孟子作者「原意」的視域融合。這說明了「詮釋者」以預取問題意識帶入詮釋立場,追問聖賢經典的當代意義,將聖賢之道詮解屬於己意的「言外之意」,同時這解釋也意謂著《孟子》等聖賢經典,始終以開放視域為立足點,召喚著歷代詮釋者以不同視野進入經典脈絡,聆聽「問題視域」展開經典意義的探索之旅。此意誠如哲學詮釋學「伽達默爾」所言:
任何時代都必須以自己的方式來理解歷史流傳下來的文本,因為這個文本是屬於整個傳統的,而每一時代則對整個傳統的內容具有興趣,並試圖在這傳統中理解自身。對於一位解釋者來說,一個文本的真實意義並不依賴於作者及其最初的讀者所體現的偶然性。 對傳世之文本的理解(understanding)與對它的解釋(interpretation)之間有一種內在的本質聯繫。如果說這種解釋總是一種相對的、不完全的運動,那麼理解就在這解釋中得到一種相對的完成。 從這個意義而言,文本是屬於整個傳統,對於文本真實意義的探索並不依賴作者及其最初讀者所體現的偶然性,更進一步地說,對於經典的「理解」就在歷代經解者的「解釋」中得到一種相對的完成。很顯然地,「伽達默爾」所主張哲學詮釋學立場,消解了作者在文本理解上特定的權威性,因此文本沒有唯一定見,當有不同理解的可能,其原因在於各種不同解釋往往皆有其文本相對的合理性。所以持此意來看,儒家經解註疏傳統,正是透過歷代經解的「解釋」對話始能被後人所理解,得以無限獲得嶄新「不同理解」以豐富經典意涵。所以,經典文本意義從「詮釋者」與「經典」的內在聯繫中抉擇,因而「詮釋者」必然帶著「前理解」的「歷史視域」解讀經典。因此,經典語境亦在歷史照鑑的長河中作出回應當代意涵的揭示,這同時也意謂著做為「詮釋者」的朱熹、戴震或《孟子》經典,都置身於「歷史脈絡」中,相互融合滲透對話獲得自身意義的完成。這說明了文本永遠是開放性的,既然文本的解釋沒有唯一的定見,鑑於此亦當不能僅視朱熹、戴震孟學詮釋純然是一種文本的傳意活動,而應正視朱熹《孟子集註》、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的意義實非是對孟子「原意理解」的再現,而是融注己意「寓作於述」的創造闡釋。這闡釋的活動,著眼從當代「歷史視域」出發,分別面對不同時代的挑戰下,如何回應轉化便是二家詮釋目的的著意之處,因此立基在文化命脈的傳承「道統」上,尊奉儒家聖賢經典,借鑑歷史「述而不作」而「寓作於述」,抉發《孟子》創造「意以載道」的時代意蘊。所以朱熹《四書集註》闡發理學思想,創造了中國政統合膺六百多年的主導思想;戴震《孟子字義疏證》「求遂其欲而天下治」、「達情遂欲」聖人之治的呼籲,啟後孟學新義接軌邁向近現代,二家孟學皆清楚獲證中國經註傳統的詮釋特色,綰合經學為治的創造義理,透過治孟展現經世致用鴻志,始終不變是孟學詮釋的精神核心。 所以,從朱熹到戴震孟學發展的變革興衰來看,朱熹回應佛老挑戰,集註儒家《四書》繼承道統並發揚儒家文化;而後,戴震孟學詮釋可謂是對朱熹理學官衙化的一種反動。依循此脈絡的發展軌跡窺見二家延續的共通點,皆是扣緊儒家《孟子》經典,藉著文本的經註活動,挑戰「歷史視域」突破時代舊有格局。因此,朱熹、戴震治經「寓作於述」進入《孟子》經典而展開,「以意逆志」接契聖賢之心,重建孟子「原意理解」經典中所潛隱未發的蘊涵,通經致用尋求經典「言外之意」的義理期待,詮釋轉化再創孟學新局。對照西方詮釋學的參照系統來看,當今西方詮釋學對於文本意義的爭議點,分述由意義確定性「獨斷詮釋學」(die zetetische Hermeneutik)與不確定性「探究型詮釋學」(die dogmatische Hermeneutik)間交錯中前進往復。簡明來看,以「施萊爾馬赫」代表的「獨斷的詮釋學」主張作品意義只是「作者的意圖」,解釋作品意義只是發現「作者原意」。施萊爾馬赫強調這做為理解和解釋的方法,是重構複製作者意圖,而理解本質是不斷趨近作者原意的「更好理解」(besserverstehen)。16而相對地,以「伽達默爾」所代表「探究型詮釋學」則主張作品真正意義並不存在作品本身之中,而存在它不斷地再現與解釋中。換言之,經典作品意義永遠敞開,始終具有一種不斷向未來理解的開放性,而做為理解和解釋方法是過去與現在中介,是作者視域與解釋者視域融合,因此理解本質是「不同理解」(Adverserverstehen),不只是複製行為更是一種創造性的行為。17所以,分判當今西方詮釋學所爭議點,置在理解者與作品之間圍繞著「更好理解」、「不同理解」或逼近作者「原意理解」的討論,因此展開不同辯證的理解立場。 那麼,在西方詮釋學的觀點參照下,朱熹/戴震「道統」傳承,所詮釋「返歸孟子」與孟子原意貼切與否?獲致孟學理解是「原意理解」?亦「更好理解」?或「不同理解」?即就孟子「原意理解」對比討論如上,朱熹/戴震孟學之評議得以獲得皆是「不同理解」。經典存在唯一不變的本意來自「作者原意」,因此尋求經典作者「原意理解」是歷代經註家對於經解上一元性的主張。但在這前提下應注意的是,任何解釋都只不過是對經典文本「原意理解」的一種復歸,經典做為一個自明性的歷史存在,它的理解視域始終是開放性,因此經典意涵並不侷限於一家之解,所以歷代註疏家對經典意涵所延伸「不同理解」自是必然。更明確地說,中國經典註疏傳統的形成,就其形式為了解釋「經典原意」與「作者原意」,然實質上則是歷代經註家通過經典權威的理解視域,「寓作於述」提供一套回應當代社會倫理秩序的規範之道。這表明了,中國經典註疏的傳統對解經者、詮釋者具有一種強烈憂世憂民的「實踐」傾向,這傾向相繫作者原意「解釋」與「詮釋」解經者的創造,建立在「理解」、「解釋」與「應用」的結合基礎上。 因此,朱熹/戴震孟學詮釋,雖皆依循儒家經註傳統傳承孔子「述而不作」以解孟,然「以意逆志」以不同關懷點所預取的「前理解」進入經典脈絡,「寓作於述」闡發「不同理解」孟學意涵。這說明了朱熹/戴震召喚《孟子》經典至自身的實踐應用,不僅重構孟學更著意是詮釋實踐的活動,開顯了《孟子》經典與當代歷史視域的融合,此「理解」、「解釋」、「應用」的實踐與伽達默爾「哲學詮釋學」的主張亦有不謀而合之意趣: 在伽達默爾看來,語言展開了世界和自我的先行關係,並使兩者相互和諧。世界不再是事物的存在,而是特定的「在世存在」的境遇,我們可以經由語言的理解而參與世界的過程。至此,詮釋學就具有了事件性質或事件特徵(Geschehenscharakter),意義的理解乃是一種參與事件。按照伽達默爾的看法,詮釋學最終應當作為一種實踐哲學。 職是來看,朱熹/戴震孟學實踐乃是直指當時生活世界「在於此世」(Being-in-the-word)的經世致用,詮釋精神所關注的是歷史課題下面對文化抉擇的問題,佛老挑戰、夷夏之辨,因而展開文化話權上「正統」之爭的經典實踐。因此,朱熹/戴震立足在自身的情境出發,循藉通經致用,參與《孟子》意識視域的融合,分別詮解《孟子》在宋/清二代「不同理解」(Adverserverstehen)的「實踐哲學」。此所彰顯的詮釋精神,不僅效法孟子「闢楊墨」,亦也是反映對人倫現實社會的關懷,深表知識分子對社會憂切的苦心。雖然,二家孟學呈顯出「不同理解」,然相同之處,其詮釋所向皆蘊涵著豐富的實踐性,通過西方詮釋學的對話參照下,可謂也是「哲學詮釋學」的表現,雖以「原意理解」做為詮釋目標,然「寓作於述」已不再是複製孟子「原意理解」,而是創造「不同理解」。持平地論,二家詮釋解讀之差異並無所謂優劣之分,而是彰顯不同於宋/清時代脈絡下,開啟《孟子》經典的當前適用性,以「集註」、「疏證」的經解方法,召喚《孟子》經典至前與時代視域融合,揭櫫《孟子》在不同歷史時代下「不同理解」的孟學蘊涵,此才是二家孟學獨特的歷史意義。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朱熹與戴震孟子學之比較研究:以西方詮釋學所展開的反思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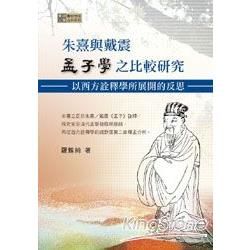 |
朱熹與戴震孟子學之比較研究:以西方詮釋學所展開的反思 出版社:羅雅純 出版日期:2012-06-0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32頁 / 16*23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01 |
中國/東方哲學 |
$ 378 |
中文書 |
$ 378 |
中國哲學 |
$ 387 |
社會人文 |
$ 387 |
哲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朱熹與戴震孟子學之比較研究:以西方詮釋學所展開的反思
朱熹與戴震孟子學之比較研究--以西方詮釋學所展開的反思
本書從思想史脈絡的溯源,立足在孟學發展史上之歷史關鍵點,以宋/清孟學發展轉折切入,以朱熹/戴震做為研究對象,探究二家思想的關聯性,並從西方詮釋學的新視野研究兩家詮釋殊異之因;透過朱熹與戴震二位理學大家,釐清由宋至清的孟學系譜,勾勒出孟學何以能從宋明理學「向內體證理路」轉而趨向清代義理「向外道德實踐」的不同蘊趣。
作者簡介:
羅雅純,淡江大學文學博士畢業,現任實踐大學博雅學部專任助理教授,曾任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淡江大學、銘傳大學兼任助理教授、華視新每日一字編寫教授等職。
章節試閱
第五章第二節 【「原意的」還是「更好的」、「不同的」理解?―朱熹、戴震孟子學之評議】
中國經解的歷史傳統參照西方詮釋學系統,透過中西對話的拓展交流,釐清解經傳統中「名實之辨」、「言意之辨」、「義理與考據之辨」的詮釋論題。中國經典悠久歷史,自先秦孔子「述而不作」編纂六經以來,歷代經解家踵武前修至清末,詮釋系譜始終附在經學的發展上,這代有解人的經註傳統,承續著「述而不作」的一貫宗旨,於是闡發義理成為經註發展的主流。「經典註疏」與「哲學建構」相互為體,解經中創新思想,朱熹與戴震即是此典型的思想家代...
中國經解的歷史傳統參照西方詮釋學系統,透過中西對話的拓展交流,釐清解經傳統中「名實之辨」、「言意之辨」、「義理與考據之辨」的詮釋論題。中國經典悠久歷史,自先秦孔子「述而不作」編纂六經以來,歷代經解家踵武前修至清末,詮釋系譜始終附在經學的發展上,這代有解人的經註傳統,承續著「述而不作」的一貫宗旨,於是闡發義理成為經註發展的主流。「經典註疏」與「哲學建構」相互為體,解經中創新思想,朱熹與戴震即是此典型的思想家代...
»看全部
目錄
出版心語自序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孟子學發展史綜論
第二節 問題意識提出
第三節 研究進路與論述方式
第二章 研究成果之省察與方法學的調適上遂
第一節 研究成果之考察
第二節 西方詮釋學與中國經典詮釋學
第三章 朱熹《孟子》詮釋之理解
第一節 朱熹註孟釋經之革故鼎新
第二節 朱熹孟子學之詮釋
第四章 戴震《孟子》詮釋之理解
第一節 明清之際註孟背景之典範轉移
第二節 戴震訓詁釋孟之新典範建立
第三節 戴震孟子學之詮釋
第五章 朱熹、戴震釋孟歷史地位之評騭
第一節 朱熹、...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孟子學發展史綜論
第二節 問題意識提出
第三節 研究進路與論述方式
第二章 研究成果之省察與方法學的調適上遂
第一節 研究成果之考察
第二節 西方詮釋學與中國經典詮釋學
第三章 朱熹《孟子》詮釋之理解
第一節 朱熹註孟釋經之革故鼎新
第二節 朱熹孟子學之詮釋
第四章 戴震《孟子》詮釋之理解
第一節 明清之際註孟背景之典範轉移
第二節 戴震訓詁釋孟之新典範建立
第三節 戴震孟子學之詮釋
第五章 朱熹、戴震釋孟歷史地位之評騭
第一節 朱熹、...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羅雅純
- 出版社: 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2012-06-01 ISBN/ISSN:978986221814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哲學宗教> 中國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