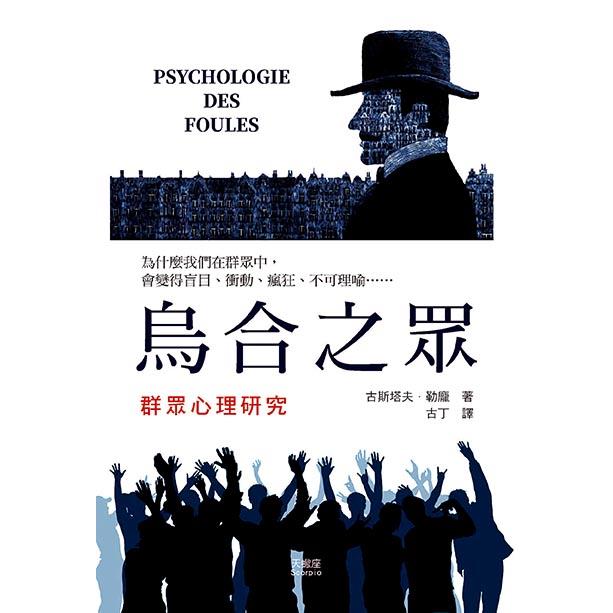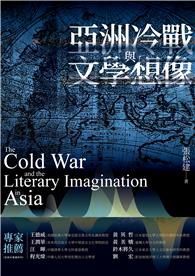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烏合之眾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84 |
心理學入門 |
$ 317 |
中文書 |
$ 317 |
心理學理論 |
$ 324 |
社會人文 |
$ 324 |
心理學理論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烏合之眾
內容簡介
《烏合之眾》是解析群體心理的經典名著,本書顛覆了人們通常對群體的認識,將群體的特點剖析得淋漓盡致,讓人先是驚訝,後是佩服,作者層層分析,逐步推進,明確指出個人一旦融入群體,他的個性便會被湮沒,群體的思想便會佔據絕對的統冶地位,而與此同時,群體的行為也會表現出排斥異議,特別化、情緒化、低智商化等特點,進而對社會產生破壞性的影響。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1841.5.7~1931.12.13)
法國社會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群體心理學創始人、物理學家,以其對於群體心理的研究而聞名,1895年出版《烏合之眾》(Psychologie des foules),認為在群體之中,個體的人性就會湮沒,獨立的思考能力也會喪失,群體的精神會取代個體的精神,該作品被認為是群眾心理學領域的開創性作品。
目錄
名家讚賞與推薦
關於本書
作者簡介
論「烏合之眾」
作者前言
導言:群體的時代
第一卷 群體的心理
第一章 群體的普遍特徵與群體思維的心理法則
第二章 群體的感情和道德觀
一、群體的衝動、易變、易怒和急躁
二、群體的易受暗示和輕信
三、群體情緒的誇張與單純
四、群體的偏執、專橫和保守
五、群體的道德
第三章 群體的觀念、推理與想像力
一、群體的觀念
二、群體的理性
三、群體的想像力
第四章 群體信信所採取的宗教形式
第二卷 群體的意見與信念
第一章 群體的意見和信念中的間接因素
一、種族
二、傳統
三、時間
四、政治和社會制度
五、教育
第二章 群體意見的直接因素
一、形象、詞語和套話
二、幻覺
三、經驗
四、理性
第三章 群體領袖及其說服的手法
一、群體的領袖
二、領袖的動員手段:斷言、重複和傳染
三、名望
第四章 群體的信念和意見的變化範圍
一、牢固的信念
二、群體意見的多變
第三卷 不同群體的分類與描述
第一章 群體的分類
一、異質性群體
二、同質性群體
第二章 被稱為犯罪群體的群體
第三章 刑事案件的陪審團
第四章 選民群體
第五章 議會
〔附錄一〕烏合之眾:人一到群體中,智商就嚴重降低
〔附錄二〕古斯塔夫‧勒龐語錄
〔結語〕請保持獨立思考
關於本書
作者簡介
論「烏合之眾」
作者前言
導言:群體的時代
第一卷 群體的心理
第一章 群體的普遍特徵與群體思維的心理法則
第二章 群體的感情和道德觀
一、群體的衝動、易變、易怒和急躁
二、群體的易受暗示和輕信
三、群體情緒的誇張與單純
四、群體的偏執、專橫和保守
五、群體的道德
第三章 群體的觀念、推理與想像力
一、群體的觀念
二、群體的理性
三、群體的想像力
第四章 群體信信所採取的宗教形式
第二卷 群體的意見與信念
第一章 群體的意見和信念中的間接因素
一、種族
二、傳統
三、時間
四、政治和社會制度
五、教育
第二章 群體意見的直接因素
一、形象、詞語和套話
二、幻覺
三、經驗
四、理性
第三章 群體領袖及其說服的手法
一、群體的領袖
二、領袖的動員手段:斷言、重複和傳染
三、名望
第四章 群體的信念和意見的變化範圍
一、牢固的信念
二、群體意見的多變
第三卷 不同群體的分類與描述
第一章 群體的分類
一、異質性群體
二、同質性群體
第二章 被稱為犯罪群體的群體
第三章 刑事案件的陪審團
第四章 選民群體
第五章 議會
〔附錄一〕烏合之眾:人一到群體中,智商就嚴重降低
〔附錄二〕古斯塔夫‧勒龐語錄
〔結語〕請保持獨立思考
烏合之眾 相關搜尋
我不是LOSER! 青年人的敘事心療發展心理學: 青少年到老年時期的發展 第二冊 (2025年)
榮格與現象學
罪惡鑑定人: 資深測謊專家與14名殺人犯的心理對決, 識破連續殺人、分屍凶案、滅門謀殺的暗黑真相
童話裡的心理學
佛教與心理治療藝術 (全新增訂版)
發展心理學: 兒童發展 第一冊 (2025年)
血色鏡頭, 新加坡真實罪案調查全紀錄: 雙槍胡金枝×白臉阿協×殺警槍匪莫達×千面林萬霖……從懸疑案件到法庭審判, 深入解析犯罪心理與社會影響
這不是隨機的惡意, 目標型殺手接近中: 性慾倒錯x種族對立x價值感低落x性暴力謬論, 想要建立完美的社會, 卻差點毀掉整個產業!
完全支配, 渴望成為神一般的殺手: 敵意歸因偏誤x被同齡人排擠x期待獲得關注, 曾經的受害者如何變成殺人不眨眼的惡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