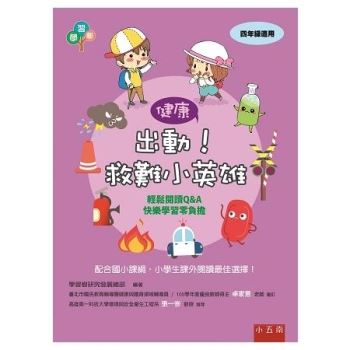推薦序
再見,拚搏
林懷民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台北社教館「慾望城國」的首演,是我一輩子中極少數難忘的劇場演出。
從幕啟時森林迷路驚悚策馬,到終場的萬箭穿心高臺吊毛,都緊扣人心,讓人在興奮中節節擊掌。
「慾望城國」的首演,匯聚了七○年代後半期以來,劇場界陸續累積的能量和京劇新生代力圖求變的渴望。林璟如、登琨豔都不顧身家地義務投入設計的工作,年輕的京劇演員也激情燃燒。原本一邊四個,木然呆立的龍套,到了「慾望城國」的舞台上,各個渾身解數,肢體有了表情,進退間也有了細節。「慾望城國」的首演夜,舞台上好像冒著煙,台下的觀眾也熱血沸騰。
看完「當代傳奇劇場」這齣氣魄磅礡,有如西方歌劇的現代京劇演出之後,對興國與秀偉的成功,我歡欣興奮。興奮過後,卻充滿了焦慮。走出「慾望城國」之後,這股氣勢如何延燒,興國如何再推出一樣轟動的好戲,我憂心忡忡。因為興國是有才分、肯拚命的劇場藝術家,台灣的環境卻不會因為個人熱情而改變。
興國離開雲門之後,一直想嘗試突破京劇的程式,走出京劇的保守世界。我建議他從小做起,從唱腔的創新著手,邀請音樂家和京劇樂手,加上兩三個演員,定期研討創新,從新唱腔來發展劇本,從小戲發展為大戲。結果,他嘔心瀝血地熬出「慾望城國」。
我會有這樣的想法,是來自自己的慘痛經驗。
一九七八年,雲門六歲,拚出了九十分鐘的「薪傳」。一九七九年,再接再厲推出大佈景的「廖添丁」,上台的舞者就有三、四十人。然後,無以為繼。做了大戲很難再回來做小品。八○年代初期,我徬徨失落,不知道要做什麼。資源與人才,都無法支持我們浩浩蕩蕩地不斷推出「鉅作」,連保存「廖添丁」到最後都變成不可能的事。這齣「大戲」給我的教訓是:在台灣這個環境工作,不能因為熱情奇想就一頭撞上去,要務實才能累積。
雲門雖小,至少還是一個擁有一、二十人,天天工作的團隊。京劇,文武場至少要九個人。興國沒有班底。
果然,「當代」的第二齣戲「王子復仇記」要等待四年。「當代傳奇」始終沒有成為一個可以長期工作的團隊,每次演出,都得費盡心思跟公家京劇團借人。製作龐大,人才的邀集、大佈景、大量的服裝、資金的籌募、票房的經營,一一蠶食著興國和秀偉的精力,往往必須在短暫的幾個月裡,在高壓下,一心數用。有時也聽到興國在首演前,幾近崩潰的消息,但幕啟時,他仍然要粉墨登場,全力拚搏。又有一陣子,為了支持劇團的生存,他到香港拍電影。在風華最盛的歲月,興國必須忍受這樣的煎熬和蹉跎,心裡很是難過。因為個人的「心病」,每次得知「當代傳奇」推出大戲,一九八六年走出社教館後的焦慮,都要跳出來重新籠罩著我。
由大而小難。九○年代推出的「無限江山」、「樓蘭女」、「奧瑞斯提亞」、「暴風雨」都是大戲,都沒有超越「慾望城國」的境界。海外邀演也一再重演「慾望城國」。
台灣的故事是愛拼才會贏,先做了再說。八○年代,因為一些今天已經故世的官員,看到歐美堂皇的歌劇院,就決定我們也要蓋一個,於是我們有了兩廳院。明年就要二十歲的兩廳院,在制度和經營上仍然還未穩定下來。
如同建造國家戲劇院的官員對歐美大歌劇院的嚮往,劇場界大製作蔚然成風。為了票房,聘用沒有舞台經驗、沒有劇場專業訓練,很難挪出時間參加排練的影歌星參與演出;可以再度推出,一演再演的好作品的,有如鳳毛麟角。
七○年代以降,熱情、衝動上路的劇場界,到了二十一世紀仍在拚博,苦撐。一個團隊到了第十季,有時仍和首季一樣的忙亂匆促,首演常是彩排。出發的時候,大家都有一個做好戲,追求藝術的夢想。但是用大製作增加能見度拼票房的後果卻是:永遠都在等待可以去做內心最想做的那齣作品的契機。也有人發了狠,毅然轉調,推出嚴肅的劇作,結果票房失利,嚴重虧損。因為觀眾的口味已經被餵養得十分辛辣,靜不下心來欣賞。
也許是想通了,二○○一年,興國推出「李爾在此」的獨角戲。去年,又編導規模較小,以演員取勝的「等待果陀」,連獲好評。我心裡很是高興。小戲,人少,成本低,雜務相對減少,可以專心琢磨,一再修改。因為輕便,花費較低,國內外巡演機會大增。在這個過程裡,編、導、演員和團隊一起成長茁壯。
興國秀偉基於對藝術的愛,用意志力撐持「當代」二十年,我衷心敬佩,也心疼不己。 因為那個艱苦的歷程,我,或者我們都曾走過。
拚搏的必要,是環境所逼,也可能是我們自己的選擇。
天下文化出版盧健英小姐撰寫的《絕境萌芽──吳興國的當代傳奇》,很清楚的記述了興國從小到大拚搏的故事,尤其是「當代」的二十年。
二十週年慶可以是由小而大的開始。過去的大製作依然在箱子裡,沒有消失。我希望週密務實的策劃,穩紮穩打,由小茁長的累積,「當代傳奇」到了三十歲的時候,在人員、經費上,體力上,都實力飽滿地重演舊戲、推出更上層樓的新作。
傳主序
我演悲劇人物 吳興國
憂傷的童年養成我對世事無常和向命運抗衡的憤怒。一歲失去父親,三歲被送孤兒院,十二歲進復興劇校,二十四歲時,獨立撫養我與哥哥的母親因病過世,臨走時,連最心愛的兒子最後一面也沒盼到。從小到大,都是握著拳頭,噙著淚水,克服一次又一次生命的難關,再加上,自演戲以來,都是扮悲劇角色居多,墜入這些受苦的靈魂世界中,令我難以樂觀面對現實人生。
這些人物走入我的生命中,他們得到在歷史重活一遍的機會,而我,卻得為他們死過一回又一回。小時候,學校給了我「吳興秋」的藝名,當時,演的是年少俊美的武生,例如:白水灘的十一郎,兩將軍中馬超,水滸傳中的林沖、石秀、武松都是見義勇為的英雄。有一回,學校演「荷珠配」,意外派我來個三路老生,為了學得像老人,我在後台面對穿衣鏡不斷練習,當時有位老師,很好奇看著我,問:「小朋友,你叫什麼名字?唱老生的?」我馬上立正回答:「我叫吳興秋,唱武生的。」老師笑著說:「吳興秋,像女生名字,我給你換個名,就叫吳興國吧!」沒幾天,學校就通知我改名。後來,才知道給我藝名的,竟然是台灣四大老生之一,鼎鼎有名的李金棠老師。這一切,都是無形的因緣,這個名也漸賦予我更多的使命和責任。
文化是文明和愚昧的集結,歷史是功績與罪惡的混合,每一個世代都有代言者,愈是險惡的時勢,愈需要吞噬悲劇人物作為祭品,這些被選中獻祭者,大多是性格所造成的,而為何偏偏每一次,我都相信自己就是那個被選中的人,那麼多「忠孝節義」的思想,植入我的腦袋,隨著我由武生轉為老生,化身成為諫昏君投汨羅江的屈原,遭萬剮凌遲的袁崇煥,被十二道金牌入罪的岳飛,帶箭戰死沙場的黃忠,烏江自刎的楚霸王……個個都身繫邦國興亡。
超越政治之上的,是人間的情。在我演過悲劇人物中,除了在政治的浪頭上翻滾,也有些令人動容的有情人,比方『四郎探母』中,為求見親娘一面,甘冒殺頭之罪,連夜奔向敵營的楊四郎,還有「打棍出箱」一出場就放聲悲哭的窮儒范仲禹,遭遇妻兒被佔的不幸,導致神經錯亂,因恐懼到極點反而嬉笑起來。最愛的是「無限江山」中文采粲然的李後主,他的一生淒迷浪漫。「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前一刻,縱舞在豪麗迷醉的狂歡中,下一刻卻見他肉袒出降,垂頸流淚的窘狀,苦難本身就是熱情,悲劇予人同體大悲的胸懷。
我愛莎士比亞,更愛抓昆蟲。做如此比喻並非有不敬之意,我在當代傳奇創作了四齣莎翁劇本,其中三齣「慾望成國」(Macbeth)、「王子復仇記」(Hamlet)、「李爾在此」(King Lear)的主角都被命運逼到盡頭,唯有『暴風雨』(The Tempest)中的魔法師終於大徹大悟,寬恕了別人,同時也饒了自己,才把悲劇轉為喜劇,讓紛爭的孤島,變成美麗新世界。
有人問我:「在舞台上奮鬥了四十年,難道不覺疲憊?」其實,一九九八年的暫停兩年,給我注入了更充沛的能量,每一次走出舞台,卸了濃妝,脫了戰甲,回到家,我總能從妻子兒女身上得到愛和勇氣,只要讓我到海邊撿貝殼,到森林抓昆蟲,就可以讓我感到平靜、快樂、與世無爭。
這是第一本有關於我學戲和成長的書,謹向趨勢科技陳怡蓁小姐及天下文化出版社致謝,在當代傳奇劇場二十年生日這一天,記錄了一個在台灣唱京劇的演員的生涯軌跡,也感謝好友健英傾力振筆疾書和張治倫工作室團隊長期給予美編協助,也以此書與所有栽培過我的老師、朋友和一起工作的夥伴一同分享。
作者序
擁護時代裡的藝術家 盧健英
七月,和吳興國密集進行訪談的時候,章詒和的《伶人往事》剛出版,書中談到言慧珠時有一段對話:
「我們這個時代,根本就不配產生言慧珠!」
對方驚問:「那配產生什麼?」
「什麼都不配產生,一個無足輕重的過渡時期。」
《伶人往事》紀述大陸名伶在風火時代裡的悲歡之歌,閱讀的過程經常心驚動魄,掩卷嘆息,隨著書中的黑白照片遙想當年風華。然後再見到吳興國時,總是跟他大叫:「吳興國,你真是生對了地方,生對了時代。」
生對了地方,生對了時代,一位藝術家才得以展其才華,將其對人生的理解透過舞台表達,而更重要的是,他的藝術上的表達,是集結了時代的同伙人所共同完成,然後鋒芒盡露。這過程裡,必須必備「逆」與「敢」兩種精神,否則最好的年代,也會成了最壞的年代。反之,最壞的年代也可能成為最好的年代。
於是,為什麼那個年代會出現吳興國與《慾望城國》?成了我想在書中爬梳理解的主要問題。
台灣不是京劇的原生地,來台的伶人中,真正具有開創性的藝術大師不多,但卻是一批傳承了戲校傳統坐科精神─規矩方正,一板一眼,堅信苦中方能成藝的老師們,他們年少時看過典範,卻還來不及茁壯去創造典範,烽火便將他們驅趕來台。他們帶來傳統,也帶來傳說,所有關於京劇的風華絕代都像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和這個時代,這塊土地沒有關聯。
吳興國的人生,本來只是為了生存而走進傳統舞台,但後來卻是為了傳統的生存而走出戲曲舞台,裡面的過程充滿了他的「逆」與「敢」,他的得天獨厚與他的憤世嫉俗,讓他正好腳跨在兩個時代的斷裂中,在師友鼓勵及同儕齊心下,激盪出像《慾望城國》這樣的時代大戲。
前期的時候,他對環境的悲憤大於野心,後期的時候,他對環境的謙卑大於期待,葉錦添有一回說到他:「越苦他就越過癮。」好像沒有拿石頭砸自己的腳,就會忘記痛是什麼感覺,他常以悲劇自況人生,這讓我想起出自英國公爵威靈頓的一句至理名言:「勝利是除了失敗之外的最大的悲劇。」這句話給吳興國,他當也會接受吧。
在他身上獨獨缺了一般伶人會有的機靈世故,剔透婉轉,挫折的機會就比別人多。直到這幾年,他才似乎漸漸放下參孫肩上的巨石,做想做的事,能做的事。
因為「與時俱進」是任何一個時代裡,藝術家都要有的「天問」,但「傳承」就要不斷香,成熟的藝術家把自己維持在最好的狀態,也是一種社會責任。
書竟之日,已吹起蕭蕭秋風,台灣籠罩在紅綠的紛雜聲中。我們或許在一個價值混亂的時代,但擁護這樣的藝術家與其相隨而生的作品,至少可以讓我們有一天回頭檢視時,欣然發現自己不是在一個無足輕重的時代。
二○○六年九月



![念君歡卷四] 念君歡卷四]](https://cdn.kingstone.com.tw/book/images/product/20185/2018561884609/2018561884609m.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