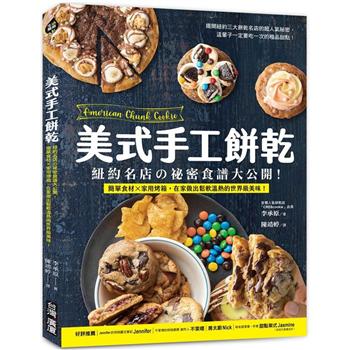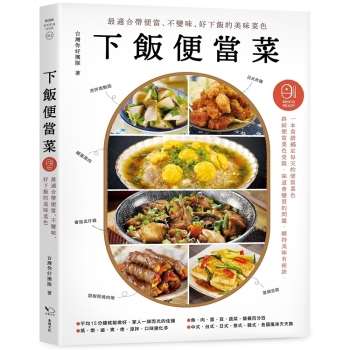學界尊稱為「武林百曉生」的林保淳,是國內鑽研武俠小說研究的專家。他以一顆俠心闖蕩江湖,也以深厚的情感與知識,寫下時代與人情的故事。
作者召喚久遠的記憶,栩栩重現兒時的點點滴滴:眼看〈父親的藥鋪〉興衰起落,爬牆偷窺〈茶室幾番風與月〉,隨著「尪仔標」飛馳在諸葛四郎的漫畫世界,重溫「抽抽樂」的童趣。妙趣橫生的〈從孫子到爺爺〉,戲謔地點出作者名字上的演變,而小兒麻痺症導致的身體缺陷,更被他自嘲地用來譜一段〈乞丐狂想曲〉。從竹中〈留級生〉到就讀〈夢幻台大〉,大學室友的「倚天」舊事,老文青的「神州」憶往,都令人不禁回憶起青春的美麗與哀愁。
昏黃燈下,故紙堆中,武俠情裡,充滿爬梳經典的劍氣書香,而夜半時分,身為學者已久的林保淳,想起年少的困頓、初戀的情愫,故人往事歷歷在目,終於執筆一圓往日的作家夢。他是潯陽江頭船上的琵琶,奏起如歌的行板,鏗鏘有力地為如煙舊夢留下美好的印記。他妙語如珠的筆有如刀劍,酣暢淋漓地舞著生命裡的歡笑與哀傷,展現行走人世的江湖智慧。
本書特色
★收錄武俠小說專家林保淳幽默自嘲的人生書寫,溫情易讀的懷舊散文。
名人推薦
蔡詩萍、李宗舜、蕭蕭專文推薦
須文蔚、石曉楓、徐國能誠摯推薦
新竹中學校友會何昇平鄭重推薦
讀保淳學長更為細膩的回憶,我的確又重新回到了往昔,穿著制服,戴著大盤帽,背著沉沉書包,滿臉青春卻不無苦悶的歲月。 ——蔡詩萍(作家)
俠,大節不移易,細節不疏略,《夜深忽夢少年事》即使在撲滿、漫畫、尪仔標、抽抽樂的細節上,也不輕忽,是記憶的刻度深,還是真情的專注度強?或許兩者都是吧!《夜深忽夢少年事》是少年林保淳的個人回憶錄,卻也是台灣二十世紀中期的歷史縮影,台灣俠義之心的自然顯現!基於此,我們期待稍晚的中壯年林保淳,再現江湖,寶劍在鞘外振振有聲。——蕭蕭(作家)
從研討會中仰望武俠小說權威的林保淳教授,到師大研究室走廊偶遇的幽默同事,從 《夜深忽夢少年事》走出的是一個詩意的風城孩子,讓人心疼又欣賞。你會看作者鍾情於寫詩與閱讀,一心投入文學研究的動人歷程,既勵志又抒情,笑中帶淚,讓人相信:原來走一條寂寞的人文路,還能滿滿的正能量,真好!這本書絕對是中學生寒、暑假最佳的選書,更期待本書能拍成影視劇,鼓舞更多台灣孩子能更勇敢與更有俠氣!——須文蔚(詩人・台師大文學院副院長)
以平易朗暢的文字風格,娓娓敘述了四號橋邊的童年生活、情竇初開的青澀初戀以及對父母永恆的憶念,日常物事在其筆下俱沾染了回憶的光暈。而青春期的歡樂與哀傷、中文系人的甘苦與自許、師友交遊的典型與追懷、教職之路的辛酸與自豪,也歷歷閃現著歲月的光澤。詩酒俠夢度半生,搦筆盡是風流往事,保淳教授的俠骨柔情,畢現於字裡行間。這是個人史的追懷,也是時代史的映現。——石曉楓(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時代遠去,舊情未了,夜深忽夢少年事,訴說的是個人生命的成長史,但流露的卻是一個時代緩慢安靜的輕愁。青春是多麼徬徨,回憶是如此漫長,夜深忽夢少年事點點滴滴的紀錄值得細讀,那不啻是一個堅毅靈魂勇闖江湖的故事,同時也是一個江湖如何塑造英雄的傳奇。一代劍俠回首年少,布被秋宵夢覺,眼前萬里江山。——徐國能(作家・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在這本夢回少年的故事中,我們可以更深入的了解保淳成長過程中經歷的許多艱辛,他雖身染殘疾,面對無數的逆境、困境,但他都能化為迎接挑戰的動力,保持樂觀進取、奮勉自強的精神,勇往向前,這是最令人讚賞、彌足珍貴的!
新竹中學創校於一九二二年,二○二二年是竹中慶祝百年校慶歡樂喜氣的年分,選上保淳的文章發表於百年校慶的校友會刊,正是因為從他文章故事中看到一個樸實坦率、真誠無偽的校友,將竹中的精神,「誠慧健毅」的校訓,發揚得淋漓盡致,是校友及在校學弟妹們以及社會各界人士的好榜樣啊!——何昇平(新竹中學校友會辦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