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門口那些人見風波平息了,也紛紛坐下喝酒打牌各玩各的。
小酒保將兩杯蜂蜜檸檬水放到老耿和齊北崧面前,兩人都端起來一飲而盡。
齊北崧原本不喝陌生酒吧提供的東西,但他之前焦躁地連開了幾個小時的車,後又心亂如麻地滿凰村找程幾,再加上和老耿吵了一架,嗓子早渴得冒煙,也就顧不上那麼多了。
程幾說:「回家吧。」
老耿不願意,說還要玩。
程幾知道以他的脾性不喝到醉不會走,醉了也無甚大礙,突然發現他情況不對。「爹?」他扶住老耿。
老耿剛才還龍精虎猛,此時就像幾十個小時沒睡覺似的,一頭栽在吧檯上睡著了。
「……」程幾猛然望向小酒保!
小酒保嚇得連退數步。
「你往蜂蜜檸檬水裡加了什麼?」程幾從牙縫裡問。
小酒保見對方實在厲害自己躲不過,便哆嗦著指著垃圾桶,那裡是他剛才扔下去的舊塑膠袋,裡面裝著他朋友給的「好東西」,某種管制類麻醉藥品。
「你瘋了?!」程幾低聲喝道。
小酒保說:「是……是你自己說少加一點就睡覺的!我沒瘋,是彪叔發酒瘋太厲害,弄壞了東西我……我叔叔真的要罵我的呀!」
「加了多少?」程幾問。
「一……一點點,半瓶。」小酒保怯生生用拇指和食指比劃了一下。
「給他也加了?」程幾指著齊北崧。
「嗯……嗯。」
「給我加了什麼?」齊北崧問。
程幾不答,盯著小酒保:「那他怎麼不睡?」
小酒保囁嚅:「我不知道……可能這位帥哥比較年輕?春紅,這東西是你懂,我不懂的呀!」
程幾回手給了他一巴掌!
小酒保被打得跌坐在地,捂著臉大氣不敢出。
「沒有下次。」程幾居高臨下,面沉如水地說,「毛頭,聽到了嗎?」
小酒保忙不迭點頭:「聽到了聽到了,沒有了保證沒有了!春紅你不要告訴我叔叔!我也是為了彪叔好,他一把年紀了真的不能再鬧出事情來了!」
「他尋釁滋事是他的罪。」程幾森然道,「你有你的罪。」他不再多看小酒保一眼,對齊北崧說:「別聲張。幫個忙把我乾爹扶回去。」
齊北崧是多聰明的人,早已聽出老耿是被下藥了,因此不再計較,惡狠狠剜了小酒保一眼,和程幾一左一右架起老耿往酒吧外走去。
經過那群看客時,大家都大笑,說什麼剛才還跳上跳下呢,一眨眼就滾到桌子底下去了,醉鬼就是醉鬼,沒救了!
兩人走出去幾十公尺,齊北崧才說:「那小兔崽子不是好東西,以後不許和他來往!」
「當然,這鬼地方!」程幾吃力地說,「老耿要來我管不住,反正我這輩子不會再踏進那門檻一步!」
老耿的意識還沒有完全喪失,被拉到外面受冷風一激,居然醒了,眼睛雖然閉著,但能手臂搭兩人肩膀上左腳絆右腳地走,嘴裡還咕噥著醉話。程幾見那麻醉藥物作用可控,略微放心了些,問齊北崧:「你怎麼不睡?」
齊北崧也納悶,他現在非但不想睡,甚至還有些興奮。「那小兔崽子是不是給我下了另外一種藥?」他問。
程幾不知道,連小兔崽子自己都不知道,總之齊北崧眼下看來是無礙的。又走了幾十公尺,拐過一道彎後老耿徹底昏睡,話也不說了,腳也不挪了,呼嚕倒是震天動地。老耿比較魁梧,體重在八九十公斤,兩人拖著他難以前行,程幾問道:「你會扛人嗎?」
「怎麼扛?」
「這樣……」程幾便鑽到老耿身下示範。那是特種兵常用的單人扛傷患的方法,簡單來講就是重心向前,讓對方橫趴於肩,腦袋和四肢均掛在下邊那人的胸前。傷患體重全部壓在一人肩上那肯定不好受,但是移動得快。程幾本來想一鼓作氣把老耿扛起來,結果腰還沒挺直就被壓趴下了,不管上輩子還是這輩子,力量一向是他的短板。
齊北崧倒是扛得動,可惜不得要領。他也不計前嫌願意背老耿,可老東西真會享福,趴在他背上一個勁兒往下出溜,非要躺平了才舒服。兩人只好採取了一個最笨的法子──抬。
多虧麵店和酒吧距離不遠,之間只隔著一條小街和一座小石拱橋,否則真要把人腰腿都累折了。他們氣喘吁吁來到麵店門口,把睡得跟死豬一般的老耿抬到門口大床上,程幾摸門鑰匙時整條手臂都在抖。進了門,開燈,實在也不可能也不想再把醉鬼弄上樓了,兩人便把幾張八仙餐桌拼起來給老耿臨時做床,再從樓上房間抱來棉被替他蓋上。忙完這一切,程幾汗流浹背地坐著休息,暗罵小酒保屁事不懂盡添亂。突然他注意到齊北崧的面色紅得不正常,頓時警覺起來:「你怎麼了?」
齊北崧也坐下,搓了搓臉頰說:「我熱……」
「熱?」
「……」齊北崧眼睛轉向他,嗓音沙啞,「……你中過催情藥麼?」
程幾怎麼可能中過催情藥?他呼啦一下站起來,神情比齊北崧本人還要慌亂!「你……你什麼感覺?」
什麼感覺?齊北崧扶著額頭想,血液鼓盪,全身發燙,臉頰發燒,喉嚨裡有血腥味,耳中聽到自己心跳的怦怦巨響,如果不是下腹部一陣陣發緊,燥熱得胸口都要裂開,或許還真和發燒差不多感覺。「小事,幾個小時後藥性就過去了。」齊北崧故作輕鬆,不想讓對方擔心。
他們倆一個面色煞白,一個滿臉通紅,對視數秒,突然程幾一個箭步衝出門外!他飛跑向酒吧,那邊剛剛消停,小酒保正在洗杯子。驟見程幾,小酒保嚇得叫喚一聲,程幾越過吧檯一把揪住他的衣服領子將他拉近,從牙縫裡問:「你給兩杯檸檬水裡加的是同一種東西嗎?」
「是……不是……好像是……」
「到底是不是?!」
「不……不是。」小酒保知道自己理虧,聲音越來越小,「這東西一瓶裡很少,因為彪叔太鬧,我想給他稍微多加些,結果一瓶就沒有了,然後我就……我就又開了一瓶,給帥哥也加了一點點。」
「兩個東西外觀有區別嗎?」
「沒有……有……」小酒保說,「都透明的,帥哥喝的那個好像顏色深……深一些,我以為是沉澱……」
「真該打死你!」程幾鬆手將其撂開,返身便跑,追打這小兔崽子已經無濟於事,他得趕緊回去照料齊北崧!
齊北崧有自救的意願,正把腦袋放在廚房水龍頭底下沖。
齊爺當然也沒有中過催情藥(誰敢給他下呀),但他目睹過這玩意兒是如何運作的,那個圈子裡誰都不是白紙一張,所見所聞俱是紛亂。
程幾從身後一下子把他從涼水裡拉開:「你這樣要生病的!」
齊北崧身上發燙,迷亂的瞳孔無法聚焦,好半天才說:「……你去哪兒了?」
「我剛才去酒吧求證了一下!」程幾用乾毛巾罩住他的頭,架起他的胳膊說:「上樓去,我給你弄藥!」
齊北崧問:「什麼藥……」
程幾不知道什麼藥對症,但樓上他的床頭櫃裡有幾瓶藿香正氣水,那玩意兒能緩解中暑,說不定也能緩解這個!齊北崧如果不喝,就給他硬灌下去!
齊北崧被他拉走,眼前五光十色,什麼都在旋轉,彷彿頭頂懸掛著早年間歌廳上空的旋轉燈。樓梯六十公分寬,程幾一個人走都嫌窄,何況還拖著個齊北崧。齊北崧十分不配合,喊:「你……離我遠點兒!」
程幾明白那不是嫌棄,而是最後的清醒。
齊北崧的清明意識就像一團被包裹在氣球裡的煙,劇烈的藥性把外邊那層薄膜刺破了,煙氣要散不散,他正在努力地維持,一旦散開,他大概也就獸慾癲狂了。齊北崧死要臉皮,寧願自殘也不願在程幾面前那樣,所以上樓期間他一直在自殘,故意用額頭撞得木質扶手咚咚作響。
「幹嘛呀你?」程幾用手掌在他額頭和木頭之間擋了兩次,「不疼啊?」
齊北崧迫切需要那份疼痛,他抓住程幾的手,低吼:「你管不著!」
程幾說:「別鬧!快來!」
齊北崧說:「別說『來』這個字!也別說『快』!」
「……」
「別說話!再說老子親你了!!」
「……」程幾大氣都不敢出。
齊北崧明明在爬樓梯,但感覺卻像是在爬山。樓梯上沒燈,只有樓下門廳處的一盞節能燈提供照明,四周昏暗,他卻覺得烈日火輪高懸中天。火燒火燎,無遮無攔,山巔、峽谷、樹叢、危岩……周圍的一切都被炙烤得滾燙,彷彿身處明晃晃的大火爐,一股股熱浪席捲著他,他幾乎窒息,只有身邊程幾是涼的,冰的,好似一汪清泉,誘惑著人將其大捧大捧掬到嘴邊!他忍不住要把臉湊過去聞他的味道,去汲取他的涼意,去舔他身上清冷的水珠,然後將他壓在身下,揉在懷裡,捧在心口,沉入在內……
程幾命令:「抬腳!」
「別說話!」齊北崧最後一次警告程幾,「離我遠點兒,別管我!」
程幾偏要管,他如果是那種撒手不管的性子,當初就不可能去救沈子默。「你別急!」他幾乎扛著齊北崧全部的體重,語氣吃力,「我一會兒把……把你放在蓮蓬頭下面用溫水沖,大不了多沖幾個小時,一定有用!」
齊北崧笑了,他笑程幾的天真可愛,以及他真的、真的很想對著這個天真可愛的寶貝兒解褲子。汗水從他的額頭滲出,漬入新鮮撞出的傷口,帶著血色滾落面頰,他已經感覺不到那皮肉的微痛,在他身體內部,饑渴、陣痛和困頓侵蝕了他,那裡已經堅硬如鐵,他距離瘋狂大約只剩半秒。他抬起汗涔涔的眼睛望向程幾的側臉,後者沒有回視,專注地盯著樓梯上方。他說:「哎……」
程幾轉眼。
齊北崧突然撲倒程幾,翻身將他壓在樓梯上!
程幾如無骨蛇一般從他身下脫困,雙手架在他腋下,猛然發力將他拽上了最後一級臺階。齊北崧重重地摔倒在地,抬手要去抓對方,程幾已經飛身跑了。齊北崧本想站起來,忽然像是被抽了無形的一鞭子,在冰涼的地板上蜷縮成一團,拳頭緊緊抵住下腹。
……又是一陣,什麼時候才是個頭……地板的撞擊讓他稍微清醒了些,他熬過一陣炙熱後嘶啞地喊:「你別走……把我弄暈啊!」
程幾不答,以最快的速度衝到樓下廚房打開瓦斯熱水器,再飛身跑回,擰開淋浴房蓮蓬頭,他用手試水溫,直到覺得差不多,準備去拖齊北崧過來,一轉身才發現那人就堵在他身後。齊北崧粗暴地將他壓在淋浴間的玻璃隔板上,撞得他悶哼一聲,熱水在隔板那一側嘩嘩流淌,蒸汽騰騰地充盈整個空間。
「叫你……把我……弄暈。」齊北崧漆黑的眸子裡只剩下慾念。
程幾真有點兒驚恐,他應付過許多狀況唯獨沒有這種,齊北崧將整個身體卡在他雙腿之間,手肘撐在他臉兩側,這是一種團團環繞不容掙脫的姿勢。過去他不覺得與齊北崧大約十公分的身高差有什麼要緊,現在知道了,原來人也和冷兵器一樣一寸長一寸強,他正和齊北崧視線相平,但雙腳已經被提溜離地,使不上力氣。他當然有技巧掙脫,但那勢必傷害對方,齊北崧是無辜的,他只是不清醒。
是我的錯!程幾咬牙想:當時小毛頭把藥水扔進垃圾桶,我不該馬虎大意,就應該盯著他一瓶一瓶敲碎!他猶豫之際,齊北崧已經俯身親了上來。
……或許那不叫親,而叫咬,叫吞,程幾腦袋裡嗡地一聲響,等回過神後覺得兩片薄唇上觸感非常,甚至是痛的。齊北崧放縱地啃噬他,撬開他緊閉的牙關將自己送進去,不知哪裡破了,血腥氣在二人口中蔓延,齊北崧一點兒也不在乎,舌尖舔過上顎,他饑渴若狂。程幾喘不上氣開始掙扎,齊北崧緊按著不讓,以力量而論他占據絕對上風,況且他現在已經瘋了。
程幾知道現在攻擊哪兒都不如攻擊那處效率高,但他不能,他怕自己一掌下去毀了齊北崧下半輩子。齊北崧正在用那處蹭他,蹭得他驚懼僵直如木樁,那感覺真是……對方還真他媽是個十足的男人了。大爺的,有權有勢有顏也就罷了,身體條件還這麼好,電線桿子都能被他蹭燃了!
「給我吧……」齊北崧突然放開了他一秒,開始剝扯他的衣服。
傻瓜也聽得懂這句話的意思,程幾知道再不跑就晚了!他右手四指併攏戳向齊北崧肋下,齊北崧疼得一縮,他趁機鑽出桎梏往洗手間外跑!沒想到齊北崧反應也快,撲過來勾住他的腿,那鬼藥讓齊公子只有一個目標,一個慾望,一種執著,誓不甘休。程幾本該蹬他,但看到他那迷亂的臉就下不去腳,於是又被抱緊了腰。
兩人在冰涼且面積窄小的瓷磚地面上翻滾撕扯,均不止一次磕到了腦袋。程幾斷斷續續地喊:「別,住手!……沖水去!沖了就好了!」
齊北崧一言不發,因為他蓄勢待發,他動作堅決迅猛像一隻獸,程幾裡三層外三層穿得那麼厚,幾乎都要被他撕開了。程幾始終沒法真下手打他,因為知道他現在有多難受!他上輩子不止一次配合過緝毒行動,親眼見過那些中樞神經被侵蝕的人,他們言行詭異但不自知,在那段時間內已不是完整的一個人,而只是人的本能,追求極致的歡欣,極端的刺激,以及最大的釋放。
除了初兩次見面,齊北崧其實待他不錯。
齊公子態度傲慢嘴還臭,行事卻是另一種風格,用凰村人的話講叫做「惡慣」──惡惡的,凶凶的,板著臉帶點兒欺負,但其實是慣著你,縱著你。程女士去世當天,他因為齊北崧而沒能見到母親最後一面,為此還揍了他;但事後想想,卻也不是齊公子的錯,只能怪陰差陽錯諸事不巧。今天也是,齊北崧不過是和老耿抬了幾句槓,他犯了什麼罪要經受這些?
程幾緩緩地抬起眼,齊北崧正在咬他的脖子,種下一枚枚鮮紅的吻痕,還好他穿的是套頭帽T,比較厚比較緊身,齊北崧那雙不太聽使喚的手到現在也沒能把它脫下來。他說:「我幫你。」
「……嗯?什麼……寶貝兒?」齊北崧埋首在他脖頸間,憑本能在啜吸。
「我幫你。」程幾說,「用手。」
齊北崧遲鈍了大約三秒,聽明白了。他停下動作,雙手捧住程幾的臉,貼著極近極近地瞪著他,突然他攔腰扛起程幾往房間大步走去,將其扔在床上。
「幫我,寶貝兒……」齊北崧站在床前,濕漉漉的額髮下垂,大敞著衣領,露出他形狀優美的鎖骨。「用手就行……」他真不怕冷,這種天氣也只不過在大衣裡穿一件雞心領毛衣,肌肉的塊壘似乎隔著衣服都能看見。陳川說他上身練得像個扇面,其實是開他玩笑,他比絕大多數人要強健,但看上去絕不誇張,他還是修長、緊實、好看的。
「別叫我寶貝兒。」程幾臊得耳朵發燒。
「你是我的寶貝兒……」齊北崧爬上床,靠近他,「我很慶幸……今天是你。」
「一會兒別叫。」程幾血氣上湧,他臉皮薄。
「……我偏要。」齊北崧說。他將外衣甩在地板上,解開了褲子。
程幾只看了一眼就覺得折壽三年,多虧他剛才只答應用手,如果用別的地兒,大概今天晚上就要死在這裡!
「你會嗎?」齊北崧舔著下唇,慢慢向他逼近,眼神深濃。
「……」程幾閉上眼睛再睜開,已經將生死置之度外了,「會。」
「你臉紅了。」齊北崧半瞇著眼睛說。
「別說話!」這次換程幾低吼,「利索點兒快來!」
「我能貼著……貼著你麼?」齊北崧問,「我像是快要……裂開了……」
程幾張開雙臂,從身後環住了他,體型上來講程幾小一圈,但男人麼,無所謂誰抱誰。齊北崧脖子後仰,將頭靠在他肩上,滾燙的嘴唇擦過他的頸側。「我喜歡你……」他低聲道,「……寶貝兒。」
「別說話,你不清醒。」程幾和他一樣躁熱,而且羞恥。
「我喜歡你。」齊北崧的執念並非來自於藥物。
「……」程幾承受著他疾風驟雨似的親吻,忍耐著那最本能的撩撥,遏制著自身同樣誠實的反應,好半天才憋出兩個字,「謝謝。」
(滴──互幫互助,讓兄弟爽爽卡。)
齊北崧扎扎實實折騰了一晚上。
程幾的兩床被子、兩顆枕頭和一顆抱枕在最開始就被他掃向了角落,他長手長腳,用強健的臂膀和腰腹在床上逞著威。每次程幾難以忍受要跑,或者準備動拳腳的時候,他又彷彿智商暴漲,拽著他的腳踝,用或沙啞或強硬的聲音吼道:「你答應過往後隨便我造的!」程幾恨不得甩自己兩巴掌,這都他媽什麼烏鴉嘴啊!
第四次時已經凌晨三四點,程幾精疲力竭連根手指都抬不起來,往痕跡斑斑的床上一躺說:「你造吧你造吧,讓我睡會兒!」
齊大公子舔著嘴唇赤紅著臉說:「好,夠勁兒!」
然後……也沒真造,齊公子這點挺好的,自始至終把那條承諾的線守著了。終於兩人鬧完,昏死一場,程幾還有點兒意識,在昏過去之前捧來被子把齊北崧蓋上,然後去洗手間關掉幾乎放了一夜的洗澡水。好在熱水器因為過熱保護早已自行關閉,否則瓦斯帳單來時,真的很難跟老耿解釋。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雜魚求生(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41 |
二手中文書 |
$ 260 |
華文BL |
$ 261 |
Comic Book |
$ 281 |
華文 |
$ 281 |
小說/文學 |
$ 297 |
中文書 |
$ 297 |
文學作品 |
$ 297 |
華文戀愛故事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雜魚求生(下)
凰村的平靜,在齊北崧抵達後宣告打破,
親眼目睹程幾和人「摟摟抱抱」,他差點氣死!
這個「乾爹」又是哪冒出來的!!
萬幸酒吧一場混亂,藉著誤中春藥的契機,
齊大少終於坦白心意,成功晉級「備選」,
眼看扶正指日可待。
兩人更進一步,還沒來得及多些溫存,
惡意已悄悄蔓延至安寧山村。
程幾只想替乾爹報個仇,沒想繞了一圈,
他又重回水月山莊,揪出更多隱情。
無辜人證慘遭惡火滅口,還累及親友,
他無比憤恨的同時,也自責不已,
凶手卻堂皇地設下陷阱,誘他入局,
看著眼前人早已性情大變,程幾終於恍悟,
但也為時已晚──
無論多困難,為了心中所愛,
他都必須逃出去!
本書收錄番外一篇。
作者簡介:
微笑的貓,晉江文學城簽約作者,有空就寫幾筆,沒空就不寫,沒有追求的鹹魚寫手。同時擁護鹹粽子和甜粽子、鹹豆花和甜豆花、鹹湯圓和甜湯圓。
章節試閱
第十一章
門口那些人見風波平息了,也紛紛坐下喝酒打牌各玩各的。
小酒保將兩杯蜂蜜檸檬水放到老耿和齊北崧面前,兩人都端起來一飲而盡。
齊北崧原本不喝陌生酒吧提供的東西,但他之前焦躁地連開了幾個小時的車,後又心亂如麻地滿凰村找程幾,再加上和老耿吵了一架,嗓子早渴得冒煙,也就顧不上那麼多了。
程幾說:「回家吧。」
老耿不願意,說還要玩。
程幾知道以他的脾性不喝到醉不會走,醉了也無甚大礙,突然發現他情況不對。「爹?」他扶住老耿。
老耿剛才還龍精虎猛,此時就像幾十個小時沒睡覺似的,一頭栽在吧檯上睡著了。
...
門口那些人見風波平息了,也紛紛坐下喝酒打牌各玩各的。
小酒保將兩杯蜂蜜檸檬水放到老耿和齊北崧面前,兩人都端起來一飲而盡。
齊北崧原本不喝陌生酒吧提供的東西,但他之前焦躁地連開了幾個小時的車,後又心亂如麻地滿凰村找程幾,再加上和老耿吵了一架,嗓子早渴得冒煙,也就顧不上那麼多了。
程幾說:「回家吧。」
老耿不願意,說還要玩。
程幾知道以他的脾性不喝到醉不會走,醉了也無甚大礙,突然發現他情況不對。「爹?」他扶住老耿。
老耿剛才還龍精虎猛,此時就像幾十個小時沒睡覺似的,一頭栽在吧檯上睡著了。
...
顯示全部內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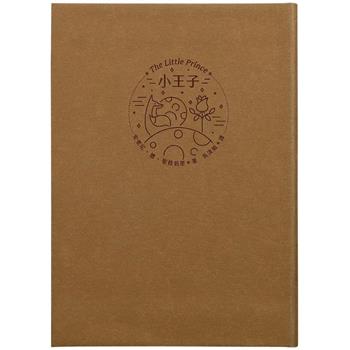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