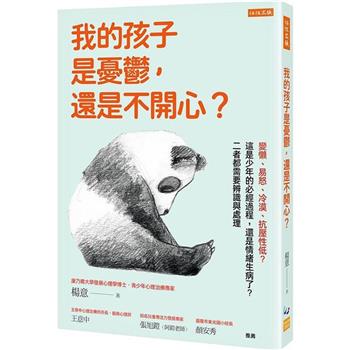第一章 活得有趣,活得自在
別綁死自己
又是新的一年,大家都在制訂今年的願望,我從不跟著別人做這等事,願望隨時立,隨時遵行便是。
今年的,應該是盡量別綁死自己。
常有交易對手相約見面,一說就是幾個月後,我一聽全身發毛,一答應,那就表示這段時間完全被人綁住,不能動彈。那是多麼痛苦的一件事。
可以改期呀,有人說,但是我不喜歡這麼做,答應過就必得遵守,不然不答應。改期是噩夢,改過一次,以後一定一改再改,變成一個不遵守諾言的人。
那麼怎麼辦才好?最好就是不約了,想見對方,臨時決定好了。喂,明晚有空吃飯嗎?不行?那麼再約,總之不要被時間束縛,不要被約會釘死。
人家有事忙,可不與你玩這等遊戲,許多人都想事前約好再來,尤其是日本人,一約都是早幾個月。
「請問你六月一日在香港嗎?是否可以一見?」
對方問得輕鬆,我一想,那是半年後呀,我怎麼知道這六個月之間會發生什麼事?心裡這麼想,但總是客氣地回答:「可不可以等時間近一點再說呢?」
但這也不妥,你沒事,別人有,不事前安排不行呀!我這種回答,對方聽了一定不滿意的,所以只有改一個方式了。
「哎呀!六月份嗎?已經答應人家了,讓我努力一下,看看改不改得了期。」
這麼一說,對方就覺得你很夠朋友,再問道:「那麼什麼時候才知道呢?」
「五月份行不行?」
「好吧,五月再問你。」對方給了我喘氣的空間。
說到這裡,你一定會認為我這人怎麼那麼奸詐,那麼虛偽。但這是迫不得已的,我不想被綁。如果在那段時間內,我有更值得做的事,我真的不想赴約。
「你有什麼了不起?別人要預定一個時間見面,六個月前通知你,難道還不夠嗎?」對方罵道,「你真的是那麼忙嗎?香港人都是那麼忙呀?」
對的,香港人真的忙,他們忙著把時間儲蓄起來,留給他們的朋友。
真正想見的人,隨時通知,我都在的,我都不忙的。但是一些無聊的、可有可無的約會,到了我這個階段,我是不肯綁死我自己的。
當今,我只想有多一點時間學習,多一點時間充實自己,吸收所有新科技,練習之前沒有時間練習的草書和繪畫。依著古人的足跡,把日子過得舒閒一點。
我還要留時間去旅行呢。去哪裡?大多數想去的不是已經去過了嗎?不,不,世界之大,去不完的。但是當今最想去的,是從前住過的一些城市,見見昔時的友人,回味一些當年吃過的菜。
沒去過的,像爬喜馬拉雅山,像到北極探險,等等,這些機會我已經在年輕時錯過,當今也只好認了,不想去了。所有沒有好吃東西的地方,也都不想去了。
後悔嗎?後悔又有什麼用?非洲那麼多的國家,剛果、安哥拉、納米比亞、莫三比克、索馬利亞、烏干達、盧安達、甘比亞、奈及利亞、喀麥隆,等等等等,數之不清,不去不後悔嗎?已經沒有時間後悔了。放棄了,算了。
好友俞志剛問道:「你的新年大計,是否會考慮開『蔡瀾零食精品連鎖店』?你有現成的合作夥伴和朝氣勃勃的團隊,真的值得一試……」
是的,要做的事真的太多了。我現在處於被動狀態,別人有了興趣,問我幹不幹,我才會去計畫一番,不然我不會主動地去找事來把自己忙死。
做生意,賺多一點錢是好玩的,但是,一不小心就會被玩,一被玩,就不好玩了。
我回答志剛兄道:「有很多大計,首先要做的,是不把自己綁死的事。如果決定下一步棋,也要輕鬆地去做,不要太花腦筋地去做。一答應就全心投入,就會盡力,像目前做的點心店和越南粉店,都是百分之百投入的。」
志剛兄回信:「說得好,應該是這種態度。但世上有不少人,不論窮富,一定要把自己綁死為止。」
不綁死自己,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花光了畢生的經歷,從年輕到現在,往這方向去走,中間遇到不少人生的導師。
像那個義大利司機,他向我說:「現在煩惱幹什麼,明天的事,明天再去煩吧!」
還有在海邊釣小魚的老嬉皮,我向他說:「老頭,那邊魚大,為什麼在這邊釣?」他回答道:「先生,我釣的是早餐。」
更有我的父親,他向我說:「對老人家孝順,對年輕人愛護,守時間,守諾言,重友情。」
這些都是改變我思想極大的教導,學到了,才知道什麼叫放鬆,什麼叫不要綁死自己。
「任性」這兩個字
從小就任性,就是不聽話。家中掛著一幅劉海粟的《六牛圖》,兩隻大牛帶著四隻小的。爸爸向我說:「那兩隻老牛是我和你們的媽媽,帶著的四隻小的之中,那隻看不到頭,只見屁股的,就是你了。」
現在想起,家父語氣中帶著擔憂,心中約略想著,這孩子那麼不合群,以後的命運不知何去何從。
感謝老天爺,我一生得到周圍的人照顧,活至今,垂垂老矣,也無風無浪。這應該是拜賜於雙親,他們一直對別人好,得到好報。
喜歡電影,有一部叫《亂世忠魂》(From Here to Eternity), 男女主角在海灘上接吻的戲早已忘記,記得的是配角不聽命令被關進牢裡,被滿臉橫肉的獄長提起警棍打的戲。如果我被抓去當兵,又不聽話,那麼一定會被這種人打死。好在到了當兵的年紀,邵逸夫先生的哥哥邵仁枚先生託政府的關係把我保了出來,不然一定沒命。
讀了多間學校,也從不聽話,好在我母親是校長,和每一間學校的校長都熟悉,才一間換一間地讀下去,但始終也沒畢業。
任性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只是不服。不服的是為什麼數學不及格就不能升班。我就是偏偏不喜歡這一門東西,學幾何代數來幹什麼?那時候我已知道有一天一定能發明一個工具,一算就能算出,後來果然有了計算尺,也證實我沒錯。
我的文科樣樣有優秀的成績,英文更是一流,但也阻止了升級。不喜歡數學還有一個理由,教數學的是一個肥胖的八婆(指愛管閒事的女子),面孔討厭,語言枯燥,這種人怎麼當得了老師?
討厭了數學,相關的理科也都完全不喜歡。生物學課中,老師把一隻青蛙活生生地剖了,用圖畫釘把皮拉開,我也極不以為然,翹課去看電影。但要交的作業中,老師命令學生把變形蟲細胞繪成畫,就沒有一個同學比得上我,我的作品精緻仔細,又有立體感,可以拿去掛在壁上。
教解剖學的老師又是一個肥胖的八婆,她諸多留難我們,又留堂,又罰站,又打藤,已到不能容忍的地步,是時候反抗了。
我帶導幾個調皮搗蛋的同學,把一隻要製成標本的死狗的肚皮剖開,再到食堂去炒了一碟意粉(義大利麵),下大量的番茄醬,弄到鮮紅,用塑膠袋裝起來,塞入狗的肚中。
上課時,我們將狗搬到教室,等那八婆來到,忽然衝上前,掰開肚皮,雙手插入塑膠袋,取出意粉,在老師面前大吞特吞。那八婆嚇得差點昏倒,尖叫著跑去拉校長來看,那時我們已把意粉弄得乾乾淨淨,一點痕跡也沒有。
校長找不到證據,我們又瞪大了眼做無辜表情(有點可愛),他更礙著和我家母的友情,就把我放了。之後那八婆有沒有神經衰弱,倒是不必理會。
任性的性格影響了我一生,喜歡的事可以令我不休不眠去做。接觸書法時,我的宣紙是一刀刀地買,我也一刀刀地練。所謂一刀,就是一百張宣紙。來收垃圾的人,有的也欣賞我的字,就拿去燙平收藏起來。
任性地創作,也任性地喝酒,年輕嘛,喝多少都不醉。我的酒是一箱箱地買,一箱二十四瓶。我的日本清酒,一瓶一點八升,我一瓶瓶地灌。來收瓶子的工人不停地問:「你是不是每晚開派對?」
任性,就是不聽話;任性,就是不合群;任性,就是跳出框框去思考。
我到現在還在任性地活。最近開的越南河粉店開始賣和牛,一般的店因為和牛價貴,只放三四片,我不管,吩咐店裡的人,一於(乾脆這樣,就這樣決定)把和牛鋪滿湯麵。顧客一看到,「哇」的一聲叫出來。我求的也就是這「哇」的一聲,結果雖價貴,也有很多客人點了。
任性讓我把我賣的蛋捲下了蔥,下了蒜。為什麼傳統的甜蛋捲不能有鹹的呢?這麼多人喜歡吃蔥,喜歡吃蒜,為什麼不能大量地加呢?結果我的商品之中,蔥蒜味的又甜又鹹的蛋捲賣得最好。
一向喜歡吃的蔥油餅,店裡賣的,蔥一定很少。這麼便宜的食材,為什麼要節省呢?客人愛吃什麼,就應該給他們吃個過癮。如果我開一家蔥油餅專賣店,一定會下大量的蔥,包得胖胖的,像個嬰兒。
最近常與年輕人對話,我是叫他們跳出框框去想事情,別按照常規來。遵守常規是一生最悶的事,做多了,連人也沉悶起來。
任性而活,是人生最過癮的事,不過千萬要記住,別老是想而不去做。
做了,才對得起「任性」這兩個字。
孤僻
年紀越大,孤僻越嚴重,所以有「grumpy old man」(愛發牢騷的老人)這句話。
最近盡量不和陌生人吃飯了,要應酬他們,多累!也不知道邀請我吃飯的人的口味,叫的不一定是我喜歡的菜,何必去遷就他們呢?
餐廳吃來吃去,就那麼幾家信得過的,不要聽別人說「這家已經不行了」,自己喜歡就是,行不行我自己會決定。我很想說:「那麼你找一家比他們更好的給我!」但一想,這話也多餘,就忍住了。
盡量不去試新的食肆。像前一些時候被好友叫去吃一餐淮揚菜,上桌的是一盤燻蛋。本來這也是倪匡兄和我都愛吃的東西,豈知餐廳要賣貴一點,在蛋黃上加了幾顆莫名其妙的魚子醬,倪匡兄大叫:「那麼腥氣,怎吃得了!」我則不出聲了,氣得。
當今食肆,不管是中餐西餐,一要賣高價,就只懂得出這三招——魚子醬、鵝肝醬和松露醬,好像把這三樣東西拿走,廚子就不會做菜了。
食材本身無罪,魚子醬醃得不夠鹹,會壞掉;醃得太淡,又會腐爛;剛剛好的,天下也只剩下三、四個伊朗人能做出。如果產自其他地方,一定鹹得剩下腥味。唉,不吃也罷。
鵝肝醬真的也只剩下法國佩里戈爾(Périgord)的,只占世界產量的百分之五,其他百分之九十五都來自匈牙利和其他地區。劣品吃出一種死屍味道來,免了,免了。
說到松茸,那更非日本的不可,只切一小片放進土瓶燒中,已滿屋都是香味。用韓國的次貨,香味減少。再來就是其他的次次次貨,整根松茸扔進湯中,也沒味道。
現在算來,用松茸次貨已有良知,當今用的只是松露醬,義大利大量生產,一瓶也要賣幾百港幣,覺得太貴。用莫名其妙的吧,只要一半價錢,放那麼一點點在各種菜上,又能扮高級,看到了簡直倒胃口。目前倒胃口東西太多,包括了人。
西餐其實我也不反對,尤其是好的,不過近來逐漸生厭。為了那麼一餐,等了又等,一味用麵包來填肚,再高級的法國菜,見了也害怕。
只能吃的,是歐洲鄉下人做的,簡簡單單來一鍋濃湯,或煮一鍋燉菜或肉,配上麵包,也就夠了。從前為了追求名廚而老遠跑去等待的日子已過矣,何況是模仿的呢。假西餐只學到在碟上畫畫,或來一首詩,就是什麼高級、精緻料理。上桌之前,又來一碟鮭魚刺身,倒胃口,倒胃口!
假西餐先由一名侍者講解一番,再由經理講講,最後由大廚出面講解,煩死人。講解完畢,最後下點鹽。雙指抓起一把,屈了臂,做天鵝頸項狀,扭轉一個彎,撒幾粒鹽下去,看了不只是倒胃口,簡直會嘔吐出來。
我認為天然才好的料理也好不到哪裡去,最討厭北歐那種假天然菜,沒有了那根小鉗子就做不出。已經不必去批評分子料理了,開發者知道自己已技窮,玩不出什麼新花樣,自生自滅了。我並不反對去吃,但是試一次已夠,而且是自己不花錢的。
做人越來越古怪,最討厭人家來摸我,握手更是免談。「你是一個公眾人物,公眾人物就得應付人家來騷擾你!」是不是公眾人物,別人說的,我自己並不認為自己是,所以不必去守這些規矩。
出門時已經一定要有一兩位同事跟著了,凡是遇到人家要來合照的,我也並不拒絕,只是不能擁抱。又非老友,又不是美女,擁抱來幹什麼?最討厭人家身上有股異味,抱了久久不散,令我渾身不舒服,再洗多少次澡也還是會留住。
這點助理已很會處理,凡是有人要求合照,代我向對方說:「對不起,請不要和蔡先生有身體接觸。」
自認有點修養,從年輕到現在,很少說別人的壞話。有些同行的行為實在令人討厭,本來可以揭他們的瘡疤來置他們於死地,但也都忍了,遵守著香港人做人的規則,那就是:「活,也要讓人活!」英語是:「Live and let live !」
在石屎森林(高樓大廈)中活久了,自有防禦和復仇的方法,不施展,也覺得不值得施展而已。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過好這一生的圖書 |
 |
過好這一生 作者:蔡瀾 出版社: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出版日期:2023-06-14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58 |
二手中文書 |
$ 300 |
現代散文 |
$ 300 |
文學作品 |
$ 300 |
新書推薦79折起 |
$ 334 |
中文書 |
$ 334 |
現代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過好這一生
明明沒有不開心,卻時常感到生活太平淡、沒什麼意思?
讓香港四大才子、老頑童蔡瀾告訴你,如何把每一天都過得盡興又有趣!
盡情發掘新事、盡情充實自己;盡量跳出框架、盡量活在當下。
當擁有美食家、旅行家、生活家等身分的他,遇到不能隨心所欲出遊的日子,該怎麼過?他說:太容易過!玩繪畫、玩種植、玩料理、玩出版……依然玩得不亦樂乎,甚至時間都不夠用。
本書收錄蔡瀾過去三年所創作全新散文70篇,總是以真性情過生活的他,透過輕鬆坦率、鮮活有趣、犀利卻充滿溫度的故事,分享80多年來的人生哲學。無論正處於人生什麼階段,都能從中收穫「無論好日子壞日子,都要讓自己快活」的豁達態度。
〈活得有趣,活得自在〉
真正想見的人,隨時通知,我都在的,我都不忙的。
但是一些無聊的、可有可無的約會,到了我這個階段,我是不肯綁死我自己的。
〈吃好,喝好,活好〉
一個陌生的地方總有一些美味的,問題在於肯不肯去找。
只要好吃,都是家鄉菜,我們是住在地球上的人,地球是我們的家鄉。
〈瘟疫流行的日子〉
與其被瘟疫玩,不如玩瘟疫。
總之,每天都學習,每天都創作,日子就變得充實,也可以告訴自己,對得起今天了。
〈好日子終會來到〉
疫情時期,大家閒在家裡發悶,我倒是東摸摸西摸摸,有許多事可做,嫌時間不夠用。我不會被瘟疫玩倒,我將玩倒它。
〈人間好玩才值得〉
任性,就是不聽話,就是不合群,就是跳出框框去思考。
任性的性格影響了我一生,喜歡的事可以令我不休不眠去做。
倪匡:「他的文章之中,處處透露對人生的態度,其中的淺顯哲理、明白禪機,都使讀者能得頓悟,可以把本來很複雜的世情困擾簡單化:噢,原來如此,不過如此。」
作者簡介:
蔡瀾
1941年生於新加坡,祖籍廣東潮州,後移居香港。
與金庸、倪匡、黃霑並稱的「香港四大才子」。
作家、生活家、美食家、電影人、主持人。曾任《舌尖上的中國》總顧問、《開講啦》特邀講師、《新周刊》年度生活家。
吃喝玩樂無不在行,文學、電影、書法、金石樣樣精通,被無數人奉為人生典範,迄今出版圖書七十餘本,深受讀者喜愛。
著有《我喜歡人生快活的樣子》、《人生大多是小事,沒有什麼了不起》、《人生真的很好玩》等作品,看似隨意的漫談,實則充滿人生智慧。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活得有趣,活得自在
別綁死自己
又是新的一年,大家都在制訂今年的願望,我從不跟著別人做這等事,願望隨時立,隨時遵行便是。
今年的,應該是盡量別綁死自己。
常有交易對手相約見面,一說就是幾個月後,我一聽全身發毛,一答應,那就表示這段時間完全被人綁住,不能動彈。那是多麼痛苦的一件事。
可以改期呀,有人說,但是我不喜歡這麼做,答應過就必得遵守,不然不答應。改期是噩夢,改過一次,以後一定一改再改,變成一個不遵守諾言的人。
那麼怎麼辦才好?最好就是不約了,想見對方,臨時決定好了。喂,明晚有空吃飯嗎...
別綁死自己
又是新的一年,大家都在制訂今年的願望,我從不跟著別人做這等事,願望隨時立,隨時遵行便是。
今年的,應該是盡量別綁死自己。
常有交易對手相約見面,一說就是幾個月後,我一聽全身發毛,一答應,那就表示這段時間完全被人綁住,不能動彈。那是多麼痛苦的一件事。
可以改期呀,有人說,但是我不喜歡這麼做,答應過就必得遵守,不然不答應。改期是噩夢,改過一次,以後一定一改再改,變成一個不遵守諾言的人。
那麼怎麼辦才好?最好就是不約了,想見對方,臨時決定好了。喂,明晚有空吃飯嗎...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一章 活得有趣,活得自在
古人四十件樂事/別綁死自己/「任性」這兩個字/孤僻/準時癖/談眼鏡/要你命的老朋友/超出常理/當小販去吧!/貓經/貓的觀察者/大業鄭/耐看/君子國/喜歡的字句/問題問題一籮筐/微博十年/老頭子的東西/為《倪匡老香港日記》作序/只限不會中文的老友
第二章 吃好,喝好,活好
家鄉菜/兒時小吃/家常湯/著著實實的一餐/反對火鍋/愛恨分明/鮮/在日本吃魚/義大利菜,吾愛/莆田/順德行草展/鹹魚醬的吃法/鏞鏞/大班樓的歡宴/最有營養食物一百種/滿足餐
第三章 瘟疫流行的日...
古人四十件樂事/別綁死自己/「任性」這兩個字/孤僻/準時癖/談眼鏡/要你命的老朋友/超出常理/當小販去吧!/貓經/貓的觀察者/大業鄭/耐看/君子國/喜歡的字句/問題問題一籮筐/微博十年/老頭子的東西/為《倪匡老香港日記》作序/只限不會中文的老友
第二章 吃好,喝好,活好
家鄉菜/兒時小吃/家常湯/著著實實的一餐/反對火鍋/愛恨分明/鮮/在日本吃魚/義大利菜,吾愛/莆田/順德行草展/鹹魚醬的吃法/鏞鏞/大班樓的歡宴/最有營養食物一百種/滿足餐
第三章 瘟疫流行的日...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