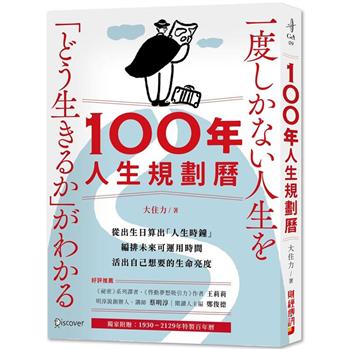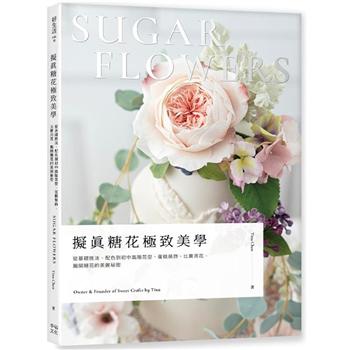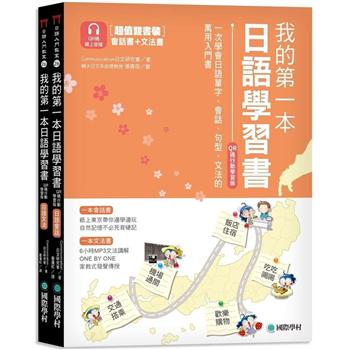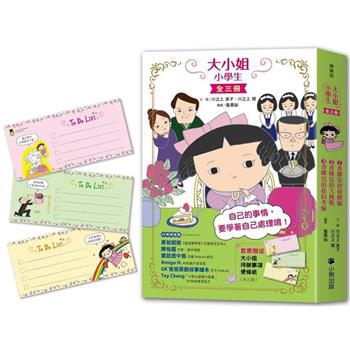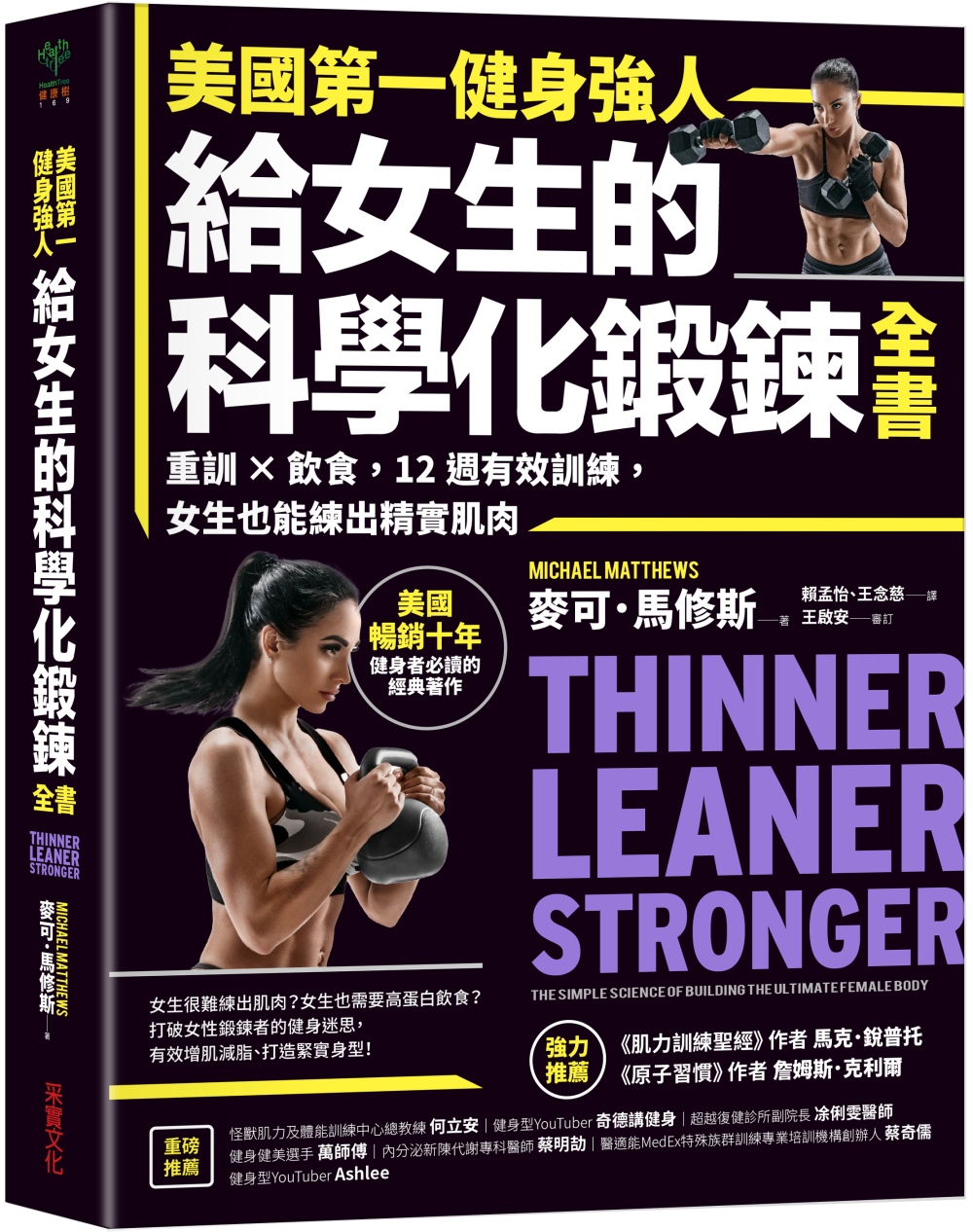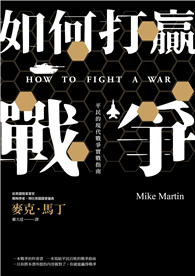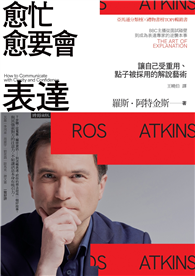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帝國主義下的臺灣(2022新譯版)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336 |
台灣史地 |
$ 379 |
台灣史概論 |
$ 379 |
中文書 |
$ 379 |
台灣研究 |
$ 379 |
讀書共和國 |
$ 408 |
財經/企管/經濟 |
$ 432 |
財經企管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永遠列名臺灣史閱讀書單
日本統治臺灣時期的「禁書」,今日為理解日治臺灣史的「起點」
2022新譯版,迎接經典的再理解和新啟發
本書自1929年出版至今,諸多立論已成學界定說,是日治臺灣研究的標竿之作。作者矢內原忠雄統整分析了1895年之後的整體史事,而著重能夠解釋全局的經濟議題。身為東京帝大經濟學教授,他敏銳的看出殖民政府必須讓臺灣對帝國有利,於是努力引進資本主義並百般維護,一切政策皆由此核心擘劃實行。以此觀點,日治時期的政治、產業、金融、司法、文教等看似互不相干又紛雜多端的單獨事實,便有了前後一貫的脈絡。
書中分析臺灣的現象時,同時參照朝鮮、爪哇和印度等地的殖民統治。將臺灣的內外環境並陳,不僅更能理解殖民當局背後的考量,也能以客觀依據凸顯臺灣處境的獨特之處。臺灣的糖業和爪哇或古巴相比,優勢劣勢分別為何?這影響了會社的經營方向,進而觸動總督府的政策,甚至日本帝國的關稅修訂。臺灣總督府真的是專制政治嗎?臺灣人能參與的政治權力究竟是大是小?和同受日本殖民的朝鮮相比,讀者便有清晰概念。
殖民政府為了統治需要,調查整理了綿密的統計數據,矢內原從這些資料中歸納出現象,再賦予意義、建立自己的詮釋,進而形成對帝國主義的批判。本書1929年10月於東京出版,臺灣總督府警務局隔年1月即下令禁止在臺上市、流通,直至1945年日本結束在臺灣的殖民統治為止,此書都無法在臺公開販售。甚至在1939年以後,日本本國的出版商也在軍部勢力的壓迫之下,不再販售此書。
今日隨著臺灣史逐漸深化於義務教育課程中,《六三法》、「米糖相剋」、「內地延長主義」等詞彙已成學子應考須熟記的關鍵字,但是對其他世代而言可能全然陌生。這些基本概念皆可回溯至本書中更完整的脈絡,因此是填補知識斷層的不二之選。現代學者也必須承接矢內原的成果而加以延伸或修正,所以閱讀此書也是掌握當代研究的必然選擇。
新譯版依據日文原文重新翻譯,並於必要處註解,排除今日讀者理解文本時可能遇到的障礙。譯者並撰寫〈解題〉一篇,說明矢內原所處的學術環境如何影響其研究取徑,而後世研究對於此書又有何評價,讓讀者更整全的掌握本書內容。
如果你曾感嘆臺灣人遭受殖民壓迫,本書揭露當帝國推行資本主義化時,不只影響臺灣,也讓日本消費者、納稅人和農業移民付出代價。
如果你知道日治時期研發出了蓬萊米,本書會告訴你為何小小的稻米竟然讓臺灣強大的製糖會社陷入經營危機。
如果你覺得臺大曾經是帝國大學頗為氣派,本書會指出在臺灣設立帝國大學為何是「腳小頭大」的教育制度,臺灣的整體文教政策又如何顯露出濃厚的帝國主義,並為資本主義服務。
如果嘉南大圳讓你想到八田與一的貢獻,本書能讓你從帝國主義的視角觀察水利工程的意義和影響,進而更深刻、寬廣的認識帝國主義下的臺灣。
作者簡介
矢內原忠雄(1893-1961)
日本四國愛媛縣人。1916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1920年獲任東京帝大經濟學部助教授,赴歐洲留學後,回國接替恩師新渡戶稻造,擔任東京帝大殖民政策講座教授。
矢內原認為關於殖民地的經濟學理論必須能夠解釋現場的實際情形,不然就必須修正或更新,因此曾先後至朝鮮、樺太、滿洲和南洋群島實地調查。1924年矢內原就接待了臺灣議會設置運動的要角蔡培火與林呈祿,到了1927年更來臺40餘日,從角板山到花蓮港、從工廠到「番社」,足跡遍布全臺。回國後發表數篇專文分析日本在臺灣的殖民統治,而後再整理成本書。1929年10月此書於東京發行,翌年1月臺灣總督府就禁止在臺灣販賣流通。
矢內原長期為被殖民者權益發聲,對政策多有批判,因此素為當局所不喜。1937年日中戰爭爆發後,矢內原因批判日本政府發動戰爭,於該年底被迫辭去東京帝大之教職。戰後回到東大經濟學部任教,陸續擔任經濟學部部長、教養學部部長,於1951年獲選為總長。在任職總長期間,積極挺身捍衛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被歷史學者譽為「日本人的良心」,今日東京大學駒場校區設有「矢内原公園」作為紀念。
譯者簡介
黃紹恆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畢業,東京大學經濟學碩士、博士,曾任教於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現為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院長、人文社會學系教授。著有《臺灣經濟史中的臺灣總督府》、《砂糖之島:日治初期的臺灣糖業史1895-1911》,譯有《經濟史入門:馬克思經濟學歷史理論概述》、《現代經濟史的基礎:資本主義的生成、發展與危機》、《日本經濟史》。
70個馬上套用的賺錢模式:半夜賣榻榻米、貴五倍的衛生紙、不怕你暴雷的試閱……這些獲利模式怎麼想出來的?現役行銷大師破天荒給你思考加速器。
基恩斯的再現性工作技術:平均年薪超過兩千萬日圓的人怎麼工作?基恩斯員工不靠運氣而是建立模式、複製成果,成為再現性人才。
攀高、續抱、快逃—K線之道:股票要漲,不能純靠題材,更需要資金拉抬。K線比財報早知道,賺到70%漲幅。
50張圖秒懂勞動權益:你在職場走跳,從求職到離職絕對不挨刀!
別讓主力賺走你的錢:115張技術圖表,買在最低風險,決定超級獲利(熱銷再版)
急性子的不累工作法:回郵件超快、喜歡多工進行、不喜歡等人更不讓人等,事事求快當然好,但如何不累不氣還兼顧品質?
當你沒有新鮮的肝-不當主管你會更累:怕累、怕煩、不想扛責?35年資歷的人資主管分享,為何你在45歲前,該逼自己當個清、濁二刀流主管!
2024年臺灣IT Spending 調查:金融業
犬性思維:讓銷售變簡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