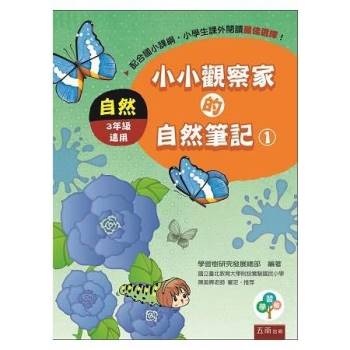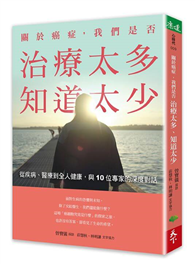●淑怡到了繁華都市
且說淑怡在祖母的強勢命令下,心情惶惶滿懷悒鬱,黯然獨自搭乘CAT班機先飛到台南。她母親勤子既然設想周到,早已把淑怡的行程寫信通知余燿得,所以一到台南機場下了飛機,余燿得已在機場等著了,隨即帶她先到他在台南的所屬機構的同事陸主任家休息。他跟淑怡說中午陸主任要請他們吃飯,並可以在他家休息兩三個鐘頭,然後再搭下午的火車去台北。
陸主任家是處佔地範圍不小,高高的竹籬笆四方形圍牆內,是獨棟的日式木造房屋宿舍,紅色的雙扇大門,從外觀看起來,會住在這種大院子大宿舍的,必是這地方上職位比較高的官。因為淑怡在澎湖縣政府所看到的科長官舍連院子都沒有,與這有大庭院的氣派相比就顯得簡陋多了。但對於淑怡這種自出生就在大四合院大古厝長大的女孩子來說,並不感覺氣派特別。到了門口余燿得伸手按了門鈴,裡頭便傳出聲音:
「來啦,來啦,歡迎,歡迎。」
木門打開,一對中年夫妻迎出來,余燿得就介紹說:
「陸主任和陸太太,陸主任是台南高分院的會計主任。」然後再介紹說:
「她就是程淑怡小姐。」
陸主任和陸太太就異口同聲說:
「歡迎,歡迎,快請裡面坐。」
陸主任高大的身材,濃眉大眼相貌堂堂,自然表現出來官位不小的氣派。經過燿得的介紹,知道果然他是台灣高等法院台南高分院的會計主任,雖然官等與余燿得大概同等,但燿得總是上級司法行政部裡的專員,陸主任卻是下屬機關官員,有管到他們的業務,自然是對他很尊重很客氣,而且兩人的交情大概也很不錯,所以更是熱絡地握手言歡。陸太太普通身材有著中年貴婦的豐腴福態,圓圓的臉蛋也是滿臉笑容和藹親切,國語都說得很標準,淑怡以不是很正確的台灣國語和她交談,但因對大陸各地方不同的腔調所知不多,當然猜不出他們是哪一省人。在陸主任與余燿得握手熱絡寒暄時,陸太太一方面招呼程淑怡一方面仔細地打量這個年輕女孩。
只見她雖然有些陌生的羞怯,身高幾乎與余燿得那種不到一七零公分左右的身高矮不了多少,身材略瘦而亭亭,皮膚白白淨淨的,瓜子形的臉蛋,雙眼皮略微深邃的雀眼,鼻樑挺而鼻準圓勻,整個看起來就是一張頗討人喜歡的娃娃臉。心想余專員真有辦法,跑那麼遠的離島去追到一個這麼個年輕的小姐,又這麼文靜而有氣質。
淑怡隨著她們進入院子走進大門,只見大約有六坪多的客廳,在左側靠牆處擺著三張並排的木雕沙發椅,中間是一長方形的茶几,另外兩張沙發椅隔著茶几向著門窗,又有兩張也是對著茶几向內。門的左邊有玻璃窗櫺,採光很好,所以雖然只是日式木屋,但窗明几淨,使這客廳顯得樸素而靜雅。大家進入客廳坐下,陸太太已泡好四杯茶送來,一番客氣寒暄後他們就很熱絡地開始聊天,聊的話題好像多是他們職務上的事情,淑怡對他們的言談內容自然像是鴨子在聽雷,有聽沒有懂,傻傻默坐一旁。陸太太大概發覺到淑怡的尷尬,傻傻地被冷落一旁,就關心地問:
「程小姐妳累不累?要不到房間裡躺一躺休息?」
淑怡清脆細嫩聲音回答:
「謝謝,我不累。」
陸太太說;
「妳講話的聲音很好聽。」
淑怡在澎湖縣政府上班時,在年終同樂會曾被拱上台清唱,被同事門鼓掌喊「安可」,當然聲音不錯。但是初到這種地方,還是只能生分地呆坐在一旁。她心裡想:在他們的心目中,她一定只是余燿得遠從澎湖鄉下找來的一個窮苦人家的女孩,模樣土裡土氣大概也沒有什麼教育水準。從他們的笑容裡,恍似讀出他們對她的可笑復可憫的評價。總之,在他們笑笑地注視下,使淑怡產生著自卑和渾身地不自在,當他們客氣地問她一些話時,她只有微笑點頭說「是,是。」「好,好。」。所以他們雖然是很親切的關心招待她,但初見面的認識,仍然免不了讓她有陷於陌生氛圍的羞怯和不自在。心裡只煩惱如今已是遠離家鄉,此去前途一片茫然,只能任憑安排一步步地走向自己無法確定和把握的將來,尤其是終生大事幾乎像是一盤賭注,福兮禍兮?讓她越想越是忐忑不安而暗自憂傷,這前途走得很不甘心又很無奈,茫茫然身不由自地隨著還算是陌生人的余燿得前往台北。
淑怡雖然心情沉重,但是仍然盡量以不自然笑臉禮貌式地與他們應對和客氣地寒暄。在余燿得和他們聊敘得很高興時,她覺得淨是在一旁默默,實在顯得很呆傻無趣,就趁他們不注意時悄悄的走出客廳,到院子看著幾叢樹木和一畦畦小花圃發呆。陸太太跟了出來,看她好像有點眼含淚光,就很溫和很關心地問:
「是不是在想家了?」
這一問淑怡眼淚幾乎真要掉下來,但一向倔強的她還是壓抑欲哭的情緒,扮出不自然的笑臉,裝作很輕鬆而不搭調地回答說:
「不是,我在欣賞你們家的院子。這院子很大哦!有果樹和那麼多種美麗的花,這般清靜雅緻的庭園讓人感覺很舒服,有這樣的居住環境真好。我們鄉下家的庭院也很大,但是澎湖土壤不好,冬季風又大,不容易培植出這樣美麗的花卉,所以只有一棵大葉欖仁樹和牆角野生的天人菊和雜草。」
這樣的回話是不是才不會讓人覺得她的見識不膚淺!?還是自卑的掩飾?陸太太可能看得來出來,但是她還是客氣地說:
「這是公家配給的宿舍,還算不錯啦。進來坐坐休息一下,你們下午還要趕火車上台北呢!」
她心裡猜想:余燿得一定是介紹她是如何在媒妁成功而被他帶來的女孩,應完全歸功於他的同鄉林太太,勤於跑到鄉下的她家,一直幫余燿得向淑怡的祖母、母親說盡好話,才作媒成功,並且很快就被「送定」(送些金飾之類)到她家,他的祖母和母親就欣然接受收下,就算是訂婚了。所以雖然只是初見面,但已經是他的未婚妻了。淑怡看到余燿得,心裡想,這個身高不到一七○公分的微胖中等身材,眼睛大大、粗粗短短的眉毛像是以破毛筆隨便撇上,不是俊帥也沒有溫文儒雅的普通相貌,顯然歲數大約有三十以上,約大她有十歲以上了。淑怡在心裡暗暗嘀咕:這樣的人怎麼會將是我的丈夫?好奇怪哦!祖母到底是在替我編導怎樣的人生戲碼呀!
傍晚時分他們到達台北車站,坐一部三輪車直接到余燿得已幫她安排好的暫時寄住處,是余燿得的長官家。在司法大廈矮圍牆內,一處庭院裡,靠矮牆而建的一排兩間連在一起的日式公家宿舍,矮牆外隔一條大路就是總統府。岳科長家是靠裡面的一戶,隔著小花園走出去就是重慶南路,這宿舍大大不如台南陸主任家的寬敞舒適。進入院子向左邊走進去就是三級臺階,臺階上去是長長的走廊,然後是四扇糊紙拉門,裡面究竟有幾個房間,人家不介紹淑怡也不好意思去探究,反正他們一家六口──科長夫婦和兩兒兩女,讓她覺得這房子並不很大,可能房間只夠容納他們一家人,根本不可能有空房間借淑怡暫住,只是暫時性地在大門內的左邊走廊處,臨時以三夾板隔成一個小小房間,剛好可以放一張單人床和一張小小書桌。在院子的左側連著屋子另加蓋了一間簡單的房子,就是廚房和飯廳。淑怡就在他們家搭伙,解決了住食問題。
他們是廣東人,岳科長個子矮小像是個老小孩,穿上中山服後才略有公務員的尊嚴架勢。岳太太比較高大略胖,相貌普通,卻是表現得一副精明強勢的姿態,常兇著臉色以食指指著丈夫的額頭大聲講話,像是在責罵,岳科長只會頭歪一下又歪一下,完全不頂嘴。有時被淑怡不凑巧看到了,岳太太才停手變成笑容對著淑怡笑一笑。因為他們的國語帶有很濃的廣東腔,淑怡講的台灣國語他們還聽得懂,但他們的廣東國語淑怡卻常聽不懂,即使簡單的交談都需要加上比手畫腳。雖然他們對淑怡很好很客氣,可是溝通上有些困難,就算同住在一屋簷下,一起吃三餐,但淑怡很少和他們閒聊,日子過得很孤單寂寞。
在萬般無奈滿腹鬱悶下,淑怡只有呆在小房間裡看書和給同學寫信。想到離開家鄉之前沒有心情也沒有空去向好同學夢慧、媛媛告別,現在略事安定了,覺得應該告知夢慧和媛媛才是,就利用在辦公室忙完工作之餘,給夢慧寫了一封信:
「夢慧:
當妳收到這封信時,我人早已在台北了。很抱歉,離開澎湖前我因為一直在和我祖母、母親發生爭執,心煩意亂,所以根本沒有心情去向所有的好友告別,如果妳們知道了我的狀況相信妳們就不會見怪的。
在祖母的強勢命令和母親早晚的以哭泣相逼之下,我很無奈地於元宵節前就到了台北,並且於二月十五日就開始上班了。是在台北市愛國東路底的台北監獄統計室當雇員,是編制內的人員,所以工作算是安定了,而我也成了人家的未婚妻,此事說來話長,以後再慢慢告訴妳吧。
余燿得暫時讓我寄住的地方是司法大廈附近的公家宿舍,是他的科長家,他們是廣東人,所以他們一家人在講話時我常聽不懂,他們跟我講話時刻意講國語,廣東腔調很重,但是還好,加上比手畫腳勉強能夠溝通,否則如何寄住並且搭伙共食?住處離總統府很近,只隔著一條貴陽街就是總統府,著名的北一女中就在隔著寬闊的重慶南路的對面。總統府前的介壽路也就是總統府的廣場,其北邊是新公園,公園很大,園內林木森森,各種經過設計成形狀不一的花圃,一小區一小區種植著各種各色美麗的花卉。周圍樹蔭森茂,中間有各區美麗花圃,隔成蜿蜒有序又相通的小路,還有亭台魚池,人行道四通八達可通向衡陽路,是頗引人嚮往散步賞景的好去處。住處環境可以說是很清靜悠雅宜人,我只是剛到台北需要去衡陽路購買一些日用品,余燿得就帶我順便轉去略微遊賞一下。自從到台北後,幾乎天天都在下雨,時大時小淅淅瀝瀝細雨紛紛,都已經來一個多月了,還沒有感受到陽光的溫暖與和風的清爽。天色常是陰霾的,在淫雨浸濕下,地方是陌生的,隨便走走,所到之處讓人感覺不是潮潮霉濕就是泥泥濘濘,只有躲在小房子內才有乾爽的感覺,讓我這初來乍到的離島人很不習慣。加上幾乎是舉目無親,大部分時間都是枯囿於屋內──辦公室和住處,繁華的大都市於我好像咫尺天涯,只有孤獨和寂寞陪伴著我。想獨自去新公園散步,又恐寂寥無邊伴孤影孑然,更加重思鄉和憂愁,孤獨的苦悶鬱壓胸懷。
日子過得甚是無趣寂寥,牙齒又痛了,忍不住跑到昆明街的單身宿舍去找余燿得,想請他陪我去找牙科診所治療,到了他們的住處。結果發現他們一群人在打麻將,我默默站了一會兒,沒有人抬頭略微看我一眼,只好又失望又無趣地悄悄回自己的住處。然後自己摸索尋路去和平東路的張牙科診所看醫生。治療好後回到住處,余燿得已經等在那裡。一見面不問青紅皂白的就狠狠罵了我一頓,我聽不清楚也莫明奇妙他在罵我什麼?只有滿腹委屈又害怕地躲進小臥室,躺在床上失望又恐懼地一直哭。
來台北之前,我伯母有把我以信大堂哥在台北的住址給我,在閒極無聊的假日就按址尋找而去,發現他們的住處,是在西園路一處傍著一條大水溝的建築工地附近的高腳工寮,以三夾板和薄木板簡單蓋起的一排相連長長寮屋,有著斜斜的木棉瓦屋頂。門口不遠處就是ㄧ條像小溪的大排水溝,以三夾木板隔成好多間簡陋的高腳總鋪的小房間,便是工人們和其眷屬的住處。以信堂哥是木匠工,一家六口分住兩間,沒有廚房沒有衛浴室設備。我去的時候,大嫂正在屋簷下大水溝邊的泥濘地上生木炭爐火準備煮午飯,我在他們通舖的屋子內,也就是床鋪,略坐一會兒,發現其榻榻米的床舖和棉被都有些潮潮的霉味,也不敢在哪裡略微躺靠躺靠,再巡視其周遭環境,可以感覺到他們的生活條件很簡陋,雖然大嫂有留我吃午飯,但我還是逗留不住地走了。知道了以信哥一家那樣的生活狀況,心裡感到有些失望和難過,本以為在這舉目無親的台北,起碼還有以信堂哥處有時可以去略微敘敘,能感到有親人可稍微寄託歇息,但他們那種窘境顯然也不很方便去打擾。瞭解這種情況之下,我心裡更增加了孤苦無依的惆悵,更為想念妳們,想念家鄉,夜裡常忍不住暗自垂淚。
對了,我還沒有告訴妳,余燿得是我服務機關的上級機關的薦任專員,所以他正在替我向我服務的機關申請宿舍,大概不會等太久我就會搬到自己的宿舍。會是怎樣的房子還不知道,只要有房子住就很好了,其餘的我不敢奢望,狀況會是如何,等安定以後我再寫信告訴妳,也希望妳有空時常給我來信。見到媛媛請代為轉告,說我人已在台北,並請她原諒我沒有辦法向她告別的苦衷。
祝妳
健康快樂
淑怡上
三月十一日」
上班一個多月後,余燿得就幫程淑怡向其服務單位申請到一戶宿舍。星期日兩人一起去看宿舍。是在杭州南路一個巷內的一排連著四戶的日式房子,長長的東西向屋脊相連,掛著斜向其南和北的黑瓦屋頂。其下分隔成四戶,後面也以竹籬笆隔成四個院子,每戶連後院子算起來約有三十坪左右,前門臨著巷道,每戶都是有兩扇拉式的大門,和有四扇大玻璃窗欞,與大門並排臨著巷道。進門處是玄關,然後有一台階,上去是一小客廳,客廳左邊是房間,房間外是走廊和廁所,客廳再進入是廚房,然後就是不小的院子。但是這屋子一進入便是霉臭撲鼻,滿院泥濘和雜草叢生。房子小但格局還算不錯,只是老舊又破爛不堪,一條條朽薄又有隙縫的木條地板,從間隙可以看到暗暗髒亂的下面,踩上去有些軟軟搖晃,好像不小心就會塌陷跌落到地板下的恐怖,而且到處是泥污髒亂和有種讓人難於忍受的霉臭味。與鄰居相隔的牆壁,多處灰泥片片剝落,竹片條條交錯赤裸,只有破敗不堪可形容。這排宿舍的附近,有很多的違章建築,從後巷處一小間一小間相連接直達愛國路邊,使環境顯得有些雜亂,見此環境又想到剛才所見的屋子之髒亂和破敗,淑怡不禁深皺眉頭,心想這種地方和那種爛房子怎能居住?余燿得見到淑怡深皺眉頭一副大為失望的表情,就告訴淑怡,說他會請求服務機關的總務單位盡快幫忙請工人來整修,保證一定會整修到像新屋一般,並且最慢會在他們結婚之前修理完成,淑怡聽到余燿得那樣說,就回答說:
「那不是要修很久嗎?我不到二十四歲是絕對不結婚的。」
余燿得聽此一說即時沉下臉來,不再說什麼。
至此淑怡也知道了余燿得的本事,竟然有辦法以他是部裡官員的關係,使基層的機關派總務單位在一個月裡就把房子給整修完成,淑怡再去看時,果然是煥然一新,裸落的竹條牆壁都填平修好並且刷上白粉漆,地板全翻新了,也鋪上了新的榻榻米,屋頂也加上天花板,刷得白潔潔的,淑怡就利用星期假日去清理打掃一番,院子還有汙泥雜草沒有清理,但因為已可以不需寄住在人家的家裡,便迫不及待地搬進去,隨即寫信稟報祖母、母親。沒想到才搬進去個把禮拜她母親勤子就來了,沒有事先的來信通知就突然的出現了,淑怡很意外!而且還是余燿得去機場接她的!就驚訝地問:
「阿母!妳怎麼快就來了的?怎麼知道這地方?我的信妳收到了嗎?怎麼沒有寫信通知我去接妳?」
「信有收到,也收到燿得的信,阿嬤就叫我趕緊來。我有給燿得回信,所以燿得就去機場接我,就這樣來了,不可以嗎!?」
口氣不太好臉色陰沉,勤子原本待人都是笑容親切的,但自淑怡父親去世後,就變成很習慣沉著臉生悶氣,尤其是對著淑怡更少見笑臉。淑怡稍微懂事時,就明白,母親因常受祖母威嚴的指責心情不好。祖母要母親勤子扮演母兼父職,就得常表現如嚴父那般的嚴肅來管教淑怡,疼愛只能藏在心裡悄悄地做,所以她那種常以生氣的臉色對付淑怡,對淑怡來說很習慣,但這次狀況有些不尋常;又看到余燿得幫拿著簡單的行李跟隨進來,淑怡就有些明白了。
以上內容節錄自《過河不拆橋》明心◎著.白象文化出版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過河不拆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76 |
現代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過河不拆橋
◎與前作《雲雀之歌》不同,以更寬廣的第三人稱視野來細膩刻畫主配角間的種種互動,真實性十足。
◎看陷入婚姻枷鎖的女主角如何運用智慧與勇氣,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在故事開展中將台灣早期的社會文化背景及諸多改革變化輾轉呈現,宛如逝去的時光重現眼前。
想自由飛翔的淑怡終究無法違逆母命,乖乖綁上婚姻的鎖鍊。
但即便如此,她依舊努力振翅、引吭高歌……
在祖母與母親的強勢主張下,她雖然很不情願卻還是嫁給年紀大她很多的他。
但有了他可依附,她才有安定的生活和圓繼續求學之夢。
組成這個家後,他們雖然幫助和提攜不少親友,卻惹來幾位不懂事的晚輩搬弄是非,徒生困擾。
而遭遇工作的競爭和生活壓力的同時,又遇上波波改革浪潮。
看小雲雀如何在時代潮流,努力奮鬥衝過重重難關,創造令人羨慕的人生。
也在故事中略窺台灣光復前後,社會種種轉變及人性的多元化。
作者簡介:
明心
本名陳素嬌;畢業於政治大學行政及公共行政研究班。
因曾經寫了一本《雲雀之歌》,讀過的同學及老同事一再鼓勵我將「淑怡」離開澎湖後的故事繼續寫下去,但因為我忙於繪畫與畫展事宜而無法靜下心來繼續創作。今年夏天,我在美國威斯康辛兒子家無所事事,女兒鼓勵我另以第三人稱試寫這個故事,目的是希望我多用頭腦以免退化,所以我就利用那三個月,完成了《過河不拆橋》一書的寫作。
封面繪圖:陳素嬌
《雲漢高距》:106x37cm
章節試閱
●淑怡到了繁華都市
且說淑怡在祖母的強勢命令下,心情惶惶滿懷悒鬱,黯然獨自搭乘CAT班機先飛到台南。她母親勤子既然設想周到,早已把淑怡的行程寫信通知余燿得,所以一到台南機場下了飛機,余燿得已在機場等著了,隨即帶她先到他在台南的所屬機構的同事陸主任家休息。他跟淑怡說中午陸主任要請他們吃飯,並可以在他家休息兩三個鐘頭,然後再搭下午的火車去台北。
陸主任家是處佔地範圍不小,高高的竹籬笆四方形圍牆內,是獨棟的日式木造房屋宿舍,紅色的雙扇大門,從外觀看起來,會住在這種大院子大宿舍的,必是這地方上職位比較高的官...
且說淑怡在祖母的強勢命令下,心情惶惶滿懷悒鬱,黯然獨自搭乘CAT班機先飛到台南。她母親勤子既然設想周到,早已把淑怡的行程寫信通知余燿得,所以一到台南機場下了飛機,余燿得已在機場等著了,隨即帶她先到他在台南的所屬機構的同事陸主任家休息。他跟淑怡說中午陸主任要請他們吃飯,並可以在他家休息兩三個鐘頭,然後再搭下午的火車去台北。
陸主任家是處佔地範圍不小,高高的竹籬笆四方形圍牆內,是獨棟的日式木造房屋宿舍,紅色的雙扇大門,從外觀看起來,會住在這種大院子大宿舍的,必是這地方上職位比較高的官...
»看全部
作者序
前言:明心引述
我從公務員生涯即將退休之前,就拜在國畫嶺南派大師黃磊生教授門下,開始學習水墨畫,曾經參加多次的畫展。所以在退休後一直努力於學習繪畫,生活過得頗為充實而愉快。
未料於九十六年初因不小心一滑跌坐下去,這嚴重的跌跤,造成壓迫性脊椎骨折,開始時幾乎整天都只能臥在床上,渾身酸痛得連翻身都困難,要躺上床或要起床都需要依賴雇請的家庭照護扶抱幫助,幾乎有一年的期間都在病痛折磨中過日子,想提筆揮毫繪畫變成是奢想。
開始時是在住家附近醫院掛號求醫診治,但沒有什麼效果;轉求中醫診斷治療,花費不少錢也沒...
我從公務員生涯即將退休之前,就拜在國畫嶺南派大師黃磊生教授門下,開始學習水墨畫,曾經參加多次的畫展。所以在退休後一直努力於學習繪畫,生活過得頗為充實而愉快。
未料於九十六年初因不小心一滑跌坐下去,這嚴重的跌跤,造成壓迫性脊椎骨折,開始時幾乎整天都只能臥在床上,渾身酸痛得連翻身都困難,要躺上床或要起床都需要依賴雇請的家庭照護扶抱幫助,幾乎有一年的期間都在病痛折磨中過日子,想提筆揮毫繪畫變成是奢想。
開始時是在住家附近醫院掛號求醫診治,但沒有什麼效果;轉求中醫診斷治療,花費不少錢也沒...
»看全部
目錄
前言:明心引述
淑怡到了繁華都市
各取所好
陋居成貴府
好人難做
住進公寓
大厝家的興衰
日升日落
日暮猶自飛
淑怡到了繁華都市
各取所好
陋居成貴府
好人難做
住進公寓
大厝家的興衰
日升日落
日暮猶自飛
商品資料
- 作者: 明心
- 出版社: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12-19 ISBN/ISSN:978986578037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60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