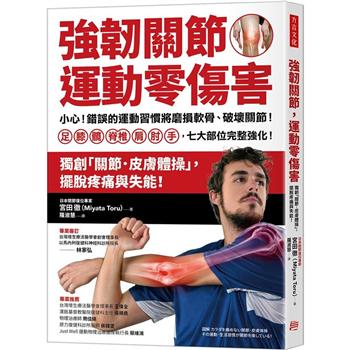三島由紀夫
本名平岡公威,1925年出生於東京。
1947年自東京大學法學部畢業,通過高等文官考試,隨後進入大藏省任職,隔年為了專心從事寫作而從大藏省離職,開始專職作家的生涯。
三島由紀夫在日本文壇擁有高度聲譽,其作品在西方世界也有崇高的評價,曾三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也是二戰結束之後西方譯介最多的日本作家之一。
三島對日本傳統的武士道精神深為讚賞,他對日本二次大戰後社會的西化和日本主權受制於美國非常不滿。1970年11月25日他帶領四名「盾會」成員前往陸上自衛隊東部總監部,挾持師團長要求軍事政變,期使自衛隊能轉變為正常的軍隊,但是卻乏人響應,因而切腹自殺以身殉道,走上了日本武士最絢爛的歸途。
主要著作有《假面的告白》、《金閣寺》、《天人五衰》、《潮騷》、《不道德教育講座》、《新戀愛講座》、《太陽與鐵》、《我青春漫遊的時代》、《反貞女大學》等。
作者簡介:
「能夠寫出這篇〈憂國〉,或許我已該滿足。」──三島由紀夫
情色與大義的終極書寫
三島由紀夫暴烈美學的極致
「〈憂國〉描寫的性愛與死亡的光景,情色與大義的完全融合與相乘作用,堪稱我對這人生抱以期待的唯一至福。」
1936年2月26日,日本陸軍皇道派青年軍官,率部兵變,要求改造國家。兵變遭鎮壓失敗,為首的多位青年軍官在審判後處死。這次兵變,稱為「二.二六事件」。三島由紀夫於1960年以這個事件為背景,寫下短篇小說〈憂國〉,主角是一位新婚不久的中尉,不願舉發事件中的同僚,最後選擇在家切腹自殺,妻子亦殉夫而亡。1965年三島並將〈憂國〉拍成影片,從道具到分鏡一手包辦,自編自導自演。並以「The Rite of Love and Death」(愛與死亡的儀式)為英文片名,發行海外。
〈憂國〉是三島相當喜愛、重視的作品,他曾表示:「如果,忙碌的讀者只能選讀一篇三島的小說,想把三島的優劣一次通通濃縮成精華的小說來閱讀,那麼,我希望讀者選讀的是〈憂國〉。」
〈憂國〉中,三島以細緻柔美的筆調呈現唯美性愛,以寫實手法描述切腹的過程與肉體產生的變化,絢爛、華麗地展現三島由紀夫式的暴烈美學──
「中尉目光所見之處,嘴唇便忠實地跟去描摹。高高起伏的乳房,擁有宛如山櫻花花蕾般的乳頭,被中尉含進嘴裡就硬了。胸脯兩側優雅落下的手臂線條極美,那種渾圓順著手臂到手腕逐漸變細越發巧緻,而更前端,是婚禮當天握著扇子的纖細手指。每根手指,在中尉的唇前,含羞帶怯地躲在每根手指的陰影中……」
「中尉想,這就是切腹嗎?那是一團混亂的感覺,猶如天塌落在頭上,世界翻覆,切腹之前看起來那麼堅定的意志與勇氣,如今彷彿變成一根細小的鐵絲,令人萌生一種必須緊抓著那個不放的不安。拳頭變得濕滑。一看之下,白布與拳頭都已染血。丁字褲也已染成通紅。在如此劇烈的痛苦中,可見的依然可見,存在的依然存在,真是不可思議。」
本書特色
★三島由紀夫自選短篇作品精華,並親自撰文解說,深具代表性。
★收錄三島16歲至36歲的作品,從書中可一窺作家風格與思考的轉變。
★〈繁花盛開的森林〉是三島由紀夫的出道作品,浪漫派風格強烈。
★〈蛋〉以滑稽鬧劇風格諷刺現實,其「純粹的荒謬」為三島難得一見的風格。
★〈寫詩的少年〉敘述了少年時代的三島與言語(觀念)的關係,為三島文學的出發點、文學宿命的起源。
★〈過橋〉描寫的是藝妓世界的勢利、人情與某一面的冷酷。
★〈月〉描寫披頭族世界的疏離、人工化激昂與抒情式的孤獨。
譯者簡介:
劉子倩
政治大學社會系畢業,日本筑波大學社會學碩士,現為專職譯者。譯有小說、勵志、實用、藝術等多種書籍。
章節試閱
憂國
時間過去,最後中尉抽身離開不是因為疲倦。一方面是因為他怕會減弱切腹所需的強大力氣;另一方面,則是怕自己太貪心,會有損最後的甘美回憶。
中尉明確抽身後,一如既往,麗子也溫順地聽從。二人光著身子,手指交纏,一同仰臥,定睛凝視昏暗的天花板。汗水暫時退去,但暖爐的火熱讓他們一點也不冷。這一帶的夜晚很安靜,連車聲都已絕途。四谷車站附近的省線電車及市營電車的聲音,也只在護城河內側回響,在面向赤坂離宮前方大馬路的公園森林遮蔽之下,傳不到這裡。就在這個東京的一角,現在,正有二派分裂的皇軍對峙的緊張感,簡直不像真實的。
二人感到體內燃燒的火熱,一邊回味剛剛嘗到的無上快樂。他們想著那每一瞬間,無止境的接吻滋味,肌膚的觸感,頭暈眼花的每一次快感。但昏暗的天花板上,已有死亡探出頭。那喜悅是最後一次,再也不復返。但,想來,今後縱然再怎麼長壽,亦可確定不會再到達那樣的歡喜,這點二人都有同感。
交纏的指尖觸感,也即將失去。就連現在注視的昏暗天花板的木紋,也將失去。可以感到死亡已逼近身邊。時間不可更替。必須拿出勇氣,主動抓住那死亡。
「好了,開始準備吧。」中尉說。
他的語氣的確毅然決然,但麗子從未聽過丈夫如此溫柔的聲音。
……
樓下的二個房間裡,夫妻如行雲流水般淡淡地分頭忙於準備。中尉去上廁所,順便去浴室淨身,期間,麗子折起丈夫的棉袍,把整套軍服與剛裁開的六尺白布放在浴室,在矮桌放上寫遺書用的和紙,順便打開硯盒磨墨。遺書該寫些什麼她早已想好了。
麗子的手指按著墨條冰冷的金箔,硯池如烏雲散布一下子變黑了,她不再認為這種動作的重複、這手指的壓力、這低微聲音的重複都是為了死。在死亡終於現身之前,那只不過是平淡刻畫時間的日常家務。但隨著研磨益發滑潤的墨條觸感,以及墨香味,都帶有難以形容的晦暗。
裸身套上整齊軍服的中尉自浴室出來了。他默默跪坐在矮桌前,拿起筆,面對白紙有點遲疑。
20
麗子拿著整套白無垢禮服去浴室,淨身,化上淡妝,以白無垢的姿態來到客廳時,她看到燈下的白紙上,只寫了「皇軍萬歲 陸軍步兵中尉武山信二」這行黑字的遺書。
麗子在對面坐下寫遺書時,中尉沉默不語,一臉認真地凝視妻子持筆的雪白手指端正的動作。
中尉攜帶軍刀,麗子在白無垢的腰帶插上匕首,拿著遺書,二人並肩在神壇前默禱後,關掉樓下的燈。中尉在上二樓的途中轉身,黑暗中妻子垂眼跟隨他上樓的白無垢身影,美得令他瞠目。
遺書被並排放置在二樓的壁龕。牆上掛的捲軸本該取下,但那是媒人尾關中將的書法,而且寫的是「至誠」二字,因此最後還是讓它掛在牆上。即便被噴上鮮血,中將應該也會諒解吧。
中尉背對床柱跪坐,把軍刀橫放在膝前。
麗子隔著一張榻榻米跪坐。她全身都是白的,於是唇上刷的淡紅看起來格外嬌豔。
二人隔著一張榻榻米,定定交換目光。中尉的膝前放著軍刀。麗子看了想起洞房花燭夜,不禁悲傷難抑。中尉以壓抑的聲音說:
「沒有介錯在旁,所以我打算切深一點。看起來或許慘不忍睹,但妳不能怕。反正死在旁人看來都是可怕的。千萬不可看了就退縮。知道嗎?」
「是。」麗子深深點頭。
21
看著妻子雪白柔弱的風情,即將赴死的中尉嘗到不可思議的陶醉。現在自己將要著手進行的行為,過去從未對妻子展現,是身為軍人的官方行為,是與戰場決鬥同樣需要覺悟,與戰場陣亡同等同質的死。自己現在要讓妻子看的是戰場英姿。這讓中尉在瞬間陷入奇妙的幻想。戰場的孤獨死亡與眼前美麗的妻子,跨足在這二個次元,具現了本來不可能的二者共存,現在自己將要死去的這種感覺之中,有種難以言喻的甘美。這似乎才是人間至福。能夠讓妻子美麗的眼睛看著自己漸漸死去,就像被馥郁的微風吹拂著死去。在那裡,某種事物得到寬宥。雖不清楚是什麼,但在他人不知的境地,他獲准得到任何人都不被容許的境地。中尉覺得從眼前妻子像新娘子般一身白無垢的美麗身影,彷彿看到自己深愛並且為之獻身的皇室與國家、軍旗,那一切的華麗幻影。那些等同眼前的妻子,無論從何處、無論相距多遠,都不斷放射出聖潔的目光,逼視自己。
麗子也凝視丈夫,她認為丈夫即將赴死的身影,是這人世間最美的風景。很適合穿軍服的中尉,那英挺的眉毛,以及緊抿的唇,如今面對死亡,展現了男人至極之美。
「那麼,我們走吧。」
中尉終於說。麗子深深伏倒在榻榻米上行禮。她的臉就是抬不起來。雖然不想流淚弄花臉上的妝,卻無法遏止淚水。
終於抬頭時,隔著淚水模糊看見的,是已拔出軍刀露出五、六寸刀尖,用白布裹住刀身的丈夫。
把裹好的軍刀放在膝前,中尉鬆開膝蓋盤腿而坐,解開軍服領口的扣子。他的眼睛已不再看妻子。他緩緩將扁平的黃銅扣子一一解開。露出淺黑色的胸膛,繼而露出腹部。他解開腰帶,解開長褲扣子。露出六尺丁字褲的純白。中尉繼續鬆開腹部,雙手把丁字褲向下推,右手拿起軍刀的白布握把。就這樣垂下眼注視自己的腹部,用左手把下腹部的肌肉搓軟。
中尉擔心刀子不夠利,於是折起左邊的長褲,稍微露出左腿,輕輕將刀刃滑過。傷口頓時滲出血珠,數條細小的血痕,在明亮光線的照耀下,流向兩腿之間。
頭一次看到丈夫的血,麗子萌生可怕的悸動。她看著丈夫的臉。中尉坦然凝視鮮血。雖知這只不過是暫時敷衍的安心,麗子還是感到了片刻的安心。
這時中尉如鷹隼的利眼強烈凝視妻子。他把刀子繞到前方,抬起腰,上半身迎向刀尖,從軍服聳起的肩膀可以看出,他正全身用力。中尉想一鼓作氣深深刺入左側腹。尖銳的吆喝聲,貫穿沉默的室內。
雖是中尉自己施的力,感覺卻像是被人拿大鐵棍痛毆側腹。一瞬間,只覺頭暈目眩,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五、六寸長的刀尖已埋進肉裡,拳頭握著的白布貼上腹部。
意識恢復。中尉猜想刀子已貫穿腹膜。呼吸痛苦,心跳急劇,在不似自己體內的遙遠深處,宛如大地裂開迸出滾燙的熔岩,湧現可怕的劇痛。那種劇痛以驚人的速度逼近。中尉不禁想呻吟,但他緊咬下唇忍住。
中尉想,這就是切腹嗎?那是一團混亂的感覺,猶如天塌落在頭上,世界翻覆,切腹之前看起來那麼堅定的意志與勇氣,如今彷彿變成一根細小的鐵絲,令人萌生一種必須緊抓著那個不放的不安。拳頭變得濕滑。一看之下,白布與拳頭都已染血。丁字褲也已染成通紅。在如此劇烈的痛苦中,可見的依然可見,存在的依然存在,真是不可思議。
麗子在中尉把刀插進左側腹的那一瞬間,看到丈夫的臉上就像落幕般倏然失去血色。她極力抗拒想跑過去的衝動。總之非看不可。她必須親眼看著丈夫死去。那是丈夫賦予麗子的任務。隔著一張榻榻米的距離,丈夫緊咬下唇忍痛的臉孔,看起來格外鮮明。那種痛苦分毫不差地正確顯現在眼前。麗子束手無策。
丈夫額頭冒出的汗水發光。中尉閉上眼,又試探般睜眼。他的眼睛已失去往日的光輝,像小動物的眼睛一樣天真恍惚。
痛苦就在麗子的眼前,與那種令麗子粉身碎骨的悲嘆無關,彷彿夏日豔陽般燦爛。那種痛苦越來越高大。向上延伸。丈夫已去了另一個世界,他的存在被痛苦還原,麗子感到他已成為伸手也碰觸不到的痛苦牢籠的囚犯。而且麗子不痛。悲嘆是不痛的。想到這裡,麗子覺得自己與丈夫之間,好像被某人豎起一堵無情的高聳玻璃牆。
憂國
時間過去,最後中尉抽身離開不是因為疲倦。一方面是因為他怕會減弱切腹所需的強大力氣;另一方面,則是怕自己太貪心,會有損最後的甘美回憶。
中尉明確抽身後,一如既往,麗子也溫順地聽從。二人光著身子,手指交纏,一同仰臥,定睛凝視昏暗的天花板。汗水暫時退去,但暖爐的火熱讓他們一點也不冷。這一帶的夜晚很安靜,連車聲都已絕途。四谷車站附近的省線電車及市營電車的聲音,也只在護城河內側回響,在面向赤坂離宮前方大馬路的公園森林遮蔽之下,傳不到這裡。就在這個東京的一角,現在,正有二派分裂的皇軍對峙的緊張感,簡直不...
作者序
解說 三島由紀夫
這次以文庫版的形式出版自選短篇集,令我感到,對於短篇小說這種文學領域,我早已疏遠。我並非跟隨短篇小說的衰亡期這個現代傳播主義的趨勢,像製線工廠縮短工時那樣開始節約短篇創作。是我的心已自然而然遠離了短篇。少年時代,我曾專注在詩與短篇小說,當時籠罩我的那種悲喜,隨著年紀漸增,前者已轉向戲曲,後者似乎也轉向長篇小說。總之,那也是我把自己朝向更有構造性、更多辯、更需耐性的作業推進的證據,顯示出我已需要更巨大的工作帶來的刺激與緊張。
這點,似乎與我的思考方式從箴言型漸漸轉向有系統的思考型不無關係。當我在作品中闡述某個想法時,我變得喜歡慢慢來,寧願多花點時間一步步讓人接受,我開始懂得避免一刀斃命式的說法。說好聽點是思想圓熟了,其實只是性急卻迅速輕捷的聯想作用已隨著年齡漸漸衰退。我等於是從輕騎兵改成重騎兵的裝備。
因此,本書收錄的內容,全是我在輕騎兵時代的作品。不過,雖然這麼一概而論,事實上其中有些作品本身屬於純粹的輕騎兵式,也有些作品已沉悶地朝著重騎兵轉型,完全是為了操練那個才寫的。前者的代表作若是〈遠乘會〉,後者的代表作,就是在我很年輕時(一九四三年)也就是我十八歲時寫的〈中世某殺人慣犯遺留的哲學日記選萃〉了。在這篇簡短的散文詩風格的作品中,出現了殺人哲學、殺人者(藝術家)與航海家(行動家)的對比等等主題,堪稱包含了日後我許多長篇小說的主題萌芽亦不為過。而且,其中也有活在昭和十八年這種戰時,處於大日本帝國即將瓦解的預感下的少年,暗淡又華麗的精神世界的大量寓喻。
24
至於另一篇戰時作品〈繁花盛開的森林〉,相較之下,我已無法喜歡。這篇寫於一九四一年的里爾克式小說,如今看來分明受到某種浪漫派的負面影響與小老頭似的矯揉造作。十六歲的少年,想得到獨創性卻怎麼也得不到,無奈之下只好裝模作樣。附帶一提,出版社堅持將這本短篇集定名為《繁花盛開的森林》,我只好選了這個。
從戰後的作品中,我毫無懸念地選出了自認為最好的作品。
〈遠乘會〉(一九五○年)是在我的短篇寫作技巧終於成熟的時期,運用平行結構(parallelism)的手法描繪的水彩畫,遠乘會的描寫本身,是我自己參加某個騎馬俱樂部出遊活動的速寫,這種在實際上沒有任何戲劇化經驗的微細速寫中穿插某個故事的手法,如今已成為我創作短篇小說的一種常用手法。
〈蛋〉(一九五三年六月號.群像增刊號)曾是不受任何評論家與讀者肯定的作品,但這篇模仿愛倫.坡滑稽鬧劇的珍品,成了我個人偏愛的對象。要解讀為是在諷刺「制裁學生運動的權力」是各位的自由,但我的目的是超越諷刺的無厘頭,我的文筆難得到達這種「純粹的荒謬」的高度。
〈過橋〉與〈女方〉、〈百萬圓煎餅〉、〈報紙〉、〈牡丹〉、〈月〉都只是當時矚目的風景或事物刺激了小說家的感性,於是構成一篇故事。其中尤其是〈過橋〉,在技巧上最成熟,我認為在文體中成功融入了某種有趣又滑稽的客觀性,以及冷淡高雅的客觀性。
〈過橋〉描寫的是藝妓世界的勢利、人情與某一面的冷酷,而〈女方〉描寫演員世界的壯闊與鄙俗以及自我本位,〈月〉描寫披頭族世界的疏離與人工化激昂與抒情式的孤獨……這些作品與以前的狂言作者依循「世界定理」的儀式設定的「世界」不同,只不過是偶然興起窺見那個世界後,那種獨特的色調、言語動作、生活方式,宛如水槽中的奇異熱帶魚,在文藻的藻葉之間若隱若現,自然誘發出每一個世界的故事。所以或許就是這樣漫長的時間,以及自然發生性,賦予這三篇小說某種濃厚感與豐饒的韻味。當然,那都是從我個人的「遊戲」產生的。我把自
己故意放在一個古典小說家的見地,一邊游弋於各種世界,一邊慢慢觀察,用琢磨過的文體寫短篇,等於是出自我腦中的小說家的紳士主義。至今我仍不免認為,短篇小說就該是這種紳士主義的產物。
25
不過,這樣的我,不見得都是用這種遊刃有餘的態度書寫所有的短篇。
本書中,〈寫詩的少年〉、〈海與夕陽〉、〈憂國〉這三篇,在乍看純屬故事的體裁下,隱藏著對我而言最切實的問題,當然站在讀者的立場,不必考慮任何問題性,只要享受故事就行了(例如銀座酒吧的某位媽媽桑,就是把〈憂國〉全然當成黃色小說閱讀,自稱整晚難以入眠),這三篇是我非寫不可的東西。
〈寫詩的少年〉中,敘述了少年時代的我與言語(觀念)的關係,道出了我的文學出發點的任性、卻又宿命的起源。在這裡,出現了一個抱著批評家眼光的冷漠少年,這個少年的自信來自自己也不知情的地方,而且從中隱約可窺見一個自己尚未掀開蓋子的地獄。襲擊他的「詩」的幸福,到頭來,只帶給他「不是詩人」這個結論,但這樣的挫折把少年突然推向「再也不會有幸福降臨的領域」。
〈海與夕陽〉,試圖凝縮展示的是相信奇蹟的到來但它卻未來臨的那種不可思議,不,比奇蹟本身更加不可思議的主題。這個主題想必會是我終生一貫的主題。當然人們或許會立刻聯想到「為何神風不吹」這個大東亞戰爭
最可怕的詩意絕望。神助為何沒有降臨—這個,對信神者而言是最終也是最決定性的疑問。不過,〈海與夕陽〉並非直接將我的戰時體驗寓言化。毋寧,於我而言,最能闡明我的問題性的其實是戰爭體驗,「為何當時海水沒有一分為二」這個等待奇蹟的命題對自己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也是不可能達成的,對此,想必早在〈寫詩的少年〉這個年紀,應該就已有明顯的自覺了。
〈憂國〉的故事本身只是二二六事件外傳,但〈憂國〉描寫的性愛與死亡的光景,情色與大義的完全融合與相乘作用,堪稱我對這人生抱以期待的唯一至福。然而,可悲的是,這種幸福極致,或許終究只能在紙上實現,即便如此也無妨,身為小說家,能夠寫出這篇〈憂國〉,或許我已該滿足。以前我曾寫道:「如果,忙碌的讀者只能選讀一篇三島的小說,想把三島的優劣一次通通濃縮成精華的小說來閱讀,那我希望讀者選讀的是〈憂國〉。」這種心情至今不變。
話說,前面的〈蛋〉也是一例,我個人也偏好全憑知性操作的小故事(conte)類型。在此,作品本身連看似主題的主題都沒有,就像被拉向一定效果的弓,保有徹頭徹尾的緊繃形式,當它被射進讀者的腦中,如果命中了等於是「聊以取樂」。同時,若能構成西洋棋棋手體會到的那種知性緊張的一局,構成毫無意義的一局,則余願足矣。〈報紙〉、〈牡丹〉、〈百萬圓煎餅〉這類小故事,就是我基於這種意圖寫成的短篇中,選出的較佳之作。
解說 三島由紀夫
這次以文庫版的形式出版自選短篇集,令我感到,對於短篇小說這種文學領域,我早已疏遠。我並非跟隨短篇小說的衰亡期這個現代傳播主義的趨勢,像製線工廠縮短工時那樣開始節約短篇創作。是我的心已自然而然遠離了短篇。少年時代,我曾專注在詩與短篇小說,當時籠罩我的那種悲喜,隨著年紀漸增,前者已轉向戲曲,後者似乎也轉向長篇小說。總之,那也是我把自己朝向更有構造性、更多辯、更需耐性的作業推進的證據,顯示出我已需要更巨大的工作帶來的刺激與緊張。
這點,似乎與我的思考方式從箴言型漸漸轉向有系統的思考型不...
目錄
目次
繁花盛開的森林
中世某殺人慣犯遺留的哲學日記選萃
遠乘會
蛋
寫詩的少年
海與夕陽
報紙
牡丹
過橋
女方
百萬圓煎餅
憂國
月
解說 三島由紀夫
目次
繁花盛開的森林
中世某殺人慣犯遺留的哲學日記選萃
遠乘會
蛋
寫詩的少年
海與夕陽
報紙
牡丹
過橋
女方
百萬圓煎餅
憂國
月
解說 三島由紀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