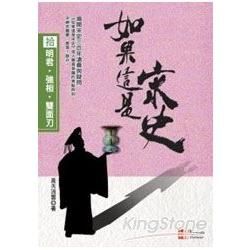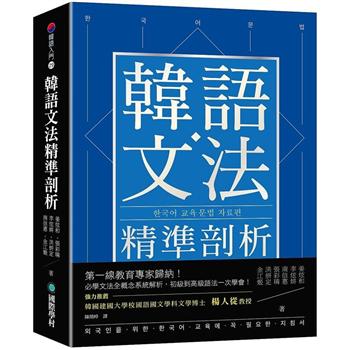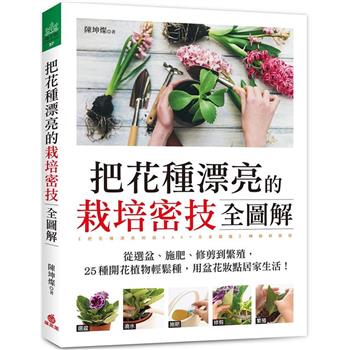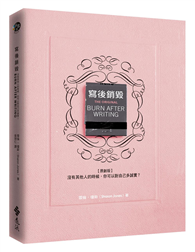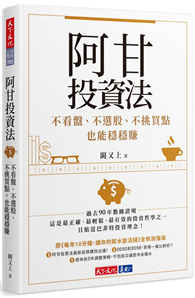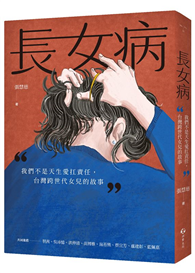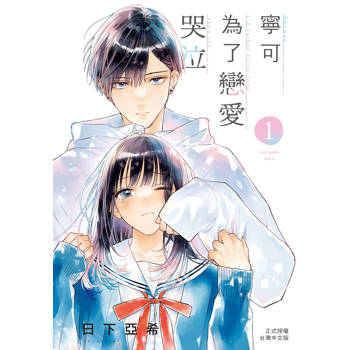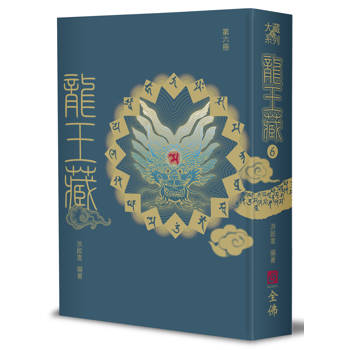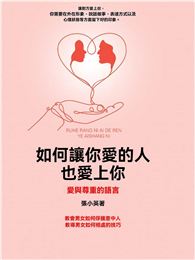﹝王安石罷相全景重播﹞
在宋朝,各種自然界災害,都能和皇帝、臣子、政治、軍事掛上鉤。至於為什麼掛上的,內蘊就太豐富玄妙了。當時就沒幾個人懂,現在……現在還有誰認為汶川大地震、海地大海嘯之類的現象和人類的思維意識變化有聯繫嗎?
所以一切的「天人合一」,都只是人類一廂情願的猜測。可惜卻總有人堅信不移。
熙寧年間就發生過兩次。第一次,熙寧六年。新政在國內如火如荼,王韶、章惇、熊本在邊境上連戰連捷,可是華山突然間地震了,土石流翻滾而下,災害相當不小。
這立即就被文彥博等人抓到了說話機會。在「天人合一」的理論下,華山崩塌,原因就是政治昏暗,百姓受苦,老天爺都看不下去了!
有了宏觀根據,文彥博還能與實際情況聯繫起來。他給神宗上了一份奏章,說的是他某次閒暇出去散心的所見所想。
那次他去大相國寺上香,嗯,很風雅,也很有宗教信仰。不過好像一直以來儒家獨尊天下,「吾乃孔門弟子,誓不與和尚為伍!」這樣的口號流傳好多年了,難道文彥博不知道?並且多年以後,各位君子大賢還以王安石信了佛教,來抵毀王安石的人品,不知用的是什麼樣的雙重標準。
閒話又多了些,回到正題。文彥博峨冠博帶,寬袍飄然地從主殿出來,心情大好,順便向附近的市場走去。
他看見相國寺內,以及御街商行裡,市易司的人員在緊張忙碌。或許是態度過於認真了,讓文彥博非常不爽。
「瓜果之微,錐刀是競,竭澤專利,所剩無幾。」這樣分毫必爭,哪還有我大宋朝的威儀?其結果,只能是傷損泱泱大國的國體,使自己國民離心。更要緊的是,這裡離外賓下榻的使館很近,讓他們看見了,會恥笑我們的!
大家什麼感覺?按文彥博說的改正,這些都得倒過來,純粹就是打腫了臉充胖子,最可鄙視的卑賤虛榮心理。明明宋朝立國之本就在錢,沒錢早就被周邊的虎狼異族給吞了,結果認真賺錢居然是丟臉!
當時各處戰爭吃緊,宋神宗頂住了壓力沒太理會。可是第二次時,神宗第一個害怕了。熙寧七年,宋朝北方大旱,一連七、八個月一滴雨都沒有下。查一下史書,這次乾旱的規範是超大的,不僅宋朝北部這樣,連更北方的遼國也旱得一塌糊塗。
只是遼國人口密度小,疆域太廣大,而且不是純粹的農耕經濟,對旱情的反應沒有宋朝這樣大。尤其是,他們沒有宋朝這樣的「文明」,沒有足夠的「理論依據」把旱情無限上綱,弄個「清楚明白」~~
宋神宗的性格特點在這時顯露,此皇帝勝不驕,卻備加小心,時刻提防敵人報復;敗,或受挫時勇於自我折磨,不用敵人施壓,他自己就會把可能發生的後果上升到災難的程度上。於是不管是勝還是敗,每時每刻都憂心忡忡,提心吊膽。
後來,他就敗在這種個性。
面對旱情,他不用臣子們提醒,自己就整天的念叨,抓住一個大臣問一次。愛卿,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是不是像「保甲法、方田均稅法、青苗法、均輸法等等法」都應該廢除呢?
大臣們這時經過為時五年的新政改革,都有了一定的政治心得了。他們一律躬身靜聽,面色沉重,若有所思,絕不開口。大家都清楚,這事兒輪不到他們說話。
終於有一天,神宗問到了王安石。
面對宋神宗的恐慌,王安石表現得非常鎮定。他說,天旱、水災這樣的事,就算在上古聖君,如堯、舜、禹、湯時也在所難免,都只是些自然現象。我們盡力而為就是,根本不必擔心。何況這五年來風調雨順,連年豐收,按比例來說,現在的乾旱也只是偶然出現。
總而言之,這都是小事(細故),上天有它的意願,我們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了(益修人事)。
這種回答,以我們現代人來看,王安石說的半點錯都沒有。本來嘛,堯、舜、禹時的大水延綿幾十年,只要以人力抗爭,不僅會戰勝,更會留下萬年不滅的美名。可是到了宋神宗的身上,他這番話就錯了。錯得非常徹底,可以說,這是五年改革以來,他和宋神宗的思維相差得最遠的一次。
神宗說,他怕的就是人事之未修,我們都做錯了!
錯了?王安石稍微有了點驚疑,卻絕對沒有再往深處想。他有那麼多的事要去做,尤其是他始終相信,神宗和他的約定,會全心全意地協助他。兩人是堅定的戰友。
於是他只是再次強調,只是小事,一點細故,沒什麼大不了!接著就又放眼天下,尋找可以生財致富,教化國民的好辦法去了。
在他身後,當時年僅二十七歲的皇帝陷入了痛苦的深淵。王安石的態度更加印證了他的擔心,不畏天的人,怎會被天所原諒?這五年來做的事,不僅人不同意,看來連天都反對啊……接下來的時間裡,王安石一如既往地改革做事,宋神宗開始寫罪己詔。
必將改正,爭求上天的諒解,獲得減刑處罰。
站在王安石的立場上,的確可以這樣想。試問,皇帝是同黨,政績很突出,外戰超輝煌,政敵?司馬光之流早就被踢出京城,到外地殘喘去了。最近連唯一敢對抗的文彥博都被貶到外地,還有什麼好擔心的?多做事,做好事,把眼前的難關儘快度過去,才能讓年輕、心慌的小皇帝鎮定下來。
從而對改革的信心更大!
但是現實狀況大出他的意料之外,對他不利的事從這時起,一件接一件,不斷地湧現出來。第一個,他的老朋友司馬光從遠方加急送了一份奏章,積極回應皇帝的挑錯號召。
他一共總結了六條,眼光獨到,我們實在有必要一條條地詳細研究,才能看出大名鼎鼎、光輝偉大的司馬溫公有多麼高超。
一:「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不知他從何處得出這種結論。比如這一句,就算是民間因為青苗法苦不堪言, 而官府居然一無所得?
那三十二間封樁庫的錢帛是從哪兒來的?
二:「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養浮浪之人,這句是最智障的一句話。
按司馬光說,那些無正當職業,無不動產實業的,都是浮浪人。好,東京城裡做小買賣的,夜市上擺攤的人,是不是都是浮浪人了呢?這些人就算都浮浪了,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那麼國家出錢,雇傭他們做事,一來有了正當職業和身分。這樣做了,他們就都不浮浪了,從此社會加倍安定,難道有什麼不好嗎?!
三:「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簡直邏輯混亂,市易法的確與民間買賣抵觸,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北宋自由商業的高度運轉,走回頭路了。可是要注意,對國家快迅積累資金卻有著極大的好處,軍費,這條最重要的問題,無論是均輸法還是青苗法,都沒有市易法來得快。
司馬光居然選擇無視了,「實耗散官物。」說夢話吧。
四:「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最讓人忍無可忍的就是這一句。敢情只有自己的國家治理得盡善盡美了,才能走出國門,去收復失地?那樣還需要關注敵人狀態,尋找最佳的出兵良機了嗎?最起碼的戰爭常識都沒有,不知這人寫《資治通鑑》時是不是有另外一副腦漿。
另外「侵擾」,用詞多好。作為歷史大師,河湟之地與中國是什麼關係,他居然不知道!「得少失多」,他住的洛陽離邊境更近,吐蕃人和西夏人走得有多近知道不?不知道,那麼閉嘴。知道,說了這些話就是該死。王韶開戰前,這兩國的上層貴族都開始通婚了!
五:「團練保甲,教習兇器以疲擾農民。」──兇器,看來農民的本分就是種地,刀槍之類東西一律禁止觸摸,以免變得暴戾。嗯,這個想法很好,和後來元朝蒙古人不謀而合,最好是讓農民們提前一百多年就七、八家合用一把菜刀,那樣就真的「純樸可愛、便於畜養」了。
他怎麼就看不見,沒有保甲法之前,北宋每隔幾年就會鬧一次民變或者兵變,實行保甲法後,這幾年裡,沒有一起造反事件,連帶著民事犯罪率都在下降。在他的眼裡,居然是「疲擾農民」了。就算是疲,也是疲了有特殊身分,知法犯法的人。就算是憂,也只是憂了司馬溫公這樣的「聖賢」!
六:「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讓數字說話吧,「起熙寧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為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合計約三千六百多萬畝。其中官地約二十萬畝。這些土地都是假的?哪來的什麼狂狡之人,怎麼能說到是「妄修水利」
多餘的話還用再說嗎?大家一起歡呼,司馬光萬歲萬歲萬萬歲————————祝您身體健康呷百二,不多不少就比王安石多活一年,好把北宋的大好乾坤像童年的那口缸一樣砸碎……
每條都不成立,但每條都搏得了巨大的歡呼。五年了,終於有人為曾經無比榮耀,現在被逼進絕境的士大夫階層說出了心裡話。
只不過,心裡話並不等同於真實話。生存在這個世界上的成年人都知道,沒有幾顆心靈是完全出於道義良知而說話的。為的,都是生存所必須的利益。
面對司馬光的突然襲擊,王安石沒在意。他沒就此事和宋神宗會談,也沒寫專門文章反駁。帝國千頭萬緒,改革初見成效,還有那麼多的事要做呢。這麼一個手下敗將,突然寫封奏章,有什麼大不了的?可是他怎麼也沒有料到,僅僅幾天之後,新法,全部的新法就被突然間罷除!
這是真正的青天霹靂,王安石被震傻了,他不知道是哪裡出了錯。甚至整個變法集團,包括號稱才幹突出精明強悍的呂惠卿、奸詐詭譎無恥鑽營的鄧綰等等反面角色,也都沒有查覺出是誰做了什麼,把這一切都翻了天。
這暴露出了王安石,以及其集團的最大弱點——警覺性太低,政治手段太劣。
政治,不止是治國,更重要是治人。就是怎麼整人。人類歷史上,有太多的事例證明,兩派相爭,根本不必駁倒對方的見解主張,只要只要在人格上、精神上消滅了對手,就等於徹底勝利。
史書記載某一天陽光明媚,天氣良好,宋神宗到後宮去看望老媽和奶奶。幾句家常話後,從前的曹太后,現在的太皇太后說了句話: 「我從前只要聽到民間的疾苦事,都會告訴仁宗皇帝的,仁宗都會批准我,讓民間好過些。現在也應該這樣。」
神宗非常警覺,回答了四個字:「今無他事。」奶奶要干政,立即就堵死。
但是奶奶繼續說,「我聽說現在民間青苗法、助役錢都不合理,你應該罷免它們。」
神宗回答:「這是利民,不會苦的。」
老奶奶直接提出最重要要求,「王安石的確有才,但得罪的人太多了。你若是真愛惜他,就讓他暫時出京補外職吧。實在想用,過一年再召回來。」
神宗再次駁回,「不行,現在的大臣裡只有王安石能『橫身為國家當事』。」
每句話都被駁回,太皇太后的老毛病發作,她洩氣了,像當年被韓琦等人欺壓一樣,不再說話。這時神宗的弟弟岐王站在旁邊,插了句嘴:「太皇太后說的都是至理名言,真理啊。皇上,您得多想想。」
這時神宗滿腔怒火再也控制不住,對弟弟吼了一句:「是我敗壞天下嗎?那就換你來當皇上!(汝自當之!)」
岐王哭了,他非常傷心,說:「何必這樣呢?」(何至是也)。
大家看完上邊的記載有什麼感想,覺得神宗小題大做嗎?我們來真正反映神宗的真實感受。無論是他的奶奶,還是他的弟弟,都在做著封建時代裡最危險、最惡毒的一件事。
──干涉皇權。
居家是父子,臨政是君臣,這才是皇權的意義。在這個層面上說話,曹老太太和岐王,都是在找死,犯了祖宗家法。
自趙匡胤開始,到趙光義成熟,宋朝的制度就是皇族不許插手政務,連當上了駙馬的人,也終生只有閒職。就算是宋朝的皇帝超寬容,不會因此而治他們的罪,他們自己也要明白犯的錯有多大。
但好玩的是,老奶奶無動於衷,心安理得。而小弟弟居然還哭了,貌似他哥對他太殘暴,讓他傷心了,真是活見鬼!
不是血親的奶奶,和一個不懂事的小弟,這兩人意見神宗可以忽視,可以怒吼,但輪到生身母親出場了,情況就會不一樣。
未來無比神勇剽悍的高太后第一次就政治問題發表意見,態度居然很煽情。她哭著對兒子說,你就讓王安石走吧,他把天下都攪亂了,快沒法過日子了!
宋神宗默然,上天發火,後院也起火,讓他怎麼做嘛。就在這時,《流民圖》、司馬光的奏摺相繼出現,讓他徹底失去自制,把苦心經營了五年新法全部罷除。
以上是關於皇宮內部事件的經過。
總體來說,王安石得罪了士大夫階層,而士大夫階層只是個統稱,裡邊還有各種詳細的劃分。比如地主階層、官僚階層等等。新法多種多樣,把它們得罪了個遍。
如青苗法損害了地主階層的利益;免役法損害了官僚階層的利益;市易法損害了大商人的利益;傷害了神宗奶奶、媽媽、弟弟利益的新法,叫「免行錢」。
話說東京是當時全地球最繁華的地方,想在這個地方過著最享受的生活,得用什麼辦法呢?就比如皇帝、皇族、大臣,這些人上之人,看中了某些好東西,要怎樣得到呢?
拿錢買?開玩笑,那還是權力階層嗎?宋朝的辦法非常巧妙,是收稅之外的再攤派。也就是說,在開封城裡做生意,除了要交正常的稅之外,官府需要的物、料、人、工,都向各個相關的商行無條件、無支付地索取。具體的做法有盤剝、索賄、貪污、參與壟斷經營。
這就是他們能保持在繁華之都的頂層享受最佳生活的奧妙所在,他們不是參與勞動,而是直接當上了最大的沒本錢的老闆。可是「免行錢」把他們的夢幻生活突然間砸碎。
免行錢,就是政府在正常收稅之後,按一定標準再收一筆錢,這筆錢之後,商行不必再向任何方面交任何錢。
相當於一刀砍斷所有皇親國戚京城大臣的發財之路,從此之後,他們全體貴族、上流人物都只能憑有限的工資過日子,這是什麼樣的生活啊,不是把人往死路裡逼嗎?
於是,才有了奶奶、媽媽不顧皇權,流淚勸告,弟弟更是敢於挑戰哥哥的至高無上地位,對國家的法令說三道四。
說到這裡,大家應該清楚了這次皇宮內院裡罷免王安石事件的真正內蘊,對於王安石本人來說,這事情太隱匿了,除非他像以前的呂夷簡、文彥博那樣和太監交情深厚,才能得到些警告,不然,只能蒙在鼓裡。
可是,熙寧六年五月時實行的免行錢,熙寧七年四月間他罷的相,近一年的時間裡,他是受過非常刺激的事件警告的,仍然沒有醒悟,仍然沒有提防,就只能說明他太不善於「整人」了。
對政治的危險性的嚴重低估!
那件非常刺激的事,發生在熙寧七年元月的花燈節上。歷史上非常有名,是著名的王安石劣跡之一。其過程充分表明了王安石有多麼的驕狂跋扈。
當時神宗下令登城觀燈,百官一齊出席。作為宰相,王安石顯得很特殊,他騎著高頭大馬,帶了很多的從人,到了皇宮的宣德門了還不下馬,進了城門仍然不下馬,再往裡走,就要出城門進入皇宮內部了,終於被當值的侍衛喝止。
侍衛非常生氣,在怒喝的同時,出於憤慨,抽傷了王安石的馬。到這裡為止,是不是應該說侍衛們的舉動非常合法呢?畢竟皇權至高無上,哪有作臣子的騎著馬進皇宮的道理?侍衛們就算粗魯了些,也是忠於職守的表現嘛。
有功無罪。
而王安石的反應,就與之正相反了。不僅不悔過,反而變本加厲,化驕狂為撒野了。
王安石大怒,下馬去找皇帝,要神宗把執班的侍衛都送交開封府治罪,不知什麼原因,還牽連到了一個御藥院的太監,也一起扭送。
神宗都答應了,可是開封府尹蔡確卻不同意,其理由就是上面所說的那些,侍衛忠於職守而已,真要處罰的話,以後還有誰敢為皇帝站崗呢?
儘管說得有理,但仍然有十個侍衛被打了板子,與之相對應的王安石騎馬擅入皇宮之罪卻不了了之,皇帝根本不過問。
下朝之後,王安石先翻史料,浩如煙海的各部門記錄中,他終於找到了宋仁宗嘉祐年間行首司的工作日記,裡邊記載所有大臣都在門裡下馬(並於門內下馬)。有了書面依據,他又去找副宰相馮京。
說來真是非同小可,看他在這件事情裡的表現。馮京仔細地回想,想了又想,再想再想,終於開口說話:「安石,非常遺憾,我忘了。」
三元及第的腦子居然把每天上朝的禮儀經過給忘了!最絕妙的是他又加了一句:「……我又隱約記得,曾經在門外下過馬。」
多麼成熟的政治修養,先定下原則——「我忘了。」就此推開所有可能的罪名,接著又表明自己的立場,他贊同文彥博。
王安石面對軟中帶硬的混蛋實在無可奈何,只好再去找線索。這次他得到了一個非常切實,非常有用的第一手資料。有線人說,中書省驅使官溫齊古曾經親眼所見宣德門當天值班打人的侍衛們事後聊天。一個說:把宰相的馬和從人打傷,這罪名可不小啊。
另一個歎了口氣,我難道不知道嗎,只是上面逼得緊,無可奈何!溫齊古聽到後,立即報告給了另一位副宰相王珪。
王珪,是王安石的同年進士,資歷相當深厚,在翰林院裡一幹就是十八年。文章寫得非常漂亮,「其文閎侈瑰麗,自成一家。」在文字高手不計其數的宋朝能得到這樣的評價,其能力可想而知。呵呵~~看他的做事風格。
此人後來當上首相,有個外號叫「三旨相公」。即上朝「取聖旨」、在朝「領聖旨」、下朝「已得聖旨」,是一位再乖巧不過,聽話好使喚的好同志。
這樣的妙人遇到了宣德門宰相被抽事件,只會有一種反應,那就是王安石得趕緊跑,最好一瞬間就出現在溫齊古面前,抓緊時間問。要不然,王珪就有本事把證人給「教育」了。
事情果然是這樣,等王安石趕到後,溫齊古己經神情癡呆,一臉懊喪,恨不得抽自己兩嘴巴。怎麼就這麼多嘴!那是多大的火坑,自己跳進去註定屍骨無存!
王安石無論怎樣問他,他的回答都只有一個,我記不得當時說話的是哪兩個侍衛了……王安石凝視了他一會兒,什麼也沒說就走了。
何苦為難一個芝麻小官!王安石不再追問什麼,讓這條線索斷掉。
堂堂首相被一群侍衛和一個太監突然橫加侮辱,並且是暴力式的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在事發現場時,王安石忍了。他選擇見了皇帝再說。
見到神宗,王安石說了經過,陳述張茂則等人打傷了他的坐騎和從人。宋神宗的回答讓每一個精研宋史的人都愕然。當然最愕然的還是王安石本人,宋神宗居然說:「哦,打傷了?真的打傷了?好,派人去驗傷……」
王安石立即如墜冰窖,這是比宣德門打馬事件更大的侮辱,以首相之位,位極人臣了,受到這樣的欺侮,皇帝居然還不相信!此朝廷再沒有立足之處。
王安石立即提出辭職。
這樣詳細地介紹宣德門事件,不是為了替王安石叫屈,為改革派出氣,而是在說王安石的失敗原因。三個版本無論哪個是真的,都傳達出一個信息。
即王安石失敗的必然性。
他實在是太大意了,強敵環繞身側,與所有舊勢力為敵,有了宣德門外赤裸裸的攻擊行為,居然還沒有先發制人,半年之後,還讓敵人搗了鬼,新法廢除了整整兩天之後,才知道問題出在哪兒。
他不失敗,誰失敗?
…………
宋神宗迅速地一百八十度轉身,把新法又都全面恢復了。看上去很美,大家按部就班,該幹什麼還去幹什麼,把改革大業進行到底嘛!
對不起,主導人世間的事情的,永遠都是思想、思路、心情、品德這些看似虛無飄渺的東西。這些東西是會瞬間改變的,而且一旦改變,就再也沒法恢復到當初。
前後只是相差兩三天,當事人的心情完全改變。焦點就在兩個人的身上:王安石、宋神宗。王安石又一次提出辭職,宋神宗像往常一樣積極挽留。這個過程又是一個感人肺腑的場景。身為皇帝,宋神宗可以說出下面這些話。
──愛卿,你每次辭職,都讓我寢食不安,我想了很久,一定是有什麼地方對你不夠好(待卿不至之處)。你是不是因為宣德門打馬那件事受了委屈?不要委屈,我查得很細,這事背後沒人指使。
王安石表示感謝,但辭職態度堅決。
宋神宗繼續說。
──不是宣德門的事……愛卿,那一定是你看出來我不是個成功的君主(必定是見朕終不能有所成功),所以才拋棄我。
王安石搖頭。不,不是的,你很聰明,很求上進,一定會成功的。而在我之後,也一定會有新的才俊來鋪佐你。
宋神宗更難過了,追問到底是什麼原因。這時王安石強調,他身體有病,實在支撐不住了。神宗立即緊張,換了個追問焦點。
──愛卿得了什麼病?京城裡什麼藥都有,我派太醫每天去給你治療,這是在南方所沒有的條件,你還是留在京城吧。何況天下的事剛有頭緒,你一走,怎麼了得?你一定是有什麼不開心的事,儘管對我說(但為朕盡言)。
王安石這次話都不說了,保持沈默。
宋神宗還不甘休,他進而動之以情。
──我知道你之所以進京為官,並不是為了功名利祿,而是身有才能,要濟世求民,不想白白埋沒。這一點,我們是共同的(皆非為功名也)。我們不是一般的君臣關係!
好了,還有很多,就不一一列舉了。總之是宋神宗激動復激動,溫馨再溫馨,但王安石始終鐵石一樣,不為所動。
看到這些,大家什麼感覺?是不是覺得王安石真是太傲了,皇帝把話說到這份兒上了,還不借坡下驢,真的把皇帝當成了媽,受多大的寵都理所當然了?
嗯,這樣想也沒錯,當年我也一樣。只是再往深裡想一層,與歷史其他的改革事件對比一下,才會知道誰對誰錯。
我個人認為,宋神宗完全錯了。他是個有為的君主不假,但也僅僅是想有為而已。在做的過程中,做得非常的糟糕。就以上面這些挽留王安石、理解王安石的話來說,他就錯了冥王星上去了。
改革是個什麼東西?它是一場戰爭。改革者是元帥,是唯一的指揮者。例子比如秦孝公與商鞅,商鞅為了法令的通行,把秦孝公的親哥哥的鼻子都割了,秦孝公也沒有二話。試問宋神宗做到這一點了嗎?翻開宋史,關於某某人的提升,某某人的貶職,哪怕只是個太監,王安石每次都要大費唇舌,和皇帝辯論,還不一定成功,總被駁回。
這算哪門子的支持?
王安石的政敵,一個個都安然無恙,拿著高薪在洛陽蓋別墅,天天小集團開會,向四面八方傳遞反對信息,這算什麼政治環境?
上面那些溫情感人的話,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正是證明了宋神宗多次拆王安石的台,讓王安石不爽,讓改革進度遲緩的罪證。
與其事後感人,何如當時認真…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如果這是宋史(10):明軍‧強相‧雙面刃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35 |
小說/文學 |
$ 260 |
中國古典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如果這是宋史(10):明軍‧強相‧雙面刃
宋史裡有一個時期是學史者、考古者、甚至是讀史者的“噩夢”!
為什麼?
因為它是說不清的:
.都是“君子”,都是能力突出的,但出發點不同,當時看,似乎都
是忠君愛國。歷史總是堆疊起千層浪,浪花滔盡,誰是真君子?誰是偽
君子?──直到今日,還有人“真”、“偽”不分!
說來悲涼,宋朝是除了唐朝之外,中國文學十分璀璨耀眼的時代,但在
傳世的不朽文學的背後,宋朝之史家,卻有著極扭曲的心靈,掩蓋的、
塗抹的、誤導的… 部份不在少數。今人追根究柢,離不開“勢”“利”二字──真貌總在最後才在有心人筆下才顯現!
.概是“賢帝”。都是為社稷百姓,但出發點不同,當時看,似乎都
是宵衣旰食。歷史總是經過後人千萬遍爬梳,誰失誤了?誰是對的?──直到今日,幾千年後,是當局者迷?抑或是局外人清?!
本書以大量翔實的資料與一貫輕鬆、人性化的言語風格使讀者對這段
“噩夢”從頭疼變得生動有趣。
作者簡介:
高天流雲
‧本名劉羽權,中國瀋陽人。
章節試閱
﹝王安石罷相全景重播﹞
在宋朝,各種自然界災害,都能和皇帝、臣子、政治、軍事掛上鉤。至於為什麼掛上的,內蘊就太豐富玄妙了。當時就沒幾個人懂,現在……現在還有誰認為汶川大地震、海地大海嘯之類的現象和人類的思維意識變化有聯繫嗎?
所以一切的「天人合一」,都只是人類一廂情願的猜測。可惜卻總有人堅信不移。
熙寧年間就發生過兩次。第一次,熙寧六年。新政在國內如火如荼,王韶、章惇、熊本在邊境上連戰連捷,可是華山突然間地震了,土石流翻滾而下,災害相當不小。
這立即就被文彥博等人抓到了說話機會。...
在宋朝,各種自然界災害,都能和皇帝、臣子、政治、軍事掛上鉤。至於為什麼掛上的,內蘊就太豐富玄妙了。當時就沒幾個人懂,現在……現在還有誰認為汶川大地震、海地大海嘯之類的現象和人類的思維意識變化有聯繫嗎?
所以一切的「天人合一」,都只是人類一廂情願的猜測。可惜卻總有人堅信不移。
熙寧年間就發生過兩次。第一次,熙寧六年。新政在國內如火如荼,王韶、章惇、熊本在邊境上連戰連捷,可是華山突然間地震了,土石流翻滾而下,災害相當不小。
這立即就被文彥博等人抓到了說話機會。...
»看全部
目錄
第一章 北宋三人行
第二章 千夫所指復熙河
第三章 到底誰是皇帝
第四章 異域鐵血鑄輝煌
第五章 王安石罷相全景重播
第六章 人只為己,天誅地滅
第七章 遼國分水嶺
第八章 習慣性誣陷
第九章 陌上花落怨阿誰
第十章 巔峰悄然退
第二章 千夫所指復熙河
第三章 到底誰是皇帝
第四章 異域鐵血鑄輝煌
第五章 王安石罷相全景重播
第六章 人只為己,天誅地滅
第七章 遼國分水嶺
第八章 習慣性誣陷
第九章 陌上花落怨阿誰
第十章 巔峰悄然退
商品資料
- 作者: 高天流雲
- 出版社: 知本家 出版日期:2010-10-29 ISBN/ISSN:978986622306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64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中國古典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