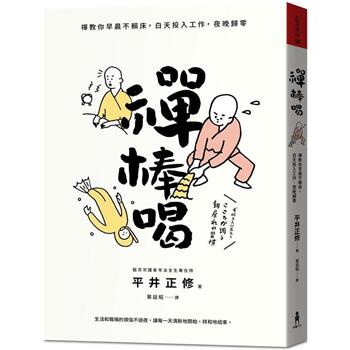她既是十七歲的少女,也是四十二歲的歐巴桑!消失的二十五年歲月,是人生最光華燦爛的階段,她要如何面對直接步入下坡的自己?一陣突如其來的午後驟雨,打亂原本熱鬧的校慶遊行計畫。十七歲的高二女生一之瀨真理子,結束忙碌的校慶活動回到家中,在音樂中沉沉入睡。醒來時,卻發現自己不再是花樣年華的十七歲,而是四十二歲的已婚婦女!已經有結縭二十年的丈夫,更有一名跟自己同年齡的女兒!到底怎麼回事?周遭的人相信她只是短暫失憶,她則堅信自己是穿越了時間縫隙,來到這個時空。但是如何才能回到原先的時空?真理子毫無頭緒。更棘手
譯者簡介:
蔡佩青,淡江大學日本語言學系畢業,日本名古屋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目前於名古屋大學文學研究所攻讀博士,從事日本古典文學的說話文學研究。曾任日語雜誌《EZJapan》主編、輔仁大學及文化大學推廣部日語講師。著有《日本語文法知惠袋》、《商務日本語會話》等多本日文文法書,及旅遊書《千年京都-陰陽師與平安朝之旅》。
各界推薦
得獎紀錄:
佐藤正子推薦(日本女詩人):.北村在執筆本書時,也受到失去雙親的打擊。據說當時辭去教職成為專業作家,是為了照顧雙親。因此更深刻感受其描述故事的技巧性,清晰性,以及誠實的人格。.本書的主角能在確認過去時光之中,以真性情往來深為家長的立場以及作為兒女的立場,是因為北村將自己的體驗託付給真理子了吧。並且將櫻木夫妻設定為高中老師,也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優勢:櫻木在書中代替北村重執教鞭?作者含願的作品裡,令中年讀者看得心有戚戚焉。.讀者將「某個時代的自己」與現在的自己結合。我們的外表雖然是與年齡相符的成熟大人,但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我,是一則故事。不管是誰都是一本書。但那本書卻掉頁了。該怎麼辦?把那本書丟掉嗎?還是繼續閱讀下去呢?」這是書中主角一之瀨真理子所說的話,縱使失去人生最珍貴的二十五年的光陰,而且或許永遠無法追回,但她仍積極地面對眼前的困境,至少,在這個世界裡,仍有該做的事。不管怎樣,都要勇敢地活下去。雖然人生處處充滿無奈,這部作品卻處處給予人信心。與其說這是科幻或奇幻小說,不如說是心理小說。時間跳躍的突兀手法,凸顯了個人主觀心理感受與外在客觀環境觀點的強烈對比。主角從十七歲跳到四十二歲,又面對自己未能經歷的十七、八歲
得獎紀錄:佐藤正子推薦(日本女詩人):.北村在執筆本書時,也受到失去雙親的打擊。據說當時辭去教職成為專業作家,是為了照顧雙親。因此更深刻感受其描述故事的技巧性,清晰性,以及誠實的人格。.本書的主角能在確認過去時光之中,以真性情往來深為家長的立場以及作為兒女的立場,是因為北村將自己的體驗託付給真理子了吧。並且將櫻木夫妻設定為高中老師,也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優勢:櫻木在書中代替北村重執教鞭?作者含願的作品裡,令中年讀者看得心有戚戚焉。.讀者將「某個時代的自己」與現在的自己結合。我們的外表雖然是與年齡相符...
章節試閱
序章
《白色巨塔》是父親在看的書,閒著沒事的星期天,偶然拿起來,就一口氣看完了。拍成了電視劇,由佐藤慶飾演財前五郎。
其實,那個佐藤慶,從他演〈太閤記〉 以來,我就很喜歡。星期六的重播也都有看,我還記得演到本能寺之變時的旁白:「明智光秀懷著背叛之心渡過桂川,是夜已泛白的清晨」。
但是,〈白色巨塔〉裡的他,感覺很像被周遭的人耍著轉的小壞蛋,魅力差了那麼一點。
「是九月吧?」
小池說。我點頭:
「九月有很多電視節目結束。」
沉默了一會兒,我看著雨。圍牆上,水濺起手掌寬的水花。有一種,整個世界只有這個學校,這個學校只有這兩個人被留下來了的感覺。
我說。
「……明天,可以跳土風舞嗎?」
文化祭時男校的學生會來看。
壓軸的終曲是校園土風舞。
「沒辦法吧。因為氣象預報說颱風要來。」
「即使放晴,這樣的地板也沒辦法跳吧。」
小池望向這邊:
「一之瀨,妳去年有跳嗎?」
我搖頭。
「──今年準備要跳嗎?」
「嗯。」過了一會兒,我繼續說:「怎麼樣都可以啦,我不想還沒結束就回家,而只在一旁看也覺得討厭不是嗎?……喂,土風舞的曲子,遠遠地聽,讓人感到一股很受不了的悲傷,對吧?奧克拉荷馬之戀 也是,販子舞 也是。妳不覺得與其聽這些曲子,還不如加入其中比較好。」
小池笑笑:
「也許吧。會讓人這麼想,那裡一定藏了叫人跳舞的陰謀嘍。」
「原來如此。是陰謀啊。」
「總而言之……一之瀨。」
「幹嘛?」
「還有明年啊。我們才二年級。」
「對啊。還不到最後。」
小池把書包拖過來,啪地打開,拿出鉛筆盒。
「剛剛的紙。」
「啊?」
「格理弗先生,拿出來。」
我從口袋裡掏出塗成紅色的模造紙,小池接過去,翻過來,放在書包上。然後,她拿出常用的青綠色自動鉛筆,沙沙地寫了些字。
還給我後,我小聲念:
「──明天會放晴。小池」
「附我的簽名。十年過後會增值噢。」
「什麼啦,這是什麼東西?」
「是紀念啊。紀念今天這個日子。」
雨水不斷地從格理弗的臉龐流下。
巨人,彷彿目擊了無限悲傷的事,無聲地哭泣。
小池站起來,伸了個懶腰。然後,一副突然想到什麼似地:
「過了十年,我們會在做什麼呢?」
「應該結婚了吧。」
「說不定兩個人都在照顧小孩。」
「真不可思議。」
小池又坐下。
「妳不覺得小學時,國中生看起來也很像大人。」
「對、對。完全不是競爭對手的感覺。」
「現在看國中生,根本是小孩子嘛。」
「照這樣的歪理,一下子就會變成大人吧。」
「這樣也很討厭。」
「……喂,妳記得《冰點》裡,內藤洋子被新珠三千代說:『妳隱瞞了什麼吧。』那一幕嗎?」
「不記得了。」
「她是這麼回答的:『太宰治說:「所謂變成大人,就是擁有祕密。」』」
小池笑了,「真是討厭的女兒。」
然而,當時我介意的是,在什麼樣的時刻,一個人會變成大人呢?大人看來像是存在於與我們完全不同的世界裡。好像在很高的樓梯上。但,實際上又是如何呢?
仔細想想,從小學到國中,然後到現在的自己,所謂「大人」的地方,也是爬在幾乎察覺不出坡度的緩坡上,不知不覺就到了吧。
「一之瀨會跟怎麼樣的人結婚呢?喂,如果可以看見未來丈夫的臉,妳會怎麼做?」
「我才不看呢!」
「為什麼?」
「因為,那樣不是很沒趣嗎?」
「說得也是。」
小池突然半彎腰:
「喂,我們不是可以這樣坐嗎?」
她拉高裙子,膝蓋處往外折,腳從正上方看變成M字型,坐在地板上。
「嗯。」
「聽說男生如果這樣坐的話,腳會痛,沒辦法。」
「真的嗎?」
我也學她的坐姿,把跪坐姿勢向兩邊倒,輕鬆多了。
「田邊說的。她哥哥和弟弟都痛得無法持續這樣子坐。」
「好奇怪噢。」
「好奇怪噢。」
雨聲,嘩啦嘩啦地更響了。
※※※
因為話劇社的人來了,所以我決定和小池道別回家去。
當然嘍,我是不可能騎腳踏車的。在公車站旁的商店等時間,然後搭上公車。因為這條路線必須先經過車站再回來,所以繞了段遠路。
沿著街道,路的左側是水溝。必須過橋才進入各個人家。汙水應該會排流進這裡,但看起來總是清澈的小河。而今天,飛沫四濺地湍急奔流。
我在前往國道和海岸道路的交叉口下車。一開傘,就要被風吹走了。從這裡到家還有一段路,很難走。風無所謂從哪邊吹來,像是從四面八方吹來的感覺。
我抱著皮書包走。才前進了一會兒,裙子已經貼在腿上了。
好不容易到家了。今天是星期六,所以看診時間已經結束。我繞到後面,但門鎖上了。
「這種日子……」
我開口發出聲。車子不在。真擔心是不是母親身體惡化了。
我把手伸向放著鑰匙的走廊地板下的柱子後面。用那把鑰匙開了門。
因為滴著水,所以我在走廊上把裙子脫下。先放在舊報紙上。
到廚房開了日光燈,但沒看到什麼留言紙條。
一定是因為這般雨勢,父親開車送護士到車站了吧。母親也跟著一道去了。今天這樣子要撐傘去買東西也很難。所以開車去了。
這麼一想,心情輕鬆多了。
把上衣掛在衣架上。雖然袖子濕了,會自然乾吧。我拿著從格理弗先生上衣裁下的一角,到處晃來晃去,最後拿起書架上文學全集的其中一冊,夾在封面下。
等裙子半乾之後用熨斗燙燙吧。
穿上長褲,換了襯衫,拉上可可色的窗簾。
才剛過四點,但因這般天氣,家裡昏昏暗暗的。我走進八疊和室,打開音響,裡面還放著莫札特。糟了,我一邊想一邊拿出唱片,噴上清潔劑。用擦拭布轉一圈擦了擦。放好唱片,按下開關,放上唱針。
輕快的序曲響起。
我躺下來,讓音樂傳進耳朵。也許是累了,聽到一半頭就開始昏沉。我把旁邊的坐墊拉過來,把頭放進坐墊底下。
坐墊套上畫了幾朵淡粉紅色和青綠色的小薔薇花。我磨蹭著半邊臉,像貓一樣蜷起身子。併攏的雙腳相互摩擦,讓右肩到手臂的部份感覺著榻榻米。「如果是夏天的話……」我想,「如果是夏天的話,裸露的手臂,一定會印上榻榻米的痕跡
吧。」
遙遠的雨聲傳進耳裡,和唱片的樂聲重疊。唱針走到最後,會自動跳起,所以睡著也沒關係。但是,就快到〈問情為何物〉了。我一邊想,旋律彷彿融化了似地,
將我包圍,
將我包圍,
現在,聽見的是費加洛唱的〈別再飛了,花蝴蝶〉。
將我包圍……
「別再飛了,妳這花蝴蝶……」
第一章
※※※
……緊閉的眼底一片黑暗。臉頰下感受到枕頭、床單的觸感。
我睡了多久呢?會感冒吧,我想,但感覺剛剛好。不熱也不冷。
雨聲,稍微遠了些。聽不見唱片的音樂。
——停了。不切掉電源不行,會被媽媽嘮叨浪費電。再一下下,再一下下,就把眼睛睜開吧。
右手指尖抓住床單。
——床單!
我驚慌地睜開眼睛。一瞬間,身體僵住了。
「這是哪裡?」
放音響的地方,擺著沒見過的衣櫃。可能是因為仰頭看的緣故,好高,好重的壓迫感。我在哪兒?
——我在房間的一隅,鋪了被墊在睡覺。
一個人也沒有。
我惶恐地起身。
到底,是誰?什麼時候?把我搬到這地方來?腳的那一頭是拉門。在那前面放著一臺機器,看來好像是電子琴。
我放低視線,看看自己的穿著,大大地吞了一口口水。衣服換過了。被誰換的?
身體突然一陣發熱。
印著淡淡碎花圖樣的上衣,和帶點駝色的百褶裙。我被穿上了寬鬆且沒有腰身的衣服。像個疲憊的人,偶然橫躺著小憩假眠一下。
可以看見窗外的樹木。這裡似乎是二樓。我站起身來。放眼望去,是隨處可見而我卻一次也沒見過的風景。房子屋頂被下了很久的雨給淋濕了。很普通的住宅區。只是總覺得哪裡不一樣。
我眺望一會兒,發現了「某個東西」。電視天線高得不像話,而且數量很多。好像是用來發射電波還是什麼其他用途,有些人家裝了像是圓盤狀的雷達。但那些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我並不認得這個房間。
——是不是該逃走比較好?
我輕手輕腳地拉開門。有個走廊,緊接著右邊就有樓梯。
我覺得好像變成愛麗絲夢遊仙境了。
忍住不發出腳步聲,一階一階走下樓。來到樓下,靠近走廊一側,放著一臺附有蛇狀管線的橘色機器。電源線露在外面,所以是電器用品。但又不是吸塵機。是什麼啊?
有扇門開著,我擔心是不是會有可怕的男人出現。想像總是往壞的一邊思考運作。
沿著走廊稍微向前進,庭院那邊響起金屬所發出的鏗鏗鏘鏘聲。嚇我一跳。透過玻璃窗看,一名穿著制服的高中女生正開了門進來。撐著花樣別致的傘。
瞥見了她的身影。
我一片混亂。霎時不知該如何是好。就那樣呆站在那裡。
走廊那端,嘎啦一聲門開了,響起「我回來了」的聲音。很平常的打招呼。沉著穩重的聲調。這裡是那女孩的家。
只能去問問她情況了。再怎麼說,她跟我同性別,而且比較年輕。要開口說話,沒有比她更適合的人選了。我下定決心,沿著走廊前進。
她的書包——不,不如說是提包。不是皮製的書包,難道不是放學回來嗎?——那提包先被擱在走廊上。接著,我看見了制服的背面。跟我們的不同,是海藍色那種雅致的藍。沒見過這種制服。很瀟灑。大概是上東京那一帶的私立學校吧。
她沒注意到我,正要往對面的房間裡去。我戰戰兢兢,終於發出聲音。
「——請問。」
她突然停下腳步,回過頭。制服胸前是向日葵色的領帶。眼大嘴大輪廓鮮明。看來在班上也是個顯眼的小孩。
她,呼地頓了口氣:
「……討厭,不要嚇我啦!」
就那樣,又要走進去了。我慌慌張張地:
「不好意思。請問……」
這次,海藍色的背確實定住了。然後,比剛才更緩慢地,回頭。我謹慎地選擇詞彙。
「請告訴我。這裡,是誰的家呢?」
她眨了眨眼。什麼樣的祕密將從她的嘴裡洩漏出來呢?像等待著宣判,我,等待著下一句話。
她睜大了眼睛看著我。然後說:
「妳在開玩笑嗎?——媽媽。」
※※※
「啊?」
女高中生所說的話,確實傳進了我的耳裡。但,並沒有轉換成有意義的語言,只是一種聲音在響。兩個音的連結——ㄇㄚ、˙ㄇㄚ。
暱稱、小名?不管怎樣,我跟這個人是第一次見面。不,是我失去了意識。她說不定知道我的事。
我們就那樣互看了一會兒。不知何處響起了汽車喇叭聲。
我終於開口說:
「不是……不是開玩笑……這裡是哪裡?」
女高中生的表情,從猶豫轉為半信半疑,然後漸漸僵硬。
我的態度、表情,是如此強烈地辯解著吧。
沉默變成一種重擔,用力地推壓著我——發生了非比尋常事件的那種沉重感,像落入陷阱的小狐狸,心臟緊縮了起來。
不久,女高中生小聲地說:
「……真的嗎?」
之後嘴巴又動了兩三下。但是,似乎因找不到適當的話語而感到困惑——彼此彼此。
我說:
「總之……」
到這裡又沉默了。「總而言之」什麼東西啊,我也想對自己說。
她退到後面,打開拉門。
「……喂,等等。」
我不清不楚地邊說邊揮手。依然緊張地,「總之」跟在她身後。
穿過和室,盡頭是廚房。
牆邊,放著電視。沒看見轉臺器。形狀怪異的電視機。畫面異常地大。在那下面,有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的機器。大概是FM還是什麼的接收裝置吧。
女高中生拉了面前的椅子,要我坐下。
「要喝果汁嗎?天氣有些涼,喝紅茶比較好吧?媽……」她止住說了一半的話,「妳喜歡紅茶對吧?」
她把水裝進茶壺,放上瓦斯爐。然後,拿起流理臺對面一只圖樣我沒看過的罐子。看來像是裝水果糖的,但好像是紅茶。
在我家,媽媽從附近商店買來的是日東紅茶。要是舶來品的話就是立頓茶包。這圖案與那兩種都不同。
她打開抽屜,取出湯匙,用湯匙柄砰地扳開蓋子。茶壺是玻璃製的。
她接著打開餐盤櫃,拿出兩只別致的紅茶杯排在桌上。
塑膠桌巾是杜鵑花的圖樣。
「太累了吧。只是這樣——對吧?」
我明白,她是故意不經意地說。嗶嗶,水煮開了。
紅茶香飄散在空中。薄瓷茶杯是帶點紅的琥珀色,很漂亮。
「呃——這是外國貨嗎?」
我想應該說點什麼,總之開了口。她瞬間停住正要示意我喝茶的手,回頭看罐子。念著英文字:
「罐子是Fortnum & Mason。但裡面的東西是在yokado 買的補充包吧——我也不太清楚。」
我彷彿被下了咒語。她直盯著我看,然後像再也忍不住似地開始說:
「學生時代執著於Jackson 的Princess Royal。年輕時只喝那種。TWININGS 的話,只限Queen Mary。喜歡紅茶,也收集過紅茶迷你罐。但要看品牌,有的沒買。開始是因為那是拍賣的贈品。本來把它排在書架前,但有了小孩後,就忙得顧不得那些。本來擺著裝飾的罐子,也在不知不覺間消失了。別說收集罐子了,連喝紅茶——現在喝什麼都無所謂了。」
我彷彿被某種東西逐漸緊逼捆綁。
「……這是在講誰的事情?」
簡直是——但,這種事,不可能發生。我不知道。什麼是Princess Royal和Queen Mary。
對方的回應也開始亂了陣腳。
「喂,真的不是在開玩笑嗎?」
我輕輕搖頭。
女高中生一臉困惑:「真有這種事?」她問的是自己,然後,下定決心般,慢慢地:
「注意聽噢,我是,櫻木美也子。櫻木是櫻花樹,美也子的『美』是美麗的美。『也』是這個字──」她在空中寫給我看,「知乎者也的『也』,『子』是孩子的子。」
櫻木美也子。然後,她看著我。意思是要我說出我的名字吧。
「我叫一之瀨真理子。」
對方一驚,看起來很不安,表情愈來愈困惑。然後:
「……第一的一,之後的之,三點水的瀨,真理之子。出生在千葉縣,對吧?」
我緊閉雙脣。她對我——瞭若指掌。
※※※
雖然覺得口渴,但就讓它乾渴吧。紅茶碰都沒被碰地擱置在兩人之間。
美也子彷彿渡著老舊的木板橋,非常慎重地說。
一慌,就會踩空噢。腳會掉到木板下噢。那底下,是一片黑暗。
「我十七歲。」
學校前的商店,有賣飲料和麵包。有細長的木頭椅子。坐在那裡吃喝著買來的東西。也有小孩利用等公車的時間吃炒麵。旁邊有桌子,堆著雜誌。
也有《Seven Teen》 。Syoken和Jouri 的黑白照片很受歡迎。對了,本間千代子模仿美國連續劇女主角的彩色照片是登在《ST》雜誌上的吧?還是不對?
這種事——我思考著這種事,是為了想拖延一下,接下來我像糊塗妖精似的回答。
我動了嘴脣,說。
「……我也是十七歲。」
為什麼?連我自己也覺得像夢囈般無法確定。的確是十七,明明是無需懷疑的數字十七啊。
美也子的大眼睜得更大了,然後挪動手,喝下紅茶。
不像是為了想喝而喝。或許是想從某個地方逃出。
她眉毛算是濃密吧,形狀很好看。人如其名的美少女──像某個人。
我,直盯著茶杯。想窺視裡面。小小的,朦朧的,水鏡。
沉默的時光又流動了一會兒。
我也不是那麼笨。如果冷靜思考,也看得出美也子沉默的……意義。要確認是很簡單的。但,教人害怕。
──這種事,是不可能發生的。
我暫且先用手摸摸身體。從腋下到肚子。然後,看看手,想伸手摸臉,又在中途打住。
這種事,──做這種事,也不能怎麼樣。
我的思緒彷彿即將飛躍深溝,我說:
「──有──鏡子嗎?」
令人欣慰的是,聲音並沒有啞掉。美也子吃了一驚,彷彿自己站在我的立場上說出那樣的話。她好像說了:「不要看比較好吧。」我的心震了一下。
她從椅子上站起來,拿了一個暗紅色的小四方鏡給我──轉到背面。
然後,是為我著想吧,她移到房間角落。然而,對我而言,有「觀眾」反而比較好。只有我自己的話,應該,很難,下決心去看,那東西──鏡子,還有,映照在那上面的東西。
我想,我應該不會抓狂吧。那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真的變成那樣,我該怎麼辦才好?總之,在他人面前抓狂,會更加悲慘。沒錯,因為我正如媽媽所說,太倔強了。
我把鏡子反過來,凝視很久。
不論什麼事,只要先想像最壞狀況,就容易忍過去了噢。真理子。
──並沒有想像中的糟。我是說想像中的。
眼角上淡淡的烏鴉腳印,似乎一笑皺紋就會加深。即使看十次《三度笠是啥東西》,看二十次《泡泡假期》,現在的我都笑不出來吧。
下巴嚴格說來肥肥的。
然後,最糟的是皮膚呈現可悲的疲憊。是因為拿美也子在眼前比較的緣故吧。不、不是的。我是和就在幾小時前,在學校看到的鏡子裡的臉相比的。
和十七歲的公主相比。啊啊,說真的,連那麼笨拙的蝴蝶結,都挺配那偌大鏡子裡的年輕孩子。
──小池,正如妳所說。我,那時候,就像個洋娃娃。
我──不是誇大其詞,真的無比可愛!
然後,過了幾個小時。
理性告訴我,這是一場夢。但是,人會做如此清晰的夢嗎?鏡子握在手中的觸感,不是現實的東西嗎?
我,必須接受這個事實嗎……
一股什麼忽然湧上。
不是悲哀。悲哀,是當我一個人時,誠惶誠恐地垂頭喪氣而來的吧。不是那種東西。
湧上的是,對某種不知名東西的思念,成不了事的憤慨。
對,真的可以原諒這麼沒道理的事嗎?
我放下鏡子,轉向美也子所在的方向。然後,連我自己都很意外,我竟對她微笑。
她站在大冰箱前,臉上多少浮現了點安心的表情。我說:
「看不出來是十七歲欸。」
「……對啊。」
我保持微笑。
「如果我大吼大叫的話,妳想妳會怎麼辦?」
「嗯。」美也子非常輕柔地,補上一句,「還有茶杯和盤子呢!」
──既然是廚房,也有菜刀喔。美也子,盤子雖然沒有破掉,但還有其他破掉的東西噢。我的心,粉碎了。
我看起來冷靜嗎?一點也不。我的腦中,現在,正吹著風速四十公里的颱風。正因如此,才繃緊臉,讓它變成微笑。因為無法安靜不動,才用說話來代替行動。
該如何是好,該如何?
「不可能是鏡子有問題,對吧?」
「真不巧──」
「真是不湊巧。」我也維持輕聲細語,緊接著說,「現在,是昭和幾年?」
她,一驚,然後,難以說出口似的:
「已經,不是昭和了。」
「啊……」
對啊,這種事也有可能發生。我出的牌被吃掉了。
不過反而因此收回伸出了一半的腳。試著問。
「從昭和變成什麼了?」
「平成。『地平』和『天成』。」
並且,她說話的同時,一邊在空中寫字教我。我好像變成小學生了。
「平成──」
美也子,重重地點頭:
「欸,該怎麼說呢?我是要問──您那邊是幾年呢?」
聽了我說的年號,美也子手指垂下。然後,在掌心上寫著什麼。是數字。在計算。
我察覺:
「距今,大約幾年前?」
美也子,吞了一口口水,抱歉似地回答:
「大概,二十五年前左右。」
※※※
四分之一個世紀。
「太過分了……」
彷彿我坐的椅子、地板以及那下面的地,突然全被撤走似的。
到此為止了,我的執著也是。
我自己知道自己的嘴脣顫抖著,臉色變了。
該如何撐下去呢?對十七歲的小女生而言。啊啊,天啊,竟如此殘酷。一伸手,二十五年實在太遠。
「但是,」美也子立刻反應。「馬上就會想起來啦。」
「想起來?」
「就是啊,到現在為止的事情啊。因為妳還能這麼沉著,沒問題的。沒什麼好擔心的。因為有點累,所以記憶亂掉了啦。」
「──等等。妳說的,是什麼意思?」
「什麼東西是什麼意思?媽……欸,唔,總之是喪失記憶吧。那個啊,就是那個『這裡是哪裡?我是誰?』」
「我知道自己是誰啊!」
「話雖如此……」
「我──一之瀨真理子,雖然不知道怎麼了,但我從二十五年前飛到這裡來了。」
我不經意將手繞圈轉。像龍捲風一樣。我,像是被迫搭上了那個。
「也可以這麼說。」
「也可以?」
「打比方的話,的確,也有這樣的說法。」
我,在心裡頓了頓腳。
「不是打比方啦。不是那種虛假的東西。」
「可是因為,那是……」
「不可能的?」
美也子,點頭。我搖頭。
「不可能,勝過,可能?我真的,直到剛才,都還是高中二年級耶。」
美也子,擺出一副已經解出難題的表情。一副「從妳那個角度來看」的表情。她,了解我的立場。
一瞬間,她的眼裡,浮現無話可說的眼神。悲慟的。忽然,我察覺了。她的表情,不正反映著我自己嗎?
美也子說。
「──我也是,高二。」
然後,她靠近我,坐下,做了個我意想不到的動作──握住我的手。
並非思考過後的安慰。沒有害羞,只是,不這麼做不行,很自然的舉動。忍不住要對孤獨伸出援手。這個接觸,平靜了我的心。
「……謝謝。」
美也子輕輕點頭,輕輕鬆手。
「一回神,就來到這裡了?」
「對。」
「妳本來在做什麼呢?」
「運動會因下雨取消,我回到家,累了,所以睡了一覺。然後,一醒來……」
「剛好是我回來的時候?」
「嗯。」
「這樣的話──」美也子,抬高視線,思考了一下,「是秋天嘍?」
「對,九月底。」
「這裡,是三月底。下著春雨。不久前還開著暖爐,現在已經不用了。罹患花粉症的人戴著口罩走路。」不懂她指的什麼。「呃……」美也子看著映像管的畫面,「妳知道電視機嗎?」
我稍稍噘起了嘴:
「當然。」
美也子慌忙地說:
「也對。」
我把視線轉向那四角形的黑色畫面,試著問:
「那個,轉臺鈕在哪裡?」
「什麼在哪裡?」
「這個──用手轉的東西?」
我用手做出扭轉的樣子。美也子從桌子一端拿起黑色板子似的東西。
「妳不知道這東西?」
「嗯。」
美也子,將那黑色板子的一頭朝向電視機,按下某處。光線伴隨著輕快的音樂,咻地從黑暗底層快速浮現。小學女生正在做菜的畫面。
我愕然了。顏色偷襲了我。彷彿要截斷我的常識般的鮮豔顏色。蕃茄,有光澤、水噹噹地映在畫面上。
我看過「彩色」的文字,散布在電視節目表。但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彩色畫面。還有,長那種樣子的電視開關。
美也子慢慢地說:
「這是遙控器。」
被她這麼一說,我腦中浮現的是模型船和飛機。
「電視也用遙控的?」
去小池家的時候,小池會差遣妹妹做事,小池曰:「這是真正的妹妹遙控器。」
腦袋裡突然浮起這種無聊的事。
「對,遙控器。」
美也子動動指頭。畫面隨之改變。
沒有一臺是黑白的。
連我自己都知道心跳變快了。好像就要聽見那心跳聲的感覺。國中時,等著出場辯論大會時,也是這樣。從那之後就沒有過了。
沒人會為了開玩笑而做出這種機器。我是真的來到另一個世界了。
美也子把那裝置遞給我。是一個比鉛筆盒還小的機器。寫著頻道的數字,如用粉筆寫在黑板上般地白,各個數字的下面,鼓出塑膠製的小小的凸起。
我戰戰兢兢地試按下其中一個鍵。
「要朝著電視機按。」
我照著她所說的去做,重來一次,像轉換世界般,畫面消失又出現。槍聲響起,男子倒地,與番茄不同的紅,在我眼前擴散。
我把東西還給她,說:「請關掉。」
廚房恢復方才的寧靜。一片寂靜中,眼前,美也子的領帶顏色,像要脫口而出什麼似的耀眼。愛說話的向日葵色。
我凝視著那光芒:
「妳是櫻木小姐,對吧?」
「美也子啦。」她一邊尋找適當詞彙,慢慢地說。「聽我說,我,是妳的──」
她試圖要我理解。我怎能理解。但我說:
「我知道。」我不看她的臉。
「……」
再怎麼遲鈍,也只能這麼想不是嗎?
「還有,其他小孩嗎?」
美也子搖頭。
「我是獨生女。」
好險。如果蹦出個年過二十的男孩,我真不知該如何是好?不,即使是現在,我也不知該如何是好。我有「小孩」,這是件如此不可思議,不,不如說是令人害怕的事──等一下!
「那個,妳不是領養的噢,是真的小孩噢?」
我想從目前的狀況中逃離,不經意地說出了無聊的話。美也子一臉不可思議:
「嗯。」
「當然是吧。」
我邊說邊顫抖。所謂真的小孩,這意味著什麼?
我有丈夫──這個答案無法立刻浮上我的腦袋。我想的,不是「對方」的事,是關於「我」的事。我早已不是數小時之前的我。這想法深深刺痛我的胸口。
我連臉紅的時間也沒有。不如說臉色已慘白。
二十五年的歲月如此輕易流過,「那種事」也不是什麼難為的事吧。但是,那齒輪,在我未知的地方轉過去了。並且──
這種事是可以被原諒的嗎?換言之,我在一場睡眠之間,被時間玩弄了。
時間肆無忌憚的加法,竟換來如此毫不容情的減法。
序章《白色巨塔》是父親在看的書,閒著沒事的星期天,偶然拿起來,就一口氣看完了。拍成了電視劇,由佐藤慶飾演財前五郎。其實,那個佐藤慶,從他演〈太閤記〉 以來,我就很喜歡。星期六的重播也都有看,我還記得演到本能寺之變時的旁白:「明智光秀懷著背叛之心渡過桂川,是夜已泛白的清晨」。但是,〈白色巨塔〉裡的他,感覺很像被周遭的人耍著轉的小壞蛋,魅力差了那麼一點。「是九月吧?」小池說。我點頭:「九月有很多電視節目結束。」沉默了一會兒,我看著雨。圍牆上,水濺起手掌寬的水花。有一種,整個世界只有這個學校,這個學校只...